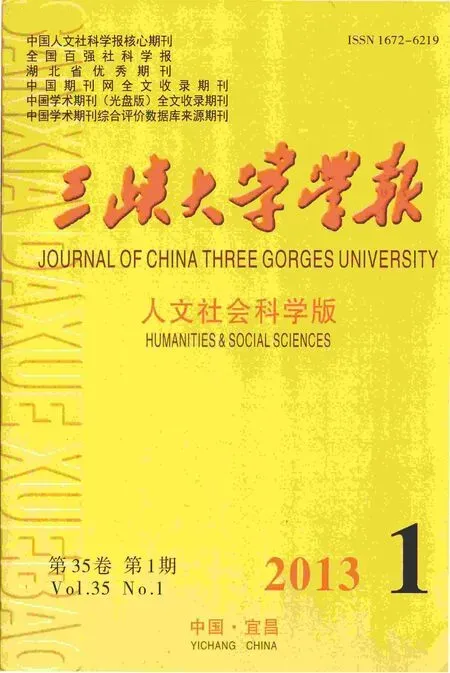《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元素之比较
2013-04-07杨书培
杨书培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莫泊桑的《羊脂球》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描写的以战争为时代背景身为弱女子的不幸命运。两部作品问世相差60年左右,虽然“战争与女人”的题材一致,但是却在人物形象设计、叙事方式和情节安排方面有较大区别,莫泊桑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丁玲侧重于对封建落后的旧思想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体现他们不同于一般写战争的作家的高明之处。现将创作元素之区别比较如下。
一、人物形象设计差异
1.外表
莫泊桑从男性审视女性的角度出发,用细腻的笔触对羊脂球上半身进行肖像描写,主要描写了羊脂球胸部、脸部、手指、唇部以及眼睛等能够显示女性躯体美的关键部位,突出羊脂球在男性眼中的丰腴的、性感的“尤物”形象。“手指头儿丰满之至,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皮肤是光润而且紧绷了的,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1]
丁玲从女性关照同胞的角度出发,没有用冗长的语言对贞贞进行肖像描写,而用穿插于情节中的“我”以第一人称写出的只言片语来描述贞贞的质朴、纯洁形象。如:“在她的背上,长长的垂着一条发辫”[2]等。此外,丁玲特别注重对人物贞贞进行眼部特写,用传统中国人“眼睛是心灵之窗”的浪漫思维方式来挖掘人物眼部变化与其心理活动、精神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借此展现人物性格及丰富情感。如:“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2]描写贞贞回乡后起初较为平静的心境。在封建传统观念的打压与宗法伦理观念的威逼下,她“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2],原本坦白、没有尘垢的眼睛变成了“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面望着众人”[2]。
2.内心
羊脂球无疑是莫泊桑肯定的人物形象,羊脂球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即使是身陷风尘,但依旧保持着纯洁、高尚的心灵,忠诚于波拿巴主义,充满希望地追求着她所向往的法兰西共和国。羊脂球会毫不犹豫地分享食物给同车的伴侣们、羊脂球会顾全大局而选择自我牺牲、羊脂球会面对敌国军人时表现出坚毅的民族国家气节、羊脂球在被出卖后会悄无声息地哭泣,这些展现出一位受尽人间冷眼,但却闪烁圣洁光辉的“可爱”的女人。
贞贞在丁玲的笔下被描写成一个不得不接受灵与肉煎熬的地下工作者,贞贞虽没有在公共场合表现出铿锵有力的民族气节,但她在日本军队大本营中的千万般“忍耐”道出了她的国家尊严感以及不屈的决心。“贞贞代表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她纯真、善良、坚强、敢于反抗。不幸落入虎口后并不自暴自弃,而是汇入抗日洪流,以自己的病弱之躯、忍受巨大的生理痛苦和心理压力为抗战服务”[3]。不同于羊脂球强烈、张扬的“爱国主义”之心,贞贞有的是一颗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看中的坚韧、含蓄的“忍耐”之心。
3.身份
妓女,不论在外国或是中国,都是被人所鄙视与拒绝的存在。西蒙波娃说:“娼妓是代罪的羔羊,男人一方面把自己的邪恶在她们身上发泄,另一方面却又唾弃她们”“而娼妓既然被否定了做人的权利,她便一古脑地承担了一切形式的女性的苦境”[4]。羊脂球无疑在当时是交际于男人们之间的“职业”妓女,她习惯于被男人的眼光所觊觎,甚至是在同一个车厢中被有妇之夫用渴求的眼光所猥亵,她点滴行为举止中保留着自己的职业习惯,但是正因为她的“职业”是妓女,就更加突出她保留的那种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多么可贵,而这正好与小说中其他法国中上层人士的国家忠诚度形成对比,一正一反,颠覆“婊子无情”的格式化形象。
二、叙事方式差异
1.叙事手法
在莫泊桑时代的法国文坛,要想在“梅塘之夜”站稳自己的脚跟则需要在创作中追求极致的“新颖”,于是莫泊桑选择从两个亮点入手:第一,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侧面描写平常生活中一个妓女的爱国心。第二,运用娴熟的对比手法。具体来说,先将羊脂球与同车“贵妇人”们做形象相比;其次,是羊脂球受辱前后自己心境的对比;最后,将羊脂球受辱前后同车贵族老爷们和贵妇人们对她的态度做对比。在对比中烘托出作者对羊脂球的肯定及对贵人们的否定。
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运用第一人称及第二人称的对白形式通过各方言语来塑造贞贞的人物形象。一方面,避开冗长无趣的肖像描写,减少全知型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灌输趋势,增强读者自身对文章社会功用和审美价值的理解与肯定,正如“一部作品如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多数读者所喜欢所肯定,那么,它必定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契合”[4]所说。另一方面,从女性作者角度切入,与女性人物进行对话,在自然的、女性同胞间心灵的交流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加强作品感染力与说服力。
2.审视角度
从羊脂球出场作者对她进行的外貌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以男性的观察视角去审视羊脂球。在描写羊脂球受到同车贵人们的鄙视时主要描写的是男性们对羊脂球从行为举止上的不屑于觊觎,如“最后这三个男人相互望了一下,使出一个友谊且迅速的颜色”[1],其次描写贵妇人们对羊脂球的语言攻击。在描写羊脂球被逼“就范”时,主要描写的是三个贵族老爷的奸计及出卖行径。因此,作者以男性眼光的感性方面来审视羊脂球的女性肉体,以男性思维去揣摩男性同胞作践、玩弄妓女的方式及感想,并最终以男人的方式来理解女人受苦的表现——“哭泣”,整部作品体现着男权对女性的同情。
丁玲对贞贞的看法不是悲观的,她反而更愿意去承认离开霞村的贞贞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正如她在文中所赞美地:“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2]。丁玲虽然赋予了贞贞痛苦的一年慰安妇的经历与回忆,破碎了一个质朴的爱情故事,将贞贞置于众乡亲白眼与辱骂中,但是最终还是成全了一个勇敢、有担当、不后悔、爱国感强烈的“新女性”形象,反而将贞贞的初恋对象夏大宝贬低,认为“他的眼很大,现在却显得很为呆板”[2]。从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丁玲作为女性作者对女性同胞的理解与关照,不像莫泊桑只是充分显示羊脂球的“可怜”并非“理解”。
三、情节安排差异
1.其他人物身份
莫泊桑将羊脂球放于众多法国上流社会权贵富阶层之中,人为加剧其等级差别,其目的在于:一方面,突出羊脂球的身份之低,显出其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之后的对比做铺垫。另一方面,服务于主旨,极力批判腐糜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虚伪与卑劣。
丁玲将贞贞放置于同为农民阶层的故乡里,更致力于挖掘历史背景,营造一个平等阶级环境中不平等的思想状态,“将贞贞被围观这一现象后隐藏深厚的奴性国民看客心理和贞操观念揭示出来,以它们在战争背景上的结合展示历史、现实都存在的双重悲剧性”[3]。
2.转折点
莫泊桑并未在《羊脂球》中深刻展开妓女的爱情篇章,而将妓女羊脂球被“出卖”后被逼“就范”作为全文的情节转折点,“就范”前后羊脂球自己的态度有明显变化,同车的贵人们对羊脂球的态度也有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升华了文章所讨论的主题:赞美羊脂球身为妓女但却有可贵的自尊心与爱国心,批判资产阶级的伪善,利用权贵势力变相压迫民众的丑恶现实。
贞贞的悲剧性在丁玲的笔下显得尤为突出:第一,忍耐着与愿相违的肉体交易;第二,为爱国主义而献身的无畏精神却无人理解;第三,面对破碎爱情的无力感;第四,“背叛”爱情的自我折磨与惩罚。贞贞与初恋情人夏大宝的彻底决裂是全文的转折点,此后贞贞的情绪不再平静,有自我惩罚的倾向,最终使自己“灵与肉”的双重践踏感升级,导致最后的“负伤”离开。
3.结尾
《羊脂球》“戛然而止”的结局设定显得意味深长,看似作者用平实的、冷漠的语言描写羊脂球的“哭泣”,实则讽刺同车资产阶级贵人们的冷漠、虚伪与卑劣。最后,莫泊桑对民主革命家格尔诺瑞在车中不停用口哨吹《马赛曲》的情节设置更独具匠心,一方面:“格尔诺瑞始终用一种猛烈的不屈不饶的态度吹着他这种具有复仇行为的单调口哨,强迫那些疲倦而且生气的头脑从头到尾地倾听他的歌唱,去记忆每一句被他们注意节奏的歌词”[1];另一方面,暗示着格尔诺瑞对羊脂球高尚爱国主义的欣赏,同样也暗示着作者自身的政治倾向与爱国意识。
丁玲与莫泊桑的战争经历使他们能够以个人独特视角穿透“战争与女人”小说的一般模式,拒绝正面描写战争而使其创作表现出对战争文化心理的疏离,更着眼于对人类本身的关照,显出人类的强大生命力。而这正是丁玲与莫泊桑对文坛战争题材小说的巨大贡献之处。
[1](法)居伊·德·莫泊桑.羊脂球[M].郁 丹,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2]丁 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魏华莹.战争背景下的批判与反思——《羊脂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比较[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0).
[4]黄恩财.“梅塘之夜”的一颗流星——论《羊脂球》的美学意义[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