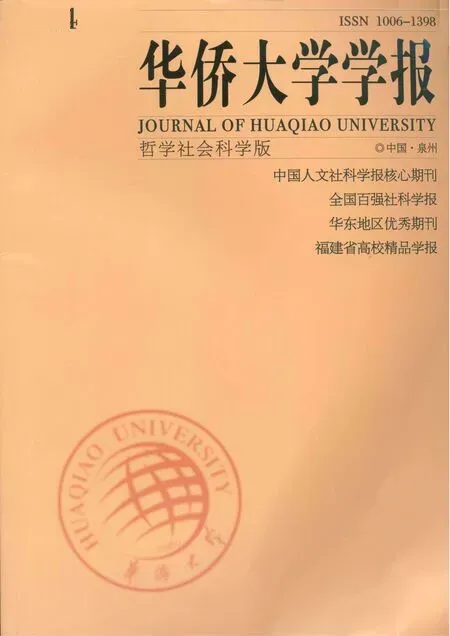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2013-04-06○孙媛
○孙 媛
(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孙 媛
(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
一 否定“社会造因说”
钱钟书对“诗分唐宋”的阐释是以他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2]35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社会造因说”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7-8,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4]1,茅盾“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5]188-189,成仿吾“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6]214,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7]137等对现代文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社会造因说的具体表现形态。在“社会造因说”的感召下,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也致力于因世求文,注重从社会时代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动因,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钱钟书力排众议,坚持认为社会时代与文学创作之间并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文学创作是独特的个性化行为,即使在同一时代和同一社会背景下也会产生风格迥异的文学创作,“社会造因说”将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创作现象强行归入社会历史框架之中,势必会有意无意地简化、掩盖甚至歪曲文学创作的真实面貌,导致文学研究的偏见和盲视。论及这一问题时,钱钟书特别提到了对文艺社会学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文论家泰纳:“Taine之书,可为例禁。”[2]35泰纳深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文学演变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种族、时代和环境是决定文学演变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32,“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8]7。在钱钟书看来,泰纳 “因世以求文”[2]35,在世与文之间 “强别因果”[2]35,势必会使文学研究者以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固禁咒”[1]734。事实上,真正推动文学演变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惯性,而并非来自于社会时代的外部力量:“文学演变,自有脉络可寻,正不必旁征远引,为枝节支离之解说也。”[2]35
《谈艺录》第七节中,钱钟书以清代姚羹湖的《昌谷诗注》、朱轼的《笺注长吉诗》、陈本礼的《协律鉤元》为靶子,集中批评了那种将社会时事附会为文学创作动因的研究倾向。姚羹湖等均从唐代诗人李贺所处的时代语境入手,认为李诗应时而发,旨在以奇诡之语讽喻时事:“元和之朝,内忧外患。贺怀才兀处,虑世道而忧人心。孤忠沈郁,命词命题,刺世弊而中时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斯愈推愈远,愈入愈曲,愈微愈减,言者无罪,闻者不审”[1]114;“读平城雁门之章,如见《东山》《采薇》之意焉。善读者可以兴观,可以群怨”[1]114-115。在钱钟书看来,这些观点牵强附会,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李贺的创作动机:“不解翻空,务求坐实,尤而复效,通人之弊。将涉世未深、刻意为诗之长吉,说成寄意于诗之屈平,……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云愁海思,化而为冷嘲热讽。”[1]115姚羹湖等人的失误从反面说明了“社会造因说”的可疑之处。社会时代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固然值得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应该流于单一的因果研究模式。
联系钱钟书的其他论述,不难发现,在休谟和加赛德那里,钱钟书找到了质疑和瓦解“社会造因说”的理论武器。
因果决定论是“社会造因说”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指出,人们所认定的因果观念基本建立在经验、观察和推论之上,在经验和观察中,人们发现有些现象往往同时出现或是次递出现,于是就习惯性地认为它们理应联结在一起,并据此推论出它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不是一种固有的存在,而是出自习惯和联想。在钱钟书看来,休谟的“习惯联想之说”对于打破简单的因果决定论、纠正“强别因果”的“社会造因说”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故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有因果关系,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虽涉因革,而不能求因果者,盖为此也。”[2]34-35在借助休谟“习惯联想之说”瓦解因果决定论的基础上,钱钟书又对“因革”和“因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社会时代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属于因革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有关①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钱钟书曾就社会时代关乎文学创作这一问题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哀愤之思,憯若风霜,憔悴之音,讬于环玦;苞稂黍離之什,旨乱而词隐,别拓一新境地。赵翼《题梅村集》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着沧桑语便工’,文学之兴鼎革有关,断然可识矣。”(见钱钟书.人生边上的边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4),但不能以社会时代判定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因人而异,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提供了某类作品的诞生可能,但是并不会决定文学创作本身,若是无视文学创作的个体性特征,一味根据社会时代特征去解释和规定文学创作的发生和发展,势必会陷入“因世以求文”的误区。
如果说休谟的“习惯联想之说”瓦解了因果决定论,抽空了“社会造因说”的存在前提,那么加赛德对心理状态重要作用的强调就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精神与时代关系的固有认识,消解了“社会造因说”的理论合理性。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将心理状态视为时代精神的根本动因。钱钟书对此颇为赞同,认为“与其把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不如把文学和思想来解释实际生活”,与其说时代决定精神,不如说“精神决定时代”。[2]218-219既然“精神决定时代”,那么文学艺术的发展当然不可能完全受制于社会时代的变革,所谓的“社会造因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 “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
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批判为钱钟书重新阐释“诗分唐宋”话题扫清了障碍。既然“社会造因说”并不值得信任,那么以社会时代更迭划分唐诗宋诗特征的做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其削足适履,将诞生于唐宋两代的诗歌勉强塞入唐代、宋代的社会历史框架之中进行归类,不如摒弃成见,从诗歌创作的特征入手,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更为合理的阐释: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1]3
在他看来,文学创作与个人的性格情致、审美取向、语言功力密切相关,是相当个体化的行为,绝非社会状况所能支配和解释的。严羽等古人以唐朝宋朝为诗歌断代分期,只是便于著述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在文学领域里,“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1]734的创作现象比比皆是。宋代诗歌也不乏注重情韵的自然感发之作,譬如:张耒 (柯山)强调作诗“直寄其意”,“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9]362-363,其诗平易晓畅,运笔自然;姜夔 (白石)说诗崇尚自然天成,认为“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9]402,其代表诗作等均无斧凿之痕,尽显天籁之妙;惠崇等九位诗僧以晚唐贾岛、姚合为宗,其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格调萧散;被合称为永嘉四灵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寄情山水田园,力主捐书为诗,无所依傍,其诗多用白描,极少用典。唐代诗歌中也不乏偏于议论的“尚理”之作,譬如,杜甫 (少陵) “思力深刻”[10]16,其诗重思理,多议论;韩愈 (昌黎)以散文为诗,喜谈哲理;白居易(香山)的政治讽喻诗针砭时事,“议论畅快”[10]16;孟郊 (东野)苦吟求新,多以独特的构思传达哲理化的人生感受。可见,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未必出于唐代人之手,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也未必出于宋代人之手,与其将“尚意兴”之唐诗和“尚理”之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倾向。“诗分唐宋”昭示的不是“朝代之别”,而是创作主体的“体格性分之殊”。论及这一问题时,钱钟书将杨万里、博纳米、席勒等中西学人的言论并置一处,使其彼此阐发相互映射,从两个层面凸显出“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
首先,“诗分唐宋”中的“唐宋”指的并不是唐朝和宋朝。
杨万里曾经谈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1]3,在钱钟书看来,“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1]3:诗唐宋也,非人皆唐宋也。与“杨序之恉”相映成趣的,是英国18世纪的文坛状况和批评家博纳米对英国散文家安迪生文学地位的认定:“犹夫英国18世纪女主 (Queen Anne)临朝,而其一代词章,乃号罗马大帝时代文学。……当时文坛主监为安迪生,而身后论定,竟被19世纪女主时班首之称。”[1]3-418世纪初是英国安妮女王在位时期 (1702-1714),但是此时的英国作家却多好模仿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英国著名散文家和诗人安迪生 (1672-1719)的主要创作集中在这一时段,而批评家博纳米却将其定位为维多利亚 (1809-1901)时代的第一位文学家。可见,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实际影响并不会受制或局限于创作主体所处的社会时代,“固知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1]4唐诗宋诗的发展理路与唐朝宋朝的社会时代变迁之间也不存在同构关系。
其次,“诗分唐宋”所标举的是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不同创作倾向:“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1]7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唐诗宋诗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
钱钟书认为,席勒分析古今诗歌特征的言论对我们理解“诗分唐宋”的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意义。席勒从诗人的主体差异性入手,将诗歌划分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如果诗人处于纯粹自然的状态中,其天性可以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表现在现实中,“诗人就必定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11]171,其创作出来的必然是素朴的诗;相反,如果诗人已经被文明所浸染,其天性的和谐就只能作为一个观念而存在,为了寻求这种观念,“诗人就必定把现实提高到理想”[11]171,其创作出来的必然是感伤的诗。古代人性较现代人性更为和谐自然,所以古代多素朴的诗,现代多感伤的诗。钱钟书将席勒的这一观点概括为:“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1]4但是,钱钟书更为关注的是,席勒已经意识到了“古之诗”与“今之诗”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古代也有感伤的诗,现代也有素朴的诗,甚至在同一个诗人或同一部诗作中,也会出现素朴和感伤两种特质:“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和今古者”[1]4。就这一意义而言,“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1]4。论及这个问题时,钱钟书特别提到,“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亦持是说”[1]4。在《艮斋诗草序》中,吴宓曾经谈到,“唐诗富于理想,重全部之领域,浑融包举。宋诗偏重理智,凭分析之功能,细微切致……德人席勒又有 (1)本真诗与 (2)思感诗之说。凡此二者之分别,亦即 (1)唐诗与 (2)宋诗之所由异。唐诗与宋诗之优劣高下,不待辩而自明”[12]260。吴宓此言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批评民国旧体诗创作以宋诗为宗的现象,有明显的尊唐诗贬宋诗倾向,这与钱钟书对宋诗价值的肯定和强调原本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谈艺录》中,紧接着《艮斋诗草序》出现的,是叶燮《原诗》、蒋心馀《诗辨》中的言论:“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1]4-5,“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1]5,很明显,在钱钟书所营造的话语网络中,《原诗》和《诗辨》中的言论已经构成了对《艮斋诗草序》的有力牵制和必要补充。经由这种牵制和补充,《艮斋诗草序》宗唐贬宋的论诗倾向被否定和忽略了,而其对唐诗宋诗差异性的分析则被提取出来,成了支持“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的有力论据。借助这一论据的支持,钱钟书旨在标明:诗人的主体差异性决定了唐诗和宋诗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分别,“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1]4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的性情心理各有特点,在诗歌创作方面,唐代诗人多重想象,追求浑融之美,宋代诗人多重理智,追求分析之妙,其他朝代的诗作均是唐宋诗风的轮回,但是,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性情心理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宋代诗歌中也有重想象的成分,唐代诗歌中也有重理智的成分,甚至在同一个诗人的诗作中,也会出现“丰神情韵”和“筋骨思理”这两种审美特质。在钱钟书看来,这种唐宋诗交缠的创作倾向主要取决于创作主体性情心理的复杂性,而创作主体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处于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会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气质性情和心理倾向,所以,“旷世而可同调”的文学创作现象屡见不鲜。论及这一问题时,钱钟书将叶燮、圣佩韦、荣格的观点并置一处,相互参照:
叶横山《原诗》外篇卷四论何大复与李空同书讥李诗“入宋调”曰:“李不读唐以后书,何得有宋诗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将未尝寓目,自为遥契吻合,则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尽非耶。”即谓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故旷世而可同调。圣佩韦好言“精神眷属”近世德国谈艺言“形态”者别作家才情为二类 (intellectus archetypus,intellectus ectypus),亦有见于斯也。[1]5
叶燮对李空同进行批评时,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文艺心理学观点:“此心此理之同”。与这一观点形成对照关系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佩韦的“精神眷属”说和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人类理智的分析。圣佩韦本着科学主义态度,坚持精神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动植物界的类别特征。基于这一考虑,他不仅专注于分辨各种精神心理之间的相似性,而且试图按照这种相似性给人类精神分门别类,划定精神家族。在他看来,文学史就是形形色色的精神家族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很多不同时代的文学都会因创作主体精神家族的同一性而体现出相似的创作特征。在康德的哲学世界中,“原型的理智 (intellectus archetypus)”可以实现对事物现实性的探究,“模仿的理智 (intellectus ectypus)”只能抵达对事物可能性的分析; “原型的理智”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存在,“我们所追求的只是适合于我们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能力就是人类能够运用的“推论知性(那是需要意象的,即需要模仿的理智 (intellectus ectypus)的)”[13]66。按照康德的观点,无论何时,在文学创作中起作用的理智只能是“模仿的理智”,文学创作所揭示的也只能是事物的可能性问题:事物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世界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不是因为创作主体的认识能够切中事物本身,而是因为该事物符合创作主体的心理需要。如此,叶燮、圣佩韦、康德的言论相互碰撞,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了一个道理:由于相同或相似的精神心理的作用,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完全可以创作出“同调”之作,生活在唐代的某些诗人可以写出宋人推崇的“筋骨思理”之作,生活在宋代的某些诗人也可以写出唐人推崇的“丰神情韵”之作。而唐代宋代前后的汉、魏、六朝、元、明、清等时代的诗作或为“丰神情韵”之“同调”,或为“筋骨思理”之“同调”。
其二,同一个人身上会交缠着不同的气质性情和心理倾向,所以,不要说在同一个时代,即使在同一创作主体那里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创作倾向:
……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徵》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 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非从朝代时期之谓矣……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1]5
钱钟书认为,很多诗人同时体现出唐诗和宋诗两种创作倾向,犹如太极之有两仪,相反相成,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两种创作倾向并存的状况是由创作主体的气质心理所决定的。论及这个问题时,钱钟书将刘邵和荣格的观点并置起来相互参证,充分凸显出气质心理的丰富和复杂。三国时期刘邵在《人物志·九徵第一》中将“明白”和“玄虑”视为人的两种气质禀赋:“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14]13-14“明白之士”行动迅捷,说干就干,勇于进取,但是往往缺乏深谋远虑;“玄虑之人”懂得静默的道理,善于观察,思虑精深,但是往往缺乏迅捷的行动能力。二者的区别所昭示的是阴阳之气的不同功能。在钱钟书看来,刘邵所谈到的“明白”、“玄虑”与荣格谈到的外倾型心理、内倾型心理基本上是一回事。荣格认为,这两种心理类型随机分布于各个历史时代和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其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客体的态度上:“内倾型对于客体的态度是收敛性的,”“外倾型则对客体持积极的态度,”[15]253外倾型促使人“以各种方式表现和张扬自身”,“内倾型的自我则具有抵触外在诉求、保守自身以避免任何与客体直接相关的能量耗费的倾向”[15]254。但是,在现实个体那里,这两种差异明显的心理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经常纠缠在一起:“很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一个人格既向我们显示为内倾型的,又显示为外倾型的……”[15]261刘邵和荣格都涉及到了不同气质心理并存于同一个体的现象。钱钟书认为,这种现象是导致唐诗创作倾向和宋诗创作倾向杂糅于同一个体的真正动因:少年“才气发扬”之时“遂为唐体,老年“思虑深沉”之时“乃染宋调”。“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证…… 《四部稿》中,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1]5促成这种倾向的,即是王世贞气质心理的非同一性。
如此,钱钟书引证中西学人观点,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内涵做出了合理的阐释和深入的分析。从他的阐释和分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学创作固然与社会时代脱不了干系,但是,较之社会时代,创作主体的性情心理才是决定文学创作倾向的关键力量。在再现说和反映论盛行于世的历史时期里,这一见解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纠偏意义。
[1]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 钱钟书.人生边上的边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胡 适.文学改良刍议[M]∥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陈独秀.独秀文存 [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
[5]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M]∥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6]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M]∥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 鲁 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法]丹纳.艺术哲学 [M].傅 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2] 吴 宓.吴宓诗话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 [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 (魏)刘 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15] [瑞士]荣格.心理类型 [M].储昭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陈 雷】
On Qian Zhongshu’s Thoughts about Differences of Poetry in the Tang-Song Period
SUN Yu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Minnan Teacher's University,Zhangzhou 363000,China)
In The Discussion of Art,with the help of theor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Qian Zhongshu wiped off the stereotyped views and made the mor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the differences of poetry in the Tang-Song period”based on the negative view that social condition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literary development.In his opinion,the poetry of the Tang-Song period could not be divided into two social productions,and regarded as two kinds of artistic creation tendency caused b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writers.The complexity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determined the mixing of the two kinds of artistic creation tendency.His idea is very helpful to correct an error made by the main literary theory of reappe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poetry in the Tang-Song period;Qian Zhongshu;The Discussion of Art
I206.7
A
1006-1398(2013)04-0114-07
在实证主义哲学观和文学反映论的强大制约下,现代中国的很多文学研究者习惯于将社会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刺激和触动视作主宰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作为深谙文学创作理路的一代鸿儒,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文学创作固然无法脱离社会时代的影响,但是,社会时代的变革并不足以决定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在《谈艺录》中,他将中西诗学话语和文学现象并置一处,使其围绕着“诗分唐宋”这一有关文世关系的话题自然而然地产生碰撞、交流和对话,共同生发出对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纠偏意义的文学观念。
《谈艺录》开篇即言:“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1]2在讨论中,谈艺者普遍坚持诗歌创作分类和社会时代分期的同构关系,即使偶有意见不同者,也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代杨士弘的唐诗选本《唐音》将唐诗划分为始音、正音和遗响三个部分,始音部分专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而正音部分和遗响部分都是既包括初唐盛唐诗人的诗,又包括中唐晚唐诗人的诗,这种划分方法已经突破了社会时代分期对诗歌创作分期的制约。为此,“《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1]2面对苏平仲、杨士弘二人的观点分歧,钱钟书坚持“士弘手眼,无可厚非”[1]2,考察诗歌创作分期时应该“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1]2,文学创作并不是社会变革、时代盛衰的翻版和再现,社会时代对文学创作也没有绝对的主宰力量,社会时代的分期与文学创作的分期虽然不乏交叉之处,但是绝不能被混为一谈。“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1]3,社会时代的唐宋之分也不等于诗歌创作的唐宋之别。
2013-01-05
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谈艺录》与中西诗学的互证和阐发”(JA12207S)
孙 媛 (1975-),女,河北张家口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