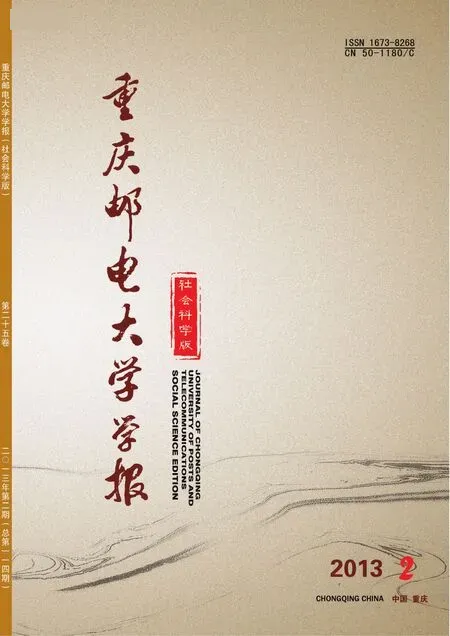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
——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2013-03-31魏志远
魏志远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071)
一、牟宗三对朱子“别子为宗”的判定
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为根据,将宋明理学诸家分成五峰蕺山、象山阳明和伊川朱熹三系。所谓道德的形上学就是从道德的入路而证成形上学,以赋予宇宙万物道德价值和意义的学说,其关心的问题“首在讨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验根据(或超越的根据),此即心性问题是也。由此进而复讨论实践之下手问题,此即工夫入路问题是也。前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客观根据,后者是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主观根据。宋、明儒心性之学之全部即是此两问题。以宋、明儒词语说,前者是本体问题,后者是工夫问题”[1]7。
以此为根据,在本体论方面,牟宗三认为:“溯自濂溪之言诚体、神体乃至太极,横渠之言太虚神体,明道之直就‘于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而又易体、诚体、神体、心体、理体、仁体、忠体、敬体,通而一之,总之是对于道体性体无不视为‘即活动即存有者’。”[1]69也就是说,濂溪、明道等人将性体(即心体)调适上遂,与天道实体“其内容的意义完全同一”,“为物不贰,生物不测”的天道能够创生宇宙万物,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存有之理,其本身也是生生不息的超越之理。而朱熹则将形上本体视为“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将心下拉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天理(即性)遂成为宇宙万物“存在之然”的“所以然”之理,“性只成存在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心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是性,并不即是理,故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理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1]91。在牟宗三看来,“即活动既存有”的天道实体是继承先秦孔子的践仁知天和孟子的尽心知天而来,因此是儒家的大宗和正宗,而伊川和朱子则歧出,但因朱子是宋明诸儒中的集大成者,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判其为“别子为宗”。
在工夫论方面,牟宗三认为宋明诸儒做工夫的目的就是探求道德本体,根据对本体的理解不同,其工夫入路也被分为逆觉体证的纵贯系统和顺取的横摄系统。“‘逆觉’即反而觉识之、体证之之义。体证亦涵肯认义。言反而觉识此本心,体证而肯认之,以为体也。”[2]它分为“内在的体证”和“超越的体证”两种逆觉形态,前者指在现实生活中良心发见处当下体证而肯认道德本体,后者则是指在与现实生活隔离的状态下体证道德本体。通过逆觉体证,从而将道德界的本心和存有界的天道通而为一。此两种逆觉的工夫并不契朱熹,他将心性情分开,天理(即性)只是静态的存有之理,心只具有认知作用,他根据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义理间架,强调在情未发时以“敬”涵养本心,使之收敛凝聚而不昏乱。在情发后进行格物致知,探究宇宙万物的存在之理。因此,只能说“心具理”。
在文献的使用上,不同于濂溪、横渠、明道等人以《论语》、《孟子》、《中庸》和《易传》为中心,伊川和朱子以《大学》为中心,“《论》、《孟》、《中庸》、《易传》是孔子成德之教(仁教)中其独特的生命智慧方向之一根而发,此中实见出其师弟相承之生命智慧之存在地相呼应。至于《大学》,则是开端别起,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所谓只说出其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宋明儒之大宗实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只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1]17。综上所述,牟宗三从本体论和工夫论出发,认为“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和逆觉体证的工夫为儒学大宗,而伊川和朱熹坚持“只存有不活动”的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歧出而发展成为另一儒家系统。
二、对朱子格物致知的再认识
朱熹将理气二分,形成心性情三分的格局。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天理是“只存有不活动”的宇宙万物存有之理,属于形而上的层面,而人心是实然的气化之心,具有认知天理的作用,是形而下的层面。由此朱熹走上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顺取之路,即通过后天探求外在的天理而使之主宰吾心,使吾心的发用时时刻刻合乎天理的要求,为此牟宗三认为朱熹学说“就知识上之是非而明辨之以决定吾人之行为是他律道德”[3]361,这与传统的以道德本心为道德创生实体和注重体悟的自律道德是不同的。
但在笔者看来,朱熹追求“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顺取之路,正是对濂溪、明道以来所倡导的重在体悟的内圣之学的有力补充和深化,与先秦以来儒家延续下来的对理想道德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牟宗三认为朱熹在理论借鉴和思考方式上更倾向于伊川,依据其“义理纲维依经验主义与实在论的路数来解析”。但在笔者看来,朱熹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之路的形成,则是与其师从李延平的教育经历和其注重分解思考的生命本质相关联的。朱熹“年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此(禅)”[3]33,后二十四五岁时见延平,而开始悟禅之非。“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3]33“某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书一般,字字仔细思量过。才有疑,明日又问。”[3]36有这一段话可见朱熹从学于李延平,其体悟圣贤之学是从日常的读圣贤书和深思多问这些平实的工夫中获得的,这与强调坐禅冥想的佛家工夫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朱熹常常强调要通过读圣贤书来学习儒家思想的原因。由此亦可看出朱熹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对事物内在之理的探索,对宇宙万物的存在之然总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如:“问:太极动而生阳。先生尝曰:此只是理,做已发看不得。熹疑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如此做两节看,不知得否?”[3]17延平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并不就分别已发未发来说,认为气化流行就是一理的流行,只进行体悟便可,而朱熹则要清楚地区分出已发和未发。由此可知,相对于逆觉体悟的修养工夫,朱熹更倾向于格物致知的注重分解的思维方式。
而且,李延平虽然平日里“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他非常强调日常的践履,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说:“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3]34他的这一治学思想对朱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平生就最不喜欢学人笼统蹈空,空守着一个本心而无实际的践履工夫。“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3]17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强调“涵养须用敬”的“敬”也来源于延平对他的影响,如“先生既从之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得力耳”[3]4。这与后来的朱熹主张在喜怒哀乐之情未发之前涵养本心,使之凝聚收敛,在情发后以此敬心于万事万物中察其端倪的格物致知工夫形态可谓是如出一辙(当然,在牟宗三看来,延平的工夫是“隔离的、超越的体证”,其体证的本体就是“天命流行之体”,这与后来朱熹“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是不同的)。由此可见,朱熹在格物致知中强调要通过读书来获得天理,做切实的践履工夫,反对空谈心性,对宇宙万物存在之然之所以然的探求都是在师从延平期间培养起来的,因此延平对于朱熹以后思想系统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
朱熹的静涵静摄系统,强调“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还与濂溪、明道等代表的纵贯系统在工夫践履上存在的明显缺陷有关。牟宗三也承认:
“北宋濂溪、横渠、明道,大体皆平说,尤其重在对于本体之体之悟,重在对于‘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体悟,如濂溪重在对于太极之体悟,对于诚体、神体之体悟,横渠重在对于本体宇宙论的体用不二之体悟(‘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明道重在‘一本’之体悟。
此三家既重在平说,重在对于本体之体悟,故随时是工夫,而亦无定格。……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亦是即本体言工夫,然亦并未开出如何识仁,亦未就如何识仁开出一确定之工夫入路。又《定性书》言‘动亦定,静亦定’,全篇皆论定心之工夫,然亦似只是论当然之理境,而未确然立出如何达此理境之工夫入路。
此种只随时随义平说,只就当然理境说,而无一确定之工夫入路为定本,好处是活转无滞,而可无异同之争辩。……然不足处,则是疏阔,未能示人以实下手处之切实有效之工夫入路也。自此而言,若用康德词语说,则此三家在工夫入路上是独断的,非批判的;是零碎的,非系统的;是捎带着若隐若显的,非著实而确定的。”[3]41-42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纵贯系统中的本心是超越的自发自律的道德本心,是与天道和天理合一的,是创生道德的实体,因此是道德行为的依据。通过逆觉体证的工夫体悟到本心并肯认之,则人就可以依据其而发出合乎道德的情感,作出合乎道德的行为了。但是,对道德本心的体悟是通过“觉”这一主观的感悟来实现的,而且他要对外界的事物有切身的感受,产生相应的恻隐之心等情感才能实现。因此由之做工夫有很强的主观性,对道德本心的体悟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会因每个人的悟性不同和情感感受不同而必然有所差别,并且是否达到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对应的参照物来予以确认,因此像明道等讲“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只是工夫的指点语和自己对道德境界的体悟,并没有提出一个客观、具体的工夫入路来引导人们如何达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为此,它就为一些人务虚蹈空、空谈心性,不做实际践履的弊病埋下了伏笔。
正是看到这一点的危害,朱熹才坚持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格物致知工夫,试图通过平实的践履实践将主观的心和客观的天理相结合而达至儒家理想的道德境地,并以此来避免空谈心性的弊端。他说:“今之学者则不然。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则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务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3]175朱熹的格物致知工夫概而言之就是当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思虑未萌的时候,要用“敬”涵养人心,即做到“外在地说,即是斋庄之仪容,内在地通于心说,即是心气之贞定”[3]147。通过凝聚收敛人心“而合于道(静摄于道),与道偕行,始能主宰乎情变,而使之发而中节”[3]165。由此外在之理内具于人心,在此两者(亦可说主观和客观)实现了统一,外在之理也通过心的感发而贯注于人的日常活动中成为人行为的主宰。在涵养人心的同时,还要做格物致知的工夫,“格物是至于物(即物)而穷究其理。……致知者是借格物一方面推致、扩大并恢复其心知之明,一方面推致其穷究事物之理之认知作用令‘到尽处’,即‘知得到’,知得澈底,知得到家,此之谓‘知至’。格物愈多愈至,其心知之明愈明愈尽。及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达至知‘太极’之境,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3]349。在牟宗三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通过对天地万物的“存在之然”而探究其“所以然”,一方面可以使得人心通过对事物之理认知的加深和扩大,而进一步澄清人心的杂念,达到“意诚”的目的,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以凝聚收敛之心进一步探求到事物之所以存在和人的道德行为凭依的最终根据,达到对“太极”境界的感悟。
另外在纵贯系统中,道德本心与性是合一的,它们是上天赋予人的天性。因此一旦体悟本心,见孺子入井则会自然而然产生恻隐之心,至于此行为何以产生的根源却未作过多解释。由此便带来一些问题,即它只是教人凭依自己的道德情感而做事,长此以往只会形成一种道德习惯而已,并未引导人们去探求这些道德行为何以这样去做而不可以那样做和超越于行为本身之外的一种客观、合理的理论依据。再进一步讲,如果遇到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那么人们依旧以原来的习惯做事是否合宜呢?对于此问题,学者杨泽波在其《牟宗三形著说质疑》这一篇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道德本心自有其主观性和客观性:
“道德本心不过是由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心理境况和境界,即我所说的伦理心境。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要受到社会生活的熏习和影响,这种影响久而久之会在心中形成某种结晶体。与此同时,人们也要不断进行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进行,总会在内心留下一些痕迹,这叫做理性的内化。社会生活和理性内化的结果,在伦理道德领域,就是形成一定的伦理心境,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道德的本心。”[4]
由此可见,道德本心的内容从客观上来说是源自于外界环境对人的熏陶并且通过主观的理性思考而形成的,并非是人先验具有的。而这一点也恰是朱熹所坚持的,他说:“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原注:此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是必至于举天地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然后为知之至,而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至是而无所不尽其道焉。(原注:此大学之道,知之深而形之大者也。)”[3]311即人的仁义礼智等义理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实践而获得的,并非先天地存在于人心之中,而是要靠主观的心的认知才能获得客观的天理。从这一方面讲,朱熹实际上是将格物致知当作沟通主观之心和客观天理的有效途径,他不但保持了人心认知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天理的客观性,心具理的实现也尽力避免了纯粹以道德本心为道德创生本体所不可避免的务虚蹈空、纵情肆意的弊端。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牟宗三一直强调朱熹因为将理气二分,从而造成天理与人心的分隔,相较于“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创生实体(即道德本心)而言,朱熹“只存有不活动”的天理使“其道德力量亦减杀”,而成为他律道德系统。但在笔者看来,朱熹虽然将心性情三分,但却依然突出了人心在实践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它依旧是一切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比如在其《观心说》中朱熹认为:“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今复有物以反观乎心,则是此心之外复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也。……大抵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广而安,其理实而行自然。”[3]300-301从这些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人心主宰人的行动和情感,通过格物致知的认知和收敛凝聚的涵养,使得人心摆脱了外界物欲和功利的干扰,不断地涵具众理,并最终达到浑然纯一的太极之境。至此天理通过与人心的合一而在心之发用下贯穿于人的行为和情感之中,成为指导日常践履的标准,使得心的发用处处合乎天理。
总之,虽然天理是超越的、客观的道德标准,但它只有通过人心的发用才能起作用,而人心作为人的行为和情感产生的根源,可以认知天理,并以之为指导而主宰各种行为和情感,使之顺理自然而行。因此人可以通过心而评判、主宰自己,从这方面说朱熹也是在讲道德自律的。
三、余 论
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这一本书中,根据道德形上学的标准,将朱熹的学说与濂溪、明道等相区别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并认为他并未能继承先秦孔孟以来儒家传统的生命智慧,而被判为“别子为宗”。但通过以上笔者的论述可知,朱熹的本体论和工夫论实际上是在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有力补充并提升了儒学的思维水平。比如先秦的儒学和后来的内圣之学并未将心性天严格地区分开,只注重通过内心的体悟并根据由之产生的内在道德情感做事,至于为何要这样做并未作过多的说明。而朱熹则将天理和人心区分开来,天理是超越地、客观地决定天地万物存在的存有之理,而心是人的行为和情感的主宰,具有认知天理的作用,因此通过“涵养须用敬”和“进学在致知”的修养工夫,人可以体认天理,探求天地万物存在的所以然之理,并依之做事。由此他不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说明了决定我们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背后的外在于人自身的理性根据,而且还以格物致知使客观实在性和主观能动性相结合,避免了心性之学走向务虚空谈的弊端,提升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论水平。而他在探求天理的过程中,强调收敛凝聚本心,做切实的践履工夫也是继承了儒家治学的优良传统。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394.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杨泽波.牟宗三形著说质疑[J].孔子研究,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