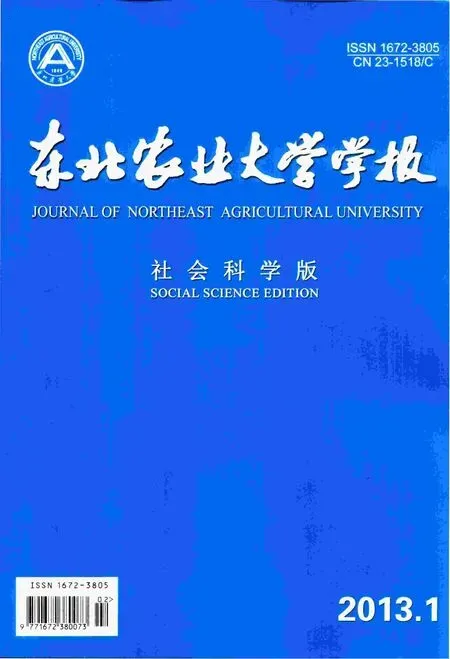叙事理论框架下新文人剧的“故事”解读
2013-03-22张帆
张 帆
(厦门理工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叙事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前苏联,主要是来自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现在大家熟知的叙事理论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典叙事理论,认为“故事”与“话语”是深度剖析的起点。“故事”作为研究“话语”的基础,要对所叙述的故事情节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新文人剧的“故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新文人剧“故事”的解读,提出三种相对的人物形象,即“英雄”与“懦夫”、“叛逃”与“回归”、“摧毁”与“重塑”,意在探寻新文人剧的叙事逻辑、句法、结构及其与“话语”的内在关系。
一、“英雄”与“懦夫”
罗兰·巴特曾指出:一切大众文化皆具备“神话”的特性,这种现代神话的“魔力”在于“它已经将现实内外翻转过来,它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且用自然填充它,它已从事件中移开它们的人性意义,而使它们能意指作用人类的无意义”。可以说,作为“现代神话”的载体——电视剧,通过其声画结合的语言表达形式,为人们描绘了光荣与梦想、虚幻与现实、狂欢与怀旧的种种世俗景观。新文人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营造着如梦如幻的“自在世界”,而主人公这样或那样地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男性“故事”的书写主要是男性作为叙述客体的一种呈现,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男性成为“被叙述”的主体。关于“故事”的论断,史洛米斯·雷蒙-柯南将其定义为“按照时间顺序而排列的一系列事件”;茨维坦·托多洛夫将“故事”理解为由平衡开始,经过不平衡的状态,最后到达平衡。在这些“故事”的表达中,男性成为“主角”。
依照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观点,尽管戏剧中的人物略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七种戏剧形象:英雄、恶棍、施主、遣送者、伪英雄、帮助者、公主和她的父亲。莎拉·考兹洛夫则认为,这种分类也可以直接嫁接在电视剧的人物表现上。无论哪种划分方法,都应找到一个合理的切入点。本文结合新文人剧中男性人物形象的主要表现对其进行重新分类,将其分为两种类型:“英雄”与“懦夫”。
“英雄”形象产生于对英雄的崇拜,英雄崇拜又显示了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观念对于“英雄”的理解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即英雄之于社会,具有超出常人的智慧、才能、胆识、魄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敢献身的精神;之于家庭,有着人间最温暖、最真挚的情感。《大明宫词》中的李隆基,对于国家而言就是一位英雄。为了李唐王朝,他置生命于不顾,面对韦氏皇后专权,显示出超凡的勇气和英雄般的气概。在被韦氏要挟之时,他恳求太平公主放弃对其生命的解救,目的是要保住李唐王朝不被“篡权”。当太平公主称实在不忍其被杀、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时,他呵斥道:“太平公主,什么是你的良心?难道仅仅为了救一个鲁莽而无能的侄子,辜负天下人的重托就是你的良心?难道为了满足自己最普通的亲情而舍弃神圣的使命就是你的良心?难道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善良心境而有愧于整个家族就是你的良心?不!你的良心太浅薄,太世俗了。你救不了我高贵的生命也不要让我失望,为了已经死去的人,为了无数活着的人,太平公主,你必须离开这里,快些走!”这一连串充满阳刚和悲壮的言语对李隆基的“英雄”形象进行了最好的诠释和凸显。
薛绍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放弃了生的权力,选择与自己的结发妻子“长相守”。当太平公主谈起爱情时,他这样讲:“你知道爱情意味着什么吗?爱情意味着长相守,意味着两个人永远在一起,不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就像峭壁上两棵纠缠在一起的长青藤,共同生长、繁茂,共同经受风雨最恶意的袭击,共同领略阳光最温存的爱抚。最终,共同枯烂、腐败,化作坠入深渊的一缕缕屑。这才是爱情,你懂吗?她的崇贵需要两股庞大的激情,两颗炽烈的心灵,缺一不可。真正的爱情是无坚不摧的。不论是天上的神明,还是地狱的命官,都不能叫她屈服,因为她本身就是天堂,代表着生命最崇高、最健全的境界。”这种对爱情坚定的表达无疑彰显了薛绍作为一个“英雄”形象所呈现的与之相匹配的语言,在这种表述中完成了对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故事”的显现。
“懦夫”往往是与“英雄”相对的,而对“英雄”和“懦夫”的判断往往在一线之间。新文人剧最明显的标签之一就是亘古不变的“爱情”主题。正是在历史、社会、制度的种种限制之下,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与表达,方能显现出其自身所拥有的人物特质。这也更加凸显了这些人物的“懦夫”形象。《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方文对于爱情,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懦弱与胆怯——想爱但不敢爱、相忘但不能忘。《橘子红了》中的容耀华,对于鏖战商场的人士来讲,他是英雄,但是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下,他则是个“败者”。容耀辉对于爱情极其向往却在大伯面前很软弱,古沛帆在容家慷慨陈词却在遇到酒醉的容耀辉时张口结舌,这些人物的前后对比注定其将烙上“懦夫”的印记。爱情理应是属于两个人最美好的感情,但在封建礼教和社会伦理面前,却是那样的脆弱。在《大明宫词》中,太子李弘不满武后对王皇后和萧淑妃遗留女儿所做出的悲惨命运抉择,与母亲武则天发生了严肃的正面冲突,而又表现得很软弱。这不仅为其凄惨的结局作了伏笔,同时也奠定了他的“懦夫”形象。除此之外,为了不背叛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他做出惊人之举——与自己的书童合欢相恋。同性之恋,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不被广泛接纳的,遑论在封建社会的鼎盛之时——唐朝。因此,剧中对于二人情感刻画得若隐若现,直到太子李弘被武后赐死,才将这段恋情公之于众。尽管这样,在为太子拟的祭文中也尽量含混不清地表述。合欢对武皇后说:“我是他的仆人,又不仅仅是他的仆人,我还是他的……爱人。”这一情节被许多人称为是对武则天最大的讽刺。对方文、容耀辉、李弘这些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出了其作为“故事”的完整呈现。
二、“叛逃”与“回归”
认同性是后现代主义反叛的基础。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反叛,一味的反叛是不存在的。反叛性是其表面特征,本质是认同性。后现代主义所提及的反叛和现代主义的反叛也有本质区别:现代主义的反叛性是为了反叛而反叛,反叛就是一切,反叛本身就是目的;而后现代主义的反叛性是有关怀的,它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旨在向人类做迄今为止究竟至极的一切挑战,其目的是解放思想,拓展视野,争取自由。这种反叛性的表征之下是认同性的本质。在新文人剧中,这两个概念表现为女性的两种行为:身体上的“叛逃”与精神上的“回归”。
在《天一生水》中,林若云与范叔涵明明相恋但却不能爱。对于范叔涵而言,如果自己与林若云相爱,无疑是对大哥的背叛。这种背叛大于对自己心灵的背叛。从林若云的角度看,自己对范叔涵的爱是源自内心的,但也万万不行,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女孩子要遵守的“规矩”。对于心灵相通的他们来说,这样的现实过于残忍,于是他们选择逃离家庭束缚。在他人看来,这是林若云对于自己和家庭最大的“反叛”,显示出其争取女性自主权的理性一面;在林若云自己看来,这是捍卫和保护爱情的有力“武器”。
在一幕幕“叛逃”的故事中,牺牲的往往是那些自认“出轨”的人。在创作者的眼中,林若云因为脱离正常社会轨道,也要受到命运的惩罚。在她与范叔涵私奔途中,在她爱情最灿烂的时节,生命遽然而止。这一系列的剧情显示了新时代“叛逆”的年轻人向传统权威发起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于当时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女孩子来讲,父母之命是不可违背的,而正是对这件不能挑战的事情进行挑战,方显现出其“反叛”的一面。但是,其本质首先是出于对“理应听从”这一行事准则的认同,“理应听从”恰恰是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也只有认同这一传统,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叛逃”,同时也正是因为“理应听从”这一事实的存在,才出现后面的“叛逃出走”事件。“叛逃出走”本身是出于对同类“弱势群体”的关怀,这刚好与后现代精神中的“关怀性”的否定精神相符。
与林若云命运相似的还有《夜半歌声》中的顾云嫣。顾家为了攀龙附凤,执意将她许配给赵公子。顾云嫣数次逃跑未成,绝望之中嫁给了赵公子。新婚之夜,赵公子发现顾云嫣并非处女,找到顾家兴师问罪,结果是顾家小姐精神失常。剧中人顾家小姐在爱情选择方面拒绝了名门出身的赵家公子,最终选择出身戏院的宋丹平,充分体现了顾云嫣“反叛”的特征,但本质上,她认同这一切差别的存在。同时,顾云嫣选择出身卑微的宋丹平,是对“女性选择‘门第显赫’的婚姻生活是最佳结果”这一普遍“共识”的否定。在与家长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她对宋丹平出身卑微的认可,也体现出其内心对于门第划分这一传统文化的心理“回归”。
《橘子红了》中的秀禾也是一例。她力图挣脱不幸婚姻,但却败于自己的“无能”与“无奈”。她对耀辉说“风筝是自由的”,于是,她主动拿起放风筝的线,“让风筝飞走”。最后,风筝断了线,象征秀禾在封建礼教的挣脱中失去爱情,也毁灭了生命。这种象征性叙事的表达是对原有封建爱情悲剧的“叛逃”,用全新的手法控诉命运不公的安排。
综观新文人剧中,此类“叛逃”的故事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主人公的眼中没有所谓的地位、出身和富贵的差别,认为一切都是“无别之物”,是他们对处于现存状态的一切事物的反叛,但实质都认同了一切事物之间差别的存在,并带有“关怀性”的否定,在其内心中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是源于此,几乎每一部新文人剧都会为观众留下无尽的思考。
三、“摧毁”与“重塑”
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创造”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创造”是不同的。现代人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将创造进行机械的理解,将其看作是随心所欲,是对秩序的破坏。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有序和过度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在现代人看来,创造是少数人的行为,将其特权化,而后现代思想家试图还创造性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来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
正如安吉拉·默克罗比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所说,后现代主义是围绕着“破碎”一词展开的。斯图亚特·霍尔也声称:“正是这种意识的分散性使得他作为一个黑人得以出现在后现代的舞台上,虽然是分裂的可是得到完全的展现。”摧毁是对常规的否定。常规的形成是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反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鼓励大多数人一起进行创造。在新文人剧中,“摧毁”与“重塑”是女性的两种行为:“摧毁”是一种身体力行,“重塑”才是行事之源。
在《人间四月天》中,张幼仪虽然不比林徽因和陆小曼抢眼,但在她身上却显示出非凡女性的特质。她在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年长四岁的徐志摩,在帮助徐家完成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任务”后,遭到徐志摩的遗弃。原本认为只要跟随丈夫就能获得新生的张幼仪,跨越重洋来到英国,这时发现徐志摩早已恋上林徽因。她接受现实,结束了自己不幸的婚姻,成为反抗封建思想,改造社会的先锋。离婚后的张幼仪,远赴德国求学,学成归国后接办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然而事业有成的张幼仪却一直没有走出徐志摩的世界,她替代徐志摩奉养徐家父母,连丧事都由她承办主持。在这位女性身上,不难发现其与当时社会情景迥然不同的一面。女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远赴大洋彼岸,即使在离婚之后,仍然承担起当时的女性很难完成的责任,这与向来以“三纲五常”为伦理准则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林徽因最终接受父亲为其定下的婚姻,嫁给梁思成。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宛若春风,拂面而来如此可亲,一旦迎身向前却只能抱得满怀愁绪,得不到结果。不同的命运选择展现的是女性在面对生命、权益时的不同态度,而结果也似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林徽因的婚姻模式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而张幼仪的命运选择却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且很难接受。因此,张氏的婚姻选择是对林氏“幸福婚姻”的摧毁,张幼仪将仅为男性拥有的“特权”——成功“普遍化”,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体现。
《大明宫词》中出现大量册封典礼、祭祀封禅、奢华宫廷宴会等场景。在一幕幕的祭典场景中,人物命运也出现种种改变。最明显的是武则天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登基。这一系列故事,表面上看是武则天“摧毁”了由男人掌控历史的模式,实质上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女人称帝的先河。再如,武则天让太平公主主持将军凯旋册封大典,颠覆了向来由太子或皇子完成的传统。由于武则天对太平公主极其偏爱,以及太平公主年幼时骄纵蛮横,因而当太平公主在与太子一同读书,喜欢上原本属于太子的桌子的颜色——明黄时,皇帝李治被迫改变多年传统,将太子之位的颜色改为大红。该剧上演的种种皇家生活情景恰恰也是对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否定和“摧毁”。
容耀辉、秀禾、徐志摩、林徽因、范叔涵、林若云、宋丹平、顾云嫣、太平公主、薛绍,这些人用自己的思想、行为谱写出属于生命本真的进行式乐章,构建出两性共有的存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英雄”与“懦夫”、“叛逃”与“回归”、“摧毁”与“重塑”就在这一幅一幅的画面和一幕一幕的戏剧中上演着、实现着、消解着。
四、结语
通过对新文人剧“故事”的分析,本文认为新文人剧的“故事”一般是以男性“话语”作为叙述的视角,只是这种男性叙述“话语”表现得较为“隐蔽”。也许是观众永远无法抓住的,甚至是创作者很难察觉到的。因此,尽管有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了女性作为表现的主体,并体现出其“故事”的一面,但在具体表现上却深深地打上男性“话语”的烙印。这是女性导演和女性编剧永远无法躲避和逃离的,她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一边完成男性“故事”的讲述,一边承担着男性“话语”的表达。因此,本文更愿意将其看作是男性“话语”的深层表达,这是在男权世界中成长并被潜移默化影响的创作者难以逃脱的宿命。
[1]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M].牟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M].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利萨·泰勒.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尹鸿.媒介图景中国影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周安华.民营的激情与想象——中国新文人电视剧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