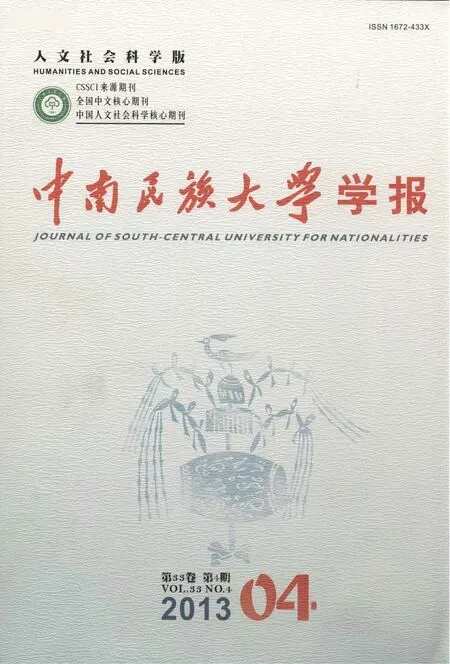独龙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认同
2013-03-21赵沛曦
赵沛曦,张 波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云南丽江 674100)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共有6930人。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丙中洛乡小茶腊村,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康普乡齐乐村和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茶隅县察瓦龙乡扎思村。历史上,各代王朝对独龙族地区的经略,使独龙族产生和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同时,独龙族因与周边的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纳西族等民族,唇齿相依、密切交往、兼容共生,而出现了区域文化的认同。并在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共生共荣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存”关系的发展。
一、历史变迁与民族、国家意识
据史料记载,独龙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群,文献中有“撬蛮”、“俅子”、“俅人”、“球人”、“俅扒”、“曲子”、“曲扒”等称谓。元代之前已居住于今独龙江流域和怒江中上游地区①元朝时的丽江路界内,《元一统志》“风俗”条曰:“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据方国瑜考证:“磨些(今纳西族)、白(今白族)、罗落(今彝族)、峨昌(今阿昌族)、吐蕃(今藏族)之记载较多,……又卢即傈僳族。又撬之族名少见,字书‘撬’读牵么切,与求读奇么切,二字音读相近,则撬即求江之居民,为今独龙族。”参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5页。。虽然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龙族所居之地自古就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历代王朝对该地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与经略,独龙族属于封建中央王朝子民的历史悠久。从政权演变情况看,该地唐宋两朝为“南诏”、“大理”属地。明代开始是丽江路的辖区。当时,丽江路纳西族木氏土司“开疆拓土”,其势力深入到今维西、香格里拉等地。中央王朝通过木氏土司对独龙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于是纳西族与居于丽江路西境的独龙族关系密切起来。清朝时,该地为丽江木氏土知府所属的西路叶枝土千总禾姓王氏(康普土司)土把总和北路土千总喃氏辖境。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清政府委任内地科举出仕的汉人流官负责管辖独龙族地区,同时,维西厅府受中央王朝之命,任命了各级、各族官员,使独龙族地区各级管理机构初步形成。无论是土官还是流官,他们皆是中央王朝在地方的代理者,经略着独龙族居住的地区。从此,在独龙族先民的心目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与其他民族有纠纷或矛盾时,可以向维西土司诉求,同样,独龙族人民若不服于维西土司,可再向清政府申诉,“官严谕头目,俱约其下,毋得侵凌。”②参见余庆远撰:《维西见闻录》。这种依赖关系,是独龙族产生对国家、对中央王朝向心力的政治基础。雍正八年(1730年)即清廷分封维西诸土职的第二年,怒族、独龙族向维西厅纳贡,“求纳为民”,正式归属内地中央王朝,体现了当时的独龙族与怒族对朝廷的向心力,说明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与崇奉已深入独龙族的族群观念中,“汉人”③这一概念在独龙族的族群观念中更加清晰。纳西族土司对独龙江、怒江北部的统治几经更迭和转移,其中维西康普土司(叶枝土千总)对其地的统治时间最长[1]292-294。但康普土千总传至禾娘时,则把统治权转赠给了政教合一的察瓦龙门工藏族土千总。1907年,夏瑚被委以“阿墩子(今德钦县)弹压委员兼办怒俅两江事宜”,办理教案①1906年,怒族、藏族和独龙族等人民发起的驱逐外国传教士、焚烧白汉洛教堂的反洋教事件。史称“白汉洛事件”或“白汉洛教案”。。夏瑚代表清朝政府勒令停止菖蒲桶喇嘛寺和畜奴主对独龙族的苛派。夏瑚两度巡视怒江、独龙江边隘,以“身历地土,目睹情形”的实地考察写成《怒俅边隘详情》一书,提出疏解民困,巩固边防的主张。在巡视途中身体力行,并委任当地民族头人为伙头,经略边疆,成为中央王朝制约地方力量的象征,备受独龙族人民敬仰。夏瑚巡视独龙江边隘,更拉近了独龙族与中央王朝间的距离。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菖蒲桶(贡山)殖边公署,这是民国政府在独龙族地区设治的开始。后分设衙署,建营房,办学校,设商号。1916年,殖边公署改为行政委员公署。云龙主政云南时,1933年,菖蒲桶行政委员公署改为贡山设治局,保甲制代替了伙头制。在当地设四保,每个自然村为一甲,甲长3年轮换一次,掌管村中各种事务,负责为国民政府征纳税收,建全了民族国家对独龙族地区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实现了封建中央王朝到民族国家在独龙族地区治理方略上的转换,进一步增进了独龙族与内地的联系,增强了独龙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历代政府对独龙族地区经略的过程正是独龙族人民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它不仅促进了独龙族与内地汉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且,客观上也便利了当地民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迩年,其人以所产黄连入售内地,夷人亦多负盐至其地交易”②参见余庆远撰:《维西见闻录》。,于是就有了“吃起盐巴想东方,没有盐巴想东方”[2]的歌谣。
1949年10月,贡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结束了历史上独龙族被异族土司、宗教势力和国民党统治的历史。独龙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昂首进入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时期。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独龙族第一次有了自己正式的民族名称,确定了独龙族的民族身份。从此,独龙族有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族称。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孔志清(独龙族)当选贡山县第一任县长,代表包括独龙族人民在内的贡山各族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独龙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的发展,跨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行列,建立起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当代独龙族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有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独龙族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独龙族人民不仅热爱自己民族,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形成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民族意识和“华夏一体”的民族认同感。
二、政治力量的变化与区域文化认同
历史上,汉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以及傣族等政治力量长期角逐怒江、独龙江流域,曾先后建立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统治政权,出现了政治上的拉锯局面,使当地民众遭受困苦,民不聊生。但民族势力的角逐和冲突没有割断各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反而因长期的互动出现区域文化的认同。
康普土千总禾娘时候,笃信藏传佛教。为使家道转运和超渡夫儿亡灵,将独龙江上游和丙中洛北部地区转赠给西藏察瓦龙喇嘛寺,察瓦龙喇嘛寺通过察瓦龙门工藏族土千总管理该区域。同时,禾娘广建寺宇[3],其中之一就是其西部辖境丙中洛的普化寺[1]298。当地的独龙族、怒族就落入察瓦龙喇嘛寺和丙中洛普化寺两股政教合一力量的统治之下。他们委派“伙头”、“甲头”(“甲”藏语称贡山怒族阿怒人)每年按期向当地民众摊派贡赋,“在奔卜喇嘛统治时期,每年到独龙江来收两次税,第一次在6月,主要是放盐,即把盐巴摊派给各户(强迫购买),规定秋后付黄连、贝母、皮革之类,第二次在10月,一方面收贡税,一方面收6月放出的盐债。收税人来之前,以木刻传示各村要为他们修住房及用具,所交贡物,每户黄功连4包、麂子皮1张、麻布5床、刀子1把。来人的食用另外摊派各村,要备下皮褥1床、麻布被1床,用麻布做成蚊帐,还要送米3升、鸡3只、水酒9碗作招待用。”[4]藏族土司和普化寺喇嘛不仅对当地的独龙族、怒族群众收取“俅贡”、“超渡费”、“香火钱粮”等,更是施以宗教文化的影响,于是,藏传佛教与当地民众的信仰碰撞、冲突、整合,几经周折,它跨越了民族界限而被同一区域的独龙族、怒族等共同信奉,以至于清末夏瑚巡察独龙江后提出“扶置喇嘛,以顺舆情”的建议,他说:“中维两厅,邻近西藏,崇奉佛教,沦肌浃髓,怒江既无官长,复无土弁,故民人尤为喇嘛是信是依。……如是则僧归官管,自不敢越礼犯分,民得僧依,亦自能乐业安居,实以该处为喇嘛报辟,故其教入人最深,有非此不乐之概。”[1]306
虽然傈僳族迁入怒江的时间晚于独龙族和怒族先民,然而他们进入怒江后在区域权利格局竞争中却逐渐处于优势地位。“距今300年前,傈僳族在纳西族及藏族的排挤下,不断从金沙江流域迁入怒江地区,结果征服了这里,成为怒江的统治者。他们强占怒族的土地,强迫怒族向他们纳贡,并经常抢掳怒族充当奴隶。”[5]同时,“上下(独龙)江与江尾,又均有所谓骨尸钱粮者(傈言俄普骨牙)。缘傈僳到处抢劫,亦到处贸易,然无不凶恶霸道,倘被人殴死,或即病死,傈又集众往其所死一带地方,抢劫烧杀,累月连年,迄无休息,不得已与之讲和,愿上尸骨钱粮。于是议定某项若干,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每年照上一份。……各村上此钱粮,有多至五六期者。”[6]
政治地位的强弱与文化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历史上,汉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文化对怒族、独龙族文化的冲击,使怒族、独龙族逐渐认可、认同汉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文化。如前所述,历代中央政府对独龙族地区经略的过程正是独龙族人民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它不仅促进了独龙族与内地汉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而且,客观上也便利了当地民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独龙族与“汉人”文化的认同。“俅民……其心理颇向中国。日用饮食起居器具,皆赖汉人供给。所出山货药材,亦皆售之汉人。”[7]53
当然,一种文化在其流布、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自我调适,吸收和整合当地的各民族文化,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使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呈现出趋同特征。20世纪初“腾冲(高黎贡山一带)夷人,别之为两大种:山居不洁,信鬼嗜杀,无文字,用木刻记事者,傈僳种也。而野人、浪僳、怒子(怒族)、俅人(独龙族)虽其名称不同,实皆傈僳种也。且其风俗习惯、嗜好、性情不同者十之二三,同者十之七八。余故曰:野人、浪僳、怒、俅,皆傈僳种也”[6]其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基于共同族源和共同历史记忆的亲近感以及地缘关系,使其文化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特质而难以区分你我。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整合
独龙族同古代氐羌族部落集团各族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独龙江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南,由北向南流至贡山县独龙江乡孟当行政村以下转向西流,经钦郎当村流入缅甸。独龙江地区北接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倚高黎贡山,西边是担当力卡山,西南与缅甸接壤。故独龙族北与藏族相邻,东与怒族、傈僳族和为数不多的纳西族、白族、汉族杂居,西南与缅甸境内各族互通有无。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以及白族等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有的地方是小范围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使他们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都呈现出极强的文化互动与整合现象。
一方面独龙语同怒语、藏语、彝语、羌语、景颇语等语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语系上以氐羌语为原始母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同贡山地区怒语颇接近,基本可以互通,同景颇语、僜语等语言也比较接近[8],与尼泊尔的罕(Kham)语在某些方面亦非常接近[7]57。独龙语词汇中有从汉语、藏语、彝语、傈僳语中来的大量借词。藏语借词多半是宗教和商业方面的[9]。有些词又是两个或几个民族相通的。察瓦龙怒族称使人生病的精灵为“朋郎”,独龙族叫“卜郎”,发音相近。独龙族对巫师称呼与贡山丙中洛怒族一样叫“南木萨”或“董木萨”。独龙族在语言表达上也呈现出与相邻民族互相交汇的特点。在丙中洛乡青那桶以北地区,怒族认为上山打猎不能说汉话和傈僳话,只能讲怒族话或藏话,否则岩神不会赐予野兽,因为岩神只听得懂怒族话或藏话。独龙江上游的独龙族进入所崇拜的岩洞时只讲藏话,不讲独龙话,相传岩洞里的鬼神只懂藏话。他们均认为所信仰和祭祀的鬼属哪个民族就只听得懂哪个民族的语言[9]。
另一方面,相同的文化生态使独龙族与周边各族在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呈现出相互融汇现象。独龙族传统宗教信仰中杂糅着相邻民族的宗教观念。如藏族的苯教、藏传佛教,怒族、傈僳族、景颇族的传统信仰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痕迹。独龙江中上游地区因与西藏察瓦龙的渊源关系,原始宗教中有明显的与苯教和藏传佛教交融的特点。独龙族的三界宇宙结构观念和以此为核心的灵魂观念,与藏族苯教的三界宇宙观极其相似。独龙族的巫师“南木萨”与藏族苯教有着特殊的联系,特别是对独龙江上游的“南木萨”来说,鼓是不可缺少的法器,苯教巫师作法也离不开鼓,而且独龙族巫师所用的鼓多半是从察瓦龙带来的,两族巫师替人禳灾祛病的职能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前,察瓦龙的藏族土司和有钱人家还专程到独龙江来请“南木萨”到家里作法。藏族苯教中称“拉巴”的巫师都能喝酒,据说“拉巴”在醉酒的情况下才具有通达人鬼的功能,而独龙族的巫师“乌”也是酒喝到半醉以后才能“替神说话”。特别是在传统节日“卡雀哇”中剽牛祭天时,“乌”是非醉不可的,酒醉状态下的“乌”好像得到了鬼神赋予的超凡力量,变得异常勇猛,能够将祭祀用的牛一竹茅剌死。“卡雀哇”时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供奉石堆、石神的习俗明显地受到了藏族苯教的以部落、家族为单位祭石堆、石神等宗教习俗的影响。祭祀时他们用白纸做成小经幡插在石堆上,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与察瓦龙等地的藏族过“罗赛节”祭石神和祭氏族神的习俗非常相似。独龙族到察瓦龙做生意或走亲访友,也兴携带一块石头堆放在所途经的山顶垭口,犹如藏族祭山神堆玛尼堆。除了天葬外,藏族地区流行的几种丧葬仪式在独龙江地区都存在[7]70-74,而且均是“坟头朝东方,脚朝西方”,独龙江上游的独龙族还在坟头插上树枝,挂上“拉达尔”(白纸条或布条),音可能是藏语“龙达(意为经幡)”的转音[9]。
基督教一开始主要是在傈僳族中传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独龙江下游地区后,逐渐被怒族、独龙族、勒墨人(白族支系)等信仰,“基督教化”便成为当地民族对傈僳族文化认同传统的延续[10]186。“自耶稣教传入怒江后,英国传教士傅能仁等才创傈僳文,宣传宗教。傈僳族、怒族‘瓦枯扒’识此种文字者,用其写信、记账,年深日久,读者渐多,今天的傈僳族、怒族的‘瓦枯扒’很少有不识此种文字者。”[11]据载,福贡地方“俅子、怒子,又被本族(傈僳族)所统治而发生同化之关系。查知子罗、上帕二设治局之傈僳,为怒子、俅子之村落伙头、排首、甲长等职,管理赋税及一切行政事项。所以,俅人、怒人每有事务必与傈僳协商。其接触时间,比较为多,有诉讼者,求傈僳头目排解之;有疾病者,必请傈僳‘尼扒’禳除之。于无形之中,该怒、俅二族,已直隶于傈僳之下也。是以怒人、俅人亦多通傈僳语,以便相互勾通文化。所以傅能仁所译成之傈僳文《新旧约全书》可以在怒人、俅人社区传教;俅人、怒人等读傈僳文之《圣经》者,因通傈僳语故也。此系傈僳文化较俅人、怒人为高,而怒人、俅人又被傈僳同化也。”[10]186基督教传入,在生活习俗、精神上重新构建了独龙族信教群众的生活,使其与傈僳族、怒族等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逐渐趋于一致。改变了当地民众嗜酒好烟、牲杀祭祀、买卖婚姻的旧俗。教徒遵守“十诫”、节俭自律。“基督教对彼等发生之影响甚可谓大。其日常生活中之衣服已较为整洁;因传教士常来之故,房中原日供奉家神之位置也改悬耶稣、玛利亚之像或其他圣经故事。星期休息并作礼拜,过复活节、圣诞节,取消原有之各种鬼神的祭祀、信仰,改变其婚丧之仪式保持诚实习惯,服从传教士。”[10]190这样传教士与教徒共同认同的“文明”风尚渐入民众生活,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四、共生共荣、多元一体思想的滥觞
长期以来,独龙族与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及白族等民族一道劳动和生息在藏彝走廊西端这一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交往密切,友好相处。不仅理念上是同源共祖关系,而且有不少民族本身就存在客观上的血缘关系。独龙族与怒族、藏族、汉族、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以及白族等民族均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各民族长期以来频繁交往,友好相处,相互交融,其融洽和谐的关系,对各民族神话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在独龙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创世纪》神话传说中,有着独龙族与周围兄弟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的生动描述。传说洪水泛滥过后,仅有兄妹两人幸存于嘎哇嘎普神山之上。为了继续生存和繁衍后代,他俩决定分头去找人。哥哥阿波去江东,妹妹阿朋到江西。不知走了多少路,过了多少江,找了多少年。结果仍是兄妹两人碰在一块,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于是精疲力尽的兄妹俩只好先盖了房子住下来。尽管晚上事先都各自睡在自己的床上,不知怎么地第二天起床时两人发现竟睡在一张床上。头天晚上拾来分开的干柴,第二天也合拢成一堆。妹妹见此情景,感到很羞愧,便用竹筒装水放在两张床中间将两人隔开。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竹筒不见了,两人仍睡在一起。兄妹两人困惑不已,久而久之反觉得这是天意。于是,兄妹两人向天起誓并祷告说,如果我们倒出的这筒水能变为江河,就表明天神并不怪罪我们兄妹成亲,否则,我们只有眼看人类从此绝种。一筒水刚刚泼出,转眼间就变为九条江,即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金沙江、狄子江、狄布勒江、狄府江、托洛江和恩梅开江。从此,兄妹二人正式结为夫妻,后来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成了上述各条江的主人,亦即后来的汉、怒、藏、白、纳西、傈僳、僜人和独龙等族[12]。其中,怒江和独龙江两兄弟关系甚密,分别前相互交换了礼物,后来虽然两人隔山隔水,但彼此说的话都能听得懂,只是音调慢慢地变了一些[13]。这则神话中所陈述的九条江正是原始先民们对自己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的具体描述,它恰与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等民族分布和活动的地理范围大体相同。神话中提及的民族之间虽有亲疏不等的关系,但独龙族视汉族、怒族、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为同一祖先繁衍而来的兄弟。在独龙族的《创世纪》神话的形成和积淀中,反映出当地各民族在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同源共祖”、“同源异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睦共处”现象,体现了区域文化认同中“共生共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我国西南边陲,以“探险”、“考查”、“传教”等为幌子,深入我国的西南边疆,勘测地形,掠夺资源,搜集情报,欺压民众,制造事端①如片马事件,即1900年1月侵缅英军入侵片马附近的茨竹、派赖等寨,1910年12月,占领片马。至1927年,又先后占领古浪和岗房。,甚至设厅置县②英国侵略军占领片马后,在他戛设厅,片马设县。,边疆危机加深。独龙族与当地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捍卫祖国领土,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00年片马事件后,左孝臣和杨体荣领导的抗英斗争,片马管事勒墨杜扒与泸水土司率各族群众的抗英斗争,1906年,反洋教的“白汉洛事件”、“怒俅殖边队抗英斗争”,1913年,独龙族民众处死英军头目布里查,民国设置俅江公安局,民国时的抗英、抗日斗争,以及1938年叶枝土司王嘉禄立“北路土司界”碑,为1960年中缅两国勘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系列反侵略及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和行为,有力地阻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妄图对独龙江一带的入侵,进一步强化了独龙族和各兄弟民族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观念形成。
[1]高志英.独龙族社会文化与观念嬗变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8.
[3]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M].刘宗岳,译.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209.
[4]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5]云南省编委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5.
[6]高志英.宗教认同与区域、民族认同——论20世纪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基督教的发展与认同变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2).
[7]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8]蔡家麒.独龙族卷[M]//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605.
[9]高志英.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多元宗教互动与宗教文化变迁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10]高志英.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福贡傈僳族、怒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研究[M]//何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11]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2]赵沛曦.独龙族传统生活中的价值观[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5).
[13]云南民族研究所.民族调查研究·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R].昆明:云南民族研究所,1983: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