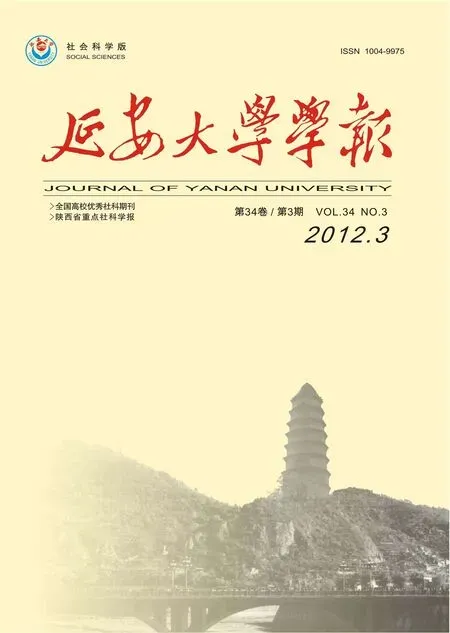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
2012-12-09何满仓任海峰
何满仓,任海峰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本文聚焦于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历史,1941年10月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的鲁迅研究,1943年徐懋庸对鲁迅作品的注释及当时的延安文人默涵、力群、萧军、周扬、何其芳、未易等对鲁迅的解读批评和争论,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探讨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取得的成果及在鲁迅传播史上发挥的作用。
一
延安鲁迅研究会1941年10月出版了《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除去前记和附录共有九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思想”、“创作”、“行传”、“学术”几个方面展开,它是延安文艺建构时期唯一一部鲁迅研究专著。专著中最有分量的论文是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全文从时代环境、辩证法、唯物论与理想主义三个方面探讨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独到的见解,他因《大众哲学》一书受到毛泽东的垂青。他的论文结构严密,论证充分。在梳理鲁迅思想转化的过程中,既有对鲁迅文学道路仔细的回顾,又有对鲁迅作品准确的引用,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对此文评价甚高。此文有些观点的确令人钦佩,作者认为“鲁迅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家,而是一个伟大的启蒙的革命战士,文艺只是他的战斗武器,或者说,文艺是他战斗的主要武器,通过文艺,他向中国人民传播他在政治上、历史上、哲学上、文艺上等等方面的革命观点,传播着他的改造民族精神,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新思想。”[1]422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依旧十分合理。文章虽没有摆脱以政治为主线理解鲁迅的思路,但高度肯定了鲁迅的文艺创作。此文值得商榷之处是,他为了把鲁迅思想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从鲁迅作品中断章取义总结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说服力有些勉强。例如文中说:“我们还可以由鲁迅先生早期的哲学证明,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多么谬误的思想。鲁迅先生在与中国旧文化斗争的过程中,既已发现了辩证法的真理,那就是说,在中国的国土上,在中国社会的前进运动中,已产生自己民族的辩证法思想。辩证法之适合于中国国情,它之成为新的中国所需要的思想,也在这里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了。”[1]428这里显然夸大了鲁迅思想中辩证法存在的意义。而面对鲁迅早期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艾思奇一方面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鲁迅“处于这样的环境而又未曾看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只能依据主观的理想来考究治疗的药方,这是必然的。”另外又说:“真正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或伟大的唯心论者,有时比庸俗的唯物论者更接近于真正的唯物论者,更易于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五四’以后鲁迅先生所以终于能够走到辩证法唯物论的方面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由于他在战斗中看见了真正民主的现实力量——即无产阶级力量的缘故。”[1]432我们发现这个看似合理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够严谨的。但是这种诠释的价值不可小视,一方面论证了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又在鲁迅身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生动实例。
而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一文则以内容详实为特色。作者从八个方面探讨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引用了许多鲁迅原文,甚至可以看做是对鲁迅主要作品的认真研究。作者对鲁迅大量作品的归纳整理为读者认识鲁迅的思想、解读鲁迅的作品、传播鲁迅的精神奠定了一定基础。文章的局限在于“罗列过多而理论分析显得不足”。[2]
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辛亥的女儿》和《一出悲壮剧》是这个研究集里对鲁迅具体作品进行研究的两篇文章。前者针对《离婚》,后者关注《伤逝》,探讨的都是鲁迅关注的女性解放和婚姻自由问题。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两篇小说进行了深入解读。第一篇文章认为鲁迅是要否定中国的封建婚姻,作者“把农村妇女的婚姻问题,跟地主的剥削关系胶合在一起来处理,这就暴露了事物的本质。”[3]454后一篇文章认为“当新的战斗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鲁迅的唯一武器便是控诉”,“控诉是与暴露不同的。暴露只是为挽救自己阶级的腐烂和没落,有望于‘改良’和维持;控诉却是为了自己和众人的前行,要激发起反抗来的。”[3]464两文的文笔犀利,富有说服力。
二
1943年,华北书店出版了徐懋庸注释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理水》。
在《释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徐懋庸在用整风话语对《阿Q正传》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触及到了对这篇小说的精神内涵——“精神胜利法”的理解。徐懋庸在注释小说的过程中将鲁迅的其他作品引来作为佐证,其文章体现出让鲁迅自己说话的特征,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是有助于读者更好的认识鲁迅。在政治话语主导作者注释思路的情况下,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鲁迅作品内质的回归,显示出作者对鲁迅作品的熟悉程度和深入钻研精神。但作者在正文前的声明中指出:“据我的研究,鲁迅的思想体系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早年的个别论点例外);因此在我的注释中,有时就直接引用了马列主义的原理”[4]1366,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徐懋庸本人对马列主义并没有其对鲁迅作品那样精熟,他在文中引用更多的其实是鲁迅的原文,所谓的马列主义原理不过是对整风话语的照搬和口号式的政治表态。此外,徐懋庸对《阿Q正传》一一对应式的解读严重割裂了文章的整体性,甚至出现自相矛盾之处。
在对《理水》的注释中,徐懋庸把禹塑造成践行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人物,禹治水过程中的做法体现了整风中的两种精神——实事求是和“倾听群众意见”。当然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毕竟在形式上有貌似之处,可是在精神上和《理水》的内涵是南辕北辙。作者口口声声反主观主义,而结果却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1943年11月10日,《华北文艺》第2卷第5期刊载了徐懋庸的《释鲁迅杂文<拿来主义>》,文章开篇点出因为日本、汪精卫、蒋介石都指责马列主义的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所以要用“拿来主义”回击,依旧是充满火药味的政治语言,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确有新中国的创业者的气魄,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却不过是破落户的混蛋子弟的行径。”[5]其实作者费尽心思的注释还不如直接用鲁迅原文说得明白有力,这里多的只是彰显自我的政治话语。
徐懋庸这种露骨地以政治化的视角,紧扣时代背景,用马列主义原理注释鲁迅作品显得牵强、生硬,也为后来图解式理解鲁迅作品树立了“榜样”。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解读方式对于促进读者理解鲁迅作品和扩大鲁迅作品在解放区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默涵的《两个悲剧——读书杂记》,作者透析了鲁迅两篇以女性命运为主题的小说——《祝福》和《伤逝》,在对两位女主角——祥林嫂和子君悲剧命运的揭示中,将造成人物命运悲剧的原因指向冷酷的社会制度和没有希望的现实,然后阐明这两篇小说的意义正在于“告诉了同行者和后来者,使他们去另寻更加宽阔的道路”,并且“终于寻到了”。[6]应该说作者的解读策略依旧是结论先行,但作者的阐释技巧要更为高超,语言表述委婉含蓄,显示出以情动人的特点。同年6月2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力群的《略论“祥林嫂的死”》,力群的文章对默涵在《两个悲剧——读书杂记》一文中提到的祥林嫂的死因——周围人冷漠的嘲弄、拒斥,从而在人间找不到温暖,因此向往地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恰恰相反,祥林嫂不是向往而是怕进地狱——因为即使死“两个男人还要争,阎罗王还要把她锯开”。力群还强调默涵的观点“不但不合《祝福》本身的逻辑,而且也大大减轻了吃人的旧礼教加于祥林嫂灵魂上永恒的痛苦,因而也就大大减轻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的重量了。”[7]一周后的7月2日,默涵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祥林嫂的死》一文,部分同意了力群的观点,文中承认力群的指摘“有的是对的”,“至于祥林嫂是向往地狱还是怕进地狱呢?我以为是这两种情绪她都有。”又说“但从全文看来,怕进地狱的情绪的确更甚于向往地狱的情绪。”[8]两人交锋了一个回合就有了默契,基本达成一致。可以说关于祥林嫂的死,围绕祥林嫂的争论双方都体现出“误打误撞”的特征,力群似乎误解了默涵的本意,而默涵的回应文章又好像言不及义。总之,这次内部争论更像是文字游戏,一个本来很有深度的讨论却落得这样的结局的确令人遗憾,这也说明延安文艺建构时期的鲁迅研究欠缺深入的文本分析,多是政治思想的自我表述,既是诠释鲁迅,更是表明自己心志。
1941年11月3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未易的《文学风格杂语》,文章简单比较了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风格,指出两个人的风格:周作人“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鲁迅则是“老吏断狱,下笔辛辣”,特别是鲁迅的风格“合着时代的步调”,“刺痛人的灵魂,促其猛省”,[9]作者的立场十分明确,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进行价值判断,拥鲁贬周。不过在延安将这兄弟二人的文章风格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比较少见,虽然作者的学理研究有些浅薄,结论也没有新意,但对于全面的了解鲁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无独有偶,1942年11月2日,何其芳的《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同样是从比较的角度发力,并用政治话语作为言说的依据,但是文章很有分量,不乏真知灼见。作者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两人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轨迹,从为人和为文两方面对两人思想发展的不同点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一个是以为集体为主,故是勇猛的战士,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故能从失望中看到希望,故在艺术上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故被有些人认为偏激。故即使谈小事物也有大见解,而其结果由寻路到得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一个是以从个人出发为主,故是掩藏在高雅之极的外衣里的闲谈家,故小处聪明而大处糊涂,故从积极而怀疑而悲观,故在艺术上实质上是一个为艺术派。故自认为是中庸主义者或有绅士气,故喜欢谈小事物,其中又多半只见趣味,而其结果从寻路到迷路,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手掌里,成为民族罪人。”[10]何其芳用诗人的眼光和诗化的批评语言作出的分析很有逻辑说服力。不过,文章的目的并不完全在此,而有更多的现实考虑。作者后面指出:“在现代的中国,叛徒与隐士就不可得兼,而且说得更透彻一点,就不可能有什么隐士。所谓田园诗的境界,所谓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为有诗意的,在现在,实在是应该唾弃的陈腐事物了。个人与集体不但是一个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质的问题。所谓抒情,所谓诗,现在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内容了,那即是为人民的战斗精神,而不再是歌咏自然风景或者个人的哀乐。”[10]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发表意见,也预示着《画梦录》时代的何其芳已经脱胎换骨。如果追溯何其芳本人整风前后的思想变化,本文更像是整风运动的“毕业论文”,比较的是周氏兄弟,彰显的还是自己。
1942年1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羊耳的《梁实秋的“投名状”》一文,梁实秋在《鲁迅与我》中对鲁迅进行了批判,羊耳的文章则是反批判。从表面看,这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因为对鲁迅的看法出现分歧而产生的纷争,但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地方:国民党的《中央周刊》和延安的《解放日报》,背后都是政党意识主导,这里的争论便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学术之争或意气之争,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之争,是政治斗争,所以羊耳在不无感情用事的分析之后指出梁实秋的一系列言论证明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既要作扫荡工作,便无法不走上反共——投降的逻辑发展的道路。”[11]这使批判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不是研究的需要,而是斗争的必需。最终使双方观点中的合理之处都被遮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萧军解读鲁迅小说的《<铸剑>篇一作》[12]于1942年4月1日发表在《解放日报》。萧军在文中首先采用了考据学的方法对故事的历史渊源和主人公眉间尺名字的来历做了考证,接着分析了小说的主题——复仇,又重复了复仇的结果,结尾处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的方法解释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眉间尺因为不冷不热的性情被萧军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黑衣人则代表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力量,应该说文章的前几节还是有学术探讨的气息,而结尾处以当时政治话语图解鲁迅作品,结论牵强附会,除了能看到萧军政治上的日趋进步外,并不能感到其对鲁迅精神的理性把握。
1942年4月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打倒叭儿的“文艺家”》是一篇反驳性的论文,其所指是郑学稼发于《中央周刊》的文章《鲁迅与阿Q》,针对郑文对鲁迅的大肆污蔑,作者认为原因在于“鲁迅生前最憎恶这些叭儿狗文人,一被他发现立刻就骂就打,绝不通融。因此就使他们恨之入骨,一直到他死后的六年还有余恨在心。”[13]事实上,国民党官办刊物对鲁迅的攻击和否定在中共将鲁迅奉为“旗手”之后,这种不同意见已不是对一位文化人的不同理解,而是两党之间政治斗争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如果我们仔细总结回顾中共在延安文艺建构时期对鲁迅的褒扬以及将鲁迅纳入中共组织内部的努力,就可以明白国民党招募的一批文人为何会咬住鲁迅死死不放,而中共每次对鲁迅遭到的围攻都会做出有力而又激烈的反应,从本质上看双方都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
周扬于1944年编选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书中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从选编文章的作者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位置越来越确定,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典化之路。这种有意识地把鲁迅添加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做法是对毛泽东有关鲁迅论述的强化,以十分明了的方式摆明了鲁迅的政治立场,也是在向广大知识分子示意。虽然这不是一部专门研究鲁迅的专辑,但周扬本人所做的《序言》还有引人注意之处。周扬在此书的《序言》中分析毛泽东的《讲话》时这样提到鲁迅:鲁迅懂得在中国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同时他也懂得小资产阶级作家是最容易翻筋斗的,其依据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家脚踏两条船的论述,以此周扬推出“所以一方面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的;另一方面,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思想来说又是有害的东西。”然后直接指出“文艺界需要整风的运动”,[14]周扬的逻辑推理能力令人叹服,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在鲁迅身上找到了依据,真是解铃还须系铃人,鲁迅在此颠覆了自己的追随者。这不就是在具体主张上将鲁迅和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高度一致,鲁迅的规范化解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延安的鲁迅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而是把他当做一面新文化的旗帜,”[15]是为政治目标服务,而且只有这样更能充分体现出鲁迅的价值,对此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予以承认。此外,延安文艺建构时期开创的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鲁迅研究也成为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同样标准进行鲁迅研究的滥觞。
[1]艾思奇.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G]//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2]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432.
[3]须旅.辛亥儿女[G]//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4]徐懋庸.释鲁迅小说阿Q正传[G]//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1366.
[5]徐懋庸.释鲁迅杂文·拿来主义[J].华北文艺,1943(11).
[6]默涵.两个悲剧—读书杂记[N].解放日报,1942-06-02.
[7]力群.略论“祥林嫂的死”[N].解放日报,1942-06-25.
[8]默涵.关于祥林嫂的死[N].解放日报,1942-07-02.
[9]未易.文学风格杂语[N].解放日报,1941-11-03.
[10]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N].解放日报,1942-11-02.
[11]羊耳.梁实秋的“投名状”[N].解放日报,1942-01-21.
[12]箫军.铸剑·篇一作[N].解放日报,1942-04-01.
[13]王子野.打倒叭儿狗的“文艺家”[N].解放日报,1942-04-01.
[14]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M]//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14.
[15]艾克恩.延安文艺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