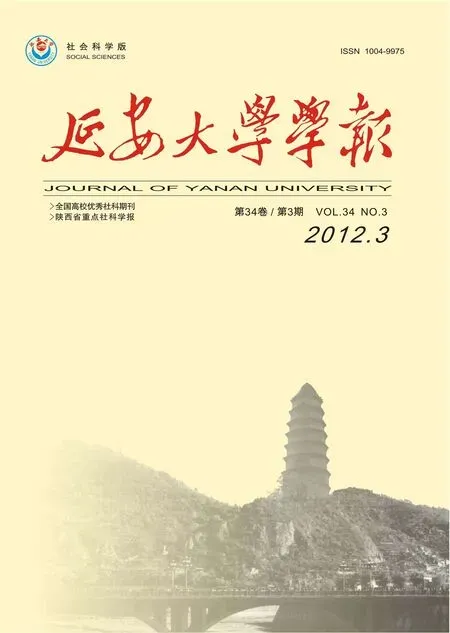对历史转折语境下遵义会议精神的思考
2012-12-09万师
万 师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安徽 马鞍山 243011)
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党的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对已经研究过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发现问题,找寻规律,提供有益的借鉴,因为党的历史是党之根基、国之命脉、民族的精神财富,正确认识与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到党的生命,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对遵义会议的精神研究,应该从历史转折的角度去认真思考,不断把握它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价值,在深入探讨的过程中,在对大量的感性材料加以理性考量基础上,不能只停留在对其转折性的意义的叙述,更不能不求甚解地人云亦云,而是要揭示在历史转折之中深层次的、带规律性的、对当前我党建设起借鉴作用的观点与方法,注重当时我党军事策略与领导智慧的探索,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
所谓历史转折是指“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主要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出现了整体性和根本性的演化创新的变更趋势。”[1]44-45因此,历史转折一般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它与时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从历史转折角度来看,可以把时间分为三个层次,即“客观时间——表示物质存在和运动的连续性和持续性;历法时间——反映着人类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历史时间——反映着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它是测量社会历史过程质向变化的特殊标尺。……客观时间是历法时间、历史时间存在的前提;历法时间受历史时间的支配,因为前者(年、季、气候条件等),是按后者系统来调整和认识的,只有历史的自然才能真正解答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1]68具体地说,将时间划分为这三种形式,是强调时间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所起的不同作用,客观时间应该是指一个或两个历史事件的相互过程,历法时间是指一个历史事件若干时间段,历史时间就是指在若干时间段中发生的事件的关联性。那么,在历史时间的坐标系上,“历史转折特指一种具有多时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它对未来而言,现实是未来的开端;它对过去而言,现实是过去的终结。”[1]71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客观时间分别是从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从“文化大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法时间分别是处在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党的六大之间;处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与“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之间;处在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之间。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时间分别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创立军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血战湘江、红军进军方向的抉择;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提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对纠正冤假错案的呼声、对经济发展的渴望。
笔者认为,我党历史上三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会议,都处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以会议召开为标志,既表明了前一历史时期的结束,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也开启了后一历史时期,从诸多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总之,八七会议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遵义会议既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我党历史发展上的伟大转变,它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时期”[2],也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那么,与八七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比,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主要表现在:
(一)领导作风的转变
所谓领导艺术是指“领导者在个人素质修养基础上,以丰富的领导经验,深厚的领导科学造诣,对各种领导条件、方式、方法,纯熟、巧妙并富有创造性运用,以及通过这种运用表现出来的领导风格和艺术形象。”[3]然而,“左”倾路线领导人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情况是怎样,也不问事情是出于什么原因,一律错误地扣上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进行党内、军内斗争。“李德处理别人从不手软,对于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辄以充分。第七军团长萧劲光因黎川失守,李德下令审判,判了五年徒刑。”[4]而“李德到中央苏区来时,共产国际对他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李德是‘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他要‘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5]77。毛泽东则注意调查研究,即使在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之后,仍然研究红军的情况,关心红军的战事与红军的前途,在长征途中,他不仅保护一批被李德等人不正确处理的红军将领,还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进行沟通,做解释说明工作,使得红军在经过湘江损失之后,避免了走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进入国民党包围圈的危险。所以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参与指挥红军之后,不仅将红军的行动路线以及红军的行动目标都向红军作宣传,让红军能够了解;同时,对重要的战事都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减少失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赢得了红军的信赖。
(二)军事策略的深刻转变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创建革命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并在反对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的战斗中,“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人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6]660-661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运用正确的军事策略,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放弃了毛泽东等制定的军事策略,而当时“左”倾军事策略主要表现在:在建军方面,把红军任务简单化,只是单纯为了打仗;过分强调军队的正规化,反对游击战。在作战方面,不考虑当时军队的装备和素质,一味主张阵地战、正规战,这样在战略上实行速决战,在战役上实施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在进攻中则采取冒险主义,“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同时在防御中就陷入保守主义状态,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没有打退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采用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策略,这种策略表现在“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战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方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敌人。”[6]661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新的军委领导下,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取得了四渡赤水的奇胜,巧渡金沙江,宣告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彻底失败,红军长征“以1935年5月过金沙江作为分界线,自然分为两个部分,渡江以前,共产党人不得不与来自各方面的敌人艰苦战斗;渡江之后,他们必须征服中国最难走的地带。”[7]214毛泽东指挥红军后,正式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亟需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红军如何生存问题与如何发展问题。从此,中央红军克服困难,胜利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正是经过胜利与失败反复多次的经验教训才树立起来,最后得到了一致拥戴。
(三)军队面貌的巨大转变
凡是历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重要的历史会议)的伟大转折,都要经历其发展、准备的过程,并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以工农大众为主的人民军队是党的事业的根基,也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因此,军队面貌的变化意义重大,它主要表现在:第一,红军由目标模糊转向方向明确。“这次战略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但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不仅根本没有作群众性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8]因此,“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高级干部,对长征计划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6]689这样,不仅广大红军指战员心中没有底,只是作被动战斗、转移,遭受了湘江血战后,难免产生不满了。“从政治意义说,这一艰难的长途跋涉(指长征——引者注)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政治局的遵义会议为分水岭: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党人只是在流浪,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会议之后,这段历程就获得了新的意义。”[7]214这种“新的意义”主要是指红军不仅对新改组的红军领导充满信心,也表明了他们对自己进军的方向与前途更加明确。第二,军队由消极低沉转向积极高昂。江华在回忆遵义会议以前的军队情绪时,他用井冈山初创时期进行对比,他当时与以前的状况相同,即都受伤了,但是他对井冈山的感觉是“当时政治路线和军事上战略战术为广大干部战士所理解,所拥护,党内民主空气又比较浓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9]从侧面反映出战士们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不被理解,情绪低落。“我军再克遵义后,部队稍作休整,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来到会场,由张闻天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对吃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从此,红军长征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之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10]
二
针对遵义会议的精神研究,人们会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遵义会议后,不同意见的人们能够求同存异,万众一心,团结奋进,共克维艰?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军队士气大振,不怕困难,英勇顽强,信念坚定?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刚刚组建起来的新的领导集体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上下一致,克服危机,完成长征?为什么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能够互相配合,分工有序,领导有方,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上述的问题既反映了人们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关注,也表明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闪光之处。因而,遵义会议的精神具体表现在:
(一)实事求是,化解主要分歧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到:“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遵义会议就是真正把握好这种时机,即遵义会议“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红军应当走哪条路线和到达哪里。这个问题与谁来领导长征主力部队的问题纠缠在一起。”[11]因此,谁来领导红军,表面上看来似乎无关大局,但在当时就关系到党与红军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同时,红军的领导权问题就决定了红军的命运问题了,所以,遵义会议就显得突出与重要。
第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遵义)会议内容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与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了责任,表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12]203毛泽东强调:“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12]204因此,周恩来后来回忆到:“遵义会议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13]175这样,容易说服人,既便于接受,也有利于团结。博古后来回忆到:“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主义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6]705李维汉也认为,遵义会议只集中讨论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很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鉴于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14]355
第二,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也被确定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对红军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沉重代价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15]在“鸡鸣三省”的地方——云南省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村,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因为“博古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他了。”[13]175“张闻天任中央委员会总负责人,接替了秦邦宪(即博古)的职务。这样毛在级别上仍低于张闻天。但他又成为中央红军的实际负责人,长征的军事方向掌握在他的手中。”[16]289“博古仍保留着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之职,并在(1935年)2月与7月间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在长征中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自觉地维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7]150总之,遵义会议后,重要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作战行动。
(二)勇于负责,敢于开展批评
遵义会议能够在三天的讨论中,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与参会者的勇于负责,敢于开展批评的精神分不开的。
首先,自我解剖,不推卸责任。周恩来在湘江血战之后,他深深地自责,他认为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若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达到两个目标,即“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站稳脚跟,然后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第二,必须有一个具备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5]145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支持毛泽东向贵州进军。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示“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同志对党中央所犯的错误的批评。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地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的代替,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7]145因此,由于周恩来主动、坦诚的自我批评,使得这次会议能够集中精力解决了主要问题,有利于红军胜利进军。
其次,求同存异,革命为重。在遵义会议上,针对左倾领导的错误,开展了批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批判,但博古却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服从组织。”[18]在遵义会议上,“他(即博古)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的讲出来。”[5]210因此,“博古虽然想不通,但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组织,于(1935年)2月6日交出了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箱子,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这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质。”[17]150因此,“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根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也不能被敌人战胜。挫折丝毫不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表现惊惶失措,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16]288
(三)独立自主,讲求解决方法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国人民,依靠本国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取得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关头,依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的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
第一,注重方法,讲求实效。张闻天说:“对我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系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在遵义会议,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未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20]张闻天的这段话反映当时在处理问题的策略,既表明张闻天的襟怀坦白,也说明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更说明了张闻天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一个更大转变。他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已深切领悟到团结大多数人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再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做工作,让正确的意思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21]
第二,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决定或决议、政策的制定,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分不开,因此,党的决策一般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面对红军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在当时状况下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向共产国际去请示,更不可能不解决去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以后才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独特的环境,即在长征途中,独特的时间与地点,只有选择独特的方式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的大事,遵义会议对红军行动的方向的选择,对红军的作战策略的变动,对组织问题的解决,都是围绕着红军指战员自身的命运问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照顾到共产国际的情绪,那就是派陈云赴共产国际去解释遵义会议的情况。因此,遵义会议是独立自主的选择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开端。从此,中国革命在艰难中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自己的问题。”[14]356
[1]张雄.历史转折论——一种实践主体发展哲学的思考[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1-42.
[3]孙敬涛.领导艺术[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1.
[4]谢远学,郭山文.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19.
[5]刘喜发.红军长征全史·第一卷:铁流滚滚——红一方面军战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7][加]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73-74.
[9]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39.
[10]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61-62.
[1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赵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4.
[12]鲁林,陈德全.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21-1949)[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
[13]周恩来.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5]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M].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25.
[16][英]韩素音.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李著鹏,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17]施昌旺.王稼祥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8]陈彪.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博古轶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45.
[19]王玉贵.毛泽东与陈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57.
[20]张闻天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42.
[21]张素华.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历史事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