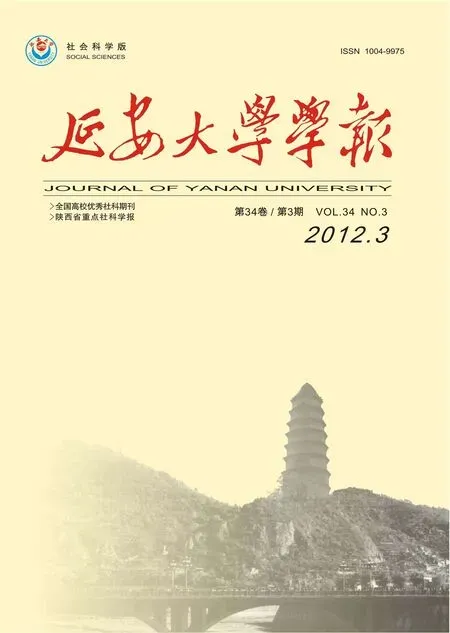伯林的人性论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2012-12-09李红珍曹文宏
李红珍,曹文宏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般而言,人类现有的种种政治理论学说或政治哲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人性理论基础,人性分析实际上构成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史上,伯林显然是最为出色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但吊诡的是,伯林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位卓然不群的反叛者,一位真正的“反潮流”思想家。伯林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历史标签,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敢于反思和批判主流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的领军人物,他试图抽去主流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并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上为自由主义进行重构,而这一切正是基于其关于人性的独特理解。伯林的人性理论在对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人性论进行批判和颠覆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超越。因此,对于伯林的人性论进行学理性考察,特别是分析其人性论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构成对西方主流人性论,也就是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和超越,对于我们理解其自由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不无裨益。
一、多元人性论对普遍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伯林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一位反叛者,与此相应,对于人性的分析伯林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更趋向于用“人的本质”这样的表述来替换启蒙理性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人性”一词。通过对人类观念史的考察,伯林指出,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关于人性的主流观念,也即将人视为具有超越时空的不变本质。伯林进而指出,这种关于人的普遍人性理论实际上是根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滥觞于古希腊自然哲学所开启的古代理性主义,并经由中世纪理性主义,一直演变至启蒙运动所张扬的近代理性主义。这种贯彻西方文明始终的理性主义传统虽然在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探究万物之本原为理论旨趣。尤其是近代启蒙以来受科学与哲学的发展的鼓舞,理性主义者们在去魅之后,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以“理性”的上帝取代“信仰”的上帝,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皆有理性,只要人经理性思考,我们就能“发现人性恒常的普遍原则”,因为“……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人,其行为具有极大的齐一性,人性的根源及运作,始终相同……你知道古希腊罗马人的情操、嗜好和生活历程吗?仔细研究一下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将你对后者进行的大多数考察转移到前者,绝无大错。”[1]这种基于人类同一的理性而得出的关于人的普遍的人性论认为存在一个人类本性的实体,人类的基本属性或本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划一的,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推理:人类,无论处于哪个国家何种时代,基于同样的理性思考和确定不变的人类基本需求,必然要求同样不变的满足,即使是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也会形成相同的目标。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人类本性的构成,既然人类本性相同,人们就无法改变其自身命运,而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经由理性去把握人类的类本性,进而理解其所蕴含的普遍原则,也就是理解支配人类的法律与规则,唯此,人类才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追求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即善”。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其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关于人类良善生活的价值原则只能经由人类的类本性而推演出来,因而这些价值原则必然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
柏林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时代相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但他同时也指出,理性主义者在推翻上帝这一神圣的“神”后,而又创造了理性这一世俗的“神”,并以理性为人类立法,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在伯林看来,理性主义基于人类同一理性而得出的普遍人性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也与人类的经验背道而驰,更是与人的自由属性相抵触。他指出,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是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构成了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2]127在他看来,人们所进行的选择行为更多时候是没有理性根据的,而是一种意志活动,这是因为人都有其自己的自由意志;生命的过程就是源自自由意志的自由创造,因而人在本质上就是自由而特异的。换句话说,人性之特异性就在于能对不同的价值进行自由选择,能自由追求他的目的和规范他的生活。正是基于这种人的自由选择,使得人们的行为和本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进而人类也为自己创造出多样的本性,人类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伯林的结论很明确,并不存在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普遍齐一的人性,人的本质是多元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多元人性论,伯林最终构建起其整体思想大厦的理论基石:价值多元论,并以此展开对作为理性主义的普遍人性论之基础的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深刻批判。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所有真正的问题有且仅有唯一正确答案,而获这个答案的可靠的途径有且仅有一条,这些答案会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伯林指出,就是这种追求终极答案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最终演变成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
于此相反,伯林认为,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因此关于所有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唯一的,获取答案的途径也并非一条,因而诸多答案之间更多的是冲突,不可能和谐一体。同样,在人类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价值,而其中并未所谓的终极价值,且诸多价值之间往往不可通约,难易形成一个合理的批判标准;即使同一价值或善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亦为多元,且要素之间不可华约甚至相互冲突;就文化形式来说,根源于不同文化形式的关于美德和善的观念也是迥异而不可通约,往往是互相冲突。[2]41-45
从根本上而言,伯林从多元人性论出发而形成其价值多元论思想,并在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进行批驳的过程中,剖析了理性主义的普遍人性论的内在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林的多元人性论无疑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82人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别种选择,是由人们的利益诉求决定的;而伯林并没有深入到人据以做出选择的利益层面,因而他的多元人性论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对理性主义普遍人性论的超越仍很有限。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者出于对人类理性无所不能的过度崇拜而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人类掌握了充足而确定的知识,就能够发现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区域的所有人的普遍规则,揭示出普遍、齐一的人性。可见,理性主义的人性论实际上包含两个向度。下文将分别从这两个向度进行论述。
二、历史人性论对非历史和历史决定论的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理性主义人性论的第一个向度就纵向而言它是“……一种人性的决定论,认为不论在何时、何处,人类都具有一些同样不变的需要、情感、与动机。”[2]257伯林认为,这是一种自然主义人性论,将人看作一个自然对象,将人性的形成过程看作一个完全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过程,在理论形式则表现为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人性论。
柏林反对这种假定人的本质是静止不动、亘古不变的人性论。他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批判。一方面,他认为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超越时空,不受任何历史条件制约的非历史主义的东西。人是能够选择并一直在选择,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正是在其不断地进行选择,人性才得以持续地形成,社会历史才得以延续下去。由此可见,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由过去和现在的无数选择所构成的充满无数不确定因素的过程。正是人类的这种持续不断的价值选择活动塑造出人的自我创造性和人性的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人类历史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充满了多样性与复杂性。既然人性与历史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么又何来亘古不变的统一人性?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性又具有历史继承性。在伯林看来,人性是在不断地进行自主选择的过程中得以展现,但这并不是说伯林是在主张纯粹的唯意志主义。相反,伯林认为,人的选择活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在上一代人的选择及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作为选择主体的人本身就是前代人做出选择的积淀物,其特性总是或多或少地地由继承、由他存在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及其伴随的语言所牢牢地框定的。[2]72-75可见,伯林的人性论是历史主义的,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他承认人性是历史发展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外,他还强调尽管人性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但前人的选择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基础,并构不成决定因素。因而,理性主义者关于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类历史的论断就只能是一厢情愿,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强调,并由此提炼出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不可避免地流于空谈,伯林进而指出,根本就不存在研究人类历史规律的这种历史科学。对这种历史决定论进行去魅,他所诉诸的方法就是确认人的选择主体地位,将人当作选择者或能动的力量,承认人们通过选择实现着自我创造和历史发展。
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尽管伯林认为个体所进行的创造活动是一种有特定意识和目的行为,然而由这些活动所推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具有目的性。他的这一非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对人性历史性的强调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将对人性的分析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把个人与历史统一起来,其目的在于强调人类本性是历史过程性和经验性,彰显人性的具体化和差异化,是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人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理性主义关于人性理解的非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决定论,因而赋予了人性鲜活的历史感。然而,他的这一历史主义人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仍相差甚远,其症结在于,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118-119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历史是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创造的,而人性的内容是随着人类劳动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获得展开和走向完善的。伯林这里的历史不过是人们追求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的价值的历史,因而其历史主义仍包含着相当程度的主观元素。于此相关,伯林坚持在个体性原则基础上强调历史主义的人性观,依然还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他只从抽象的人性角度出发把理性人的选择能力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而不是从改变世界能力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所以无法理解人们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人类越来越走向自由。
三、社会人性论对原子式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理性主义人性论的第二个向度在于认为人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伯林指出,自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得以张扬。而理性主义者在推翻上帝这一神圣的“神”后,而又创造了理性这一世俗的“神”,对人的理性予以神化并以理性为人类立法。在理性的神话之下,他们以理性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唯一前提,并将之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最终泯灭了人的感性生命的世界。而当感性因素被剥离于人的本性之外时,人就变成一个个独自进行理性选择的理性人,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所谓的人类社会不过是无数理性人所组成的纯粹机械式集合。理性主义对人类理性的过度神话,也就将现实的人变得虚无缥缈。这样一来,组成人类社会的个体人已不再是经验的感性的多样化的个人,而是徒具理性的千面一律的原子人,是“多神形态”的偶像而已。与此相关,启蒙理想一来对人类理性的强调是要突出人的主体性。随着人的觉醒与人的主体性的日益确立和发挥,由此人们便不知不觉地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本来多样而鲜活的人类个体,在理性的奥卡姆剃刀之下,逐渐被抽去其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最终成为超越时空的抽象化了的孤立原子人。
伯林反对理性主义人性论关于原子式个人的观点。与原子式个人的人性观点相反,伯林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人对价值的自主选择不仅创造着个性自我,而且也影响并创造着社会。尤为重要的是,人的自主选择不仅以前代人的选择为基础,同时还深受同代人选择的影响。人总是属于某一个人类族群与社会,是处于某一特定族群与社会中的个人。因而,他不是在完全独立自主地选择,其用以指导选择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无一不受其所处族群与社会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正是这些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塑造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其带有他身处其中的族群、社会和政治机构本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烙印。原因在于,个人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是由其所处的族群、社会与政治机构提供并构成的,人的尊严与自尊也并非主要依赖于拥有个体权利与自由,还依赖于个人摆脱作为某一民族的成员或作为某一文化传统的实践者所可能遭受的压迫的自由。[2]101-10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断言,如果说族群的生活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个人就是一片树叶或一条嫩枝,是族群生活的这棵大树赋予个体以生命养料;所以,一旦个体与这种族群生活分开,个体就会因为失去生命支撑而变得无所适从甚至调零,而剩下的仅仅是曾经经历过与兴奋过的记忆片段。一言蔽之,只有按自己族群生活的方式来行动和发挥作用,并理解这些行动和作用,才能对个体过去曾经是什么以及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赋予某种意义和价值。[2]106-109
在这里,伯林强调个人的价值观念和目标乃至个人的选择活动无不受其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和制约,人的个性的形成有赖于共同文化形式,这些并不与他所持有的非普遍主义观念构成冲突。这是因为,个体借以进行自我创造的共同文化形式不是一种虚拟的普遍的、一般的形式,而是具有具体的特殊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理性主义者所鼓吹的千人一面,因为对人的个性塑造中最关键的那些因素,比如出生地点和时间、母语环境、家庭背景以及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都是最偶然的东西。
不可否认,相对于理性主义原子式个人人性观,伯林之具有社会性的人性观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性。一方面,他指出,每个人无时无处不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自由属性。正是由于这种选择既创造着自我的个性,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他认为,个人的价值观念、目标以及其所进行的选择本身,无不受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塑造和制约,因而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实现就必须要依赖于族群和历史文化传统这棵大树。更为深刻的是,伯林已经看到即使是民族群体本身也有其自身的生存价值和发展目标,在与其它族群的交往中,一旦这种价值与目标与其他族群价值目标和目标发生冲突时,便会本能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和捍卫。可见,伯林关于个人与社会二者关系的如是理解,相对于原子论个人主义而言,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更为重要的是,它避免了否定个人自由选择的整体主义弊端。
尽管如此,伯林关于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还是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性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而各种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始终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它决定着其他社会关系,包括人们之间观念的关系。这就是说,所谓的人性——如果有的话——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在伯林的理论中,社会关系所指的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关系——人们价值观之间的承继与影响关系,还远未深入的生产关系这一更基础的层次。
总而论之,伯林的人性理论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历史性与社会性相对于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非历史的与历史决定论的、原子式个人的人性论而构成一种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超越,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们对人性进行研究不可绕过的一大理论资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伯林毕竟是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人性理论所蕴含的学术立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带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和阶级烙印。伯林对人性的理解与分析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没有深入到经济的层次,从而脱离不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他对人性的理解更多是强调主体上的分立性,内涵上的利己主义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类之间的相互排斥性。对此我们还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剖析,当然这就属于另一个理论问题了,需另文撰述。
[1]Hume D.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Oxford:Oxford Univers ity Press,1999:150.
[2][英]约翰·格雷.伯林传[M].马俊峰,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