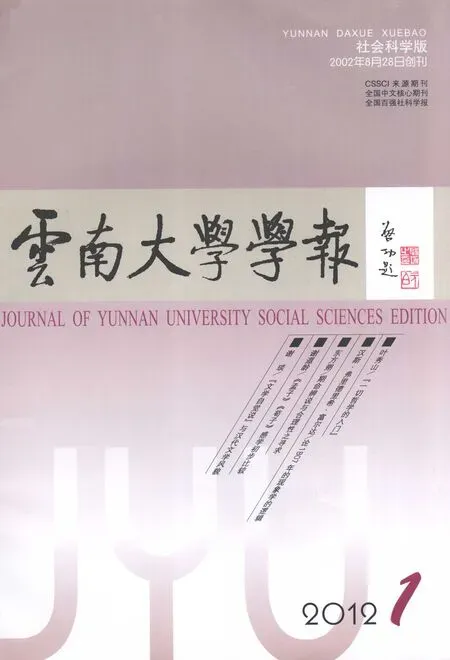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史外传心”与社会行动的结构
——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2012-12-09刘昆笛安徽工程大学芜湖241000
刘昆笛[安徽工程大学,芜湖 241000]
“史外传心”与社会行动的结构
——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刘昆笛
[安徽工程大学,芜湖 241000]
胡安国;仁;社会行动的结构;《春秋》学;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世称武夷先生,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政治家。他以《胡氏春秋传》为经学代表作,践行并完善了二程等北宋理学家的经学文本诠释路向,形成了解读《春秋》文本的新流派,并对理学之四书五经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胡安国看来,两宋之际的政治困境正是王安石废黜《春秋》所造成的恶果:“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1](P6)据胡安国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理论架构,可从三个方面解读《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胡氏春秋传》的宗旨;《胡氏春秋传》对《春秋》书法原则的理解;用北宋理学阐发的义理来对《春秋》案例进行评判。
一、《胡氏春秋传》的宗旨
在儒家的经学传统中,“五经”为孔子晚年定论,是传承道义的文本载体。经学时代的理论创新往往以重新诠释经典文本作为合理性的基础,进而将重新构建的理论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经学的义理论释,首先是揭示出儒家经典的宗旨,即概括六经或五经基本的学术内容、理论目标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功能等。”[2](P164)儒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维系“名分”上,历代对《春秋》经传的诠释着重突出了这一点。胡安国结合自身的理学背景,将孔子作《春秋》的意蕴概括为“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1](P6)这可以看作是胡安国对《春秋》文本的核心观念的理解,也是其作《胡氏春秋传》的指导思想。
自北宋中后期出现有关“尊孟”的激烈辩论以来,孟子对《春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极力推崇孟子的思想,认为唯有孟子能够真正地理解孔子作《春秋》的本意,指出“《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1](P5)可以说,《春秋》已经上升为传承圣人“心法”的典籍,其目的在于彻底消除邪说暴行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构建能够保障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公共生活规则。而“孔子作《春秋》”这一历史事件,可以与禹治洪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相提并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P273)不过,孟子也意识到,作为鲁国的旧史,《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倘若借助“笔削”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似已构成僭越的嫌疑。但出于“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胡安国毅然继承了孟子的“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3](P273)的学术传统。
宋代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以经学阐释为核心的所谓“宋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理学的影响。作为儒家经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学”在义理阐发方面与理学有着高度的一致,突出地表现为主要的经学家往往也是理学家。理学家在阐发义理时,通常也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方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4](P11)宋学和理学的相容相生,使得宋学较之汉学在逻辑架构上更加深刻,同时也具有浓厚的伦理说教色彩。“理学是理性程度很高的学术思潮,宋学因此获得了对传统经学(汉学)中非历史、非科学的内容的发现和批判的能力。理学也是伦理道德观念极强的儒学思潮,这又使宋学经说的义理内容中伦理(即理学之‘理’)的色彩分外鲜明。”[2](P137)胡安国的《春秋》学研究就是在这种浓厚的理学氛围中展开的,他也从程颐那里学到了先领悟理学大义、后进行经典诠释的方法,将理学大义贯穿于对《春秋》经典文本的解读中,创建了理学体系中的《春秋》学研究流派。
胡安国将“明天理,灭私欲”的思想贯穿于对《春秋》文本的诠释过程中,这是对二程理学的继承与推进。二程指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矣”,[5](P312)认为“天理”和“人欲”构成了对立关系。胡安国根据二程的义理,提出“有国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灭之也”,[1](P51)通过在君臣父子之礼、兄弟之伦、夫妻伦理等方面的展开,用以诠释《春秋》案例,发挥对两宋社会与政治伦理建构的指导作用。《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国旧史之后的产物,或笔或削,即是对原史文本中的一些文字或加以转载,或完全削去,以体现自己对历史事件的好恶评判;《胡氏春秋传》则将孔子的评判分为“书”与“不书”,以此表达不同程度的褒贬涵义。在胡安国的经学视野中,孔子笔削《春秋》,以鲁国历史为对象,评判二百四十二年中出现的历史事件,为实现拨乱反正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案。
胡安国认为,孔子笔削《春秋》的功罪评判,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了此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1](P6)并由此指出了《春秋》对儒者的重要意义,即儒者在学习“四书”,获得初步的义理后,应当对《春秋》进行深入研习,在解读具体案例的过程中深化对义理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掌握义理,才能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更好地贯彻义理,如果只停留在对义理的浅层理解上,就会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知所措。“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1](P6)其主要原因在于义理仅从语言层次上来看是比较简单的,而在内容上却是十分庞杂的,如果缺乏对具体案例的求证过程,就无法把握义理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
二、《胡氏春秋传》对《春秋》书法原则的理解
胡安国对《春秋》书法的诠释,不仅体现在君臣之礼上,还体现在包括夫妻伦理、长幼之序、“夷夏之辨”等诸多方面,这就使得后人将《胡氏春秋传》归为“一字褒贬”的《春秋》诠释文本序列。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了“一字褒贬”的定义:“谓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即借事明义也,谓一字不敢胡乱下,即一字褒贬也。谓书字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亦即一字褒贬之旨。”[6](P72)其又在《经学历史》中将《胡氏春秋传》归入主张“一字褒贬”的诠释路向中,认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榖》,皆不得谓其非”。[7](P250)然这种划分却是片面的,其原因在于忽视了胡安国辨析《春秋》中“阙文”的尺度。所谓“阙文”,就是《春秋》文本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有时会缺少地点、时间,甚至对某些时间段的记录出现了空白,以及一些书法中的常规用语亦有缺失。
在《春秋》学史上,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政治立场,研究者对《春秋》文本的诠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崔大华先生在《儒学引论》中指出,《春秋》的义释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历史原则、书法原则和记实原则。[2](P186)历史原则是对《春秋》所记述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左氏春秋》属于此类;记实原则是直接将《春秋》文本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记述作为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记载来分析;而书法原则是训释《春秋》记事的表达原则,《公羊传》和《榖梁传》便属于此类。综观《胡氏春秋传》可以发现,胡安国的《春秋》义释模式属于书法原则。他扬弃了《公羊传》和《榖梁传》中的书法规则,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时包含褒贬之义,而对《公羊传》和《榖梁传》中的褒贬书法持扬弃态度,将褒贬的标准定为理学大义,认为理学大义和孔子“书法”的本意是相通的。
若从孔子笔削《春秋》的角度出发,胡安国全然可将这些阙文视为孔子表达贬斥或者隐讳的特殊处理方式,但他主张根据《春秋》文本中类似事件的比较,来确定是否鲁国旧史中确实出现了漏记或佚失,从而使得孔子转录时出现了空缺。“凡阙文,有断以大义削之而非阙者,有本据旧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増者。”[1](P26)这反映了胡安国进行文本诠释时是尽可能保持客观态度的。比如,桓公十四年的记载中出现了“夏五”的记载,这在胡安国看来就是典型的“阙文”,他认为出现的原因就是鲁国旧史疏漏或者经典文本在传承中出现的佚失。而《春秋》桓公三年“春正月”而不是常规的“春王正月”,在胡安国看来,这是孔子对鲁桓公即位三年中无人为隐公报仇、“臣贼子肆其凶逆,无所忌惮,人之大伦灭矣”的现象而感到愤怒,故而将“王”削去以贬斥桓公及其臣子目无王法的行为。胡安国辨析《春秋》“阙文”的尺度,说明了他在进行文本诠释时的审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书者,有矣。尽亦视此为鉴,可也。”[1](P153)他不因“阙文”随意增加《春秋》文本中的文字,慎重对待元典,因而区别于以篡改经典作为掩饰政治意图的诠释活动。
在对《春秋》进行诠释的文本中,最先采取书法原则的当属《公羊传》和《榖梁传》,此二传所树立的书法原则按照各自的师法体系被传承和发挥,直至宋朝方被中止。胡安国对待三传的态度则相对客观,他的《春秋传》中所阐释的书法原则兼采三传而又突破三传,朱熹称其为有“开阖精神”。比如在对《春秋》所记战争的书法“侵”和“伐”的区分上,《左传》认为“有钟鼓曰伐,无钟鼓曰侵”,因此,“侵”和“伐”只有战争形式与礼仪上的差异,而没有德性方面的区别。胡安国则先后考察了《尚书·泰誓》、《诗经·皇矣》和《周官》中的有关记载,赋予这两种战争方式以道德属性,以进行褒贬上的区分:“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声罪者鸣钟击鼓,整众而行兵法,所谓正也;潜师者衔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谓奇也。”[1](P70)而解释桓公元年《春秋》经文仍书写“春王正月公即位”这一现象时,《公羊传》认为,这说明了桓公即位的合法性,理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子以母贵”,隐公即位并不具备合法性,只是为桓公摄政而已。胡安国将《公羊传》的解释斥为邪说:“礼不得为而惠公纵其邪心而为之,隠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为邪说而传之,汉朝又引为邪议而用之,夫妇之大伦乱矣。”[1](P40)因此,胡安国倾向于《榖梁传》以长幼之序来确定隐公即位合法性的说法。分析三传不足之处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都充分展示了胡安国《春秋传》的书法原则对三传的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书法原则的创新,原因在于他将理学大义贯穿于对经典文本的解释之中。
三、为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供经典依据
《春秋》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在儒家的叙述方式中,直接阐发义理属于“空言”,借助于评析历史事件来具体说明公共生活规则的调适作用,可以称为“行事”。“空言”与“行事”构成了体用关系,具体说来,“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1](P6)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案例中呈现义理,这正是理学话语环境下的《春秋》学研究的基本理路,而其旨归见诸于当下社会的具体政治行为实践。这也是理学体系中“外王”路径的展开。
胡安国结合两宋之际的政治现实,提出了其作《春秋传》的宗旨:“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1](P6)并认为这和孔子笔削《春秋》的宗旨是一致的。“尊君父”是对北宋以来经学的“尊王”思潮的跟从,也是胡安国对孙复与朱长文一脉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两宋之际,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妥善解决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流话题,胡安国在《春秋传》中贯入的理学大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尊王攘夷”。《春秋》学话语体系中的尊王有两种解释,以何休为代表的一系主张“王鲁”,假托鲁国国君为天子;另一系则认为尊王的对象应是周天子。胡安国将《春秋》学中的“尊王”解释为尊崇周天子,投射于北宋末期的政治状况,则表现为拥戴北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胡安国在《胡氏春秋传》的开始部分就“元年春王正月”这一书法作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解读,他指出:“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1](P23)从纪年方式来看,这种书法显示了孔子对周天子的尊重。《春秋》经文开始于隐公元年,此时周王朝的正月开始算起,而不是鲁国旧史中的实际时间,这足以让后世知道,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仍然是周天子统治下的历史,而非《公羊传》为了推崇王道而盛赞的“大一统”。从《春秋》经文不书隐公“即位”这一事例来看,胡安国认为,孔子在这里极力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尤其表现为对诸侯的控制与震慑。当然,这只是一种推崇中央集权的政治观念,并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
胡安国从经典文本整理出来的“讨乱贼”这一条例,充分反映了他本人在化解南宋政治危机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从南宋政治的实际状况来看,内忧外患迫在眉睫。胡安国主张驱逐朝廷内部的奸党,要求君主必须亲近贤臣,同时严厉镇压诸如钟相、杨幺等发动的农民起义。在发挥国家机器作用的同时,必须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问题,“辟邪说”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两宋之际,政治秩序混乱,思想领域出现了许多与儒家正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异端邪说,严重地影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例如,有些学者主张放弃正统的儒家思想,代之以汉唐的治国方略,以霸道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胡安国将这些危害儒家思想的理论观念视为异端邪说,要求朝廷采取有效可行的措施,彻底消除这些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破就有立,“攻乎异端”只是为理学的发展扫除思想方面的障碍,而遵循上述路线,将理学上升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胡安国的梦想。可以说,《春秋》学只是胡安国思想的外壳,而隐藏在经典诠释背后的理学思想则是胡安国为之奋斗终生的社会理想。两宋之际的理学,并非是空洞的道德说教或者类似于明清时代的帖括之学。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此时的社会状况可以概括为“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尤其是朝廷南渡以后,统治阶层沉湎于安逸享乐,无暇虑及收复失地、光复中原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面对这种颓丧的局面,胡安国感到非常忧虑。儒家特有的忧患意识促使他通过经学诠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要求统治阶层以身作则,借鉴《春秋》案例,祛除心中滋长的不合理的欲望,按照天理行事,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胡安国的这一主张不仅具有伦理道德层面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根除南宋朝廷所面临的政治痼疾。统治阶层的奢靡与苟安是最为突出的“人欲”,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就很容易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外敌入侵时刻威胁着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统治区域内部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会酿成社会剧变,直接促成南宋朝廷的灭亡。因此,消除统治阶层不合理的欲求,激发民族意识,同心协力,共度难关,成为胡安国最想表达的政治诉求。
“用夏变夷”则是处理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原则,其要旨在于不仅要在地域上坚决抵抗外族侵略,更要在思想层面上防止蛮夷意识的渗透。针对两宋之际愈发尖锐的民族矛盾,胡安国反思了自唐五代以来民族政策的失误,他承继孔、孟和二程的夷夏理论,高度强调夷夏之辨,表现在政治主张上是坚决抵抗金朝的进攻,不向金朝妥协,也不承认金朝的对等地位;表现在思想方面则主张肃清社会文化中的夷狄因素,防止“以夷变夏”。不过,胡安国也反对在抵制少数民族入侵方面穷兵黩武、赶尽杀绝,只主张将他们赶出中原,为他们留出一定的生存空间。胡安国的“夷夏之辨”思想对元、明、清初数百年的民族政策都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对近代的中西关系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四、结 语
胡安国在承继二程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的政治主张,以此作为自己作《春秋传》的宗旨,目的在于以《春秋》文本为载体,表达自己在消除内忧外患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倘若认同汉儒所谓《春秋》为万世立法的基本信念,就不难赞同胡安国所谓“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在这种极具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学说中,儒家的治国道理通行于千秋万世,因而孔子在笔削《春秋》时贯注在其中的义理,在千百年后仍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具体行动,只不过特殊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理学家所谓“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在胡安国的经典诠释中显现得尤为突出,他说:“然世有先后,人心之所同然,一尔。苟得其同然者,虽越宇宙,若见圣人亲炙之也,而《春秋》之权度在我矣。”[1](P6)这里所说的“人心之所同然”是指义理,从终极层面来看,义理的存在形式是超越的“一”,尽管不同的儒家学者有着形态各异的思想学说,受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但深入体认“理一分殊”的存在方式,也能与圣人的经典文本相契合,更能登堂入室,成为传承《春秋》大义的有功之臣。从社会行动的结构来看,“胡安国阐明《春秋》‘大义’所以强调封建纲常,突出‘尊王攘夷’是着眼于现实,立足于‘经世’的。”[4](P241)当然,这也是历代《春秋》学的主要内容。
[1]胡安国.胡氏春秋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崔大华.儒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侯外庐,邱汉生,张恺之.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陆继萍
B244
A
1671-7511(2012)01-0055-05
2011-03-21
刘昆笛,男,哲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