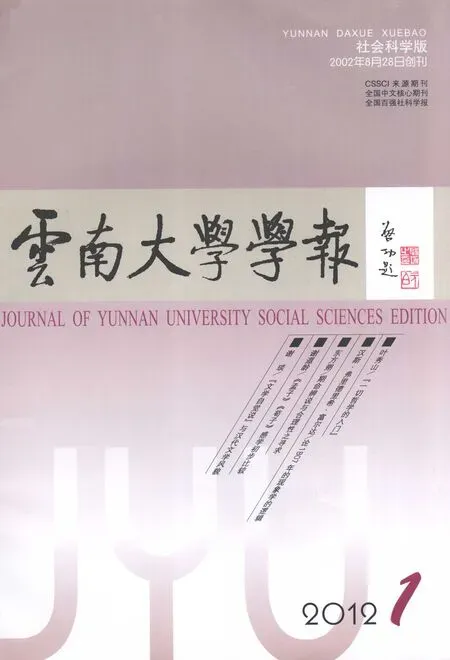期命辨说与合理性之寻求
——荀子辨说理性的一种了解方式
2012-12-09东方朔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东方朔[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期命辨说与合理性之寻求
——荀子辨说理性的一种了解方式
东方朔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荀子;期命辨说;确定性;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荀子不竞求价值根源,倚重于礼法,不免有导致专制之倾向。但荀子言辨说而主“兼听”、“兼覆”之德,倡“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之兼术,更呈“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辨”之德慧,其开放性之胸襟、合理性之预设或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反省和重视。荀子虽坚执“先王之道”的信念,然而,在其辨说理性的慧照之下,此先王之道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开放性和合理性之特征。
一、 引言
在荀子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皆认为,荀子的思想具有专制、独裁之倾向,易于堕入强制性的权力机栝之中。此种看法,或非只是空穴来风,相信必有其所以得出如此看法之依据。在理论上,言礼义法度必须先区分“奠基”与“动机”问题之不同,前者所涉及的是礼义法度之作为道德规范的义务性或道德性的理性根据问题,而后者所要解决的则是为了何种目的而去实践道德的问题。若对礼义法度之最终的理性根据的追问转成对礼义法度之情境性使用(“因事制宜”)之解释,在理论逻辑上即可能导致堕入对外在权威之服从的机栝之中。故劳思光先生认为,“荀子所论之价值根源,既不归于‘心’,又不归于非人格化之‘天’……荀子价值论之唯一出路,乃只有将价值根源归于某一权威主宰。实言之,即走入权威主义。”[1](P339)*此外,徐复观先生认为,荀子所言之礼完全限定于经验界中,否定了道德向上超越的精神,且此一不以仁心为基底的礼,也引出重刑罚、尊君、重势的意味来,以致多少漂浮着极权主义的气息。[2](P258~259)
在当代新儒家中,对荀子最具了解之同情者,似无过于唐君毅先生,此固不赘。然而,在唐先生对荀子思想的诸多疏解中,我们发现,其中有一段唐先生对荀子之论言辩的分析颇有意味,亦颇值得注意。荀子在《正名》篇中云:“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故明君临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荀子此一言论,其初意乃在说明,在“理想”的政治状态之下,明君只当守其国君之名分,以道一民,而不必与民辨说是非,盖民众愚而难晓,故明君可临之以权势,导之以正道,申之以命令,晓之以道理,禁之以刑罚,如是,则民化道神速,何用辨说?!然而,今君子之所以汲汲于辨说,正在于“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荀子此段话固从外在机缘上阐明了君子必辩之理由,但另一方面也向我们传达了何以在理想的圣王政治之下人们毋须辨说的原因。然而,唐先生却由此看出了问题,以为“荀子此言,固有流弊。因以势以刑临人而禁人之言,正为下开李斯韩非之以政摄教之说,导致焚书坑儒之祸者。荀子于《非相》篇,亦已有奸人之辩,圣王起,当先诛之之意。孔子之杀少正卯,正缘荀子此意而为法家学者所传,为孟学者,盖决无此唯以势与刑临人之论也”。[3](P276)
但凡具有存在之实感的人,相信对唐先生之幽怨皆会有感同身受的领会,殊非只是对月兴叹,枉自吟哦。荀子之思想,根本六经,枝叶诸子,在本质上为儒家之一代表而与法家有根本的区别,此已为多数学者所赞同。然而,一般人常常认为,荀子尊君、重势,其起隆正、察是非、治曲直,言议辨说之间,似乎一切皆以王制为标准,以致人们不免会认为荀子之思想具有专制、独断的色彩,良非无故。
对上述看法我们无意于提出异议,但我们的问题却由唐先生之论荀子的辨说引发而来。在先秦儒家中,荀子好辩且善辩,显然,此辨说或言辩,就其本义而言,乃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寻求一合理性之结论。具体到荀子,在圣王不作的情境下,则此所谓“言辨”乃是“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勇;有兼复之厚,而无伐德之色”(《正名》)之辨,亦是“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正名》)之辨,或依唐先生,此辨说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人所共认,而具公共之客观意义者”。[3](P268)果如是,则我们不免要问,一方面,在理想的王道政治之下,荀子似乎要以势以刑临人而禁人以言,使民无说、无辩而流弊于专制或独断;但另一方面,在荀子的辨说世界中,他却又主张“兼听”、“兼复”,说以仁心,听以学心,辨以公心,以求是是非非,表现出强烈的平和、宽容的合理性寻求。我们的问题是,上述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结论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究竟是如何统一的?荀子之辨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主义品格,其合理性和意义究竟何在?本文无意于从整体上说明荀子的思想与专制和独裁之关系,而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荀子之“期命辨说”观念以揭示其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二、为何辩?责任的担当与成人的根据
在理论上,“为何辩”的问题乃是要究明辨说的原因,不论此原因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但荀子为何要“辩”?简言之,即是要在战国时期百家奔竞、嚣嚣多言而又徒相为訾的情况下,说服他人接受由理性发现的真理(先王之道)。
然而,话虽这么说,要真正实现此一目的却又谈何容易,盖战国之际,世衰道丧,百家异说之间,或是或非,哓哓而无定准,流弊所及,“上诈谖而弃信,说炜华而谲诳”。顾炎武认为,春秋时的礼文风尚,至战国已荡然消散。*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牟宗三先生则认为,战国之精神表现为一尽“物量”之精神,亦即只表现其原始的物质生命的清爽与粗暴,而无理性之根据为其背景。各国君主皆沉浸在战争的棋盘之中见其清脆和爽朗,好勇、好色、好货,冲口而出,毫无遮掩。然而,在物质生命之奇光幻彩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生命的僵固和苍茫,文化理想黯然不彰,周文所凝结的政治格局及价值关怀土崩瓦解。[4](P100~112)荀书记所谓“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尧问》),已将当时之情状描绘得淋漓尽致。从学术上看,似乎人人各呈其能,百家各立异论,说士盈天下,然而,他们多是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为说而说,为论而论,游戏诡辩,有文奸邪说之意,而无合文通治之实。“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儒效》)*杨宽认为:“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确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重要门径,因而游说和从师也就成为一时风尚……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5](P403)他们或趋炎附势,徒骋浮辞,或愤世嫉俗,游离梦想,各派相竞,舌底翻澜,欲其自成。此一政治、思想上的悖乱,其直接之结果即是造成人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终失其正求。故荀子云:“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解蔽》)
黑格尔曾言:“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6](P54)此一没落表现于孟子之好辩,则在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荀子之“为何辩”的外在原因与孟子一脉相承:辟邪说,明大道,正是非,经国定分,此皆儒者之所以为儒者的历史责任和道德义务之担当,毫无假借,毫无躲闪。然而,荀子之“为何辩”的原因尚有进于孟子者,即在于荀子将此“辨”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规定和特色。荀子云: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
在荀子那里,“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而此“辨”又是以人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分”和“义”来表示的。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既在于有辨,则人自应发挥此一特色,以远离禽兽。[7](P83)但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客观上,现实世界所表现的“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是非不明,名实混乱”,在荀子那里,只构成了“为何辩”的外在原因,此一外在原因转而成为一种儒者的道义担当。当然,此外在原因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亦当分为两层,即“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为一层,“是非不明,名实混乱”为另一层。就“为何辩”的问题而言,前者偏于儒者立场之宣示,后者则偏于事实问题之解决,两者之间应存有微妙的差别。但另一方面,荀子之“为何辩”的原因又根源于人的规定性本身,就人之所以为人在其“有辨”而言,以此“辨”发而为辨说固然是儒者的不二选择,但荀子之此一看法显然将“为何辩”的问题由外转之于内,换言之,辨的问题已经转变为“成人”(being a person)的必要条件,故云“人道莫不有辨”(《非相》)。如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荀子累言“君子必辩”,此“必”除了衬托出客观情势之必要、必须和迫切之外,辨说也是使人成其为人的必需和必然。我们曾言,荀子之“辨”是以人在社会之共同体中的“分”和“义”来表示的,若此“分”和“义”作为一种价值以为“辨”的实质性表示,引申而言,则荀子此“辨”实非单纯的认知能力,或至少其不满足于只是一种认知能力,而可包含自我理解与诠释在内,*牟宗三先生认为,荀子此“辨”乃“治辨之极”之“辨”,非思辨义之辨。[8](P210)庄锦章教授认为,荀子此“辨”乃是划分社会界限和等级的能力。[9](P90)“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故君子必之。荀子云:
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
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非相》)
凡人皆乐于言其所喜之言,此似可以理解为一种普遍的陈说,亦即人皆有好辨说之特点,但对何以“君子必辩”,陈大齐先生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辨说既以象道为任务,故必确能尽此任务的辨说,才有价值,不能尽此任务的,便成为无价值的辨说……故必自己所见的道理确属是而不非,确属合于礼义,且亦有助于平治,而他人犹未能信从,或犹有所怀疑,于是才用得到辨说,才不可以不辩,以尽开悟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必他人的言论确属非而不是,确属不合理义,足于招致悖乱,而其人与徒众犹误信以为是,于是才用得到辨说,才不可以不辩,以尽纠正的责任”。[7](P85)但荀子何以谓“君子为甚”?又,荀子何以汲汲然而言“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的确,多读荀子的著作,人们皆不免有一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即荀子之言辨说有极强的目的性,辨说乃是为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正名》)而此所谓“道”即圣王之道,“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解蔽》)由是而言,所谓“期命辨说”,乃是“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名》)。许多学者或据此以为,在荀子的思想中,“先王之道”、“礼义法度”等早已在实质上成了其所谓“辨说”的最终目标,故推而言之,则其所着力讨论的辨说充其量不过是为“辩”成或“证”成此一目标之手段而已。此一看法的言下之意或包含着——荀子之辨说并无独立的意义,至少此辨说由于其目标的先在性而削弱了其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其拒斥和责难别家学说也一样表现出某种狭隘的、实用的观念。此类看法并非没有一定道理,但或有失之片面之虞。对此,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首先,就“为何辩”而言,何以“君子必辩”以及何以“君子为甚”,表达的是一位儒者在面对天下大乱,而君子又“无埶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情况下,为“正道辨奸”以求一“正理平治”之社会而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所以,君子之“必”和“甚”,表达的是一种信念和担当。然而,既谓之“信念和担当”,则必有其心志所向往之目标,必有其立场之选择和信念之落实,此非独荀子为然,各家亦然。故就此而言,荀子念兹在兹于先王之道,乐于言先王之言,并坚执于圣人之辩,乃属于个人畅达其生命之途的选择问题,且此一问题正好是“为何辩”之疑问之所涵。其次,个人信念和立场之持执并非等于说其所持执之信念、立场可以不经由合乎辨说程序或辨说理性之检验就可为他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这是属于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为何辨”与“如何辩”在我们的观念中必须有层次上的区分。辨说,若作为一个有待追问的问题(“如何辩”),理论上当集中于辨说所表达的原则、规则或一些程序性理性之表达,而这些问题与“为何辩”原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不可完全混作一谈。换言之,就辨说而言,目标(目的)之确立固然与手段(方法)之选择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此处并不妨碍我们就手段或方法问题作一相对独立的考察,而这正是本文的任务。目的是否合理是一个问题,而方法是否合理又是另一个问题。当然,此两者之间亦确有影响,具体到荀子而言,即辨说目标之确立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辨说内容和范围的开放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别家别派之精神和宗旨的全面认识。荀子云:
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有所止矣。(《儒效》)
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非相》)
此处“有所止”之“止”非停止、止息之意,而是确立目标、目的之意,意即君子之辨说非一味地随题而走,漫无目的,而此目的就是确立自己辨说的“本分”,杨倞注“分:上下贵贱之分”,亦即礼义之道也。换言之,荀子之言辨说乃必以礼义之道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外此即不辩、不听,故荀子又云: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天论》)
从上述说法中我们不难看出,荀子之辨说有着极为强烈的目的性和现实性,凡有益于治道者,立之,凡无益于治道者,废之、弃之,此一情怀与当年孟子“闲先圣之道,距杨墨,防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以及“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之说不能不看作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两者又皆强烈地表达出儒家“价值优先”的立场,其间的得失,固不待言。[10]依荀子,那些对秩序之建立和国家之平治毫无裨益的言论,君子不与辩;而对于那些徒呈辞巧以及枭乱是非之言论,荀子即直斥之为奸言、奸事,“非辨治乱,非治人道”乃是君子之所以不言不辩的标准,违此标准,即是奇辞、怪说和奸说;就辨说本身而言,主张之确立与辨说过程中所当体现的理性仍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此亦理之易明者也。
基本上,对荀子而言,“为何辩”的问题主要出于三个方面。一则作为儒者的道义担当,亦即在天下枭乱、圣王不作的历史情境下,高扬和“说出”儒家的真理,此所表达的是立场之宣示。二则在是非不分、名实混乱的情况下,藉由辨说以明是非、正名实。但此处之“是非”、“名实”又可有两面:一是在立场视角下所表达的价值标准,谓合不合先王之准则、规范;一是在客观的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颠倒黑白、指东为西的现象,后者所表达的是中性意义上的事实。三则是荀子把辨说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此一原因亦可包含中性意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荀子之辨说(“为何辩”)并非完全归于个人的立场和主张的宣示,而是有其超越立场之外的客观需要。
三、如何辩?确定性之获得
“如何辩”让人想到技术问题或方法问题,但任何方法皆是针对问题而来。我们的重点当然不是醉心于展示在荀子的思想中问题与方法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要透过荀子对问题的解决本身所展示给我们的辨说理性和辨说原则,并藉此来分析其中所存在的合理性因素。
诚如所云,所谓辨说,简言之,就是为了摆事实、讲道理,是以语言(language)或言语(speech)为媒介把自己的观念、想法或道理表达出来。辨说不是一个人的兀自独白或喃喃自语。一般人常常认为,辨说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有两方面的目的,即以“成功”为目的或以“理解”为目的,前者既可以通过诡辩和巧辞来达到,亦可通过以“势”与“刑”为奥援来达到,但显然这种辨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辨说本身的意义,而带有宣教的色彩,对此,本文无意置辞。后者亦即以“理解”为目的的辨说乃是以展示合理性为基础,以他人表示同意(达成共识)为完成。以“理解”为目的的辨说若其最终达成了理解或共识,即可意味着此辨说已经成功,但此成功却不同于前者只以“成功”为辨说之目的的成功,换言之,以理解为目的的辨说若其真正达成了理解,即已经包含了成功,所不同的是,此成功之获致乃基于辨说理性而非基于诡辩或其他奥援,此间道理当不难理解。
然而,辨说若要达成辩者之间的理解或共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是要寻求名言、辞说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换言之,辨说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的“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便是一个必要的预设,甲是甲、乙是乙,是为是、非为非。若说甲为乙,指是为非,辨说固不能进行,连日常之间的对话亦成困难。《正名》篇谓:“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此段若剔除其“意识形态”的成份,我们未尝不可将之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现实的描写,荀子还把当时擅作以乱名的现象总结为三种表现形式(“三惑”),即宋子和墨者的用名以乱名,惠施、宋子和墨者的用实以乱名,以及墨者的用名以乱实,并一一求其对治之方。
我们曾指出,荀子之正名有其政治上“正理平治”的要求,非只为纯逻辑之兴趣而讨论名学,所谓“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王制》)但另一方面,不论何人出于何种政治主张或政治立场,若要使辨说得以顺利进行,即名言概念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必得首先加以肯定,此即荀子所说的“直”。何谓“直”?荀子云:“是谓是,非谓非,曰直。”(《修身》)思维上的“直”表达的是对正确思维的规律性的认识,此即《正名》篇所说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而这不正是辨说所能够进行的先决条件么?
荀子所谓的“名”大体类似于逻辑的“概念”,但也不尽然。若站在现代逻辑的立场看,概念当是反映对象物之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亦即概念与对象物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摹本关系,从这一意义上看,荀子之“名闻而实喻”、“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等说法显然与此具有大体相当的含义。然而,荀子的“名”还有语言理论的意义,而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用于表达思想、交流意见以协调行动的工具,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所谓“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足于相通则舍之矣”(《正名》)。这样,“名”(语言)就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而有异于“名闻而实喻”,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正名》)。这种相异即说明了“名”的逻辑意义与“名”的语文意义之不同。荀子的“名”除了具有逻辑的、语言理论的意义之外,又具有政治历史文化的意义,所以,荀子提出了“刑名”、“爵名”和“文名”等概念。毫无疑问,详细讨论荀子之名学并非本文的任务,荀子不仅对制名的目的(杨倞谓“物无名则不可分辨”)和制名的根据(人的感觉经验加上心官之理解)有认真的分析,而且对制名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有精当的说明。就辨说得以进行所必要的名言的确定性而言,制名的原则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何谓制名的原则呢?荀子云: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正名》)
此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应是荀子制名的一个根本原则,盖凡对象物为同实亦即同一类事物,即令其以同名;凡对象物为异实亦即异类事物,即令其以异名,不可错杂混乱。
辨说过程中除了名言概念要有统一性和确定性之外,显然还要讲求兼合主宾概念以表达一完整的意思,此即荀子所谓的“辞”。“辞”大体来说相当于普通逻辑所谓的判断。荀子有一段论述,对名、辞、期、命和辨说有一完整的说明,荀子云: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
关于“名”,前面我们已经作了说明,它是用来期会“实”的,名实相应即志意可通,沟通、辨说乃可得以进行,故云“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正名》)依荀子,有一对象物,而人不知,然后命之以名,使人知晓。命名之后,或因此名尚未流行,或因此名人不熟知,还不能起到传达的作用,则须继之以期,待人知道此名之所指,如是,即名就可以达意了。若期而不知,就须加以说明,说明后或由于误解,或由于歧义,仍不知,那就需要反复辨说,以求真切了解,所以,荀子认为期命辨说乃是人类文化的大作用,也是政府施政的起点。
《墨辩·小取》有所谓“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一说,“辞”的作用在抒意,但如何“抒意”却未说明,而荀子认为“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杨倞注:“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如此看来,“辞”是兼合主宾概念以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判断,这显然要比《墨辩》更为严密。如一个辞被表达为这样一个句子:“天空是蔚蓝的”,若按照荀子制名之原则,在这样一个句子中,“天空”与“蔚蓝”便是两个异实之名,把这两个异实之名连接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便是一个逻辑上的判断,即是辞。
了解了为物制名,以使名通晓,辨说乃为可能。依荀子,辨说是用始终同义、没有前后矛盾的名言来阐明事理的,而辨说的目的和任务即是为了明是非、决嫌疑,当然,最终即是为了明白治理国家恒常不变的道理。明道是最高目的,但此并非意味着,为了明道就可以指是为非,罔顾名、辞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即便为了阐明和辨说圣王的原理、原则,也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正确地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若依此道理为标准以辨淫辞、奇辞之说,那么,就可以像引绳墨以定曲直一样一目了然,如是,则谲诳之言、曲辩之议便不能淆乱人的思想,存此以立照,则其他百家也不能藏匿其正邪之形迹。
四、如何辩?合理性之寻求
辨说基本上是在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之间进行的对话活动,此一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当然要以名言、辞说的统一性和确定性作为先决条件,然而,当我们把辨说作为对话活动来理解时,当马上想到,荀子辨说的对象不仅是当时的诸子百家,还包括各国君主,而荀子之所以要辨说,又包含了相当强烈的目的性,亦即要说出真理(先王之道),并说服人们接受他所认可的真理(先王之道),换言之,荀子辨说中所表现的对话活动,是一种说服中的对话,或在对话中的说服。
说服并不排除合理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并不矛盾。合情合理、以理服人,本身即为“说服”概念之所含。所当注意的是,所谓“以理服人”之“理”,不论此“理”是在自由对话和辨说中展开、生成出来之理,还是作为个人信念意义上的某种先在之理,在辨说和对话的情境中,其之所以能够“合理”、“服人”,当下即意味着此“理”可以经得起辨说,而真正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此一辨说过程中,荀子是如何展开其辨说规范或辨说原则的?又在哪些方面能够体现辨说的程序理性?以下我们即简略地勾勒荀子在辨说过程中所表现的合理性寻求。
首先,是“接引术”之提出。
基于客观现实的特殊状况,荀子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辨说的技巧或基本的方法,可谓之“接引术”,但显然,此一技巧或方法乃从一般的辨说得以顺利进行的要求着眼,或为在辨说过程中成功地实现理解之目的的必要方式,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性因素。荀子云: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非相》)
意思是说,辨说或劝说之难在于以先王至高至治之道,说末世志意至卑至乱之君。然而,在是非离乱、不知所可的情况下,要顺利进行这种辨说,又不可径自直言,必须援引古今以为佐证。但远举上世之事,又怕他误会为谬妄,下举近世之事,又怕他误认为庸鄙。故而,辨说的技巧在于折衷两者之间,必定举上世而不致被误认为谬妄,举近世而不致被误认为庸鄙。因时、因地制宜,或徐缓,或急遽,或多言,或少说,委屈俯就,如同河堤制水、檃栝正木一般,如是,既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又不因辨说而刺伤对方的自尊心。*参见李涤生《荀子集释》第86~87页。本文有关荀子文本之解释多使用李先生该书,故不再出注。荀子此段话为我们描述了在乱世中一种有效辨说如何进行的方法,亦即迂回曲折地接引他人,不可操之过切。但这似乎是对各国君主而言,其间辨说的意味有,但劝说的意味重。不过,重要的是,荀子由此得出一辨说的原则,其云:
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非相》)
“抴”是指划船的桨,所谓“度己以绳,接人用抴”,依郝懿行,谓“君子裁度己身就用准绳,接引人伦就用舟楫。谓律己严而容物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辨说的过程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则可为天下人模范,宽以待人则可以容纳天下各种不同的意见。说到底,所谓“接引术”之所以能够接引人,即必当有律己以严、待人以宽的胸襟,此既可以是一种辨说之技巧,更表现为一种辨说的原则。荀子又云: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非相》)
从“矜庄”、“端诚”、“坚强”等字眼上看,此段话犹在说辨说之态度。但技巧必表现于态度上亦理之易明者。依荀子,辨说之作为辨说,要郑重其事,存心端诚,意志坚强,此三者或可在不同的程度和侧面上表达了辨说过程中对智、仁、勇三种不同品格的要求;“欣驩芬芗”,依王念孙,“皆谓和气以将之也。”意思是说,辨说要设譬称把事理讲明了,要分析区别把异同辨清楚,而以愉快的心情、和乐的口吻向他人言之,同时,自己要宝爱、珍视、贵重、神奇其说。果如是,即其说便自然会常常为他人所接受,虽不取悦于人,但人莫不贵重其说,这就叫做能使人贵重他所贵重的。不必怀疑,荀子在这里的确是试图让人明白一种辨说的技巧,以最后达到使人“能贵其所贵”。透过这种辨说技巧,荀子亦同时给人们展示了一些合理性因素:实现让人贵其所贵,即便此“贵”乃是个人持有的信念,其方法亦不是通过“势”或“刑”,不是通过强辨或诡辩,而是通过尊重他人、宽容各种不同的意见、深入浅出地讲理以及态度的庄重、存心的诚恳、坚强的意志,将道理以和乐的形式表达出来。
其次,是建立“理想型”(ideal type)的辨说模式。
但凡阅读过荀子之著作的人,皆不免有一深刻的印象,此即荀子善于通过对人格等第之比对的方式以凸显其心目中的理想或价值,士、君子、圣人乃是荀子理想人格之三层,而及荀子之论士,又谓“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不苟》);论儒又有大儒、雅儒、小儒、俗儒、陋儒、腐儒、散儒、贱儒等分别(见《儒效》)。顺此思维,荀子之论辨说,亦复有圣人之辩、君子之辩和小人(奸人)之辩之别。此处最让人感到踌躇的是,就辨说而言,荀子分别圣人、君子和小人之辩,会让人感觉此辨说因其有先在的价值谓词之限定而有碍公正的辨说理性之提出,此的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荀子言辨说乃是在说理而尊重他人、容纳不同意见,且在心存诚恳的前提下展开的话,那么,此处分别圣人、君子、小人之辩亦确有其就辨说理性展开之结果所作出的一种评价的意思,亦即我们不必一定在先在的价值认定上去理解,而可以就辨说之结果的事实上去理解。就此意义而言,荀子之所以要通过凸显两种不同的辨说特点,目的乃在于藉圣人、君子之辩所表现出来的正当的辨说理性,以映照出小人之辩之不足取(谓不符合辨说理性也),并进一步彰显其扭曲的(distorted)辨说方式。荀子云:
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非相》)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非十二子》)
此处“圣人之辩”可兼合“多言而类”一条共看,所谓“不先虑,不早谋”云云,乃荀子心目中所向往的一种辨说“境界”,此境界当然不就实际中所发生的辨说而言,所以,真正有对比意义的是“君子之辩”与“小人之辩”。依荀子,君子之辩要预先思考筹划,须臾之间发言也足于细听,盖其言有文理而信实,且渊博而正直。今就合乎辨说之理性而言,预先的思考筹划,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无疑是使辨说得以进行并推向深入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与那种为辩而辩、为名为利而辩的所谓辨说划清了界限。[11](P113~114)与此相对比,小人之辩说则言辞辩捷而无原则,言谈则唇吻调适,或辩或唯则亦中节,这都足于表现其夸大傲慢的性格。就此而言,小人之辩乃纯粹为辩而辩,为期以力胜对方,不失腾挪舌根,驾雾腾云,言而无准则、无统绪,故此辩所表现者实乃伪诈而手段巧妙,辞慧而乖逆常理。荀子甚至不惜以“奸说”来名此小人之辩。荀子又云: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正名》)
此意是说,君子之辨说辞浅而意精,礼貌待人而有条理,论事理之是非似若不齐,而终归于齐一,其辨说,用名正确,措辞恰当,务以表明心中之志义,所谓“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劝学》)。与此相反,愚者之辨说,*此处荀子所谓“愚者之言”实其意亦即是小人之辨说。看似微妙而实则粗略,看似深刻而实则无类,誻誻多言而实则纷乱且无头绪,其辨说,用名则欺诳不正,用辞则迷乱不实,殊无深刻之志义可言。
我们不必去深究何以小人之辨说会表现出这些特点的历史根源,只需知道天下乃为一战争棋盘这一事实,似乎就足于解释这些现象了。诚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并非就是合理的。对于合理的辨说而言,荀子对小人之辨说所表现出来的“无理”(谓其名辞欺诳迷乱)、“无力”(谓其期人为胜而争辩)、“无体”(谓其为辩而辩而无原则)必当有所正之,并以正面斩截而出,此即“正其名而当其辞”、“是谓是,非谓非”、“博而党正”。陈大齐先生又从消极方面提出荀子辨说时之“三戒”,谓不争、不期胜、不苟察。[7](P90~94)荀子云:
君子……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苟》)
辩而不说者,争也。(《荣辱》)
有争气者,勿与辩也。(《劝学》)
依荀子,君子言辞辩捷而不争胜,事理明察而言不激切。何以不争?盖争则动乎气血、出乎情绪,而有害于辩说理性之清明,故“有争气者,勿与辩也”。
辩而不争则提示了不期胜,盖争者动乎意气和情绪,其结果即是“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性恶》),强词夺理、愈辩愈晦,自是情理中事。为此,荀子提出了“说不贵苟察”的主张。“苟”者,不存德义,谓之苟且。辨说虽然明察,然若无当,即是苟察。何谓“当”?其根义和实义自是礼义之中,故云“人无师无法……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儒效》)。但此“当”亦包含了超越个人主张或信念的含义,此即如前面所说的在辨说过程中所表现的名言辞说、态度存心等等的合理性,故不可全归之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唯一可以说的是,在荀子那里,前一种意义的“当”已然包含了后一种意义的“当”。但当我们注目于荀子辨说理性之了解时,强调指出后一种意义之“当”似乎不是一种架屋叠床之举。
最后,是为展开辨说,设立“程序理性”(procedural reason)。
我们曾言,辨说就其作为辨说而言,是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尝试去了解对方,说服对方。但辨说是否是出于一种公正的讨论,是否合乎理性,抑或是在一种强辞诡辩、暴力胁迫和其他不平等、不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理性”之设立。就荀子所主张的辨说而言,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他有强烈的个人信念,但当我们暂且将此搁置之后,仍然可以隐约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类似“程序性的”理性,注意到这一点,或许可以使我们在荀子的辨说言必称先王的表象下面,发现其对合理性的寻求。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作一简略的辨析。
(一)在辨说的过程中,辨说的参与者应该是人人公平的,辨说应是公正的。就荀子之整个思想系统而言,他对公平的意识有着强烈的关怀。荀子不仅认为“公平者,职之衡也”(《王制》),而且尽力提倡“公正无私”(《赋篇》)。有学者甚至认为,“荀子相当清楚公平是社会公道相当重要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在公道的社会体制中都应该是‘直立而不胜’(《不苟》)。这意味着人,作为社会存在,都是有尊严的,不应相互压制。”[12](P289)无疑,上述说法从根本上隶属于荀子思想的另一领域,与本文讨论辨说中的公平和公正尚有差距。但荀子也的确主张在辨说中要“贵公正而贱鄙争”(《正名》),盖人存心公正则明,而存心偏私则暗,就这个意义上说,荀子所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强国》),实未尝不可以与其所主张的理性辨说相融一。荀子又云: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
杨倞注:“以仁心说,谓务为开导,不骋辞辩也。以学心听,谓悚敬而听他人之说,不争辩也。以公心辩,谓以至公辨他人之说是非也。” 在荀子看来,辩说当然要讲求辞让得当,顺应少长进退之礼,忌讳怪异不逊之辞,即所谓“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劝学》)。但辩说非为争胜,而在说理,还在能虚心倾听对方的意见,做到无党无偏无成见,而唯理是从,如是则我们可期望从辩说中获得真理成长的可能性。要言之,荀子之言辨说,其方式、方法乃明显地表现出诉诸某种公平、公正之合理性的辨说途径,以使先王之道成为人们所共守的价值原则。此公而无私、平等开放,乃显出荀子辨说灵魂之高洁,此辨说之“仁”也。
(二)辨说之所以能够获得理性的基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辨说的参与者在辨说的过程中所求得的“同意”或“共识”乃是一种非强制性或非强迫性的。人们之所以同意某一标准,是出于支持此一标准的理由比支持其他标准的理由更充分,因此,辨说应言必当理,不应受、亦不应为任何外在权力或利益的诱惑和胁迫。提出这一点,在荀子所处时代或尤具特殊意义,盖当时纵横术士,或为名,或为利,或诱于权势,舌底滔滔,搅动世界,他们的辨说似纯粹为外在利益所牵引。对此,荀子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以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荣辱》),这一品格应用于辨说,即是“勇”。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性恶》)荀子此言毋宁说是一种循理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自然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信念、道德勇气,同时更表现出一种理论勇气。理之所在,毁誉得失,全无挂于心,故荀子又云:
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正名》)
此即在荀子看来,辨说除了要尊重他人,公平公正之外,辩者还应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不为众人的诽谤和夸奖所动摇;不掩饰观者的耳目,以取悦他人;不用财物去买通富贵者的权势;也不利用便辟近习的美言,以博取他们的喜欢称誉。这样,便能守辩道而不二心,虽困诎而志不夺,虽通利而不流荡,尊崇公正而鄙视无原则的争吵。不必讳言,荀子所说的上述四个要求的确构成了理性辨说之所以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此所谓辨说所需要之“勇”也。
(三)然而,在“勇”的另一面,还需要辨说之“智”,此“智”之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有述说,亦即荀子所谓辨说之原则也,今不烦再次强调几个方面。荀子云:
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正名》)
此所谓“动静”者,依杨倞,谓是非之理也。意即在辨说的过程中,辩者所用的名言必须始终一致,不应前后矛盾。辨说乃是为了达成共识或理解,若概念不清,曲为异议,结果即是非不明。在此基础上,荀子又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
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类推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正名》)
依杨倞,“正名而期”,谓正其名以会物,使人不惑也;“质请而喻”,依王念孙,“质,本也。”“请,读为情。情,实也。言本其实而晓喻之也。”意即辨说时所用之名既正确,同时也为人们所通晓,所举之实亦为人们所公喻;在辩论的过程中,所同所异之把握不超越主题范围,依类推度而不悖其类之共理;而在态度方面,听人辨说要恭谨而合乎礼文,自己辨说则要将理由尽量说得详尽。
由上可见,荀子言辨说乃根之于仁,基之于智,进之于勇。一般而言,期命辨说能奠基于仁智勇而求其合理性之获得,实属难能可贵。
(四)就辨说所应体现的“程序理性”而言,还有一点颇为重要,此即辨说者参与辨说当持有开放的心态,态度谦恭,心胸开阔,认真而诚恳地聆听他人的意见,无固执己见之傲,有从善如流之行,所谓“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不苟》)。荀子当然清楚,“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富国》)故而在辨说中,荀子主张以善言动容人、接引人,其云: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荣辱》)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非相》)
就人之常情来看,在辨说中以善言赠人,其对人心的温暖胜于布帛,而以恶言伤人,其对人心的伤害胜于矛戟。这的确可以理解为荀子对辨说中所表现的人性现象的观察,这种观察与荀子接引人的目的自然有关。但另一方面,如果辨说中直以为理之在我,出言不顾形色冒犯,甚至视他人如无物,即既不能平怀示人以理,辨说亦不能真正地进行,此正所谓“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也。(《劝学》)
态度上谦恭、尊人是一方面,观念意识上的兼容和开放又是另一方面。在辨说中,兼容而能博,兼听而能明,兼覆而能厚,此三者实乃辨说中说理之所以能臻其诚、继其高、宏其大之究竟原委也,而在儒学史上抑或惟有荀子能条陈出之,彰以示人。荀子云:
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非相》)
“罢”通“疲”,谓疲弱不任事之人。“兼术”即兼容并包之道,意即君子贤能而能包容无能,明智而能包容愚拙,识博而能包容浅陋,精粹而能包容驳杂,此兼术显示出荀子辨说中包容和开放的胸襟。荀子又云:
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正名》)
杨倞注云:“是时百家曲说,皆竞自矜伐,故述圣人辨说。”此辨说有“兼听”、“兼覆”之德。“兼听”,依李涤生,谓“百家曲说,无不在明鉴之中”;“兼覆”,谓“百家之人,无不在爱护教诲之下”。然而,辨说虽有此“兼听”、“兼覆”之德,却没有“矜奋之容”、“伐德之色”。辨说如被采纳,天下就正理平治;辨说不被采纳,就彰明其道,幽隐其身。[13](P523)荀子的“兼听之明”、“兼覆之厚”固然意味着作为个人信念的先王之道能够经得起辨说,但此一“兼”字同时也提示我们,荀子所主张的“理”和“道”不是完全封闭的、容不得批评和改正的,辨说固然要是谓是,非谓非,唯理是从,但持守此理之胸襟却是开放的,而非故步自封、固执己见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可以容纳别人的意见和批评的。
五、结语
就思想之总体而言,有学者认为荀子不竞求价值根源,倚重于礼法,不免有导致专制之倾向,此一看法相信不无其根据。然荀子即辨说而言“兼听”、“兼覆”之德,去“矜奋”、“伐德”之用,主“礼恭”、“辞顺”、“色从”之态度,倡“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非相》)之“兼术”,被“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非相》)之宗旨,更呈“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辨”之德慧,则其开放性之胸襟、合理性之预设,或可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反省和重视,荀子虽坚执“先王之道”之信念,然而,在其辨说理性的慧照之下,此先王之道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开放性和合理性之特征。
当然,由于受价值优先立场之主导,荀子之辨说在逻辑思维原则、明道证道之间所表现的理论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等问题上或仍存在一些可争可议的地方,此亦不可否认者。从道德理论的角度而言,在荀子那里,藉由辨说所寻求的(先王之道)合理性,似乎只限于规范的正当性问题,而并不是道德规范的最后奠基问题。准此,荀子虽尽力通过揭示理性的辨说原则以期望合理性之获得,但在此一思路中,有关礼义法度和先王之道的正当性的最后奠基问题,显然不是他所着重关心的问题,其关切之重心毋宁说乃在于实践的方法及其有效性方面。
[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M].台北:三民书局,1984.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香港:东方人文学会,1974.
[4]牟宗三.历史哲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5]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陈大齐.荀子学说[M].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6.
[8]牟宗三.名家与荀子[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9]庄锦章.Early Confucian Ethics:Concepts and Arguments [M].Chicago:Open Court,2007.
[10]林宏星,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J].河南社会科学,2011,(1).
[11]陈文洁.荀子的辨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2]蒋年丰.荀子与霍布斯的公道世界三形成[A].文本与实践——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
[13]李涤生.荀子集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责任编辑/陆继萍
B222.6
A
1671-7511(2012)01-0033-11
2011-03-20
东方朔,本名林宏星,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