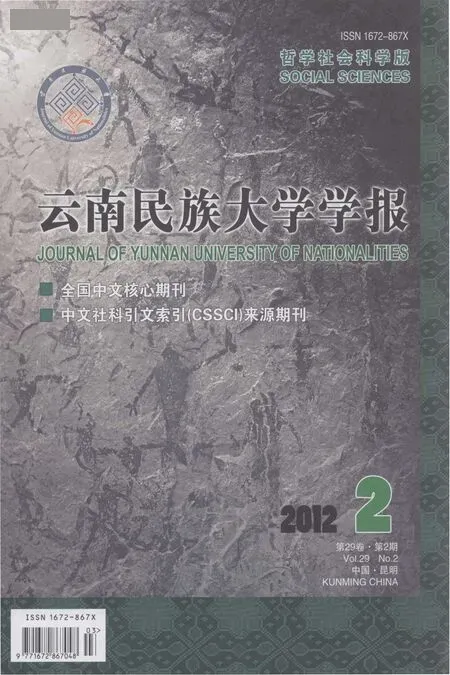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2012-12-08赵旭峰
赵旭峰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在中国传统历史记载中,边疆始终是中原王朝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稳固。[1](P69-73)从元代开始,为加强在云南的统治,帝国政权就尝试在云南与内地之间提供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构建共同的认同基础。但元朝的统治不足百年且为蒙古族所建立,虽有儒学之推行教化之实施,终究因各种政治势力划地而治而没有能改变云南的文化结构,浓郁地方色彩的习俗和文化依然占主体地位。继起的明王朝在边地云南广建孔庙、兴办儒学、施行教化。明王朝教化政策旨在有效防止汉人移民的“蛮化”并兼有培养忠诚土司的目的,进而确保包括汉人与非汉人在内的云南成为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明政府“以夷治夷”策略,也使中央的教化搁浅在汉人和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之间,不能渗透到边疆各族下层民众之中。清朝作为满族所建立的一个王朝,是历史以来中央集权统治对边疆云南民族地区经营最为深入的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清统治者,是为何变传统的“以夷治夷”思想为“以汉化夷”?清朝统治者又做了何种应对最终收到了稳定和巩固对云南统治的效果?本文拟从云南与内地同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分析清代前中期云南各民族是如何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建高度的国家认同。这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的巩固与发展仍然有重要价值。
一
在统一战争中,为争取西南各民族和土司的支持,并孤立和消灭当地的抗清势力,清统治者原则上沿袭“以蛮夷治蛮夷”的土司制度,实行招抚和羁縻政策;而当时的西南地区地方土司们为保存自己的利益也愿臣服于清政府,这似乎就给人以一种清朝统治在此稳固存在的印象。但是,事实情况远要复杂曲折得多,清朝在西南边陲的统治并不深入。大大小小统领较大武装力量的土司存在,成为清朝在当地统治的潜在威胁,吴三桂甚至以此为基地一度发动了威胁清朝对全国的统治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控制这块多种政治力量角逐而尚未稳定的多民族地区,成为清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清朝虽为满族建立,但其主流文化依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入关之初,清兵采取了极端的杀戮政策妄图以武力征服汉等民族,但是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并危及自己的统治。对于这个仅占全国人口少数的民族政权,采取何种措施巩固其统治,是清初统治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事关全局的问题上,清统治者借鉴明王朝广兴文教的治国策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清康熙帝就认识到:“致治以服人心为本”[2](P105),而服人心的重要方法就是力行教化,而且也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方法。于是,在全国提倡“尊圣人之道,重人伦之责,广王者之化,育天下之才”[3]的文教政策。随着统一大业向西南边疆地区的推进,清朝继承了明朝重视云南地区治理和稳定的传统,仿明黔国公沐英故事以吴三桂镇守云南,并在民族地区推行教化政策以培养忠诚土司。
云南边疆之地被纳入中央王朝后,清廷直接控制的地区主要是州县系统的府、厅、县以汉人人口为主的地区,而当地部族之民居住的地区则授命原来的部族“土酋”即土司来治理,即所谓的“以夷治夷”。土司作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他们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相当的政治自治特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向中央领取俸禄,主要向辖区内的土民索取,并且对其管治下土民拥有基本没有限制的权威,这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央对复杂边疆领土和人民的控制。但土司是其辖区内最高的统治者,常常与其治下的夷民结合起来,互为掩护,使中央的政令难以推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中央对土司的授职、承袭、进贡、赋税、差役、供调、奖惩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从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程度看,土司制度实施后,中央王朝不断扩大自己在土司承袭这一最关键问题上的权力,在土司世袭制度实行的过程中,为使应袭之人成为封建政府的保疆守土的忠实臣子,封建王朝抓紧对土司子弟的教育,出台了应袭子弟必须入学习儒家礼制的规定。早在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政府就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4](卷310,《湖广土司传》)。自此,西南各土司均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学习。1658年,清军在追剿南明残余势力途径贵州挺进云南时,顺治下了一道诏令:“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5](卷396,《礼部·学校》),敕谕西南各省督抚敦促土司接受官学的正规儒学教育。
距顺治下诏不到一年,在贵州巡抚赵廷臣的建议下,清廷又出台了土司应袭子弟必须入学习儒家礼制的规定:“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6](卷126,P978)清廷希望地方省级官员更加积极建立官学并为土司提供教育,并认为这些土著精英通过学校教育接受更多的汉文化,今后将能够开始承担起在边疆地区传播汉文化开化夷民的职责。通过这一途径,使儒家的教化如涓涓细流渗透到非汉民族的基层中,最终完成对土著社会的教化,消除阻隔中国内地与边疆土著社会的文化樊篱。
二
对云南地区实施文化上的一体化,在康熙年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真正付诸实践则是从1722年具有雄才伟略的雍正皇帝即位才开始的。
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秩序重新恢复正常,政府开始认真地恢复因受战乱而毁弃的学校并引进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义学。明代对边疆各民族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汉民和土司上层,对普通少数民族子弟的教化则寄希望于土司。但土司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继续自己的统治,往往实行“土民皆不受学”的愚民政策,使中央的教化搁浅在局部和上层集团,不能渗透到边疆各族下层民众之中,[7](P153)妨碍了中央王朝教化的深入以及中央权威的建立。清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明代教育体制的局限,部分有影响的清朝官员甚至康熙本人都大力支持在西南地区推广国家官学教育,以确保包括汉人在内的西南各民族人民通过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最终成为帝国直接管治的臣民,土司地方成为帝国控制下的府、州。1686年,康熙准允礼部奏请谕令各土司官:“有愿送子弟就近府州县读书者,命该教官收纳训诲”[8](卷125)。西南各地官员将礼部命令通告给各地土司,要求各地土司开列其土司治理境内预期入学学生名单。这样,清廷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仅仅5年,就将只允许土司家族的男性子弟入学规定改变为面向土司辖地内所有男童提供汉文化教育。为推进对土民子弟的教育,在西南地区的学校建设运动随之而起。[9](P197)“义学”原是清廷为培养满族子弟创建的免费学校,这时也被统治者推广到西南地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令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康熙五十二年(1712年)又“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要求把义学推广到帝国统治更边远的云南地区。[5](卷396,《礼部·学校》)康熙后期,云南设立的地方学校明显增多,据《云南通志》记载,1704年至1722年,云南新设立的地方学校达91所。[10](卷7)
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是中央政府对土司治理地方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清政府废除了土司的世袭制,改土司区为州、县,中央王朝直接委派州县官员,加强军事管制,设兵防、建铺递、分乡里、编保甲、查户口,在原土司统治地区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政权机构,将其纳入到帝国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而土民自身身份的转变和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并不因改土归流而立即形成,开办义学教育,推行“以汉化夷”,将基础教育进一步辐射到少数民族聚居腹地,既是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工作的一种积极姿态,也是政治工作的需要。在原土司治理下,土民从来不愿意来读汉书,一方面是不习惯与不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土司之阻隔和禁止。土司为求其世袭职位之巩固,采用愚民政策,不愿意土民有知识,土民不得土司之许可,则不敢贸然入学。为建立和保持改流后土著基层对中央的身份认同,对云南非汉民族进行教化是必不可少的。而如何既能保留各民族原有的习俗和文化(改土归流后,清廷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并不强求剃发易服,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又能在各民族平民习俗不同与文化差异基础上建构一种为当地民众所认同的同质文化,无疑是帝国统治者首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种策略在稳定当地土民的身份识别方面的作用更胜于采取激烈而且血腥的“改土归流”,是对土民更为重要和深远的管治措施。事实上,鄂尔泰在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也在云南发起了集中建立学校的运动,就有安边抚夷之目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到云南任职的陈宏谋,基于化解因“改土归流”而造成的民族隔阂之目的出发,在云南广泛地建立学校推行教化。在陈宏谋的《查设义学檄》篇章里,他直接指出在云南创办义学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文中说:“滇南越在遐荒,夷多汉少,土田哓脊,居民穷苦,多有俊秀子弟,苦于无力延师;又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急当诱掖奖励,俾其向学亲师,熏陶渐染,以化其鄙野强悍之习。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陈宏谋在上任之后四处查访,很快发现土民虽摆脱土司控制,但教化未开,仍“不谙官语,不识条告,一任夷目指使播弄”。为此,他提出了“夫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10](卷29,《艺文七·查设义学檄》)的教育理念。为发展云南的民族教育,使更多的乡村贫贱之人也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陈宏谋以一省布政使的身份督令全省各府州县有令必行,采取措施支持地方办学。陈宏谋举办的义学,不仅强调对边疆民族孩童的启蒙教育和道德改造,而且也注重选拔有培养前途的贫困学生能走出穷乡僻壤,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深造。
陈宏谋在云南前后不过6年,但在他的努力下云南实际建立的学校总数达到近700所,除绝对的总数外,地域分布也更为广泛,真正达到他所期望的“今欲使成人、小子、汉人、夷人,不以家贫而废学,不以地僻而无师”的情形。据史料记载:云南改流后仅雍正朝就开设义学463处,改流区开设148处。其中滇东北昭通府在改土归流后设立22馆义学;滇南的普洱府,历代均未曾设立过任何学校,雍正十年至十三年间共设府、县义学12馆,[7](P154)新近改流地区成为义学的快速增长区。清政府在这些新改流区广设学校和义学,教学内容注重对边疆民族孩童的启蒙教育,陈宏谋为“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 《大学衍义》”[11](卷307,《陈宏谋传》),作为义学的教材,通过教化促进了汉文化的一些先进思想理念、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在云南民族地区的传播,使边疆民众从小就能感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增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汉文化不仅是作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而出现,也是改土归流能彻底完成的润滑剂。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云南民族改变的是自己的文化认同,即认同中原王朝代表的汉文化,而非一定就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很多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民族的习俗与文化。
三
“人是文化的载体。某种文化现象与拥有这种文化现象的人或集团紧密联系。某种文化下的人活着群体迁移到新的地方时,会将该文化传播到该地。”[12](P28)在文化传播中,移民是最活跃的载体。汉族移民由于长期生活着中原王朝的统治下,深受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熏陶和影响,自身就是汉文化的载体。因此,汉族移民的迁徙、流动,实际上也就成为汉文化的迁徙、流动。
秦汉至元时期,虽有少量汉族移民云南,但夷多汉少,对云南的民族分布、人口构成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明朝建立后,大批汉人以镇戍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身份进入云南,居住在城镇、平坝和军事要隘等居民点,分布呈现出零星插花式的特点,与当地民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往开始密切起来。但土司制度的存在,云南少数民族居住的核心地区由于治理方式、文化生活习俗与汉族差异很大,汉族很少有人敢冒险进入土司辖区。这种情况在18世纪的清代发生了改变。一方面,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原土司辖区与内地之间的民族壁垒被打破,汉人可以往来于少数民族居住的核心区;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长给中国内地本来已经存在的人地矛盾造成巨大的压力并产生大量的流民,为解决流民的生计问题,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汉人以持续不断增长的态势向荒地甚多的云南移民。
清代立国之后,虽然经历了“三藩之乱”,但人口增长很快。康熙十八年(1679年),人口就增长到1.6亿;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增加3.115亿。[13](P832)但人口增长多集中于内地省份,人地比例逐渐失调。为了缓解内地人地矛盾维护统治的稳定,清政府力促向人口密度和开发程度均低的边地移民。如雍正元年四月(公元1723年),政府就规定:“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相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青吏亦不得阻扰。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6](卷6)云南地旷人稀,土地开发不足,直至17世纪康熙年间,云南还是一个半开发地区,大片可耕地尚未开垦。这对于寻求谋生机会的内地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流民涌入云南各地开荒。由于云南多山地少平坝,腹地平坝可开垦之地很快被开垦完,之后迁徙来的内地移民大多数只好到条件较艰苦、以前汉人很少涉足的山地与边疆,与当地民族交错杂居、并邑同耕。有关记载如:雍正六年(1728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云南镇沅府开垦夷田四百三十顷有奇。”[6](卷72)雍正七年(1729年),许多流民和移民涌入“地广人稀,非民力所能遍垦”的滇东乌蒙一带。[14](卷138)云南东南部的广南府在改土归流之后,“山地不自殖,租与川、楚、黔、粤贫民垦种,故近年民物繁滋。”[15](《广南府舆地图说》P19)普洱府设于雍正七年,史载,“国初改土设流,由临元分拨新嶍营兵驻守,并江右、黔、楚、川、陕各省贸易之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地渐开。”[16](《风俗》)就连改土归流没有触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有大量移民进入。如乾隆年间,清政府用兵缅甸,汉人由是开始大量进入今德宏州的梁河傣族地区。据《南甸司谱》载:“清乾隆征缅,道光禁烟以及洪杨杜发难,入居者愈众,山区全部为汉族所据有,坝区亦不少杂居。”再加上外省流寓云南各矿山的谋食穷民,汉族移民总数不下数10万。曹树基依据《嘉庆一统志》与光绪《续云南通志稿·食货志》测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国人口已由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31150万增加到38310万,增长率为23.0%;而同期云南人口则由788.4万增加到1029.9万,增长率为30.6%。[13](P244)期间,云南人口的增长率远超全国,与外省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有直接的关系。学者苍铭对这一时期的云南移民史有所研究,也认为:“滇东南、滇南、滇西南澜沧江以东地区,滇西怒江以东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地区”[17](P45)。移民散处分布在土著民族原聚居核心地区,普遍与当地民族村落杂居在一起,使原先一个个相对封闭的民族地域,成为各民族共居的开放流动型交融区,云南各民族聚居格局渐渐形成。
在相互交往之中,掌握先进技术和工具的汉族移民从物质文化方面和精神文化方面都深深影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檀萃《滇海虞衡志》载:“自前明开屯设卫以来,江湖之民云集,而耕作于滇,即夷人亦渐习于牛耕,故牛为重。”[18](卷7)思南府“处平隰者,则驾车引水以艺粳秫”,“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思州府辖地的“土人架木槽引以灌田”。说明汉民族先进的牛耕、灌溉和经济作物种植技术传入了彝族地区,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各民族在这种边疆的治理和经济开发之中形成了一个利益攸关、彼此依赖、共同发展的多民族共生格局。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也使与汉文化相适应的表现仪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流布于云南各地并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可。汉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节日由移民带到民族地区成为许多民族的共同风俗和节日;忠君、爱国、崇官、孝悌等儒家伦理观念深入各民族村寨,使云南各民族对汉文化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大大增强。与此同时,汉文化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诸如语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的若干元素被带进汉语里,从而对云南方言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19]这样,一个囊括众多民族、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逐渐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和响应。[20]
四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科举制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创造了条件。肇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对各民族人们自觉学习汉文化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独特的文化整合作用,加速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的进程。满族人入关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保持了儒家科举传统,通过科举取士吸收儒家优秀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进而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以文化的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
清代云南的教育同科举结合得更为紧密,一种非科举不得为官的制度不仅在汉人居住区确立,更是深入到刚刚改流的非汉人地区。改流之前,“土官以世系承袭,不由选举,其祖父势利相传,其子弟恣睢相尚,不知诗书礼仪为何物,罔上虐下”[21](《第二疏·制土人》P426-427)。改流之后,原土司地区和内地一样实行普遍的纳税制度,姓氏制度的建立才成为必要,因为政府要建立户籍以便于税收,土民与官府发生了直接联系并开始被登载于王朝的版籍。这样,原来的土民成为中央王朝治理下的“正式臣民”,有知识通汉语的土民还意识到通过科举考试能晋升更高的社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清政府在这里普遍开设了学校,民智稍开,人知向义。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被派往云南查监狱的杨怿曾在他的《使滇纪程》一文中写道:“滇省倮倮之属,多有在衙门充当书使者,其明敏胜于汉人”[22](P299-302),有的人更成为了汉文化的饱学之士。
科举制度的推广为包括原土司地区在内的夷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从政入仕的机会。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多少数民族以前是没有姓氏的,通常只称呼名字,参加科举极易造成混乱,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已属必然。但少数民族深受歧视,很难中举为官,为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能谋得一官半职和光宗耀祖,攀附汉姓、假报民族身份成为最佳选择。夷民所采用的姓氏大多数是从汉字借用过来的,比如赐姓、谐音借用等。当少数民族用姓氏的方法追认祖宗时,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本来与汉族不同宗的少数民族变成了祖宗大多数都是汉族人的情境。成书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滇系·典故系六》说:“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23](《典故系六·沐英传》P32)今天,在云南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至少有100个宗姓的人认为自己是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而来。在云南蒙自历史上有影响的清代翰林禄(陆)应谷,本是彝族,但陆家的家谱、碑刻也记为南京籍;蒙自彝族第一进士、十里铺李学周也是改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中进士的。众所皆知的普姓彝族,在百家姓中都没有,可以说是彝族独有的姓氏之一,但在蒙自地区普姓汉族、壮族也为数不少,其原因可能是自然的融合,也有可能是改报、假报隐瞒身份。当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及其土民子弟通过科举成为有“出身”的仕人,当这些具有一定汉文化知识而更能令夷民敬服的民族精英登上滇云政治舞台,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这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身份与命运,更是带动所属民族人民对正统儒家道德规范的认同,“汉裔情结”也在对国家主流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成长和流露出来,云南的各民族也从“西南夷”发展为“云南人”。
从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来看,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不可能改变基于地域和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云南各民族文化多样性。清帝国在云南的科举考试促进了汉字普及和少数民族的儒学化,使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但云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儒学这样一个同质性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民族在一个樊篱尽失的文化场合中交流融合、共同发展,成为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关键。
综上,清朝在继承前朝边疆治理政策的基础上而又有所新政,制定出一套符合云南民族地区实际的教育政策,在云南与内地之间建构起一种同质性文化,并通过这种文化将帝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声望渗透到边疆社会,使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在思想上、心理上自觉认同代表这种文化的中原政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信念深深印记在云南各民族的历史记忆里。即使到了近代,列强觊觎,中国边疆出现严重的危机,云南作为西南的门户曾多次遭到列强的渗透和侵略,但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争,保家卫国,对统一国家的认同表达相当强烈。面对列强的挑拨和阴谋,这种构建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观念没有受到丝毫的挑战与摈弃,始终稳固地保留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当然清政府在云南推行“汉化”,并不意味着要求当地少数民族放弃其民族特性。事实上,有差异的云南各民族也从未放弃过他们的风俗和习惯,自然也没有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景观中消失。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文化认同的力量,而且对于审视今天中国所面对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袁剑.清朝场域中的西南印象——读《亚洲边陲:清代云南边疆的变迁》[J].书品,2009,(5).
[2]康熙起居注(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党乐群.云南的科举 [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4).
[4][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清]昆冈、李鸿章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Z].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6]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7]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8][清]马齐,朱轼纂.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Z].北京:中华书局,1985.
[9]John E.Herman.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司制度的改革[A].于晓燕译.陆韧编.现代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 [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10][清]鄂尔泰.[雍正]云南通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8.
[1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赵荣,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4]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M].1949年铅印本.
[15][清]李熙龄.广南府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16][清]郑绍谦.普洱府志(卷九)[M].
[17]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8]檀萃.滇海虞衡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云南汉语方言志编写组.云南方言的形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3).
[20]周智生.明清汉族移民与云南少数民族和谐共生[N].光明日报,2010-4-21(10).
[21]蔡毓荣.筹滇十疏 [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8[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2][清]杨怿曾.使滇纪程[A].[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C].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3][清]师范.滇系(第14册)[M].云南通志局出版,光绪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