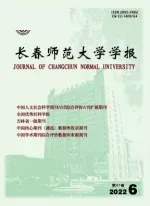社会资本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
2012-08-15辛桐
辛 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社会资本与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
辛 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由“行动因子”和“表达因子”构成。社会活动因子只影响政治参与的行动因子,社会网络和大学生校园内部交往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表达因子。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非常有必要将校园内社会资本与校园外社会资本进行区分。
大学生;政治参与;社会资本
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这一问题,学界已经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和研究,绝大多数是从思想教育方面进行理论阐述,以实证与经验研究为依据的探讨并不多见。一些实证研究细致地分析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不同层面的特点。比如,卢平运用经过修正的“政治效应感”量表发现大学生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或者说,大学生对政治的低层次的参与和投入(对政治大事表示关注)高于对政治的高层次的参与和投入(直接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
事实上,现存的高校体系类似于某种缩小了的单位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这一范围内展开,其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事务,也是依托于所属的学校、学院展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将大学校园称为小社会并不为过,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是否是党员、能否在学生干部的竞选中获胜,与其在校园内的社会资本,比如与班级辅导员的关系、与同班同学的交往状况等因素关系密切。关于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2]。目前,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既有的共识是: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社会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二是一系列相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3]。由于本研究是实证研究,本文定义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
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
美国政治学者孔奇认为,如果参与活动并不涉及全国的或地方的国家结构、权威和(或)有关公益的分配决策,比如像参加邻里计划,加入邻里协会这样的团体行为,就不是政治参与,而只能算是“社会参与”。本文对政治参与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将所有和政府部门有关的政治接触都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范围之中。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认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与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占有量有关,即社会资本对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政治参与者占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足,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活动越活跃。为了检验这个研究假设,笔者在2011年4月至5月对F大学的本科生的社会资本状况、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F大学2007级至2010级的本科生。此次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9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75%。在制定了统一登录标准基础上,由两个登录员进行数据登录。数据处理主要采用SPSS18.0统计处理软件,涉及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频率统计、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此次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下:有效样本数为399个,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0.9%,女性占49.1%,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这表明样本基本符合本次探索性研究的要求。
在本项研究中,调查问卷共列了12个方面的项目测量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有8个项目按照李克特量表方式设置成“没有”、“1次”、“2次”、“3次”、“3次以上”等5个等级,提问方式为“最近一年你是否有以下经历”。这些项目包括:为维护同学的权益(例如评优、入党积极分子)找过班主任、辅导员或者学校领导;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打交道;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表达自己对某项政策或某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在网络上(论坛、微博等)发表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在宿舍里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在会议或者学术论坛中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在课堂上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参加过听证会、市民论坛或者旁听人民代表会议与政协会议。另有4个项目是回答“是否”,这些项目包括: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参加竞选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参加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竞选投票;帮助过别人竞选班干部、学生会干部。
在8项李克特量表测量中,只有6.0%的调查对象曾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打交道。7.7%的调查对象曾经参加过听证会、市民论坛或者旁听人民代表会议与政协会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表达式的政治参与比较活跃,有38.3%的调查对象曾经在网络发表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在表达式政治参与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大学生在宿舍中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有71.2%的调查对象有这方面的经历。其中有11.8%的调查对象有1次,有8.8%的调查对象为2次,有2.5%的调查对象为3次,有48.1%的调查对象为3次以上。在课堂上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有29.8%的调查对象曾经在课堂上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其中6.3%的调查对象在过去一年曾经在课堂上3次以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在回答“是否”的4个项目中,有51.9%的调查对象曾经帮助过别人竞选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有86.7%的调查对象参加过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竞选投票,有67.2%的调查对象参加过竞选班干部、学生会干部,而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只有17.8%。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表达式参与多,行动式参与少;二是政治参与偏重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领域;三是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有校园政治的色彩,竞选班干部、学生会干部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方面。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数据结构,本研究对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的8项进行了因子分析。通过数据旋转,以及删除掉≤0.5因子载荷得分,共提取2个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为54.438%,表明提取出来的这两个因子可以解释54.438的差异。根据因子载荷得分,这两个因子可命名为“表达因子”和“行动因子”。“表达因子”下面的项目包括“在网络(论坛、微博)发表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在宿舍表达自己对政策的看法”、“在课堂上表达对政策的看法”。“行动因子”下面的项目包括“为维护同学的权益找班主任、辅导员或学校领导”、“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打交道”、“参加听证会、市民论坛或者旁听人民代表会议与政协会议”等5个项目。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在理论上解读这两个因子的理论含义。第一个维度是对现实的介入程度。在这个维度上,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在网络上、宿舍、课堂发表自己对政策的看法更多的是表达意见,其对现实的政治介入程度比较低。与之不同的是维护同学的权益,维护自己的权益,参加听证会、市民论坛,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意见则是付诸于实际行动,其对现实的政治介入程度比较高。第二个维度是与政治参与主体的利益距离。不难发现,找辅导员、校领导维权与在课堂上发表对政策的意见,这两种政治参与形式相比,前者与政治参与主体的利益距离更短,而后者则更远。同样,在利益距离上,参加听证会、市民论坛、旁听人民代表会议也比在网络上发表政策意见要短。通过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政治参与表现出表达式参与多、行动式参与少,利益距离化以及校园政治化等三个典型特征。
二、社会资本及其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社会交往、社会活动和参加社会组织这三个维度测量大学生的社会资本。首先是社会交往。本研究用“上一星期联系的人数”、“上个月的手机资讯费用”、“过去两周和朋友通话的次数”、“过去两周收发邮件的数目”以及“过去两周和非家庭成员吃饭(聚餐)、喝酒、唱K的次数”。
在调查的样本中,上一个月的手机资讯费平均值为46.86(元),过去两周和朋友通话的平均次数为13.97(次),过去两周收发电子邮件的平均数为8.93(封),过去两周和非家庭成员聚餐、喝酒、唱卡拉OK的平均次数为2.79(次)。从标准差看,手机资讯费的标准差最大,为39.123。这说明在调查样本中,手机资讯花费的内部差异比较大,手机资讯费的最大值为500(元),最小值为10(元)。通过这些基本数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新社会阶层社会交往的基本概况。
社会资本的另两个测量维度是参加社会活动和参加社会组织。本研究试图用六个项目进行测量。但因子分析并不能析出上述两个因子。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这六个变量只能提取出一个因子。这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为43.73%。本文将这个因子定义为“社会活动因子”。这个因子下面的六个项目为“参加同乡聚会”、“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学术论坛”、“参加集体活动”、“参加社团活动”以及“参加兴趣小组”等六个项目。
为了分析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本研究用性别、政治面貌和户口作为控制变量,以测量社会资本的七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性别、政治面貌和户口为虚拟变量。在多元回归中共检验了四个模型。模型A1、B1的自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和户口,因变量分别为行动因子和表达因子。模型A2、B2除了上述自变量之外,还加入了测量社会资本的七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根据四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数据,可以得到以下基本判断:首先,性别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难以确定。在四个模型之中,模型A1与模型A2显示性别对政治参与不构成显著影响。这表明性别不是行动式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而在模型B1与B2中,性别对表达因子的影响是显著的,即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讨论政治。其次,政治面貌将影响政治参与。在四个模型中,只有在一个模型(A1)中,政治面貌存在显著影响。在其他模型中,政治面貌都是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从标准系数的方向可知,与中共党员相比,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显然要低。再次,户口、春节联系人数、和朋友通话次数、参与同学活动、收发邮件均对政治参与不构成影响。观察四个模型的数据可以发现,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几个变量对政治参与构成显著影响。
观察这四个模型可知,从模型A1到模型A2,方差从1%改善为8%,解释能力的改善程度是比较客观的。这表明社会资本变量的加入的确改善了模型解释变异的能力。从模型A1可知,社会活动因子对大学生行动式的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与此相反的是,社会活动因子对表达式的政治参与不构成显著影响。这说明社会活动能力影响行动式政治参与的活跃程度,但却不会影响表达式政治参与的活跃程度。在模型B2中,可以发现,对表达因子构成显著影响的是“手机通讯费”和“和同学、朋友一起聚会的次数”。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变量解读为社会网络和大学生校园内部的交往活动,即大学生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大学生校园内部交往活动将影响大学生表达式的政治参与。但从模型解释变异的能力看,从模型B1到模型B2,只增加了2.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社会资本诸变量加入之后,解释变异的能力仅提升了2.8个百分点,这是非常有限的。因此,通过模型B来得出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的结论之前必须谨慎考虑模型的改善程度。总之,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三、结语
对比研究假设和研究发现可知,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显得过于粗糙。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社会资本在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中并非那么显著。当然,这并不能以此来否定本研究的价值。我们将社会资本引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过程中,似乎忽略了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群体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圈子比较小。而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强调的是通用的社会网络、社会活动与社会组织。我们把这样的“社会资本”引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研究之中,其实是削足适履。社会活动因子只影响政治参与的行动因子,社会网络和大学生校园内部交往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表达因子。这两个结论启示我们:在接下来的关于大学生政治参与和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中非常有必要将大学生内部校园交往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校园外的社会资本区分开来,而校园外的社会资本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概念。
[1]卢平.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效应及其评价[J].青年研究,1994(2):25-29.
[2]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的新进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3(3):55.
[3]陈捷,卢春龙.共同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J].社会学研究,2009(6).
[4]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XINTong
(School ofPhilosophy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ndongUniversity,Jinan 250000,China)
University student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composed by“action factor”and“expression factor”.Social activityfactor onlyaffects the action factor of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social network and students’communication in universitycampus affect the expression factor ofstudents’political participation.In future research,it is verynecessaryto distinguish the social capital in campus and outside campus.
universitystudents;political participation;social capital
D64
A
1008-178X(2012) 02-0007-04
2011-12-18
辛 桐(1989-),女,广东中山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