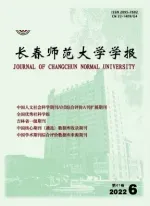对1921年《小说月报》中小说文体认识的考察
2012-08-15亓丽
亓丽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广东广州 510300)
对1921年《小说月报》中小说文体认识的考察
亓丽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广东广州 510300)
1921年《小说月报》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向旧文学宣战,它像一道巨大的分水岭将文学的“新”与“旧”截然分开。但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汇下,新文学创作者不能立刻摒弃旧有的文学观念,并因概念不清而对小说文体产生认识上的混乱。
小说;文体;创作
尽管自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十二年间大量刊登小说作品并兼而论及小说的创作和理论,以初步的现代文体分类观念建立对小说文体的认知,为现代文学的形成和确立提供创作和理论基础,但试图以“用现代的文学的原理”[1]建立新的文学形式、以创造中国新文艺为己任的新文学者仍深感不满,所以从1921年起茅盾接替王蕴章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后对其进行了一次从内容到栏目的全面革新,这次革新将“新”与“旧”两种文学形态截然分开,此次革新被无数研究者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改版后的《小说月报》旨在建设新文学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评介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从长远来看这次改革不仅是对文学内容选择上的变化和观念上的深层变革,更是对文学文体层面的全面审视和研究,对现代文学形式的确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理念和西方文学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当时的新文学创作者对各文体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甚至以现代文学原理的眼光评判来说显得有些混乱。就小说而言,尽管茅盾等人竭力以现代文学观念编辑栏目、介绍西方文艺思想,但刚改版的《小说月报》对小说文体的混用并不鲜见,在新旧文学观的双重影响下新文学作家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体出现了集体性的认识偏差,本文以1921年出版的十二期《小说月报》为例,以时人对小说文体的认知作为考察对象,从小说文体这一特定角度入手探析现代文学发生期小说成长的真实历程。
茅盾以创作和翻译相分离的思路将《小说月报》设为创作、译丛、论评、附录、丛谈等十一个栏目,把翻译和创作的小说划归在各自的栏目中。十二卷第一号的“创作”刊登了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等六篇小说作品,“创作”栏目一直延续到1921年最后一期即十二期,直至1922年1月十三卷一号栏目更改为“短篇及长篇小说”及“诗歌与剧本”后“创作”栏目取消。“创作”一词本义为创造文学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都可以视为创作,但因《小说月报》在“创作”的名下刊登的作品以小说最多,且这一说法与“旧”小说划清界限,强调了小说的“新”和创作性特点,进而被广泛应用,“创作”一时间在很多场合成为小说的代名词,“创作小说”的提法也因之衍生。郎损在“春季创作漫评”中提到“现在国内月刊、周刊、季刊以及日报上的创作小说一定不止我们所见的八十多篇”[2]。《小说月报》十二卷七号的“创作讨论”栏收录了九篇文章,除郑振铎的《平凡与纤巧》外其余八篇都以“创作”作为标题主要内容,其中叶绍钧的《创作的要素》、庐隐的《创作的我见》以及郎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文中所指的“创作”都是小说。实际上《小说月报》之外的当时其他杂志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比如署名凤兮刊登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自由谈》1921年2月27日)。这种对小说的称谓方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33年8月由申报月刊社主编的《创作小说选》、1940年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中国创作小说选》、1947年上海经纬书局的《当代创作小说选》等都以“创作小说”指代小说。汪曾祺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文学革命初期以‘创作’称短篇小说,是的,你要创作。”[3]以“创作”代指小说是现代文学的特有现象,仔细考证就可以发现以“创作”或“创作小说”代指小说并不代表当时的文学创作者不知道创作除了小说外还包含诗歌和戏剧等其他文学形式。改版之前《小说月报》在十一卷十二号通过“特别启事”对“创作”作了如下解释:“国人自作之新文学作品,不管长篇短著,择尤汇集于此栏”,这一说法表明编者所指的“创作”是国人自作的新文学作品,绝非专指小说,瞿世英的《创作与哲学》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认识:“我所谓的创作便是具有文学的特质的创造的(creality)作品,包含诗,小说,剧本和其他文学的散文。若简而言之自然就是文学的作品了。”[4]这说明无论是创作者或者编辑都对“创作”有明确认识,但由于他们对小说的内涵外延并不十分明确,或者说他们或许有理论上的清醒,但因实际运用不熟练出现不自觉的混用。
中国的现代小说概念由西方输入,《辞海》中这样解释:小说是“文学的一大类别。叙事性文学体裁之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这个概念中,主体是人物形象,两翼是情节和环境。按照现代小说的定义,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叙事性、虚构性和文学性”。这一小说概念与中国有较大区别。中国的小说概念在汉代基本确立,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小说的文体特征呈动态演化,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先后出现,从短短几句话到鸿篇巨著,其内涵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人都依据各自的观念将某些作品划入了小说的范畴,清初著名小说评论家刘廷玑很早就发现这一问题,他在《在园杂志》中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在古今之别,相去天渊。”反对一切旧传统急于建构现代性文学的创作者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小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5]“中国小说本来就是不成体统的。……所以严格说来,竟可以说中国以前没有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6]在当时这类反叛传统带着决绝姿态、言辞过激的评论并不少见。他们试图与旧小说彻底划清界限,被彻底否定的不仅是小说作品,古代小说文体也在全盘颠覆之列,“中国古籍中无小说。‘小说’之名,始自《汉书·艺文志》,然《艺文志》所谓之小说,非吾所谓之小说,非文学上所能承认为小说者也。此犹指小说之名而统言之耳。”[7]在内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小说既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传统文学形式,又是国外进口的舶来品的矛盾体。如果从现代的小说观念出发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并不难以梳理,但由于中国小说的传统理论多是只言片语地散见于各论述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念,所以尽管晚清小说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在当时多数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仍然含糊不清。
新思想的新文学倡导者以觉醒的现代小说意识以及去旧迎新的外向性文学态度,期待借助西方近现代的小说文体观念完成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的建造。然而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积淀使得文学创作者陷入尴尬境地:他们冀望从根本上把旧的文体观念全部抛弃但又难以完全摒弃,他们推崇西方文学理论,却因为文化差异及语言障碍而不能吃透。细读改版前后的《小说月报》不难发现这些双重合力的结果。《小说月报》改版前一期即十一号十二期的栏目为专件、小说新潮、弹词、剧本、笔记、杂载、补告。其中“小说新潮”栏目自十一号第一期开始设立,虽然当时王蕴章仍担任主编,茅盾已经将其革新的理念渗透到新栏目中。这一期该栏目刊登的是周瘦鹃翻译的小说《畸人》,茅盾在“小说新潮”栏目推出的同时发布了《小说新潮宣言》,表达了创造新文学、介绍新派小说的愿望。紧接着又在该年第二期发表“小说新潮”的征文广告:“不论译著,每篇以一二千字至七八千字为限,兼收新体诗歌及剧本。”茅盾将视野投向新潮,忽略了诗歌、剧本和小说之间的文体界限。这一栏目在该年度一共刊行十二期,其中登载文章以翻译小说和剧本为主。将剧本放入小说栏目意味着编辑认为小说和剧本都可视为小说或小说类的作品。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1921年,虽然茅盾希望通过改版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把《小说月报》打造成传播新文化、创造新文学的平台。正如我们深知在打破传统重新建立的道路中必然存在一些摸索和曲折的痕迹一样,1921年的《小说月报》在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上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概念混用的问题。除上文以“创作”或“创作小说”指代小说外,基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沿用传统说法,将小说称为“说部”。《小说月报》第一号的改革宣言中“译丛”栏目这样解释“译丛: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中也用到了“说部”。他说:“这几节都不是用了纯粹的说部的白话可以译得好的。同一期茅盾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中提到“文学到现在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这种表述和改革宣言的说法基本一致。这种认识的形成不无历史根源。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第一期中编辑谈到:“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古代的“说部”包含范围很广,是对小说的另一称谓,它包含的内容远比现代意义的小说复杂,小说、戏曲、笔记都包含其中。将文学分为诗歌、戏剧和小说是西方的文学分类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时期一直到现在,有一种把文学总体化为三个大类的倾向:诗歌或抒情诗类(全部使用第一人称);史诗或叙事作品类(其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同时让作品里自述);戏剧类(全部由剧中人物自述)。”[8]所以以“说部”指代西方小说或代指新文学发生期的现代小说都不合时宜。茅盾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称谓指代西方文学形式,必然出现涵盖不全或所指范围不一的问题。
第二,将小说和短篇小说作为不同的文体并称。1921年《小说月报》中刊载的文章多次出现小说和短篇小说并用的情况。按照现有的体裁方式一般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四种,小说与另外三种文体并列,小说有多种分类方法,根据体裁分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等类型,正如它可以按照题材划分为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一样,短篇小说只是小说的形态之一,是小说文类范畴下的一个子类别。这一认识在当下毋庸置疑,但1921年的《小说月报》中却不尽如此。第一号沈雁冰的《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这样来介绍这位挪威作家:“他的著作,小说,短篇小说,剧本,诗都成名,范围广些。”茅盾将短篇小说被视为单独的文类,在对他的介绍和评价中对他的小说和短篇小说进行分别评论,把短篇小说独立于小说、剧本、诗的文体之外。第六号郑振铎在《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一文中谈到“Novelett一字是比小说(Novel)短而比短篇小说(short story)长的一种小说,在中国简直是无法译他出来。”实际上,西方的小说即Novel,它的含义和我们的“小说”并不相同,中国的《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巨制在外国被称为Novel(小说),所以上面两端文字中所指的“小说”应该是“长篇小说”,如果把上文两段中的“小说”替换为“长篇小说”也就更容易理解作者表达的意图。西方人的“小说”和我们的“小说”内涵外延并不相同,但这一差别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被淡化和漠视。
第三,对“短篇小说”的不确定性。茅盾在第八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谈到“《故乡》而外,这三个月中又有几篇短的感想小说,我也很爱。”这里所指的短的感想小说是否指短篇小说呢,而在此之前他在《春季创作坛漫评》也有类似含糊的表达。“这两篇都是‘sketch’体的短篇”这两种说法表明作者认为这样的创作是短篇,但是不是能直接划归到短篇小说类别还有待探讨。十一号的“海外文坛消息”刊登了一篇题为《俄国文坛现状一斑——寓言小说》的文章,指出:“俄国人素来喜欢寓言小说,托尔斯泰的短篇寓言,薛特林的寓言小说,都是极为农夫所爱听。”寓言和小说本属于不同文体,作者把两者拼贴出新的小说形态,实际上无论“寓言小说”还是“短篇寓言”都强调其篇幅短小的特点,与短篇小说有紧密关系,作者也许认为这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但由于当时对短篇小说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把这小种说归为小说类的小说。
短篇小说自晚清进入国人视野,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上第一次开辟短篇小说专栏,号召并同其他作家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然而新文学家对他们的创作并不认同,胡适最早对短篇小说进行系统介绍,“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纂,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9]。胡适认为西方的短篇小说和中国古代及晚清的短篇小说截然不同,正如散见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笔记、杂纂、唐传奇、宋元话本中的短篇叙事性文字不能称为短篇小说一样,按照篇幅的长短来判断是否是短篇小说也不正确,必须有“横截面”的“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做成的小说才是短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初期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也由于其篇幅短小、易于刊载的特点备受新文学家的推崇。“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9]短篇小说不仅是《小说月报》也是当时其他文学刊物刊登最多的文学形式。1921年围绕短篇小说展开的讨论颇为热烈。张舍我的《短篇小说泛论》、凤兮的《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自由谈》1921年1月9日)、清华小说研究社编写的《短篇小说作法》、静观的《读<晨报小说>第一集》(《文学旬刊》第2期,1921年5月20日)以及六逸的《小说做法》(《文学旬刊》16、17期1921年10月11-21日)等文章从写作技巧、文体特点对短篇小说进行深入探讨,短篇小说的概念和界限也因之逐渐明晰,为现代文学短篇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1年的《小说月报》对小说文体并没有达成准确的统一认识,无论是编辑、创作者还是文学评论者都有自己的标准。然而正如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小说创作免不了技巧上的幼稚、拙劣一样,这一阶段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和评论必然缺乏精确和到位。这既是现代文学发生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举步维艰的真实足迹,也是文学打破旧樊笼、建立新秩序不可跨越的必经环节。从郑振铎、茅盾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文坛并非没有察觉到小说文体混用的现象,但五四打倒一切、重建一切的决心使他们依然在实践摸索中寻求真理,勇往直前。可以说没有1921的艰难跋涉就没有现代文学后来的辉煌,没有新文学创造者的勇敢无畏的摸索就没有现代文学日后的辉煌。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现代文学踟蹰前行,浴火而重生,恰如鲁迅先生的名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郑振铎.文艺丛谈[J].小说月报,1921,12(1).
[2]郎损.春季创作漫评[J].小说月报,1921,12(4).
[3]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J].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43).
[4]瞿世英.创作与哲学[J].小说月报,1921,12(7).
[5]钱玄同致陈独秀信[J].新青年,1918,3(6).
[6]静观.读晨报小说第一集[J].文学旬刊,1921(2).
[7]张舍我:短篇小说泛论[N].申报自由谈,1921-01-09.
[8]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7.
[9]胡适.论短篇小说[J].新青年,1918,4(5).
On the Novel Stylistic Awareness of“Novel Monthly”in 1921
QI Li
(Management EngineeringDepartment,GuangdongIndustryTechnical College,Guangzhou 510300,China)
The“Novel Monthly”in 1921 with newcontent and formdeclared a war to the old literature,which separated“new”literature from“old”literature like a huge watershed.However,under the collision and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the new literary creators can not immediately abandon the old literary concept entirely and have confusion for novel style because ofnot knowingthe concept clearly..
novel;stylistic;creative
book=173,ebook=173
I207
A
1008-178X(2012)07-0066-04
2012-03-14
亓丽(1977-),女,山东莱芜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