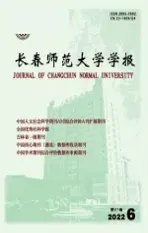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
2012-08-15于逢春
于逢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 100005)
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
于逢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 100005)
迄今为止,世界级前近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磐且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惟有中国。与世界其他几个从大河流域崛起的世界级帝国的核心力量都是在帝国中心地带兴起,一旦灭亡,支撑着帝国的核心力量便随之冰消瓦解的情景不同,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中原地带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帝国;五大文明板块;大一统;天下观;华夷共祖
一、在古代世界帝国废墟上浴火重生的现代世界大国
1970年,GDP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是10,255亿美元,排名第14位的中国是272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38倍左右;2011年,GDP仍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是15,065亿美元,排名第二的中国是6,98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2倍左右。历史回溯到清中期的乾隆时代,清帝国的GDP曾占世界的40%左右,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但19世纪30年代末以降,清朝先是惨败于英吉利人,继而大大小小的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纷至沓来,大的如沙俄,小的如葡萄牙;远的如英国,近的如日本,无一例外地都曾欺辱过近代中国,并从晚清及民国时代之中国获得数量不菲的战利品。一时强盛的清帝国最终被淘汰出世界级帝国行列。但事过170年(1840~2010年),今日中国作为清帝国绝大部分版图、人民与文化的承继者,正以现代大国之姿缓慢却坚定地重返世界舞台,中华民族复兴之期已经可望且又可及。
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级古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继承者能够凤凰涅磐,比较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时间久远的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莫卧尔帝国,近的如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等。这是因为上述世界级帝国的瓦解,或由于内部冲突而起,或因外部强敌打击所致。而这些瓦解后的帝国均没有内在动力使其重新崛起,不但在前近代没有,即使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也鲜有复兴者。这些帝国消亡后,其废墟上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强大的前近代世界帝国或现代性世界大国,相反,这些地区均先后形成了多个政治中心、多个国家的复杂局面。
与上述帝国的“兴起-隆盛-衰退”仅有一个周期,且消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复兴过相比较,前近代中华帝国的历史却有例外性。譬如,在上述诸帝国中,即使将西罗马与东罗马帝国前后叠加,作为享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也只延续了近千年,仅有一个兴衰周期。古代中国虽然没有一个享国历史如此长的阶段性帝国,却有着前后相继、嫡系文明传递的多个帝国链条,一脉相承2000多年。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帝国,嗣后,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先后崛起与消亡了许多阶段性帝国。在这诸多帝国链条中,每个世界级帝国的兴衰周期基本都是四五百年,如由汉帝国(前221年~316年)①,中经唐帝国(317年~915年)②,再到元帝国(916年~1367年~1632年)③,最后到清帝国(1368年~1911年)④,大都如此。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那么,为什么单单古代中国能够拥有若干个前后相继的世界级帝国链条,并且获得了在2000多年时间里兴衰更替而不废的天赐际遇?这种例外性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之间是否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的话,中国疆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路径是什么样式的呢?与其他世界性帝国相比较,前近代的中华帝国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
关于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与中国疆域的形成路径问题,笔者曾分别提出了“中国疆域底定于1820年说”与“构筑中国疆域的五大文明板块论”(简称“五大文明板块论”)。
所谓“1820年说”,是从法理的角度探讨中国疆域究竟在哪个关键时间、在何处正式奠定的问题。具体是指纂修于1820年⑤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及该志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并且,还附丽着俄罗斯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重修一统志》及该志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的极点。该年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古代中国国势由强转衰的最后时刻。故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
所谓的“五大文明板块”⑥,主要是探究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途径及特点,探究构筑中国疆域的空间向度问题。具体而言,就1820年中国疆域的内圈与外缘的人文地理态势,亦即生产方式来看,如从公元前3世纪初以降匈奴与前汉分别统一游牧区与农耕区算起,大体上可粗分为五种类型的“文明板块”:(1)大漠游牧文明板块。自战国秦汉长城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从大兴安岭,经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蒙古高原、天山山脉以北,至锡尔河流域以西一线,这片广袤的草原地带是游牧部族的天堂;(2)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从秦汉长城一线到南海与中南半岛北部,从巴颜喀拉山、横断山以东迄渤海、黄海、东海,这片土地加上夹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通过河西走廊与世界屋脊东麓下的黄土高原相衔接的南疆绿洲,是农夫的家园;(3)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位于大兴安岭山系、秦汉长城之辽东段、朝鲜半岛北部山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与外兴安岭山系之间的辽东地方,呈现着渔猎耕牧交汇经济形态,该板块最终于10世纪由辽朝初次统一;(4)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四周环绕着喀拉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川西高原、横断山、喜马拉雅山等高山的今西藏、青海全境与甘南、川西、滇西北,以及今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与印属拉达克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该地域呈现着高山地带适宜游牧、河谷地带有利农耕的生产方式,740年前后被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5)海上文明板块。沿着欧亚大陆的东缘,从堪察加半岛西南角下行穿过宗谷海峡,再偏西南行越过朝鲜海峡,途经台湾岛,傍加里曼丹岛,有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若干个海域圈组成的系列链条。围绕着此诸海,自秦汉,特别是隋唐以降,以中国的官府与移民、海商与海盗、帆船与交通、货物与信息、渔民与捕捞等为核心,形成了若干个由人、物、信息、交通、渔场所构成的移动的空间。该板块至少从唐代开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则开始左右中国社会进程。
这五种类型“文明板块”的划分,是根据底定于1820年中国疆域的自然地貌、人文地理态势与社会形态来推定的。这些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的文明板块,经过数千年的相互撞击与攻防,彼此融合与和解,最终被溶合为一体。各个“文明板块”在不同的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
可见,中国疆域的奠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她没有被完全“统合”前,经常存在着几个从不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起来的“文明板块”,并以此为根基建立各种各样的王朝,或单于朝、汗朝、赞普朝、王国等。它们或向着同样的目标前进,或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此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多线式的。各个板块的统合为一,是其相互撞击、彼此交流、渐次统合的最终结果,这个硕果的瓜熟蒂落仅仅是190多年前之事。故从战国后期“天下一统”观念的发轫到这种观念变成现实,竟耗时两千多年之久。
尽管如此,以往人们谈论中国疆域问题时,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其他“文明板块”被有意无意间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并且其他“文明板块”即使进入中原也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的经济等。
关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出现“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等论调。国内学者也大都未脱出中原王朝中心史观的窠臼。
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视角,以长时段、大空间为研究对象,推断中国疆域形成的基本趋势与模式。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中国疆域底定的关键时间与“五大文明板块”的空间向度;(2)中国疆域统合粘合剂;(3) 中国疆域形成的模式。
二、中国疆域底定的关键时间
关于中国疆域的范围与形成时间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始于新中国成立。当时不少学者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第一次讨论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疆域与形成时间论题。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可粗分为两类,即白寿彝提出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1],孙祚民提出的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2]。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不少学者就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谭其骧、翁独健、杨建新等在上述的白氏、孙氏观点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1) “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3]、(2)“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4]、(3)“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5]。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出,谭其骧用鸦片战争前100多年的历史时段作为中国疆域奠定的时间,使人难以搞清究竟哪个“关键时间”是中国版图最终形成的标志。除了谭其骧等之外,国内学者大都从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等中原王朝的视角,描述中国疆域形成史,并未脱出中原王朝中心史观的窠臼。虽然国内学者们大都将进入中原的周边民族政权纳入叙事体系,但对没有定鼎中原的单于朝、汗朝、赞普朝,以及各类割据王朝、王国等,或忽略不计,或视之为外国,或将其置于中原王朝的附属政权或地方政权境地。
在笔者看来,惟有解答下列几个问题,才能判定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即关键时间究竟应设定在何时。(1)清帝国是否具备或何时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与主权;(2)清帝国是否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与边境制度;(3)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存在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4)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国家边界是否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等。对照上述几个基点,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6]
另外,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不管他们对中国疆域范围或奠定时间持什么样的观点,大都没有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与构成的特点。另外,这些学者大都没有厘清构筑中国疆域的内在力量来自何方,也没有解明中国如此广袤的疆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另外,这些学者也没有论证古代中国的各地域与各民族在中国疆域奠定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问题。
三、“五大文明板块”的空间向度
1.“五大文明板块论”的构想基础
上古“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或国家,从远古走来时就呈现出多民族(族群)的特质,中国历史上兴起的四个世界级帝国(汉、唐、元、清),都是由一个统治民族(族群)为主体、包含多民族(族群)的国度。任何一个统治民族(族群)的性格形成都离不开地缘因素。上述古代中国的四个世界级帝国崛起初期,都有自己的发祥地与核心文化传承及文明圈。嗣后,伴随着这些帝国的渐次强盛,或快速或缓慢地进入中原地带或原帝国的核心地带,并以此为基地征讨四方,号令天下。
实际上,笔者在考察中国疆域形成问题过程中,之所以提出了“五大文明板块论”,就是因为笔者在考察上述的汉、唐、元、清四大帝国的形成地域、文明渊源及其开国君主的出身民族(族群)时,看到了与以往的惯常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以往的教科书等,经常在有意无意间倡导中原中心主义思想,以及汉民族先进于周边少数民族等历史观与价值观。
1949年以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陆的确立,以往的旧史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旧史观”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在各种论著里,“中原中心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原中心论”的核心内涵大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发祥地;(2)中原文明是先进的,其他地区是落后的,是作为中原文明的辐射对象与接受者而存在的。该史观大致肇始于先秦后期,迄于民国,在中国社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直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共鸣者。
从学术上对“中原中心论”进行“清算”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以抽筋剔骨式的方法,颠覆了经学家所构筑的“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时代,解构了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朝为以一贯之的正统王朝体系的神话[7]。同时,另一些史学家则主张借助于已有的考古成果,跳出经学窠臼,从源头上梳理中国历史脉络。其中,徐旭生、傅斯年、蒙文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徐旭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华夏文化。[8]傅斯年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中原地带大体上有东夷、西夏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9]。蒙文通则运用区系类型学原理,认为炎帝、黄帝、泰帝 (太昊伏羲氏)三族渊源不同,分别出于江汉、河洛、海岱。[10]承继蒙氏、傅氏、徐氏三位先贤研究之余绪,苏秉琦于1975年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他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各区系之间经过数千年的接触、交流、战争,逐渐融合,形成多源多流的战国七雄和多源一体的华夏民族[11]。
但不可否认的是,先贤们的着眼点大都没有脱离“泛中原板块”。即便如此,顾颉刚、徐旭生、傅斯年,特别是苏秉琦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却是“五大文明板块论”得以构想的思想火花触发器。那么,“块论”说又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呢?这首先起源于笔者对“泛中原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奠定过程中的实际地位的探讨;其次得益于笔者对汉、唐、元、清这四个世界级帝国的发祥地,以及开国集团核心成员出身地为什么大都在中原或旧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的理论思考。
就“泛中原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奠定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在秦汉及以前,该板块曾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其他板块起到过主导作用。同时,各大板块最终被统合于“中国”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同源”谱系架构等也发祥于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国时代以降,由于生活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局限,从“泛中原板块”上孕育出来且由汉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往往善文治而乏武功,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不是表演者本身。
实际上,在中原地带由部落而古国、由古国而方国、最终到帝国的历程中,催动帝国诞生的力量并没有在狭义的中原地带产生,而是由夏、商、周、秦这些中原的“外来户”逐步完成的。苏秉琦认为这些“外来户”中的先周、秦与西部有关,夏则有源于东南方的线索,商人则认辽东为老家。正因为如此,“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11]。
但按照“中原中心史观”的逻辑,建立汉帝国的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大都应该在秦帝国核心地带——关中与中原。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大都出身于该地带的边缘——泗水郡。如果说刘邦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还大都在“泛中原板块”的话,其余三个世界级帝国——唐、元、清的开国集团核心成员的出身地则均在旧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乃至于“泛中原板块”的边缘,其出身的民族(族群)也非汉族。
以往论说中国历史时,往往“汉唐”并论,以昭示其国力之盛。但李唐王朝的开国者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其创业与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鲜卑人[12],人所共知,不待赘述。至于男系,虽然其姓氏好像是汉族的“李”氏,实则不然。《新唐书》说,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乃追录其功,封唐国公,谥曰襄。襄公生昺,袭封唐公,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13]。无论是北周还是西魏,皆为突厥化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王朝,其具有世袭贵族性格的“八柱国”从来都没有汉族出身者。在这一点上,李氏与同为北周与西魏贵族及“八柱国”、并拥有血亲关系的隋文帝杨坚家族相同。李渊的本姓,据《旧唐书》说:其“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仍赐姓大野氏”[14]。这里披露出来的信息是“仍赐姓大野氏”之“仍”字,“仍”者,一仍其旧也。也就是说,李渊的祖先本姓大野氏或其他胡族姓氏,后来改为李氏,而今周文帝又将其本姓——大野氏复赐予之。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此不赘述。关于杨氏、李氏的男系家族,退一万步说,即使像后来他们自造家谱所标榜的那样——分别为弘农杨氏、陇西李氏,但至少说明他们在北朝时业已胡化。无论是从血亲上还是文化认同上,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出身或认同胡姓的干系。为了揭穿此事,陈寅恪考证出李渊、李世民自称其先世出自西凉李暠之正支后裔纯系捏造,并“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而“初古拔或车辂拔乃当日通常胡名”[15]。实际上,早在唐宋时代人们都知道此事,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6]。
就唐帝国的制度文明而言,李唐王朝的核心文物制度系承继其本民族——鲜卑族创立的北朝而来。对此,陈寅恪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17]。正因为如此,杨氏隋朝、李氏唐朝的一系列体制,如经济上的均田制、政治上的任官与选举之权归属中央、军事上的府兵制、官吏选拔上的科举制等,皆是以往汉族王朝所没有的制度。又因李唐王朝创业者君主身上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使得他们既有着农耕出身的汉族君主所不具备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性格,也有着汉族出身君主所不容的“收继婚”(如唐高宗李治娶其后母武瞾)等胡人风习。
元、清王朝皇室及该二王朝的开国集团分别出自蒙古族与满洲族,二王朝的发祥地分别在金王朝的岭北界壕边、明王朝的辽东边墙外。也就是说,取代没落的金、明帝国的元、清帝国是在原金、明王朝政治秩序的边缘发展起来的。联想此前的汉帝国发祥于秦帝国核心区域的边缘、继承了北朝的唐帝国开业君主先祖及核心集团成员先祖出自长城外的蒙古草原与辽东的西部等史实,使得笔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疆域形成的真实脉络与动力源泉问题。历史的事实是,汉、唐、元、清,特别是元、清这两个世界级帝国的创立均是在原有帝国秩序圈的边缘完成的,这两个新建立的帝国不但分别将其发祥地(大漠板块、辽东板块)带进了崭新的帝国秩序,而且在征服了原有帝国疆域的同时,还开拓了新的疆土。凡此种种,莫不使笔者对以前所接受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汉民族比周边少数民族先进等史观产生怀疑。于是,笔者将目光转向了与中原文明渊源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更有别于中原的其他地域。
2.五大文明板块的基本样态与发展趋向
(1)冒顿单于:大漠板块的最初统合者
关于游牧经济何时形成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根据考古资料,在蒙古草原,至少在4000多年前,作为游牧文明象征的马业已家畜化。但在欧亚草原地带卷起狂飚,两千多年来给旧大陆带来一波又一波巨大冲击的成熟游牧文明的出现,却是公元前9至前8世纪之事。此后,无论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还是中部,抑或是西部,均相继出现装备了青铜马具与武器的游牧部族,次第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历史上最初留下盛名的骑马游牧部族,在草原地带的中部为塞人,在东部则是迟后几个世纪出现的匈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人与匈奴人的光辉业迹之所以能名传千古,是因为东西方双峰并峙的两大历史学家分别予以纪录之故。这便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及其不朽的巨著——《历史》与《史记》。有意思的是,二人虽分处东西方,时代不同,语言不通,更无法交流,但彼此所描述的对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游牧民的移动性与生存条件紧密相连。根据20世纪初的现地调研资料,在精耕农业区的江南,一二亩良田就能基本上解决一个五口之家的吃饭问题,但即使在水草丰茂的陈巴尔虎右旗游牧区,一个五口之家必需的放牧面积则至少为22,860亩左右,且这个牧场还是游动的⑦。在该游牧地带,正常年景至少需要移动8~10次。至于每次移动距离,由于受旗地制度的限制,蒙古游牧民的移动空间业已大为缩小,即便如此,近者一次需走42~53公里,远者达265公里左右[18]。生活在这样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畜惟有不间断地移动,才能获取生存资源,从而也因此增强了游牧民突破其他社会“边界”的能力,形成了与定居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判断尺度与思维方式。
游牧民因移动性而衍生的快速机动性与瞬间集聚性,造就了游牧世界对定居农耕世界的军事优势。自公元前750至前700年间中亚及南俄草原出现了斯基泰(Scyths,skythai)人游牧铁骑,直至乾隆皇帝于1755年击败准噶尔部,在长达20多个世纪中,诞生于大漠板块上的马上弓箭手们对定居地带的农夫们一直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对古代和中世纪而言,马上弓箭手们投射的飞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全副武装的可轮流换乘的马队既有开路护体的价值,又有着步兵不可比拟的速度。这一兵种,在面对冷兵器时代的定居民时,其战斗力与摧毁敌人士气的威慑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迨至近代,面对由农夫们组成、手持长矛大刀的太平天国军,特别是在遭遇了游荡在黄淮平原上的捻军时,曾格林沁马队曾为游牧铁骑的荣誉做过回光返照的一击。但当1860年曾格林沁的马上弓箭手们在京东八里桥面对着近代欧洲的火炮填充手、火枪射手们的时候,那西洋大炮的隆隆声便毫无悬念地终结了一个长达20多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时期。
公元前3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即位后不久,臣服东胡、击走月氏。同时,南并楼烦,夺回被秦占领的河套及阴山一带,北服丁令等部。进而于公元前200年大败刘邦32万大军于白登。嗣后近70年间,汉朝不敢与匈奴争锋于长城内外。于是,冒顿单于凭借快捷的骑马兵团,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第一次统合了长城以北、西伯利亚以南,东起辽河、西至葱岭以西的“大漠板块”。而此时,“泛中原板块”尚未最终统一。
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先后依靠该板块建立若干个“北朝”。与此同时,具有突厥与鲜卑双重血统的李氏唐朝,承“北方汗庭”之余绪,第一次使“大漠板块”与“泛中原板块”实现了完全的统合。元朝则以“大漠板块”为基地,第一次统合了古代中国的陆上板块。
可见,该板块在构筑中国历史疆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2)汉武帝:“泛中原板块”的奠定者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大体上指今日河南,后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笔者所界定的“中原”还有“大中原”与“泛中原之分”,“大”者指秦朝统一的地域,“泛”者指汉武帝及其子孙统一的疆域。
公元前21世纪夏代,在“泛中原板块”上有“执玉帛者万国”。嗣后,经过10个世纪的互相攻战、彼此融合,到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在位时,中原尚有八百诸侯。春秋初年,犹有五十余国,至战国中后期,尚余七雄。到了秦始皇登场,灭六国,首次统一了中原。就居民族属而言,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夷夏共同体——汉民族在秦汉帝国时期最终形成。
在该板块上,如果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算起,到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的征讨事业尘埃落定,经过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由夏启开辟、经秦始皇初步构筑、再经汉武帝再拓展始告奠定。随之而来,真正意义上的“南朝”也呱呱坠地。继西汉之后,东汉、曹魏、西晋、具有突厥与鲜卑双重血统的隋,以及宋、明等先后依靠此板块建立了若干个“南朝”。
汉武帝构筑之“南朝”与冒顿单于构筑之“北朝”,形成了“南北朝”,双方既对峙,又相互承认。其后,中经东汉-匈奴、东汉-鲜卑、西晋-鲜卑、北朝-南朝、隋-突厥、北宋-辽等、南宋-金等、北元-明、瓦剌-明等,迄至清中期,中间只有唐朝短暂、元朝近百年统一过南北朝,其余时间大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许多地域被本文划归到“泛中原板块”,但这只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大的方面和总的趋势来界定的。譬如西南地区、辽东半岛、西域地区的文明,有时或经常与“泛中原板块”有所区别,此不赘述。
(3)松赞干布:雪域板块的缔造者与“西朝”的奠基人
据信史记载,公元6世纪后半,活动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吐蕃部落开始强大,渐次吞并临近部族。7世纪初,松赞干布承继父祖之业,东征西讨,君临整个青藏高原。到赞普赤松德赞时,吐蕃已是东接今四川西部、甘肃西部,南邻天竺,西占西域,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的强大赞普朝。
763年吐蕃攻陷长安,立李唐子孙为帝,设年号,大赦天下,署置官员,但不久因天气炎热而主动撤退。嗣后,唐、蕃皆有罢战之意。于是,双方于783年商定在清水会盟,划分疆界:靠近唐朝首都长安的陕西西部、整个甘肃与宁夏的大部分也收归于赞普帐下。
821年,唐朝为了减轻压力,又与吐蕃会盟于长安王会寺。盟词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奠其两疆,西为大蕃,东实巨唐”[19]。与《旧唐书》这段盟词相互参照、可彼此印证的还有至今仍耸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其碑文曰:“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中略)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以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20]。
此时此刻,唐蕃双方彼此承认各为东、西方之主。按照当时的“中国”景况,可以说,唐朝与吐蕃实际上构筑了古代中国的“东朝”与“西朝”,双峰并峙。然就实力而言,西朝睥睨东朝之态,跃然纸上。
但吐蕃王朝统一雪域板块还不到百年时间,嗣后,该板块内部再也没有产生过统一力量。这是因为雪域板块内部大体上可分为以农业与半农半牧为主的卫藏、以游牧业为主的安多、以半农半牧为主的康巴三个文化单元,特殊的地貌造成了同一文明区域内的农业与游牧业生产方式的二元分离。不同的生产方式衍生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使在同一个地理单元中,每一个高山深谷又程度不同地形成了在谷底冲积平原与缓坡上种植青稞、小麦与油菜等农作物,在山上游牧与狩猎的经济形态。在藏语中,生活在河谷地带的藏人(Yul或Rong pa)被称为低地农夫;游牧在高山草原地带的藏人(aBrog pa)自称为高山草原牧人。从而使得一个山谷上下分别衍生出了以游牧与农耕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
由于定居农业与游牧社会的二元分割,不但二者彼此难以统合,即使农耕区与游牧区内部也是四分五裂。正因为如此,吐蕃统一王朝崩溃后,该地域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的崛起,都离不开外来势力的扶持。同时,藏传佛教能够充分发展,也得益于这种羸弱的经济与割裂的政治局面。由于政治与经济、文化与族群、地缘与生活方式的紧密关联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历史的发展自松赞干布赞普以降,始终具有强大的东向性。对此,石硕提出了西藏种族与文化东向发展说:“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事实: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趋势”[21]。无论是统一吐蕃时期迎娶文成与金城公主、占领陇右、陕西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在长安建立短期政权,还是蒙元时代阔端与藏传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八思巴及萨迦派领袖世代被封为大元帝师,抑或明朝时期设河州与朵甘及乌思藏三卫、1578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仰华寺会晤、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乃至于清代五世达赖喇嘛晋京、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莫不验证此倾向。这种既不南下进攻极易得手的恒河平原及南亚-东南亚,也不西进获取印度河平原及中亚-南亚的态势,使得崛起于“大漠”与“泛中原”及“辽东”诸板块上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始终对其起着决定性作用。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卡拉斯科说:“从西藏历史的开篇之时,西藏就以不同的方式蒙受中国人的影响”[22]。
在雪域高原上崛起的统一吐蕃王朝曾一时间入主中原,立马灞上,惜因时令等原因而最终丧失了君临天下之良机。但统一吐蕃将原本各自政治独立,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承乃至于族群构成迥异的雪域高原统合为完整的社会共同体,使“雪域板块”从此作为一支聚合的力量横空出世,与李唐王朝争霸天下。统一吐蕃瓦解后的藏传佛教通过宗教的力量将“雪域板块”的一体性延续下来,妙用文化力量参与并深刻地影响着元明清三代的中国疆域构建历程。
(4) “辽东板块”的逐次崛起
“辽东板块”的南部与西南部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渔猎业;以今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部地带以农牧渔猎混合业为主;西部以畜牧业为主;西北部与北部以游猎业为主;东部与东北部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上述不同经济类型的大体布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中期,大体上一直被延续下来。
与这四大经济类型相联系的是东北地区的濊貊、肃慎、东胡、汉族四大族系。将“辽东板块”初次统合为一体的为辽朝。由本土力量将该板块最终构筑成型的应属女真人及其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2世纪初期,渔猎耕牧于松花江干流南岸支流——阿什河领域的女真完颜部,仅用10多年时间,便消灭了辽、北宋,把领土远远地拓展到淮河流域。引导金朝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其独具特色的国家体制。而金朝最有魅力、最能体现通古斯系民族特色的体制,莫过于集军事、行政、生产为一体的“猛安谋克制”。就军事而言,与“猛安谋克制”密切相关的是骑射与围猎习俗。
逮至入关,为了保持八旗骑射的传统,延续通古斯系民族固有的骑射与围猎习俗,清朝曾对东北与内外蒙古进行封禁。清帝国藉不满10万将士塑造了陆疆130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与众多的属国或属部尚不计在内的强大帝国,莫不依托其基干的、在“辽东板块”上铸造出来的铁骑。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人在入关前就汲取汉文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在创立与巩固后金(清)政权过程中,大力采纳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清皇室的汉文化修养之高,不仅远远超出少数民族皇室,即便是历代汉族皇室也罕有出其右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洲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这为他们汲取与农耕文明密切相连的汉文化提供了心理的与现实的保障。
可见,“辽东板块”与“大漠板块”是有区别的。前者兼有渔猎游牧与农耕文明二者之优势。其强悍与擅骑射乃渔猎游牧民族之所长,此乃优于农耕民族之处;其不亚于农耕民族的文功,得益于其本身固有的农业传统,此乃优于纯粹游牧民族之处。
在“辽东板块”上兴起的最早的强盛政权当属建立于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次则为树立于698年的渤海。而首次将“辽东板块”势力扩展到中原腹地的应属女真人及其建立的金朝。金朝灭亡后350年,即1583年女真人后裔努尔哈赤起兵辽东深山,经其祖孙七代,历经230多年的努力,始以辽东一隅之势,继举全国之力,所经何止数百战,终于缔造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帝国,最终于1820年将中国五大“文明板块”真正统一。
(5)“海上板块”的形成与内敛
人们以往考察中国疆域问题时,经常将视点落在陆地上,今日看来,这明显是不充分的。围绕着前述的诸海域,位于其周缘的国家与地域及其交易城市相互影响,构成了历史性的重要海域交易圈。在各交易圈的交错地带,形成中继都市,这些中继都市的市场相对整备,并形成商人居住区,发行通货,交易条件较为完善。这些连锁的海域与朝贡贸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海域圈在连接着“陆”的地域圈的同时,还保持着独自性。
所谓“独自性”,是指海域世界呈现出相互协调的多种族性、多文化性,具有流动性、商业指向性、多样性等特色,成为有别于“陆”域的秩序空间。
古代中国人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已能畅通无阻地横渡渤海海峡,至少在4千年前的殷商初期已出现了帆船。西汉航海家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洋东部海域的航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家不但开辟了南海直达波斯湾的航线,而且还有慧深和尚扶桑国之航。进入隋唐时代,唐帝国除了维持与日本之间的原有古老航线外,渤海人开通了多条从今海参崴等地到日本各地的日本海航线;黑水靺鞨人开辟了从库页岛到堪察加半岛的鄂霍次克海航线。同时,唐帝国船队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抵达红海与东非水域,纵横驰骋于北印度洋上。经过唐宋两代600多年的持续发展,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到了元朝臻于鼎盛,明初达到巅峰。嗣后,古代中国的官府与民间势力虽然渐次退出印度洋,但在东亚海域仍然维持着主导地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如果以19世纪初期富尔顿发明汽船为分水岭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帆船曾以无与伦比的优势,在东亚诸海域乃至于北印度洋上纵横驰骋了近2000年左右。
故弗兰克说,从1400-1800年,中国不但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23]。
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松浦章将17-19世纪的黄海、东海、南海称为“清代的海洋圈”[24]。国际知名学者滨下武志是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海上事业的:“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以此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夹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欧美各国为寻求亚洲的特产品,携带着白银也加入到这个贸易圈中来”[25]。
由是观之,明清以后的海上板块之构筑,海商与贸易、帆船与移民、海上交通与海盗是起了主导作用的。虽然得不到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清朝的海上贸易事业还是有所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承认,清代早中期所形成的海洋圈,应该说是大陆的自然延伸部分,还是陆地中心主义的产物。但经过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六次关于“海防”、“海权”大讨论,清廷朝野对海洋、海权的认识已相当深入,具有一定海洋意识与海洋思维的“海上板块”脱颖而出。
四、中国疆域统合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华夷同源”谱系、“天下观”
1.“五大文明板块”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
就“大一统”思想而言,该思想肇始于战国时代的孟轲,中经董仲舒、司马迁的诠释,再经李世民的实践,特别是司马光的理论升华,最终定型于蔑里乞·脱脱、爱新觉罗·胤禛等。司马光曾对大一统之内核有过辨析: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26]
司马温公从理论层面上诠释了“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实际上也是在为崛起于其他“文明板块”上的各政权入主中原正名。“大一统”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历代有识者的努力,他们把难懂的、学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所以,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耐人寻味的是,在两千多年中,无论是出身于中原的汉族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出身于边鄙地带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以孔子为导师;在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各个“文明板块”都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理论。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领袖企图去寻求以新的统治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实施有异于其他领袖的地方自治或独立体制。他们心中的国家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像的或理念之物。随着“大一统”思想渐次成为“五大文明板块”上各种政权的共通意识形态,各个板块上的人们也随之逐步累积了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物质基础。
2.“天下”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之间的重合
在古代中国,与今天意义上的“国家”一词相对比较接近的汉语词汇当为“天下”。至少从战国中期以降,该词语就已经在比较确定意义上被使用了。此后直到清朝中后期,大都是作为从空间意义上概括性定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或地理认知范围的词语而出现的。
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通过探究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所编纂的经书等典籍及其时人对这些典籍的诠释,认为这个时期“天下观”的特点是“扩张的天下”。同时,渡边氏认为作为比较成熟且确指政治共同体空间的“天下”一词,出现在战国中期,到了前汉末期趋于定型。天下的领域也从方三千里,进而到方五千里,最终达到方万里[27]。
前汉以后,许多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即便如汉唐这样强大帝国的史学家,也大都将天下与郡县等同起来。如班固是这样描述从周朝到秦朝的领域的:“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汤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28]。即秦朝兼并七国后,七国之地变成郡县。在此,天下与郡县相互重叠。
关于唐朝玄宗时代的疆域,《旧唐书》是这样界定的:“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29],即十五道的总和为天下。《资治通鉴》是这样表述的:天宝元年,“天下生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30]。也就是说,唐朝的天下领域为三百三十一个直属州与八百个羁縻州之总和,而且这个天下不是无限伸展的,故有边境。
应该说,古代中国的皇帝统治是通过版籍来实现的,即运用户籍制度将臣民固定于不同的区域,通过郡县机构予以统治。而天下作为皇帝所能直接支配的领域,是被限定于郡县制所及的有限范围之内的。
但另一方面,与史学家的客观记述历史不同,经学家们基于儒家经典所提倡的德治观,认为古代中原王朝皇帝还对周边夷狄负有德治之责。皇帝通过版籍来支配的天下是有限的,但通过德来支配的天下就有无限拓展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原王朝皇帝始终以上述两种传统支配方式的相互作用为基础。渡边信一郎认为,天下观之所以具有单一政治社会型面貌与复合型社会面貌这两个侧面,也正缘于此。天下型国家是以存在成为天子德治对象的夷狄(四海)为其成立条件的。
渡边氏认为,“天下=中国”说,与“天下=世界·世界帝国”说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列阵于鸿沟两侧的分别是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国民国家论是对诞生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并概念化的产物;而帝国概念则缘于欧洲古典时代,是从其与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出发,论述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论。对于前近代中国之天下,用源于欧洲的国民国家概念与帝国概念来诠释,首先需要直面的是适用与否的问题。不可否认,前近代中国之天下与天下理念,与国民国家概念及帝国概念之间,确实跟任何一个都很相似,但又都不太像。在中原生活或入主中原的人们,是把天下作为国家(被政治性编成的社会)来表达的,同时将其理想样态视为“天下大同”之世。换言之,在前近代中国人那里,天下是有两个不同的境界的,即现实的天下与想象的天下,前者是指王朝本身所能管辖的领域,后者是作为理想之物,是可以无限放大的。由此可见,清朝中后期以前的所有王朝,均不能等同于嘉庆25年奠定的“中国=天下”。
以往,许多深受儒家经典影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常以所谓中华之世界秩序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在理论上,这个秩序至少应有三个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核心(内)的、伟大的、文明的;而蛮夷是边缘(外)的、渺小的、野蛮的。但只要我们认真地梳理一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能够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华中心之世界秩序,只是许多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相互传承,长时段地建立起来的一个主观的“虚构”。
就古代中国汉文化传统而言,譬如孔子在修《春秋》时,他既把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渗入其中,使得这个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里影响了数十代士大夫与儒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王者无外”,无形中给后人增添了许多想像的空间。所以,讨论以汉族为主的古代文人所声称的“天下”时,应尽可能厘清“虚幻”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同时,在前近代中国,文化的分界与政治的疆界之间,经常是不一致的。应该说,“天下”与“中国”之间的最终重合,已是1820年以后的事。
3.“华夷同源”谱系
大一统思想也好,天下观也罢,它们更多地是从哲学的层面来阐释中国疆域构造问题,唯有《史记》从血缘、谱系入手,从华夷同源视角,构筑了大一统思想体系。笔者曾就此问题撰文阐述,兹概述如下[31]。
春秋时期,齐、鲁、晋等中原诸侯自称为“华夏”,位处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等,则被称为“夷狄”。进入春秋晚期战国初期,伴随着秦、楚等夷狄诸国的强大与问鼎中原,它们也随之跻身于“华夏”之列。与此相呼应,“夷夏之防”的观念也被抛弃。不消说,“华夏族群”边界自然随之扩展,部分夷狄族群被化成或自化成华夏族群。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夷边界大移动乃华夷变态的第一波,第二波则随着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最终达成。因为此时的汉朝已是“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的华夏帝国,帝国内部充斥着夷狄族群,帝国边缘环绕着夷狄部落或国家,汉朝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这些夷狄族群、如何与这些夷狄部落或国家相处的问题。诞生在这种境况下的《史记》,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素材,加之自己的远见卓识,将夷狄族群与华夏族群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构建。那就是司马迁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架构。如前所述,“源”为黄帝,就“流”而言,黄帝后裔除了华夏族群之外,还有秦、楚、吴、越,进而涵盖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蛮夷族群。
在古代中国极具宗族色彩的社会环境中,族群性始终被体验为一种血缘现象,即一种在自我的持续以及在几代人之间共享祖先联系的持续。所以,当司马迁构筑“中国”大一统思想框架时,建构华夷一体、华夷共祖认同的历史体系便成为最紧要的一环了。因为没有华夷界限的移动、没有华夷共祖的认同,天下一家、四海如一的“大一统”便无法架构。即使勉强架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应该说,司马迁所架构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或许反映了华夏知识分子或官方单方面的意向,但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不同,族群可以被外人来辨别和认定,并且不必有自我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构筑的华夷共祖认同体系不但为华夏族群所认同,而且为夷狄族群所认同,进而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之夏与刘渊之汉、鲜卑人之前燕、南凉、北魏、西魏等政权,莫不以黄帝之裔自居,并以此作为入主中原的法理根据。
五、中国疆域底定的必然性与中国疆域形成模式的例外论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性的帝国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的尼罗河流域,埃及帝国一时间地跨西亚北非;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亚述帝国,首次将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两大文明地区囊括了进来。时间距今最近的拿破仑帝国崩溃于19世纪初期。期间,许多世界级帝国兴衰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迄今为止,除了中国之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级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就此点而言,中国前近代国家形态,特别是疆域构造与形成路径是独特的,是例外的,欧亚所有的世界级帝国的历史经验都无法在此得到验证。
但这种例外性并不意味着前近代中华帝国的形成缺乏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前近代中华帝国的性格、疆域构造与奠定路径是东亚特定的地理态势下、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特殊的文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种特殊性在于前近代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圈。经过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冒顿单于统一大漠游牧区、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统一泛中原农耕区,“五大文明板块”的初步轮廓开始显现。嗣后,再经过漫漫两千多年,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特别是生产方式相差较大的五大“文明板块”最终融合为一体。期间,各个“文明板块”上兴起的势力有如接力赛,前后相继,先由边缘兴起再逐鹿中原,尔后再向周边拓展,最终于1820年完成了中国疆域的统合。而其他所有世界级帝国消亡后,其废墟上均先后产生了多个政治中心,旧帝国文明往往冰消瓦解,出现了多个国家的复杂局面。
就古代中国疆域的奠定路径而言,“五大文明板块”都先后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它们置身于缔造古代中国疆域的接力赛之中。期中,最先崛起的是“大漠板块”与“泛中原板块”。
就“大漠板块”来说,蒙古草原处于比较恶劣的气候带上,冬天是西伯利亚酷寒气候的延长地带,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炎热气温的纵深地域。那里几乎是10年一次的冬季暴雪或春季旱魃,导致牲畜死亡或牧草枯萎。此时,游牧民往往将目光投向黄河流域肥沃温湿的土地。况且游牧业属于单一经济,它需要农耕区的粮食、茶叶、铁器、各类日用品等来支撑其生存。在这种状况下,游牧民对农耕区的定期性推进便成了一条自然规律。这些草原之子,莫不属于头脑清醒、身强体壮与注重实际者。当农耕区政权腐败无能时,快如飓风的铁骑每每轻易地将其征服,他们成了“泛中原板块”的皇帝。毋庸置疑,这些征服者不但带来了固有的文化,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接受农耕文化,并使之相互融合。人们津津乐道的盛唐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代表性产物。同时,崛起于“大漠板块”上的各种政权也经常是农耕文化的继承者乃至于代言人,如北朝及隋唐、辽朝、元朝等。
就“泛中原板块”而言,在秦汉及其以前,该板块曾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其他“文明板块”起到过主导作用。同时,五大“文明板块”最终被统合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华夷同源”谱系、“天下观”等理论发祥于此。另外,各“文明板块”入主中原后共通的交流工具——汉字也在这里产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国时代以降,由于生活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局限,从“泛中原板块”上孕育出来且由汉族为核心集团成员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往往善文治而乏武功,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不是表演者本身,而“泛中原板块”所能做的则经常是提供一个表演舞台而已。“泛中原板块”最终未能在武功上担负起统合中国疆域的历史使命。
位于东北亚核心区域的“辽东板块”,在前近代,她既有着与“大漠板块”大致相同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有着游牧铁骑同样的南下冲动,但更兼有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之长。唯其如此,康熙帝、雍正帝与乾隆帝祖孙三代最终实现了将“天下归于一统”的长久理念。这个理念自战国时代生成、前汉业已成熟,但在康雍乾三帝之前,始终没有人能够将其变成现实。
“雪域板块”介于印度、中亚与中原文明之间。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雪域板块”为什么最终能够成为中国疆域的有机构成部分。究其要者,人文地理条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的青藏高原,唯其东北部低缓,并且有若干个山口与“泛中原板块”相连。这些山口既是吐蕃人祖先移住青藏高原的通道,也是其欲回归故土、回归母文化的回路。自吐蕃民族共同体形成之时,吐蕃人就有着与生俱来的东向发展与东向拓展的潜在冲动。恰恰是这种东向发展的态势,以及相对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元朝开拓青藏高原提供了切实的机会与条件。
从西汉到明初,以中国官府与私人社会力量为核心,辅之以东亚其他力量,曾主导着“海上板块”贸易近2000年之久。明初至清中后期,一支反抗母国禁海政策的中国私人海上力量先被母国水军追杀,后来明清朝廷水军又与西方殖民者前追后杀,朝廷与西方殖民者均欲灭之而后快。但这支海上私人力量前仆后继,在该海域贸易体系中仍维持着主导地位,并为明清乃至于民国货币银本位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通过“海上板块”大量吸收日本、美洲白银的直接后果,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些迅速增长的人口携带着从“海上板块”传来、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与马铃薯等高产、耐旱、耐寒、耐瘠土的作物种子向东北、北部、西北与西南等高寒、高纬度地带移民,使得这些地域与中原地带迅速均质化。同时,官府则凭借着从西方传来的火器开始征服西南等地抗命土司,讨平以游牧铁骑著称的青海蒙古和硕部与西北蒙古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因大海之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统一台湾而使中国今日仍拥有巨大海域。凡此种种,莫不表明“海上板块”对中国社会进程,特别是疆域变更的影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古代数大文明发祥地大都形成过世界帝国。但除了黄河流域文明之外,今日所有主导旧帝国废墟的人们,都不是旧帝国原文明衣钵的嫡派传人。那么为什么单单中国例外呢?这似乎应该从统合中国疆域的意识形态中寻求答案。
无论是“大一统”思想,还是“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实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大一统”而言,该思想原本是晦涩难懂的哲学命题,但通过历代有识者的努力,他们把难懂的、学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所以,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伴随着这个“大一统”思想逐渐衍变成历代帝国的意识形态,历代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也获得了统一天下的思想武器。秦汉以降,历代世界级帝国开创者心中的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像的或理念之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如是观。这也意味着,在近两千年时间里,要重新创建和重新形成帝国体制,总是有现成的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可以利用的。中国各个时期的较强大的王朝,如唐、元、清等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论理。否则,如果国家只是力求用军事手段延长自己的统治寿命的话,就会在强制性资源和控制手段方面引起难以收拾的问题,从而造成国家的瓦解。因为唐、元、清即使在全盛期,相对于其1300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陆疆而言,其不足百万的军队,面对前近代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与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唐、元、清时期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的社会特点,改变策略和人员配备,以促进统合和控制。尽管如此,汉、唐、元、清四朝都能根据当时各地的社会特点,随时改变策略和人员配备,始终以微量的军力维护帝国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它们高举“大一统”思想旗帜、心存“天下观”理论、有效运用“华夷同源”谱系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其他几个从大河流域崛起的世界级帝国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心地带兴起,而后向周边扩充。但该帝国一旦灭亡,支撑着帝国的核心力量便也随之冰消瓦解。而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狭义中原的边缘或泛中原板块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
[注 释]
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步统一中原,为后来的汉帝国崛起准备了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中经汉高祖、惠、文、景帝的经营,汉帝国渐次崛起;自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帝国趋于鼎盛;自公元前32年汉成帝即位,到公元220年曹丕建立曹魏政权,直至316年西晋政权灭亡,期间汉帝国由衰败而中兴,但也没有挽救其命运。三国西晋虽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乃至于主体统治族群上,继承汉帝国而来,但没有一个政权能够挽救颓萎不堪局面,从而摆脱短时期便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②自317年以降的“五胡乱华”,随之而来的东晋十六国,及后来的南北朝、杨隋时代,莫不是唐帝国崛起的前奏。各种政权与势力经过三百年的彼此攻伐,各种族群经过三百年的相互融合,一个崭新的“外汉内胡”帝国——唐帝国伴随着李世民的登场而趋于强盛,中经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的经营,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达到了鼎盛。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帝国进入衰退渠道,渐次衍化成“五代十国”局面,最终无法收拾。
③契丹人与蒙古人同属游牧民族且血缘甚近。916年,契丹人兴起于蒙古草原东南部,尔后向四周拓展。中经契丹-辽帝国对蒙古高原、今东北、京津,及冀、晋北部的经营,再经金帝国在此基础上向南推进,长时期对黄淮海流域的开拓,凡此种种,均为蒙古-元帝国的横空出世铺垫。自1206年成吉思汗兴起于斡难河畔,到朱元璋政权占领北京,此时期为蒙古-元帝国的鼎盛期。自1368年元顺帝退狩蒙古草原开始,元帝国走向衰落。到1632年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元帝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④就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而言,清帝国文明有三个源头,分别为满洲人与生俱来的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明王朝废墟上的农耕文明与政治制度、北元王朝-鞑靼汗朝废墟上的游牧文明与对草原统治的合法性。清帝国经过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的经营,到了康雍乾三朝,达到了繁盛,形成了世界帝国的模样。嘉道以降,清帝国缓慢地走向衰落之路,迨至1840年清英之役,再也无法恢复其元气,从此走上不归路。
⑤清朝第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由穆彰阿等主持,历时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因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断,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⑥该“板块”只是借用板块构造论(plate tectonics)的名词,表明各个不同地域的动感的、立体的形态。
⑦[日]后藤十三雄著、布林译:《蒙古游牧社会》,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研究会1992年编印,第24~28页。根据甘肃农业大学编《草原调查与规划》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一只带羔母羊为一个羊单位,一匹成年马与牛相当于5个羊单位。
[参 考 文 献]
[1]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N].光明日报,1951-05-05.
[2]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N].文汇报,1961-11-04.
[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4);陈梧桐.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古代民族战争[J].求是学刊,1982(4);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2005(4)
[4]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4);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3).
[5]杨建新.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J].兰州学刊,1986(1);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J].云南社会科学,1989(2).
[6]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
[7]顾颉刚.禹贡注释[M]∥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M]∥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81-182.
[10]蒙文通.古史甄微[M]∥蒙文通文集·第五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110-138,53-54.
[12][宋]欧阳修,等.高祖纪,太宗纪[M]∥新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宋]欧阳修,等.高祖纪[M]∥新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后晋]刘眗,等.高祖纪[M]∥旧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188-189.
[1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 136:历代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8:3245.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3.
[18][俄]迈斯基.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C]∥汉昭,译.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集,1988:215-216.
[19][后晋]刘眗,等.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传下[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姚薇元.唐蕃会盟碑跋[J].燕京学报,1934(15).
[21]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内容摘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2][美]皮德罗·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与政体[M].陈永国,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235.
[23][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文版前言[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4][日]松浦章.清代的海洋圈与移民[M]∥来自于周缘的历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25][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魏黄初二年三月”条:“臣光曰”[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27][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M].东京:校仓书房,2003:40-60.
[28][汉]班固.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29][后晋]刘眗,等.旧唐书·卷 38:地理志一·序[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
[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5:唐纪·“天宝元年一月”条[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31]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2).
On the Ultimate Route and Modal of Chinese Boundary
YUFeng-chu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of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5,China)
Until now,it is only China,whose real heir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ve revived,that has successfully returned to the aggregate of world powers after the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worldly empires have been raced out in the games of great powers.The core power of other worldly empires which rose along the large river basins all emerg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empires,once vanished,the core power that supported the empires would resolve.Different from that situation,the worldly empires of ancient China were all formulated around the edge of central China,and provided successive and continuous energy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chain style worldly empires.Though the imperial founders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races(ethnic groups),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concept of“Great Unification”,the theory of“World View”,the lineage of Hua-yi’s Sharing the Common Ancestor,which have been maintaining the operation of empires chain,have never been interrupted.Consequently,among the worldly empires in ancient China,there was an internal cultural heritance and boundary continuity.
empire;five civilization continents;Great Unification;World View;Hua-yi’s Sharing the Common Ancestor
A
1008-178X(2012)11-0001-13
2012-08-19
于逢春(1960-),辽宁东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边疆史地、边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