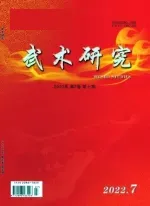中日历史中的僧兵现象对比研究
2012-08-15蔡银针郭春阳王晓东
蔡银针 郭春阳 王晓东
(1.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河南大学体育部,河南 开封 475001)
佛教在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急剧发展,再到隋唐达到鼎盛时期。日本佛教于公元六世纪传入,在平安、奈良时期势力不断壮大,至幕府时期已达顶峰。同一宗教,其生存的地域不同,被支配的阶级不同,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它的思想和制度也就会随之变化。
在中日两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一种孕育于寺庙中的特殊武装力量——僧兵,并在两国的社会与宗教发展史上扮演了相应的角色。然而,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不相同,僧兵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发展也不尽相同,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更深层地理解中日两国的历史与文化。
1 僧兵概念的界定
在对中本僧兵进行比较之前,首先,让我们来阐释一下僧兵的概念。在中国僧兵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僧兵是指所有的武装僧侣,从狭义上解指官方所允许的僧侣武装,或为朝廷而战的僧人。前者的身份是“僧”,主要指练武的僧人,即武僧;后者的身份主要在于“兵”,和武僧有所区别,武僧为僧兵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日本僧兵指的是手持武器组织起来的僧人集团,古代称之为“恶僧”,到了江户时代史书才称之为僧兵。本文所讨论的是一种包含两者的僧兵,即是有规模的寺院武装集团。不根据国家意志来判定其身份,只是根据其行为判定的。综上所述,僧兵即是有规模的寺院武装。
2 中日历史上的僧兵活动
2.1 中国僧兵发展史
2.1.1 中国早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及五代十国的僧人习武活动
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乃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直到魏晋南北朝(公元4-6世纪)急剧发展,这一时期乃多事之秋,战争杀伐连年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寺院等如何保卫自己也就成了大的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僧侣习武的现象。
根据史籍记载:一是“《魏书》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骑宿于瀍西杨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3]僧侣若没有武艺,孝武帝应该也不会让其负玺跟随;二是魏太武帝西伐至长安,到了一个寺庙中“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4]”。寺内藏有兵器,说明该寺有僧侣可能习武;三是北齐将高湝“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士者亦数千人。[5]”当时北齐崇佛,北周灭佛,来应募的僧人主要是为了卫教而不是钱财,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但能来应募参战,平时习武应该理所当然。
隋唐时期的中国达到了空前富强和统一,佛教也以此为背景进入了繁荣时期。[6]创立于隋代的有天台宗、三阶教、三论宗;产生于唐代的有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和藏传佛教。隋唐换代时,即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围击洛阳王世充时曾联合少林僧众,此乃十三僧助唐这一史事。这可以说明少林寺僧具有尚武的传统。据史籍记载:唐永昌元年五月:“己巳,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以击突厥……八月癸未,薛怀义为新平道中军大总管,以击突厥”。[7]宋灭南唐时,僧人为前锋保卫金陵,“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右之明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徒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8]
以上所列乃中国僧人习武及的记载,其身份还是“僧”,亦可称为“武僧”,这一时期的僧人习武多是因为在兵荒马乱之时用作守卫寺庙之用,或为零星的习武僧人参加军事行动,但也些也为后期僧兵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2.1.2 宋金辽元时期的僧兵活动
宋代前后320年,是秦汉统一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国外有金、辽并存。佛教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的。
以下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宋代僧兵的抗金活动。“靖康之扰,聚其徒习武事于山上。钦宗召对便殿,眷赉隆缛,真宝还山,益聚兵助讨,州不守,敌众大至昼夜拒之力不敌,寺舍尽焚,……莫谦之,常州宜兴僧也。德佑元年,纠合义士捍御乡间。诏为溧阳尉,是冬,没于战陈,赠功夫大夫。时万安僧亦起兵举旗曰‘降魔’,又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旋亦拜死”。[9]
根据马明达先生所考:“在宋代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到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的太原围城战役期间,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之后,五台山僧兵都参加了抗击金人的侵略战争。两次抗金战争证明了五台山积聚了相当力量的僧兵。五台山僧兵抗金失败后,清凉寺遭焚,到金代中后期仍未恢复昔日辉煌。明代中期五台山僧人还有武事活动。明末农民战争兴起后,五台山又曾经被卷入战祸中,自此后便一蹶不振[10]”。宋抗金时“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11]这时很明白就是僧兵为军了。辽代记载:“盖大辽旧少食粮食,以食粮军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为不足;又募僧兵。[12]”这是对辽代募僧兵的明确记载。金代记载:“犯罪大者即施行,之小者籍之事定,始论其罪。谕枢密院萨哈连:‘所签军有具戒僧人,可罢迁之’。[13]”这说明金代也曾征僧人参军。元代时僧兵记载:“明安喀喇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诸色人,不当差者万余人充柱齐,明安领之[14]”。这则记录表明元代时亦有入伍。
这一时期的寺院武僧是作为有一定规模的寺院武装集团出现在战场的,和之前的武僧活动大有不同,所以应称其为僧兵,佛教僧兵也是在此之后在中国络绎不绝地出现。
2.1.3 明清时期的僧兵活动
中国僧兵进入明清以后所参加的战事日益增多,尤其在明代。明代僧兵抗击东南沿海倭寇,已是被学者反复证明了的。书上记载也有不少:“明代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15]“如鸷,嘉靖注略僧天元讲《楞严》于天池山。苏州抚臣知其武,召之出。募游僧八十,制衣,内皮外竹甲,造枪钩铁挺诸杖,每战为官兵前,或倚诸军战酣,群僧跃击如鸷,倭贼畏之”。[16]
据程大力先生所考:“明代时僧兵共参加的抗击倭寇的战役记载的有七个:杭州之战(公元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赭山之战、翁家岗之战、白沙滩之战、叶谢镇及马家浜之战、六里桥之战、巢门之战七次。[17]”关于明代僧兵的历史记载比较多,如《武编》、《江南经略》、《日知录》、《学礼质疑》、《筹海图编》、《元诗选》都有僧兵记载。此外,还有地方通志记载,如《山西通志》、《湖广通志》,明代僧兵除参加御倭战争外,还参加了其他的军事活动,如戍边、镇压反叛及流民、农民起义等等。
顺治年间,僧兵还帮助朝廷剿灭强盗“有剧盗陈、许二姓,又僧超忠聚僧兵千人,据铜钵山上,尤横江诱擒。超忠密布方略破许贼于罗汉岩,进兵大柏江捕获陈姓于乌桥东”。[18]此外,魏源集七言古诗中有句诗云“秦王倘用少林寺,秉拂登坛万人敌。佛门广大多英雄,老向普陀空太息”[19]反映了僧兵在当时已具有重要影响及官方势力对僧兵力量的重视。明清时期僧兵的主要作用是评定叛乱或抵御外敌,也就意味着佛教已参与到军事等世俗事务中,佛教武装也经常性的为国家服务。
2.2 日本僧兵发展史
2.2.1 平安时期及以前的僧兵活动
佛教约在公元六世纪由百济正式向日本传入佛教。经过物部氏及苏我氏争斗,后以支持佛教的苏我氏胜利而开始在日本传播,在圣德太子的扶植和提倡下,此后佛教便迅速渗入日本社会。至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或学派有六个,即:三论宗、诚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此也被称为:“奈良六宗”。因奈良位于平安(京都)之南,因此奈良佛教也称为“南都佛教”。此后,桓武天皇迁都至平安,这一时期产生了天台宗和真言宗这两个新的佛学宗派,称为“平安二宗”。“奈良六宗”长期与“平安二宗”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在10世纪中叶后形成主要由下层僧人组成的武装——僧兵。
日本僧兵究竟具体始于何时现已经无从考察,但是到天台宗第十八代座主良源(公元912-985年即平安时期)僧兵势力已显著发展。
至平安末期,毕睿山延历寺、园城寺(三井寺)、法相宗的兴福寺、华严宗的东大寺及京都地方上的药师寺、醍醐寺、鞍马寺、清水寺、太山寺、大山寺、真宗的高野山及根来寺、熊野山、笠置山、白山、彦山、多武锋等寺院,也拥有僧兵,其中延历寺的僧兵(被称为“山法师”)和兴福寺的僧兵(被称为“奈良法师”)是最强大的两支。
这些寺庙经常以僧兵为前锋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斗争,也常常与地方以至朝廷对抗。斗争的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抬着本寺院的镇守神舆到京都强诉。到平安末年为止,兴福寺僧众奉春日神木入京共有八次,山门奉神舆入京共九次。第二种方法是直接采取武力,将对方寺院或者房屋烧毁。如,天台宗内部因座主继承问题导致分裂后,“山门”与“寺门”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
南都佛教中最凶残的是法相宗的兴福寺,安和元年(公元986年)兴福寺与华严宗的东大寺因庄园纠纷进行合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兴福寺因清水寺的归属问题与延历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上述两种方法经常被交织使用,互相之间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以上山、寺二门及南北佛教的倾轧都反映了僧众拥有强大势力。
2.2.2 仓镰幕府时期的僧兵活动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庄园制。佛教是镰仓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还从中国传入了禅宗。旧有的佛教宗派势力强大,并且对新的佛教宗派的传播进行阻挠和压制。但因新佛教宗派教义易于理解,及幕府的支持,新佛教随后广泛流行起来。
镰仓幕府时代是日本佛教史的中心,这一时期建立的佛教宗派有净土宗、净土真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禅宗。佛教宗派林立矛盾更复杂化,除了宗教寺院之间的斗争外,宗教寺院还与幕府军冲突,如“建宝元年(公元1213年),山门僧众要烧毁清水寺,幕府军制止,于是与幕府军冲突。幕府军攻到山门上逮捕恶首30人,杀10余人”。[20]这一时期,僧众的斗争到镰仓后期已变得非常复杂了,宗派寺院之间,宗派寺院与幕府之间矛盾都在不断升级,僧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磨砺,到了室町幕府时期他们就更加骁悍了。
2.2.3 室町幕府时期僧兵活动
延元元年(公元1336年),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失败,足利尊氏宣布实施武家政治,至此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其也包括南北朝时期和战国时期。庄园制到室町时代已经基本瓦解,各地的守护大名几乎控制了所管辖地域内的一切土地。这一时期内各佛教宗派战争亦不断,主要发生的有真宗武装斗争,史称“一向一揆”,中国有的史书译为“真宗起义”,指真宗对抗守护大名或其他宗派武装集团的斗争,百年之间真宗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直到最后被织田信长制服。还有日莲宗的“法华一揆”,是以京都为中心发生了日莲宗的武装斗争,当时战国时代两大割据势力细川晴元和三好元长各自利用真宗和日莲宗这两宗门徒作战,随后天台宗在六角定赖及法相宗兴福寺的支持下,与日莲宗也展开激烈斗争,攻陷日莲宗的21本山,双方死伤很多,史称“天文法华之乱”。在整个战国时代,各个佛教宗派利用其僧兵武装势力与各地武装大名进行抗衡,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其中僧兵的骁悍程度不逊色于大名所养的武士,俨然就是佛教中的武士一般。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人严厉的武装打击和高压政策下,僧兵的政治势力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 中日僧兵现象的对比
同是一种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其思想和制度也就会跟着变化。佛教传到中国即被中国化了,中国化的佛教传到日本之后也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中日两国的僧兵虽都由佛教产生的,但两者却表现出很多不同之处。笔者将从社会环境、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四方面对中日僧兵进行对比,从而更深层次地分析两者的不同。
3.1 政治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此后,中央集权的制度便一直延续至清朝结束。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朝代里,没有任何事物或者人物高过皇帝的地位,也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势力的存在。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乃因佛教势力过于庞大,以至于威胁到国家统治。如魏太武帝西伐至长安沙门“入其便室,见有弓矢矛盾”,于是太武帝下令灭佛。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难免带来教权至上的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上,实质上是争论把谁的准则置于更高的位置而已。佛教倘若摆不正这个位置,过分的扩展教权的政治势力,就会与皇权形成冲突,朝廷必将以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那就是灭佛。“三武一宗”灭佛之后的千余年,再也没有发生灭佛事件,主要原因应该是皇权对佛教已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天皇在日本乃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的表率与象征,天皇在神道教中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故具有神性。佛教进入日本后先是被当做“蕃神”,后在圣德太子提倡下才广泛推广。太子进行大化革新时弘扬佛教,并将其作为新政的基本精神。在奈良时代,日本大力推行佛教政治,如行基、良弁、道境这些僧人当时都进入了政界。平安时代“当时的贵族阶级一般都深信王法与佛法之间的相互关系,王法依佛法而兴旺,佛法有赖王法的保护,即所谓佛主王从的相互关系。[21]”这些说明了,在日本佛法是同王法一样至高无上的。此外,日本还出现了大量的皇室、贵族的皈依。在天平二十年(公元748年),天皇、皇后和皇天后出家受戒,这也是皇室受戒出家的开端。平安朝以后,有白河天皇、后鸟羽、石嵯峨、厚深草、龟山诸位天皇都落发出家,其皇子也相继穿上法衣;南北朝的时候,后醍醐、长庆、后龟山诸天皇以及北朝的光严、光明、崇光等都深深归心佛教,源赖朝、北条氏、足利氏等人也深深皈依佛教。另外,还有上皇在寺院中办理政务,从白河天皇开始了(应德三年公元1086年)到安德天皇末年(寿永四年公元1185年)这一段时间称为院政时代(“院政是指政治实权归于上皇,也就是‘院’,院设院厅处理政务,院下达的‘院宣’比天皇的诏敕、宣旨还要重要。”[22]),也可以称为佛教政治。院政时期佛教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中日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对两国僧兵的形成及以后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3.2 文化背景
中国在孔子时代封建制度就逐渐破裂,打破许多迷信,抛弃君主神权思想,而推崇平天下和平民的思想。后建元元年(公元135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客观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统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与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及皇权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时的魏晋南北朝就和儒家进行了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论战,如,齐梁时期范缜所著《神灭论》在当时影响极大。后来佛教逐渐采取吸取儒家思想的策略进行传播、发展,如佛教徒倡导的“三教合一”,佛教开始尊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无国无家,无父无子的观念向忠君爱国思想靠拢等等。但无论佛教发展到何种程度,儒学从来都是被视为正统的,如在佛教大发展的唐朝时期“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23]在中国,儒家文化始终居于最高正统地位,思想独立,所以僧兵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忠君爱国的行为。
日本自佛教传入之前信奉的是本国的民族宗教—神道教。佛教初传日本时虽遭迫害,但最后却以胜利而告终,佛教以其先进的文化及宗教理论,对日本本土文化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尤其对顽固的神道教的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后来产生了著名的“本地垂迹”。“‘本地垂迹’,实质就是神佛一体的思想。‘本’指的是本源,事物的原有姿态,佛家所指的是佛的真身,而‘迹’则是佛的真身在现实世界中普度众生的显化,佛是神的‘本地’,神是佛的‘垂迹’”。[24]这样佛教既避免了与日本神道教的冲突,也可将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教中来。日本在早一时期吸收的儒家文化大部分是通过佛教传来的,圣德太子新政时期也采用了这些儒家及佛家外来思想,但是固有的神祗思想也同样受到重视。日本到了近代,也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除去欧洲所输进的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传来的哲学宗教思想外,相比当时思想文化发展已经十分成熟的中国,日本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就略显幼稚了。
3.3 社会环境
中国的封建社会,国家总在改朝换代中度过。每当朝代更替动乱之时,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内心也会陷入极大的惶恐,此时佛教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思想上的慰藉。此外,由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使佛教向儒家忠君爱国的标准靠拢。“僧兵”就以忠君爱国的思想出现在疆场,为国家为人民进行浴血奋战。如宋代有名的五台山的抗金僧兵;明朝抗倭僧兵;还有一些戍边、镇压反叛及起义的僧兵等等,他们都是在国家、社会有需要的时候由朝廷或者地方招募而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正义之师。并且,当战争过去以后,国家和平昌盛之时,这些僧兵也就退出了军队。
日本虽然自从开国以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家族就从未更迭过,不似中国的封建社会总在改朝换代。但是,其内部的争斗却从未间断,如围绕着佛教传入之始,苏我氏与物部氏之间的权力争斗;镰仓幕府之前源赖朝与天皇的权力争夺战;室町幕府之前足利氏与源氏的战争;战国时代各守护大名之间杀伐不断;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战争等等。日本中古至下古时期也处于战争连连的社会动荡期,佛教思想是社会的需要,日本社会上层对佛教则表现出过分的依赖,如从佛教传来后就不断有皇族、贵族的皈依和营建诸寺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在平安时代初期政教分离之时,皇室对佛教的皈依仍然很深,乃至到平安朝以后,皇室、贵族出家的愈益增多,从而造成佛教势力日益强大及僧兵的飞扬跋扈。
3.4 经济背景
在中国宗教寺院的财产一方面来自统治阶级的投入,一方面乃是僧众们的自我垦植。寺院过分的扩展教团经济势力就是对国家经济势力的一种削弱,这会与国家收入形成冲突。佛教传进中国初,就被当作方外之宾,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特别是劳役、兵役、赋税。有了这些好处,僧侣的队伍不断的被扩大,国家本身就要对宗教寺院进行投入,反过来,不纳赋税,不服劳役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使得寺院经济日益得到壮大,从而损害国家经济。唐武宗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之时,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收良田数千万顷。”从这些数字上可看出佛教寺院经济的庞大,“会昌灭佛”后寺院经济一直在皇权的统治之下。宋代也有规定一切寺院必须缴纳助役钱和免丁钱。寺院有时候也会隐蔽的拥有大量田产,但是官方若发现此类问题也会去严厉追究的,而不是姑息、纵容其发展,如在清代宣德间,广东安察司佥事曾鼎奏“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处寺观田地,多在临近州县,顷亩动以千及,畏之寄庒,止纳秋粮,别无差科,……又有荒废寺观土田,报为寄庒,收租入己,所在贫民五天可耕,且多徭役,而僧道丰富,安坐而食。”即反映了佛教寺院占田丰厚,贫民却无田可耕种的事实,从而损坏了朝廷的利益,官府上奏也是责成僧侣承担一些经济上的义务。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期的土地制度中,神田、寺田和公廨田属于不纳租的田地,并且神社、佛寺对神田、寺田的占有和使用权力要比其他各种田地大得多,几乎是近于所有权。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政府鼓励开垦土地时规定“允许垦田永世私有”,于是各大寺院所占土地和财富显著增加。到平安末期其经济结构已从班田经济逐步变为庄园经济。庄园拥有者包括一些大的社寺,他们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势力,也就有了产生僧兵的条件和必要。安和元年(公元968年)兴福寺因与东大寺发生庄园纠纷,双方僧兵合战,伤亡惨重。这也是日本庄园制基础上僧兵的典型活动,特别是在室町幕府后期的战国时代,各大寺院的僧兵还与各个大名领主集团相抗衡。
4 结论
中日两国的佛教发展史中都有僧兵产生,且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其所产生的背景上是不相同的。中国皇权强大,儒家思想成熟,加上对佛教寺院经济的严格控制,从而僧兵除了在兵荒马乱之时用作守卫寺庙外,就是参与评定叛乱或抵御外敌,即为国家所用。日本由于天皇幕府之间常年的权力争夺,对佛教寺院经济无限纵容,为僧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加上本土文化相对幼稚,佛教以其信仰及思想在文化上的优势,影响日本的统治者,继而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势,进而僧兵飞扬跋扈成为寺庙与政治之工具。
[1]《日知录》卷二十九.
[2]《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十》.
[3]《周书》十二卷《齐炀王宪》.
[4]《新唐书》卷四.
[5]曾达臣.《独醒杂志》卷一.
[6]《宋史》卷四五五.
[7]《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8]马明达.说剑从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66-71.
[9]《三朝北盟汇编》卷一百十.
[10]《金史》卷十四.
[11]《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12]《明史》卷九十一.
[13]《元明事类钞》卷十九.
[14]程大力.少林武术通考[M].郑州:少林书局,2006:32-37.
[15]《江西通志》卷六十五.
[16]魏 源.普陀观潮行,魏源集(下卷)[C].北京:中华书局,1976:724.
[17]杨曾文.日本佛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1.
[18]村上专精(日).日本佛教史纲[M].杨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13-326.
[19]坂本太郎(日).日本史[M].汪向荣,武 寅,韩铁英译.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56.
[20]坂本太郎(日).日本史[M].汪向荣,武 寅,韩铁英译.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53.
[21]任继愈.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41.
[22]孙雪菲.论日本神道教与佛教的融合关系[J].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3):15.
[23]《史传三编》卷二十七.
[24]余继登(明)典故纪闻(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