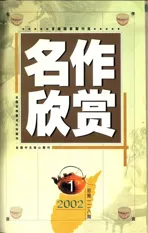在深度与风度之间徜徉
2012-08-15北京
/北京_冯 雷
(冯雷,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名作欣赏》自改版以来整体面貌有不小变化,在我看来,编者乃是努力想要在学术深度和文学风度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刊发的文章大多既不失扎实的考证、细密的论证,又不失枕边或是茶余阅读的乐趣与闲适。2011年第12期上的几篇文章大多具有这样的风致。
由于平时研究与教学的关系,我对现当代部分更加注意一些。周小舟通常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而进入公众视野的,吴心海先生的文章《周小舟早年文学活动管窥》则比较清晰地呈现了周小舟早年作为文学青年的侧面,很有分量。现代作家大多使用过多个笔名,笔名及佚文的认定可能会刷新我们对某位作家的认识。吴心海先生从周小舟的笔名考订入手,顺藤摸瓜,查阅了《文史》《世界文学》等原始刊物,通过翔实的史料,认定周怀求、周筱舟、周小舟同系一人。通过吴文,我们可以知道,周小舟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现今所见主要是在翻译和诗歌领域。在学界当前对现代主义的趋奉之中,高尔基已经鲜有人问津,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却是让国人高山仰止的文学大师。吴先生顺带讲述了一则发生在王蒙和胡乔木之间的小故事,涉及到周小舟翻译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由此不难看到译者当年的眼光。在诗歌方面,吴先生考证指出最早提出“现代派”的是周小舟,这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发现,日后文学史的编写也许要多记一行重要的注解了吧。
贺仲明先生是我所熟悉的学者。《以淡写浓,别赋深情》一文主要从情感把握和散文写作的角度来品读周作人的散文名篇《故乡的野菜》,落笔之处切中了周氏散文的特点。不过读后却略微觉得有些不过瘾。想来大概一则,文章开始处紧扣作品本身,但后面的讨论却未能附着在作品之上;二则周氏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冲淡平和,而内里却有一种生涩,一种“隔”,而贺先生也提到“在作品力求客观化的叙述中依然若隐若现,始终传达出很强的情绪感染力”,不过却未点破这一层。关于这一点,被视为是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废名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知堂先生近来常常戏言,他替人写的序跋文都以不切题为宗旨。”由是观之,周氏在行文中如贺先生所言“采用了知识化的方法,运用大量的引文,穿插大量的风俗知识介绍”就不仅是有意为之,而且是别有所求吧。如此再翻回头来看周作人的“平淡”,恐怕会有更多所思所得吧。
李兆忠先生的长文《纵情的极限》,我是当做传记来读的,我想也只有在《名作欣赏》上才能读到这样随性而又不失认真的文章吧。李先生从郭沫若早期爱情生活入手,考察郭氏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很有些“发生学”考证的意味。刘文荣先生在《爱的书写》里向我们“推销”了一本小说选,而他最动听的理由便是那个离奇的爱情故事。我一直记得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里曾感慨,文学史真的那么重要吗?有好的作品就足够了!我深以为然。如果碰到了刘先生推荐的爱情小说选,就买一本吧。只为了读几篇精彩的小说,这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汉诗重镇》里登场的几位大多是我所熟悉的诗友,罗振亚老师和李少君兄不久前刚在湛江现代诗第六届研讨会上见过,冯强兄曾在我的寝室里栖身、卧谈。看到他们的名字是忍不住要挂上几分微笑的。冯强兄远涉重洋,赴德国求学,马上就是新年了,你在他乡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