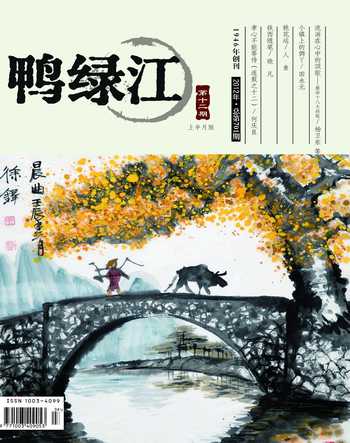孝心不能等待(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之十二)
2012-04-29何庆良
何庆良
2007.6.28 周四 重庆
童稚语,祖孙情
午后,手机上传来了儿子写的一篇悼念祖母的祭文:
《因为奶奶去世,我热泪盈眶》
作者:何忠煌
“我从妈妈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贺凤云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5月14日10时40分,病逝于大连市中心医院干部病房16床。
当我看到消息,悲伤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就像《和时间赛跑》的作者说的一样。我明白:
“你的昨天过去了,就永远都不会来了。”
想到这些,我就想哭,泪水就流出眼眶。我努力排除自己的忧伤,让自己高兴起来,如果奶奶在天堂看见我欢笑,她一定会高兴。”
这是一篇充满着期待的祭文,尽管文字和感情都很幼稚,但泪水还是涌出我的眼眶。
没人去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写这样的文字,没人去教他去表达这样的感情。他没有去参加奶奶的葬礼,不知奶奶去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更何况,他是一个“雨人”,是人们心目中认为没有或者说是缺乏情感交流的孩子。
虎仔曾经是奶奶心中的一个痛。如今,奶奶的去世却成为孙子幼小心灵中的一个痛。原来,痛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升华的,是可以世代相袭的。
虎仔五岁多还不会说话,也不愿意与人交流。这让视孙子为掌中宝的奶奶夜不能寐。她为孩子的忧虑和担心是无言的,却是最为深切的。直到虎仔开口说话,奶奶才松了口气。后来,妈妈对我说,她曾整夜睡不着觉,想起虎仔就揪心。
虎仔虽然有交流上的障碍,却有着过人的记忆能力。对于日期、车次、电话区号、航次、交通路线等数字的记忆能力让人瞠目结舌。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幅北京的活地图。他可以不借助任何提示,随时报出当时的时刻,几乎没有正负五分钟的偏差。他的长项成为短项的补偿,让老人又有了一丝宽慰。
妈妈去世前三年,每年都有五六天与虎仔相处的日子,这是奶奶最高兴的事儿。虎仔也表现得十分乖巧,讨奶奶的疼爱。外出游玩,他会跑前跑后围绕奶奶转,拾到掉在地上的一朵花,他会殷勤地送到奶奶手里,好像是他淘宝的新发现。每次和奶奶分手前,他都要显得依依不舍的样子,让老人顿生无限的怀想。特别是老人卧床不起的那个春节,虎仔给病中老人以精神的安慰。他俯在奶奶的脸旁,说些让人听了不知是感动,还是发笑的稚语。尽管那些话是模仿大人说的,从孩子的口中说出让人觉得可乐,却足以见得一颗童心的纯真。
老人与虎仔并不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极有限,奶奶也许在他的印象里只是一个称呼。但血缘的传承把时空的疏离淡化了。祖孙之间的血脉是相通的,那是一种天然的纽带,是任何的地理空间和物理的时间都难以割断的。
奶奶的弥留之际,听到孙子从手机的话筒中传来的祝福,眼睛也微微地一动。那是她生命烛光的最后一闪,那是她在冥冥的阴阳之界最后的期盼。老人走之,没有孙子的守灵,但千里之外的那颗童心却感受到了失去祖母的哀伤。他用稚嫩的语言道出了他内心的悲痛与祝福。妈妈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告慰。她日思夜想而为之焦虑的那个孙子,对奶奶的慈恩已经懂得了回报。
2007.6.29周四重庆
妈妈倒下了
妈妈是二零零六年五月初被意外撞伤倒下的。
那时,她的摔伤刚刚恢复。因为前一次的摔伤极大地限制了妈妈的行走和生活空间,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不小冲击。
对于这样一个勤劳一生不知疲倦的母性来说,受人照料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这次意外的严重伤害几乎彻底摧垮了这位暮年的老人。
医院检查诊治回来,表面上看,只是胳膊骨折,吊起打着石膏的绷带,并不严重。但妈妈告诉妹妹,她的眼睛看不清物体,耳朵也听不见了。不久,身体的健康每况愈下,双腿浮肿,血压居高不下。
六月初,妈妈被送进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被迫出院了。因为医保只允许病人住院半个月。然后,再入院治疗。据悉,这是为了收“门坎费”。
妈妈坚持到十一月,又不得不再次入院。此时,长期卧床的妈妈开始痴睡呓语,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妈妈的症状稍有缓解,但已经无法自主行动了。她被救护车用担架送回了家。
妈妈在病榻上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与家人分享了亲人团聚的最后时光。那时,她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忙里忙外,为亲友们做饭炒菜,端茶倒水,只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了。从妈妈深深的叹息中可以体味出,她是多么渴望为家人做奉献的满足感。
正月十五,恰好赶上大连风暴潮。或许是气候影响的原因,妈妈的病情骤然加重。她双眼呆滞、神情恍忽。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种眼神的妹妹被吓怕了。电话中用哭泣的声音告诉我,妈妈病得很吓人,她已经不知该如何是好。
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闻讯而至,将妈妈连夜送进医院抢救。妈妈度过了一劫,却没有任何康复好转的迹象。她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
她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抗争。她渴望自己能够重新下地,自主地活动,继续地操持着这个温馨的家庭。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妈妈对妹妹说:“你哥能回来就好了,他能找个好大夫治好我的病……”。妈妈的话吐出了她的心声,表达了她对生的渴望与向往。
然而,进入三月之后,妈妈的各种老年性疾病相继出现加重的症状,仅靠各种药物已经不见疗效。无奈之下,妹妹多次打电话报急,请求我回家处理,但限于当时的工作无法脱身,只好又将母亲送进医院紧急救治。
医院用常规的治疗收效甚微。妈妈身体的生理机能开始衰退。医院可以治病,但不能救命。转眼半个月又过去了,妈妈又被迫出院回家。
此时的妈妈已经不能自己吃饭咀嚼了,甚至吃药都成了难题。她只能勉强吞咽一点流食,且一边喂一边流。一顿饭要吃个把小时也吃不了多少有营养的东西。
稍后,她已经不能坐起和站立。即使这样,妈妈也坚持让两人搀扶着去解手。因为她不愿意给家人添麻烦。妈妈用尽最后的力气,直到她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为止。
随着四月的来临,妈妈生命的脚步再也迈不动了。她开始整日昏迷,神志不清,甚至连终日厮守她的妹妹也有时认不出来,呓语中时常呼唤我和远在美国妹妹的名字,常常提及早年的家事和亲人。老家的妹妹闻讯赶来,见到昔日她们印象中的老人如此的病况都不禁失声痛哭。
妹妹一次又一次告急,妈妈可能不行了。面对危在旦夕的妈妈,我不得不电告姑姑从山东德州先行前往大连,为我照顾妈妈。姑姑迅速启程前去照看妈妈,随即来电告知,希望我尽快返回大连。从姑姑的经验判断妈妈随时都有离去的可能。姑姑说,她已经让妹妹给妈妈订定装殓的丧服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电话两边都已经泣不成声。
但是,工作和任务都不允许我马上脱手回家去照顾病危中的老妈妈。
一天夜里,妹妹突然来电告知妈妈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家人判断妈妈可能挺不过今夜。
情急中,我拨通了同学和朋友的电话,请求他们立即赶往家中帮忙。同时又叮嘱妹妹立即呼叫“120”,将妈妈送往医院急救。
妈妈生死的脚步停下了,却在阴阳两边的临界线徘徊。
她没有走,是她的意识中还在期待着没有归来的儿女与子孙。
2007.6.30周六重庆
大爱无言
妈妈的爱是深藏在心中的,从不言表。
她对长辈的爱,化为赡养的孝敬,太爷和太太都是九十岁以上的高寿。他们的晚年是这位长孙媳妇像照料儿童一样,将他们送终。太爷每天三顿必喝酒,妈妈会不厌其烦地想方设法为老人整好下酒菜。逢年过节又要为来访的亲朋好友置办酒席。
太太是个十分爱清洁的满族老太太。铺盖从来一尘不染,白线袜子直到破了,补了还是本色。身上的大褂洗了要浆,浆了要踩出线。记得小时候,我也帮妈妈干过这道活。把衣服裤子叠得整齐后再铺上被单在脚下翻来覆去地踩。效果就相当于今天烫斗的工艺。
妈妈从奶奶六十岁那年起,每年都要回家给老人过生日,直到奶奶九十一岁过世。有一年,妈妈和姑姑回老家给奶奶过生日,从城里回家的途中,三轮车冲进了一家理发店。妈妈和姑姑被翻倒在车里,腰部和脸部都受了伤,却不讲给老人听。第二年,妈妈还是照旧回老家履行着做儿媳的孝敬。有一年,奶奶在姑姑家生病,妈妈就做些好吃的饭菜送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
妈妈对同辈的爱,化为慷慨的给予。有一年,老家的小叔叔要盖新房子,这在农村是件大事。妈妈问爸爸,能给多少钱表示赞助。爸爸说只有两千元的存款。妈妈说,老家盖个新房不容易。无论怎样也要给出五千元。妈妈张口把妹妹的钱借来先凑上。这一笔钱恰好给叔叔解了燃眉之急。不然,那新房子就不能赶在雨季前封顶。
一九七九年,妈妈要搬进楼房,原来住平房那些家俱和许多生活用品难以上楼了。收购的乡下人都看好这些物件,但妈妈把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了姑姑。邻居以为是送给姨舅家亲戚的,后来得知是送给姑姑,都敬佩不已。
妈妈对晚辈的爱,化为无私的奉献。自打我们记事起,妈妈从来没带过子女们出游、看电影、吃饭店, 但妈妈把她生命的每一天都给了我们。春夏的夜晚,妈妈种地管护菜园;秋冬的夜晚,妈妈做鞋缝袄。她似乎有做不完的家务事儿。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由于城市扩建,住宅历经三次搬迁。为了迁居盖房修院,妈妈把日子过得很紧很紧,攒钱攒粮又攒油,为的是花在最吃紧的那几天,不亏待前来帮忙干活的工友。为了我们能有一个温馨的家居,这些艰难的日子在妈妈的记忆始终挥之不过。直到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她在梦呓中还说:“那年头的日子度日如年,真难呵!整宿都睡不着觉。”但鼾睡中的儿女有谁知道妈妈那时的心境?我们的梦乡里从来没有想象到妈妈的艰难与辛酸。
妈妈对街坊邻里的爱,化为大度的宽容。妈妈是邻里和同事心中最具有亲和力的人。在农村,乡里乡亲的却经常为些鸡零狗碎的事儿骂街吵架。妈妈的大度和亲善让左邻右舍张不开口,放不了粗。不论是本家的还是外姓的提起妈妈,无不交口称赞。妈妈进城几十年,每次回乡,老少爷们,七大姑八大姨都亲热得不得了。那时不懂得什么是和睦社会,只觉得妈妈的“人缘好”。
在城里,楼上楼下的邻里磕磕碰碰的事儿更多。许多时候是为了孩子间的打闹引得大人之间发生火拼。妈妈的忍让和宽容让悍妇和莽汉也不好意思出言不逊,放肆无理。每逢搬家,都有新邻居,各色人家都得相处。妈妈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和好一家邻,结下一门亲。邻居间的冲突往往是妈妈去说和,道理不大,可双方都服气。
在单位,家属工中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是造成不和的根源。“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一群家属工中,经常是两人的对台戏。
工厂的领导往往镇得住工人,却管不住职工家属。遇到两个家属工口水相向、不可开交的情景,工厂里的“清官”往往是无所作为、不知所措的。一些强势的家属工也不把管他们的“芝麻官”放在眼里。交战的双方经常会转移火力,对劝战的“工头”实施交叉火力打击,搞得劝架的人反倒更加狼狈难堪。这种局面下,妈妈是常常被请去说和的,久而久之,连党员都不是的妈妈被同事称之为“何书记”。
妈妈用她无言的爱感动着老人,感化着我们,感染着与她相处的人。
妈妈从不把她的善良和慈爱用语言说与世人,却用她无言的大爱、仁爱和博爱赢得了亲人与友人的敬重。
2007.6.31周日 重庆
淡定的人生
妈妈的一生很平凡,很普通,就像一棵路边的小草。
我们只听到她唱过一首歌《小草》。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草的命运和妈妈的一生几乎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个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妈妈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就宛若晴朗的夏夜天空中一点遥远的星光,无人瞩目。
妈妈的人生很平和,很淡然,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妈妈婚后的五十八年里赡养和抚育了五辈人。五辈人的衣食住行,五代人的生老病死,五十多年的家里家外,五十多年的起早贪黑,有说不尽的艰难与困苦,但妈妈的口中没有怨言。从不议论人家的短长。
妈妈生活得很淡泊,很透明,就像一汪清冽的山泉。
记忆中,妈妈没有任何的生活嗜好与追求。在那些生活艰苦的年代,一个背负着全家生计重担的母亲很难有个人的奢求。但是,即使晚年的妈妈完全有条件可以颐养天年的时候,她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妈妈把好衣服寄送乡下的亲戚,捐赠给灾民。旧的衣服就拆洗干净缝抹布。她把旧毛衣拆线重新织成好多件毛衣毛裤,说是留给爸爸和我。她担心自己走了,无人照顾我们父子。她从来不奢求给自己留下什么,占有什么。就像李商隐的诗句写的那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妈妈生活得很平定,很坚强,就像一颗抵得住风霜雨雪的劲草。
她把生活的阳光留在脸上,把自身的痛苦埋在心底。记忆中,妈妈受过几次创伤。有一年冬天,妈妈给外孙开家长会,雪后道路又硬又滑,妈妈小心翼翼地走路,还是重重地摔了一跤。回家后,妈妈照常做着家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当晚,摔伤的右臂肿涨起来,直到第二天检查才发现,严重骨折。妈妈吊着一只胳膊依然像往常一样闲不住,操持着家务。
一次搬家时,妈妈被玻璃板割断了手腕上动脉血管,鲜血吐涌而出。小妹妹惊慌地把妈妈送到医院,却赶上医护人员午休吃饭。鲜血不停地涌出,小妹妹吓得说话都发抖,但妈妈却镇定地等待着,没有任何惧怕与慌乱的表情。
妈妈最后一次被意外撞伤是很严重的。她忍受巨大的伤痛,强忍着下地解手,洗漱。临终前,她把实情告知爸爸。她因为担心爸爸会去找邻居讨个说法。为了不影响爸爸的情绪,她一直强装笑颜,把痛苦隐蔽在心里。病榻上的妈妈为了不给女儿增加负担,坚强地面对各种病痛带来的折磨。妹妹流着眼泪回忆说:“病危时的老太太真是太可爱了。她特别地要强,从来不因为自己的病痛而发脾气,让子女为难。”小妹妹哽咽着说:“在妈妈已经不能说话的时候,还拉着我躺在她身旁,让我休息。”
妈妈的一生是平实的,她活得平平凡凡,实实在在。她默默无闻地为家人和他人奉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她把做好事善事当作平凡事从不张扬夸耀。她把艰辛和痛苦留给自己,不去向别人抱怨诉说。
妈妈的人生之路,一言以蔽之:从容,淡定。
2007.7.1周一重庆
高天万里祭母魂
七月一日,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七期”的最后祭日。
京城入夏以来,最大最长的一场雨已时断时续地下了三天。
最让人震撼的是昨日午间的大雨,如同倾盆一般从高天泼下,溅得大地一片雨雾朦胧。豪雨荡涤着空间的浮尘,冲刷去草木上的落尘,清洗着道路上的泥尘,也在净化着心灵上的凡尘。
黎明时分,黑沉沉的天边始现一抹蓝天。阴霾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褪。天空开始逐亮,黑云由灰变白,太阳终于出来了。
川航3U8884航班正在待命起飞。
今天,是祭母“七期”的最后一日,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入藏的日子。这两个特殊的日子恰和在一起,也应该是天意吧。
对于西藏的向往由来已久。最初的萌动是来自西藏风光摄影家车刚赠予的个人摄影专辑和同学李亚平的新闻通讯集《人在高原》。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入藏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巧合的是祭母的“七期”。
西藏,是“世界屋脊”雄踞的地方,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也是我心中的圣地。这里是神山圣湖汇聚的地方: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有世界是最高的湖泊——纳木错,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也有最神秘的日光城——拉萨。西藏高原的风光壮丽奇特,绚烂多彩。皑皑的冰峰雪岭,如同银雕玉琢,浩浩天际荒原,天高地阔。据说,这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通过飞机的舷窗,可以眺望茫茫的云海,像一幅奇幻的童话世界。那些造型奇特的云朵似人似马,似山似峰,像天上人间的世界,热闹非凡,奇妙无比!。
在这万里云天之上,遥想妈妈的恩情,追思无限。
妹妹告诉我,一天,妈妈在梦呓中说,她去赶海,赶到一大筐的螃蟹。早年,妈妈在老家时,每年秋天都去赶海。那时的渤海湾十分丰饶,特别是海河交汇的浅海滩,鱼虾螃蟹和蚌类应有尽有。冥冥之中的妈妈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机灵的小妹妹意识到,妈妈可能是想吃螃蟹了。于是,她买来几只大螃蟹送到妈妈的面前说,这是她到海上赶起来的。妈妈高兴了。红红的螃蟹端上来时,妈妈却示意先不吃,等你哥哥回来再吃!
妹妹的讲述和着泪水一起流淌。
妈妈病重的时候,一夜要换几十次尿布。最后,妹妹改用尿不湿,以便让妈妈能多睡一点。当她清醒一些的时候,喃喃地说:“买了那么多的尿不湿,把你哥哥的钱都花完了,他怎么吃饭呢?
这些平实无华的语言,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口中说出,其感人之深并不亚于那些赴汤蹈火的壮举。
追思在泪水中涌动,窗外的高天流云变成一片模糊……
一阵颠簸,空姐甜润的声音传来,飞机开始下降了!
俯瞰脚下的西藏风光,魅力无限。苍翠的大草原,犹如一幅巨大的茸毯,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阳光下绿浪翻涌。越来越近的青藏高原,令人神驰,令人心往。
此行的最大心愿:是在纳木错掬一捧透彻的湖水,在大昭寺燃上一炷浓郁的沉香。向着神山圣湖给妈妈祭拜:
妈妈,愿您在天堂快乐。
来世,您还做我的母亲。
后 记
一本写给天下儿女的日记
这几十篇日记是在三种心境下完成的。
第一部份,是在守护母亲的二十五个不眠之夜写成的。为了看护生命垂危的母亲,我要随时关注她的反应,不断地为她做各种护理。稍有片刻的时间,我就在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此时此地的心情与感受。那时,我是抱着极大的希望与恐惧,希望妈妈能康复,起死复生,恐惧的是妈妈真的要走。
第二部份,是在妈妈治丧期间分分秒秒地抢记下来的。从母亲离去至火化的四十多个小时里,我的神经和身体没有片刻的停歇。即使这样,我强制自己把当时的场景用钢笔和相机记录下来。那时,毅力与坚强是支撑我继续写下去的力量,是悲痛产生的力量。
第三部份,是在对母亲的追思与祭奠中完成的。痛定思痛,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创深巨痛。每天深夜,不论多么疲倦我都坐在妈妈的遗像旁,续写着这本日记。那时,追悔的泪水常常伴随笔下的文字一起涌流,对妈妈的祭奠化为了对她一生令人敬佩的品行的追忆。
写下这本日记的初衷是留给我自己的。我担心往事如烟,会淡忘这些不堪回首的日子与情感,想把自己对母亲的怀念永久地留存下来。
2007年5月13日——“母亲节”之前,大连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王小伟,为了作奉献给母亲节的专辑节目,恳请我把日记借给她摘录部分段落,并承诺绝不透露作者的姓名与母亲的有关病况。我考虑再三,才同意了她的恳求。这期互动节目播出后,让我受到了巨大的心灵震撼,想不到那么多人收听了节目,也想不到有那么多少年哭诉自己的良好祝愿。
从听众的反馈中,我顿悟到:世界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就是母亲的呼唤(但丁语)。同样,人世间也有一种最难以弥补的遗憾,那就是未能报答的孝心!
从那一时刻起,我觉得这本日记是为了那些未能尽孝和未能表达遗憾心情的天下儿女们代言,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对母亲的深情。诚如作家大仲马所说:“母子之情是世上最神圣的情感。”“母爱胜于万爱”(莎士比亚语)。我要把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崇敬与追念抒发出来,要把母亲对儿女的慈爱和奉献记录下来。
这本日记没有构思,没有斟酌。它像感情和泪水一样的自然流淌,不假雕饰,不掩瑕疵。为的是保留那一份真情,一份实感,一份追思,一份遗憾。
最后,衷心的感谢那些对母亲表达敬意和给我鼓励与支持的亲朋挚友,是你们的真情与期待,让我有勇气把个人的日记付梓示众。
同时,也真挚地感谢为这本日记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值得一提的是,我和重点图书编辑室的吴立平和周显军两位资深编辑素昧平生,从无过往。但是,面对这样一本日记,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用热泪与真情完成了书稿的编辑和校对,去实现一个共同的心愿——把这本日记献给母亲节,让孝心不再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