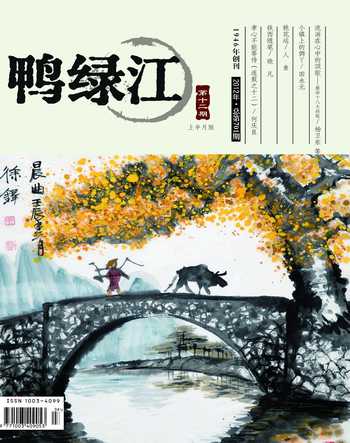铁西随笔
2012-04-29晓凡
晓凡,当代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当代诗歌》《当代作家评论》两刊主编,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专职副主席,现为省作协顾问。主要著作有长诗《生前死后》,诗集《灿烂的青春》《美的诱惑》《晓凡诗选》等,散文集《裸体的日本》《随笔写天下》,诗论集《诗歌创作技巧问答》。
人在什么地方努力认真地生活过,就像把生命的一部分种在了那片土地上,那里总是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常青的记忆。
区长与市民
那时候我上下班路过铁西区政府小院,常见篮球场上有位年龄较大的球员,中等个头,敦敦实实,皮肤偏黑,投篮很准。后来听说,他是铁西区区长,好像姓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性的大饥荒也使沈阳人民的口粮严重短缺,民间流行很广的瓜菜代、增量法等种种画饼充饥、自欺自骗的小法宝,都已无法缓解坊间普遍存在的饥饿问题。人们凭粮证购买的口粮,远远不够吃的,市场上又几乎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民间食品买卖交易,都算黑市投机倒把行为。只在连接铁西区与和平区的两洞桥下,深夜里会有郊区农民来偷偷出售自制的杂粮大饼子。他们把“货”揣在棉大衣内紧贴胸口的地方,如此藏匿一为不被发现,二为保温。不足二两的饼子两块钱一个,多数人是掂掂重量问问价,嫌贵走开了,人们实在买不起。那时厂里中专毕业的技术员,月薪只有37块钱,他们解嘲戏称自己是3728部队战士,即每月37块钱28斤粮,几乎整天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依然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今说来恍如天方夜谭,它却是半个世纪前沈阳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难以忍受的严重饥饿,使人产生幻思幻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沈城涌起了到小河沿的泥塘里挖取并食用“救命土”的风潮,它由东向西推进,很快蔓延到了铁西区。这引起了区长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有关科技人员请教,很快得出结论:那腐烂苇根和褐色淤泥生成的粘稠泥土,不止毫无营养,而且有毒。他转身又到工人住宅区和小河沿实地考察,发现很多工人和家属,天不亮就成邦结伙地带着草筐、铁锹赶往小河沿。他们先是跪拜神仙保佑他们挖到的“救命土”显灵普救苍生,然后就跳入泥塘动手抢挖“救命土”。泥塘里黑压压人海一般,区长被惊呆了,他在那里伫立了很久。
几天之后,在铁西区的许多街巷,同时贴出了《敦请区内居民千万不要挖食“救命土”的公告》,落款是“区长焦锋”!
中国百姓历来常把属地长官俗称父母官,这位区长的劝阻行动,真就如同当家者叮咛劝说家人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领导者,才有可能与普通百姓建立起互为家人般的感情。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台湾当局在他们的报纸上影印转载了这张布告。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区长也就因为这张布告被转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也许还不止于此)。
回顾往事,温故知新,发人深思,也令人痛心!
工友与厂长
我与沈阳市铁西区结缘,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生活所迫也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感召,决心到劝工街北端的东北实验工厂即后来的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厂——四四三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去报考学徒工。那时候铁西区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南站北二马路通往铁西北部工厂区虽然有一趟公交线路,可是只有三、五部破旧不堪的匈牙利产大巴士运行,二十分钟发一班,乘客总是满满的,很难挤上去,只好步行前往。
北二马路宽阔却很不平坦,砂石水泥路面已有多处翻浆,坑坑洼洼,像是大路上的一块块补丁。每当载重卡车通过,都会卷起黄褐色尘土,走在这样的马路上,心情依然很好,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快活极了;更快活的是我在那里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大工业区:从最东头的第三机床厂开始一路向西排开,高中压阀门厂、低压开关厂、风动工具厂、冶金机械修造厂、沈阳造纸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冶炼厂……极目望去,直到看不清的远方,一律是工厂和工厂,真正的宏伟壮阔。
那时候能够进入国营大厂当上工人,都有一种行将成为国家主人翁的幸福自豪感。新进厂的职工,不论年长的年少的,急切要办的事情中,有一件是不会被忽略的,那就是把新领到的厂徽别在胸前,三五成群、神气活现地到照相馆去拍照,庆祝自己成了工厂的主人。大概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多年之后依依惜别下岗离厂的一天。进厂和离厂,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进厂不久,就发现厂子很大,很重要,名声也大。那时候沈阳市是中央直辖市,在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上,经常能读到有关重型机器厂的重要新闻:新中国第一台400KG空气锤和430X250颚式破碎机在沈阳重型机器厂诞生、沈重职工造出国产第一台大型卷板机支援鞍钢改造与建设工程、新中国第一台2000吨水压机在沈阳试车成功……种种冠有“新中国第一”字样的报道使沈重声名远播。
厂大名声大,领导也很“大” ,书记厂长们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有的还是走过长征路的红军老战士。他们官大却没有官架子,常在大食堂排队买饭就餐,和工人打成一片,跟普通职工一样,受厂规厂纪制约和管辖。
厂前区的大墙上有一片很大的揭示板,经常张贴表扬、批评或处分职工的大字公告。记得有位名叫王X新的主管生产安全的副厂长签署的文告比较多,内容几乎都是提示车间、有关处室强化安全生产措施的指令,工友们都称赞王厂长关心大家的生命安全,真抓实管生产安全。后来厂里发生了一起伤亡事故,半月后就见揭示板上贴出了上级机关“关于王X新同志对伤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
围观的工友们都为这位平日重视安全生产的厂领导扼腕痛惜,同时也认知了厂规是严肃的法律文件,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真实意义。
舞动着的博物馆
诗人郭小川在他的诗中说:好日子要比春风还快,拉过来扯过去就是一年。生活确实如此。
我离开工厂四十多年之后重返铁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这历史的瞬间我们的铁西区换了人间。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中共沈阳市委常委、铁西区委书记李继安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生动准确地介绍了铁西区的惊人变化之后,又亲自引领我拜访多处铁西新景观。其实对我来说,在整个铁西区,每一地每一处都是新景新地新风光。
利用沈阳铸造厂原地原物建起的铸造博物馆,令人浮想联翩,因物及人,因人及物,让我想起我们铁西区的许多英模人物。这个厂的张成哲,早在半个世纪前就主动参加了铁西区职工创建的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组织。他常在下班后奔走在区内大小工厂,协助对方攻克技术难关,饿了吃一口自带的干粮,继续工作,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人们熟知他的特点,在技术协作队伍里,许多人暗中努力向他学习。
当年我为写作大型报告文学《红心壮志》曾经采访铁西区的这些先进人物,他们中的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引出一段好汉故事:吴大有六请刀具王——为邀请重型机器厂的“刀具大王”金福长出山替兄弟厂解决金属切削方面的重大难题,青年车工吴大有顶风冒雪一次次连续拜访邀请都被拒绝。直到第六次夜访,这“大王”终被感化说:当年刘备不过三顾茅庐,你小吴比古人还执着、真诚、热情,我老金还有什么可讲的?金福长这位“大王”这位金属切削专家终于加入技术协作队伍,为省内多家企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钓鱼迷丢杆弃网——这位钓鱼迷名叫吕德顺,八级焊工,有一手绝活“仰脸焊”。区内一家工厂的大汽罐出现顶上漏洞,多次堵焊失败,部分车间几乎被迫停产。技协得知后立即派人探访钓鱼迷。吕师傅回话说他上班厂里干活,下班河边钓鱼,没有时间去为外厂解决问题;更怕别人说他外出干黑活、捞外快……可是当他得知吴家柱、王凤恩、金福长、吴大有、张成哲等许多名人能人都在积极参与技术协作活动时,他立刻改变主意说:跟着这些人走,准没错儿,我去试试!这钓鱼迷真是身手不凡:他焊枪在手,一试成功,现场一片欢呼声。钓鱼迷深受感动,心有所悟,从此丢杆弃网,一心扑在技术协作上,不断做出新贡献,成了远近闻名的技术“大拿”,颇受同行们的敬仰。
铁西区的技术协作队伍滚雪球般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的行动在省内外工业战线产生了巨大影响。彭真同志到辽宁视察,特意在沈阳与这些先进人物见面,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席间称赞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都是企业的政治骨干、技术骨干。当场有人说,我们的金师傅到现在还没能入党呢……彭真同志说:没入党也是政治骨干!——“刀具大王”金福长,技术高超,无私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我看他具备入党条件,我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金直夫(时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同志,你看呢?
此后不久,金福长终于成为党的一员。
华罗庚先生来东北推广优选法,一到沈阳就提出要与铁西区的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们座谈。见面时,主持人正想一一介绍这些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华老笑着说:我已经从《红心壮志》书里认识各位了,今天就试试,看我能不能认出来:这位是刀具大王金福长,这位是钓鱼迷吕师傅,这位是革新能手张成哲,边说边和他们一一握手,几乎一个也没说错,可见铁西好汉们的模范事迹深深感动了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还用畅谈读书感想的方式在北京的报刊上撰写长文,赞扬、推介沈阳市铁西区的技术协作活动。
在铸造博物馆,我感到这里是铁西人抚今追昔的好去处。历史和民众会感谢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建立博物馆的创意。无论我们多么富有或贫穷,都不该在前进路上把历史遗存轻而易举地抛洒在路边,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拿着放大镜在尘埃中寻找记忆的碎片!
我们的铁西区正在快速成长、发展、壮大,遥想若干年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我们484平方公里的整个铁西大地视为“舞动着的新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史博物馆”。
中国辽宁沈阳的铁西区,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