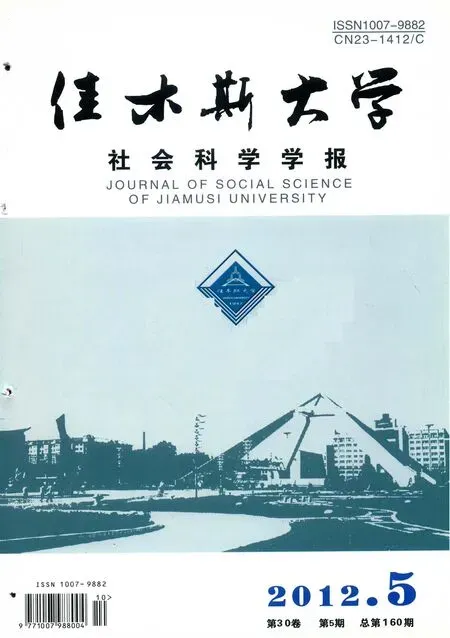《高兴》的别一番“城市”叙事①
2012-04-18李丽
李 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091)
贾平凹在《秦腔》里不忍向行将逝去、破败不堪的故乡告别,他想为故乡立碑。他的乡土情结是坚韧而执着的,设若告别了乡土之后,能去哪里呢?是去城市吗?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必然要不断向周边扩展,乡村文学只能留下最后的挽歌,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所不可回避的残酷现实,生于这个贫穷落后急需变革时代的作家必须面对这种心灵上的折磨,《高兴》的问世意味着贾平凹决心开启城市生活:“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市生活。”[1]那么,走出土地的农民们来到城市里将如何生存下去?他们会高兴吗?得不到高兴,他们又该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反映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尤其是底层社会现实深深的忧患和关切,《高兴》就是作家用来追索、记录进城农民在城市中辗转流离的文本。如此说来,贾平凹对故土以及生息于其上的人们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命运的关注一以贯之,未曾稍已。
一
“我”和同村的五福在时间刚过千年,新天新地悄然降至,举国欢呼雀跃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狂欢盛宴之际,带着进城挣钱的“高兴”心情,怀抱融入都市的远大“理想”,来到西安城。尽管“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但自从将肾卖到了西安城,“我”便觉得自己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也尽管“我”不会说普通话,并且怎么也都学不会,可“普通话是普通人才说的话,毛主席都说湖南话的,我也就说清风镇话。”身份的自我转换和重新认定让颇为得意的“我”,“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
然而,繁华却陌生的城市让老实巴交的五福一下火车便紧张得肌肉僵硬、浑身冒汗;身上穿着的最好的衣服如今也显得是那样的土得掉渣;甚至手也不知咋的“一下子就黝黑了”。“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更是笨拙可笑。“我们”处处与城市格格不入。城市的繁荣富足孕育、催生着“我们”的梦想,但是,但城市的冷漠坚硬却又让“我们”心寒。处于社会底层的拾荒者根本分不到狂欢盛宴中的一杯羹,“我们”徘徊在耗资数亿、豪华气派的仿唐公园门外,歆羡着隐隐传来的馨香和丝竹,就是领不到入场券。
作为农民,“我”和五福难以在城市讨生活。好在西安城“每天数百辆车从城里往城外拉送垃圾”,有了垃圾,“我们”就能存活下去。拾垃圾足以让“我们”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我们”成了“垃圾的派生物”。于是,西安城里的拾荒者变得不计其数,俨然形成了一个阶层。对于城市来说,正是由于这些拾垃圾者的存在,才使来自千家万户的废品得以回收利用;正是由于大量农民工的涌入,才使各项生产建设得以蓬勃开展,然而这批穿梭游走的都市边缘人却并不被接纳和认同,城市是排斥异己的,冷漠的。
“肾”是小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隐喻,它是乡村与城市、乡下人与城里人关联的一个纽结,蕴含着二者之间割舍不断的血缘情脉。肾是人生命精气的动力源,人没有了肾,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动力。在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乡村不仅向城市大量输入廉价劳动力,更给时时面临衰竭的城市提供动力源,这就好比乡村把自己的“肾”给了城市。然而,乡村没有了“肾”,它自身不就要衰竭了吗?更致命的是,乡村人那么心甘情愿、洋洋自得地把肾割给城市人,从生命情感、文化认同等方方面面便与城市及城里人有了亲近感,甚至误以为自己也是城市人了,他们单方面对城市产生了哪怕再大的歧视和斫伤,都无法摧毁的坚实的认同感和广阔的宽容度。于是,尽管一身皮肉都是清风镇的,自从将肾卖到了西安城,“我”便觉得自己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这就难怪即便五福痛骂着:“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刘高兴却始终如花朵狂吻马蹄般地宽容着、深爱着城市: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
刘高兴更执拗地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只肾,因为肾维系着他坚实又脆弱,混杂着自卑、自恋和自傲的认同——“我”的一半在城市,“我”终将成为一个城里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在城里人韦达身上寻找到的不是肾,而是肝,这实际上隐喻了乡下人与城里人、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分离。刘高兴们虽然在城市中讨生活,但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城市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的户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他们是被城市拒斥的漂泊者,终究找不到那条通往城市肌体深处的生命通道。
五福是不愿意死在城里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故土的妻儿,怀想麦收季节里昆虫和麦仁的气息。然而,酗酒让五福终于魂断打工路,“我”却无法兑现承诺,让他死后回到魂牵梦萦的清风镇,埋在父母的坟旁边,甚至无法让他的妻儿按照乡俗祭奠他。“五福一向把我当作依靠,是百事通,是十二能,我也以为我了不起”,而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懂得太少、能力有限,“我”终究只是一个连拾到了钱包都惶恐得束手无策,只能求助韩大宝的“少经见”的农民,五福的游魂只能在这个根本不可能接纳他的城市里飘荡。“我们”原来是失去家园的永恒漂泊者,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不是“我们”的栖居。
二
究竟该如何安妥这些都市漂泊者们根本无法安妥的身体和灵魂?贾平凹能给他们寻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倘若没有出路,他希望他们如何去面对这没有出路的生命困境?如果说经历现代化不久的中国还无法给出答案,我们是否可以借镜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洗礼的西方社会?早在19世纪,现代城市文明便在欧美各国登陆、蔓延。被舒缓、宁静的农业文明熏染了太久的人们,初次面对这样的庞然怪物时,也感到了无比的震惊。雨果觉出了前所未有的杂沓和轰鸣:“莫名的人流!嘈杂!那些声音、眼睛、脚步/谁也看不见谁,谁也不认识谁/一切都在躁动!城市在我们耳畔嗡鸣/喧闹盖过美洲的森林和嗡嗡蜂房。”(《沉思的爱好》)雪莱则感到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地狱是个很像伦敦的城市/人口众多、烟雾弥漫的城市。”(《彼得钟》)这些经典作家处理城市的方式和态度,成为西方后世的作家看待城市的基本眼光。不过,在喧嚣、罪恶等印象以外,还有一种更杂沓、更矛盾也更辩证、更有力的态度——波德莱尔的“游荡者”的态度。在“游荡者”的眼中和梦里,现代城市文明会有着什么样的片段映现?我们来看看波德莱尔的诗歌《醉酒的拾破烂者》。
随着工业化脚步的加快,“巨大的巴黎”吐出如山的渣滓,拾荒者随之大量滋生。游荡着的波德莱尔注意到了这群在垃圾桶旁徘徊、翻检的人们,他在《醉酒的拾破烂者》中描绘了这样的景象:
古旧的郊区中心,泥泞的迷宫/人烟稠密又拥挤,孕育着暴风/风吹压着火苗,把玻璃罩敲打/在这盏路灯的红色的光亮之下//常见一个捡破烂的,跌跌撞撞/摇头晃脑,像个诗人撞在墙上/毫不理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直把心曲化作宏图倒个干净。
拾荒者贫穷、褴褛、卑贱,像臭虫,像土拨鼠,在巴黎最幽暗、污秽的角落里出没,消化着垃圾,也使自己成为城市的垃圾。但是,卑贱的他们却拥有最神圣的液体——酒精。波德莱尔经常为这一神性液体歌唱。他说,用苦难、汗水和炎炎灼人的阳光酿成的酒,“是帕克多河,耀眼的摇钱树”,不但能让诗人激动万分,灵感不断,产生美好的幻觉,酝酿出的诗歌“如一朵稀世之花向上帝显示”(《酒魂》);还给孤独者以“希望、青春和生命”,赋予他们“高傲,这清贫者珍视的品行”,“就像那天神”(《酒醉的孤独者》);“骑上酒,就像骑着马一样/奔向奇妙的、神圣的天上”(《醉酒的情侣》)。在波德莱尔笔下,酒似乎有了人性,它不会害人,不会把恩情遗忘;它对苦人歌唱充满光明和友爱的歌;它用琼浆玉液温暖着劳累过度的人的喉咙,让生存竞技场上的孱弱的人们筋肉发达。更重要的是,酒精给予拾荒者源源不断的勇气、斗志以及能够与神祗比肩的骄傲,光荣的梦想和抱负更是诞生在酒醉之后。当酒精的微蓝色火焰在血管里一路燃烧、一路狂奔时,拾荒者的生命不再匮乏,而是那么的丰盈,他们的人格不再卑贱,而是那么的高傲,他们醉醺醺的胡话,竟成为生之欢歌、赞歌。于是,他们藐视第二帝国的密探,滔滔不绝地倾吐着胸中的愤懑,欢唱着自己高尚美好的理想:“他发出誓言,口授卓越的法律,/把坏蛋们打翻,把受害者扶起,/他头顶着如华盖高张的苍穹,/陶醉在自己美德的辉煌之中。”这些醉酒的拾荒者竟然是叛逆者,是未来的主人,是颓废的“王”。他们仿佛掌握着巴黎所有的隐秘,甚至命运。他们豪情万丈,他们的生命拥有无限的可能,沉酣的狂舞中,便是地动山摇:
他们又来了,气味如酒桶一般,/跟着一些久战沙场的老伙伴,/小胡子搭拉着像古旧的军旗,/战旗、花饰,还有胜利的弓矢,//在他们面前起立,庄严的魔力!/在号角、阳光、喊杀声和战鼓的/震耳欲聋、光彩夺目的狂欢中/把光荣带给陶醉于爱的民众!
波德莱尔还非常诡异地把拾荒者等底层阶级比喻成浑身泥巴、饥肠辘辘、到处流浪的该隐。在那个遥远的传说中,“亚伯一族,可耻荒唐/利剑斗不过投枪”,而“该隐一族,自登天堂/却把上帝扔到地上”(《亚伯和该隐》),虽然他们必将付出在大地上流离飘荡的代价,但革命的风潮已经蠢蠢欲动了。对于底层阶级的革命潜能的开掘,其实在法国文学中并不鲜见,比如《巴黎圣母院》里的“乞丐王朝”则是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证。
除此之外,波德莱尔更略觉夸饰地把自己也比喻成了醉酒的拾荒者。在写作《醉酒的拾破烂者》的前一年,他在一篇散文中画出这样一幅自画像:
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编纂纵欲的年鉴,描绘垃圾的日积月累。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这些垃圾将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鄂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2]
诗人原来也和拾荒者一样,都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的时候,迈着“踉跄”的步态,怀抱反抗社会的“宏伟意图”,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他在在词、片断和句头组成的废墟中浪游,在荒漠的街道上闲逛,“找到了社会渣滓,并从这种渣滓中繁衍出他们的英雄主人公”(2)。如此说来,自我麻醉和放浪形骸,其实是诗人与污浊的现实世界相对抗的一种方式,一个面具,醉酒的拾荒者成了对于被抛入现代性语境中的诗人的最富戏剧性也最华丽的隐喻——“人加上了酒”,便成了“太阳的圣子”,让上帝都感到悔恨不已。
三
贫穷的拾荒者地位虽卑贱得微不足道,然而一旦用酒精来刺激神经,便振奋得敢于藐视第二帝国的密探,滔滔不绝地倾吐胸中的愤懑,表达自己高尚美好的社会理想,这些醉酒的破烂王显得是那样的豪迈和振奋。巧合的是,《高兴》中的主人公不仅属于穷困的拾荒者阶层,也同样嗜酒成性,因此刘高兴们也就是正在经历着现代化淘洗的中国的“醉酒的拾破烂者”。然而,他们能否像巴黎那群醉醺醺的破烂“王”那样——其实是些“革命的炼金术士”,其实蕴蓄着改天换地的伟力——掌握着凡人们不可能掌握的关于城市命运的秘密?他们具有所谓“革命”的潜能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可以助兴,可以浇愁,可以会友,更是文人灵感的催化剂。但是,这里的酒是贫穷、哀凄、无奈和罪恶的象征。它是麻痹迷失在城市里的拾荒者们灵魂和身体的麻醉剂:穷困潦倒的“我们”喝酒,因为“不喝酒人就愁死啦”;怀乡情笃的“我们”喝酒,因为只有酒才能让人暂时忘却孤独的悲哀;相濡以沫的“我们”喝酒,因为没有比醉酒更好的报答兄弟情义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喝酒就会“放开喝,往醉里喝,往死里喝”,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它更是奸商糊弄农民,敲诈他们劳动力的诱饵,一只装着三斤廉价白酒的塑料桶便一笔勾销了刘高兴们数日来挖地沟的辛苦。它甚至还是扼杀五福生命的刽子手,五福就是因为喝酒过量,脑出血而亡。正是酒让我们惊悚地发现,刘高兴们的社会地位竟是如此的卑微,如此的低贱,如此的尴尬。他们来到城市,求最基本的生存而不得,只能借酒来壮胆,借酒来释怀,借酒来慰藉贫穷的落魄,驱散思乡的情愫。他们无法在神秘液体的助推下,像那些诗仙酒圣一样逸兴遄飞,更无法像骄傲的破烂“王”一样,焕发着眩目的诗情和反叛的蛮力。中国的底层不仅无法呼吸遥远的法兰西的馨香,就是本土的雅文化,与他们也是毫不相干的。
《高兴》明显模仿了《堂·吉诃德》的人物设置、故事模式。刘高兴与五富闯荡西安城,就好比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的行侠游历。堂·吉诃德花言巧语、信誓旦旦地说服桑丘·潘沙追随自己冒险,刘高兴也对五富描画了一片永远抵达不了的“梅林”——只要扎根西安就能挣很多的钱。刘高兴如堂·吉诃德一样,颇有智慧且锄强扶弱。他让五富悄悄地将胶水倒在凳子上,使恃强凌弱的看门人屁股粘着板凳出尽了洋相。他冒充报社干部惩治了企图霸占保姆翠花的雇主,并帮她讨回了被扣压的身份证。他施计教训了专事罚款的市容纠察员和靠乞讨为生的石热闹。他还不顾生命安危拦阻企图肇事逃跑的汽车。除了富有同情心、好打抱不平之外,刘高兴还略通文化,吹得一手好笛子,并且也像吉诃德先生一样多情,把来自乡村,靠卖淫挣钱的孟夷纯看作自己的心上人,一心一意地帮助她摆脱困境,虽然这种帮助就像堂·吉诃德挥动长剑,同风车和羊群决斗一样天真徒劳。五富极像桑丘·潘沙。他们都矮且胖,满脸憨态,外表邋遢,目光短浅,自私狭隘却又忠心耿耿。就是五福跟欺负他的门卫握手时故意用力,让对方吃个闷亏,临走时还多装三根钢筋和一串螺丝帽;将鼻血抹在脸上,配合着刘高兴,帮助翠花讨回身份证;买纸牌送给家属大院的老太太们,博取她们的好感,以便自己到大院里拾垃圾,种种机灵和狡黠,也是桑丘·潘沙式的。不过,堂·吉诃德的高蹈、虚浮和不可救药的乐观,其实洋溢着放眼天下、心系苍生的阔大情怀,流注着中世纪渐渐过去、现代性步步降临时西方世界的幽自己一默的自信,更是对于人性之一翼的最深切的洞观,这一洞观同样是以自信打底的。而高兴扎根城市发家致富的梦想,全然被现代化浪涌推动,是被动得偏执,已经内化了的主动,其眼界是小的,瞻前顾后的。他怎么有资格和那个倔强的浪漫骑士相提并论?就是堂·吉诃德临死前的幡然悔悟,也是高兴无法追摹的。因此,这个经常高瞻远瞩地褒贬时弊,说话饱含哲理的底层“哲人”,只能一边咒骂着城市,一边沉醉在融入城市的幻梦之中,永无醒来的可能。
于是,“我”剩下了最后的武器——高兴。“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要高兴,我就是刘高兴,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我”高兴自己长相贵气,“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福不一样”;我高兴自己精于心算,会耍小聪明;“我”高兴自己能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戏,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却保持干净熨帖;“我”高兴自己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我”还高兴自己会笑对苦难,从不怨怼诅咒,受到轻蔑还能噗嗤一笑:“拾破烂怎么啦,拾破烂就是环保员呀!报纸上市长发表了讲话,说要把西安建大建好,这么大的西安能建好就是做好一切细节。那么,拾破烂就该是一个细节。”高兴哲学原来就是犬儒和自欺,就是哄自己玩儿,就是鲁迅早就痛心疾首的“精神胜利法”,就像阿Q往往从小D们身上获取慰藉和平衡一样。西方看来并无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贾平凹只能如实记录下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经受的独特又充满了痛感的经验。
四
在《高兴》的后记中,贾平凹这样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意图:
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3]
原来,作家只是想写就一份“社会记录”,一份真实客观地描绘了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们命运遭际的记录,留给历史。他无意也无力去揭穿和评判刘高兴们的生存哲学。正因如此,作家才会前后删改五次,将许多情节和冗长的议论文字都删掉,并沿用了《秦腔》中的底层叙述视角,让拾破烂的刘高兴去唠唠叨叨地叙说这一切:“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谈起来痛快的及其夸张变形的虚弱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因为情节和人物及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3]确实如此,《高兴》采用了单线式叙述结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相当简单,只是讲述了刘高兴及其同伴单调到了近乎乏味的拾破烂的生活:寂寞孤独地在兴隆街拾破烂,无人正视地回到池头村的剩楼吃饭睡觉。对此,贾平凹解释道:“原来是沿袭《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同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3]
《高兴》所叙写的,用现在一种通行的说法,就是“乡下人进城”的生活。乡下人进城的叙事,自然不能再继续称之为乡村或者乡土叙事,但是,它是城市叙事吗?一直以来,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基本叙事形态。乡土叙事,是以乡土生活为基础的叙事,它浸透着乡土文化、乡风民俗,以及乡村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等,充盈其间的是作家深厚浓挚的乡情,以及对乡土生活的回忆和重构。乡土叙事是传统精神的体现,城市叙事则是都市文化的表达。然而,如今的乡村生活方式及文化思维正在发生着裂变,乡土和城市的变化在今天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它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其背后隐喻着中国以现代化进程为标志,深刻而全方位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叙事的转型。《秦腔》作为乡土叙事,倾注了作家难以割舍的怀乡情感,但面对现实的他最终也不得不发出:“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的喟叹,《高兴》是对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尝试城市新生活的叙述,其中的人与事,既是城市中的,又游离于城市之外;既是乡下的,又离开了乡土,因此,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叙事,但也不算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叙事,而是一种城市化背景下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痕迹的叙事。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叙述或者说记录的,恰是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的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到文化思想的历史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城市文化为标志的现代生活形态和文化思想,冲击并改变着乡村,乡村及其所承载的乡土文化精神在不断被消蚀,乡村与城市这种二元对立性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在被颠覆,传统乡土叙事也随之被拆解,这就必须重新建构一种与后乡土生活及文化情态相适应的叙事结构,《高兴》正是通过描述都市里一群“醉酒的拾破烂者”,精彩地提供了表达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城市叙事”,其叙事的历史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贾平凹.高兴·后记[J].当代,2007,(5).
[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9:98.
[3]贾平凹.我和刘高兴·后记(一)[J].当代,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