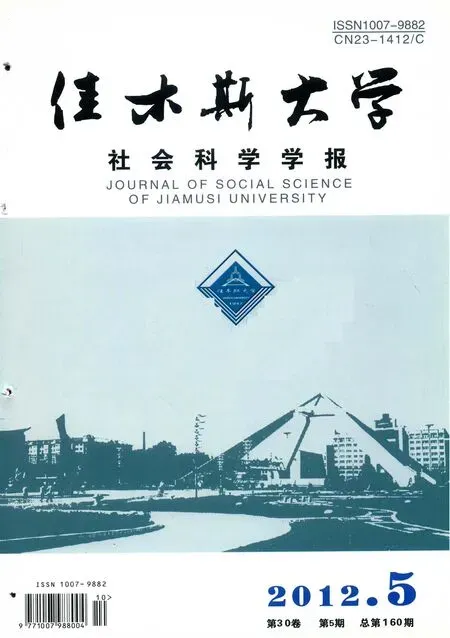浅析刑法中的伪造罪①
2012-04-18李英伟
李英伟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伪造类型犯罪是以行为方式即伪造进行归类的一类犯罪,我国刑法对伪造行为犯罪的规定,根据其侵犯客体的不同,散见于分则不同章节中。但鉴于此类犯罪在犯罪构成特征特别是“伪造行为”这一客观方面行为方式的相似之处,有必要将其加以整理提炼,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里首先界定本文拟讨论的伪造罪的外延,伪造罪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伪造罪指单独以伪造、非法制造为行为方式的类罪,而广义伪造罪的行为方式则不限于伪造,还包括与伪造密切相关的变造以及后续行为如行使、取得、交付、买卖、投入流通、持有、运输等一系列犯罪,我们在狭义上讨论伪造罪。
一、伪造罪的范畴与分类
(一)法定范围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顺序,具体包括的个罪有:
1.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伪造货币罪(第170条),伪造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第174条第2款),伪造金融票证罪(第177条),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第178条第1款),伪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78条第2款),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206条),非法制造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第209条第1款),非法制造发票罪(第209条第2款),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第215条),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伪造有价票证罪(第227条第1款)。
2.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第280条第1款),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第280条第2款),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第280条第3款)。
3.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伪造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375条第1款),伪造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第375条第3款)。
(二)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犯罪划分为若干种类,上述刑法分则按伪造罪行各自侵犯客体的不同,将之分别安排在不同章节中,其实就是一种法定分类。在这里,为了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对伪造罪进行另一种分类,而这种分类标准就是行为对象的不同,据此标准,可以将我国伪造罪概括为四大类:
1.伪造货币罪。这是伪造犯罪中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因此有必要加以专门研究。
2.伪造有价证券罪。本处指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伪造金融票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狭义)、伪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伪造有价票证罪。
3.伪造发票罪。包括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制造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法制造发票罪。
4.伪造文书印章罪。包括伪造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
二、伪造罪的犯罪构成
(一)伪造罪的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利益,按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利益层次的不同,可将之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在伪造罪中,根据其所在章节,可直接确定同类客体,刑法分则第3章和第5章又下设几个小节,这小节归纳的客体可视为同类客体项下的次客体,如伪造货币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次客体则是金融管理秩序,次客体所表述的社会利益较之同类客体又具体、前进了一步。但对于直接客体,由于并无法律具体规定,因而在学理阐述和解读过程中,难免有所分歧,特别是对那些客体较为复杂、抽象的犯罪,更是如此。
依通说,伪造货币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伪造有价证券犯罪客体是国家对有价证券的管理制度,伪造发票类犯罪客体是国家对发票的管理制度,伪造文书印章罪客体主要是国家对文书印章的管理制度和相关机关、单位的正常活动。从上面各类伪造罪所归纳的直接客体来看,都是侵害了国家对某一方面的正常管理制度,但这也只是表层意义上的概述,未触及实质,且有同义反复之嫌。本文既然把伪造犯罪归为一大类,自然要探讨其侵犯社会利益的一般共性内容。在西方,无论刑事立法上,还是理论界都认为伪造类型犯罪所侵犯的是社会的交易安全和公共信用体系。在立法上,如《意大利刑法典》、《法国刑法典》都将伪造类型犯罪集中规定在“妨害公共信用罪”或者“侵犯公共信义罪”章节之下。“货币、文书、有价证券或印章、署名,这些在以经济交易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中,作为证明事实的手段起了重要作用,如危害这种公共信用的真实性,则会危及经济的以及法律的交易安全,引起社会混乱。[1]”正如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所言:“货币、有价证券、度量衡以及文书等四者在日常社会生活与经济交往活动中,均极具重要性,确保此四者之真实无伪,自为社会共同生活上不可缺少之重要生活利益,对于此四者之伪造、变造或行使等行为,均是妨害社会之公共信用,并危及整个交易安全”。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有“货币、有价证券、度量衡与文书等之差别,”但其“行为后果均为公共信用与交易安全之妨害。[2]”由此,本文认为,尽管各种具体伪造罪名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客体,但作为一类犯罪所侵害的共同客体,应认定为社会的交易安全和公共信用体系。它与通说的国家对相应对象的管理制度是表里的关系,国家相应管理制度是表层体现,而其所蕴含和内在体现的深层次内容则是交易安全和公共信用体系。
(二)客观方面
1.伪造。“伪造”一词的含义,我国刑法没有具体解释,而在外国刑法中,有的国家则对之作了明确的立法解释。较有代表性的为《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其第28条规定“伪造,是指使一个东西相似于另一东西,且企图通过这种手段实施欺骗,或者是明知此种做法可能产生欺骗。”对于此条,释义1:就伪造而言,模仿的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释义2:当某人用一个东西仿照另一东西时,此仿照可能会被其用来欺骗,除有相反证明以外,应当假定此人使一个东西相似另一东西,且企图通过这种手段实施欺骗或者应明知此种做法可能产生欺骗而为之,即认定构成伪造行为[3]。从中可以看到,这里的伪造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和本文立论角度一致。对于伪造,学理上还有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之分,前者指文书成立真实性的伪造和“伪造名义”,后者指文书内容真实性的伪造,即行为人伪造文书内容的行为。笔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伪造行为往往同时兼备上述有形与无形伪造两种表现形式,同时有形与无形的具体区分标准,还有不同主张,使得理论研究人为复杂化,因此二者区分并无太大必要。
2.伪造与变造的区别
伪造相关犯罪中,最主要的三种行为样态为伪造、变造、行使,当然其他还包括取得、交付、盗用、运输、持有、减损、买卖等。如果采取广义伪造概念,则后述一系列行为均可包入其中。各国立法例也均是将伪造及变造等犯罪统一加以规定,这里主要对伪造与变造行为加以区分。伪造指无制作权人擅自制造对公共信用和交易安全具有法律意义物品的行为,变造指无权更改对公共信用和交易安全具有法律意义物品之内容的人,擅自对其内容进行更改的行为。变造是在真正文书上进行的更改,伪造一般是凭空制作新的物品,但如果就货币或他人的真正文书、有价证券进行加工改造,由于改造变更的程度与情形不同,究竟属于伪造还是变造,则不能一概而论。就利用真货币造出假币而言,如果对真币的改变在没有损害真币同一性质的限度内,则属于变造,而如果是采取熔解真币的方法,用真币的材料重新制成完全不同货币的时候,那就是伪造而不是变造[4]。就针对真正有效的有价证券进行变更而言,如果这种变更没有失去有价证券前后的一致性,则属于伪造,但如果利用既有的有价证券,变更了它的主要部分,则应认为是制作了全新内容的有价证券,这就超越了变造的范围而成为伪造[4]。就对真正文书进行变更来说,如果变更了原有文书的关键部分,破坏了文书前后内容的一致性,那么尽管形式上只是改变了原有文书的内容,也因改变结果而使其内容失去真实性,故而应认定为伪造,如果变更行为使原有文书的本质或前后一致性并未遭到破坏,则属于变造。[4]
(三)伪造罪的主体
在我国刑法中,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类犯罪主体。关键是单位可以成为哪些犯罪主体,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单位成为犯罪主体须以分则条文和特别刑法明确规定为限。具体而言,伪造货币罪只能是自然人主体,单位不能构成;伪造有价证券4个罪中,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伪造发票3个罪中,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伪造文书印章7个罪中,除伪造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伪造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以外,其余4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四)主观方面
伪造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这一点上学界并无争议,而伪造罪在故意之外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犯罪目的,以及持何种目的,学界则有不同观点。以伪造货币罪为例,通说认为应当具有使伪造的货币进入流通的意图或目的。一般来讲,伪造货币的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但法律并未将此目的作为构成本罪的要件,因此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出于牟利目的,只要伪造货币,并意图使其流通,即构成本罪[5]。我们认为,刑法分则本条以简明罪状方式表述,并未直接规定本罪的目的要件,这就需要根据犯罪构成理论和分则条文的解释原理来对其作出合理解读,不能简单的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认为本罪只须具备犯罪故意即可,不必要求有特定目的。因为“在有些犯罪中,仅从罪过内容和行为性质尚难决定是否构成犯罪,或将此罪与彼罪区别开来,或者为了缩小打击面,因此,有必要规定以某种目的为构成要件。[6]”我国刑法以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作为定罪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惟一根据,而分则具体犯罪构成的规定,则是以此类行为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对于伪造货币行为,如果行为人出于故意实施该行为而没有进一步将其流通、扩散到社会的目的,如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收藏、欣赏或者炫耀自己的复制、仿造技艺,根本不打算将伪造的货币流通,则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或者说不会产生达到动用刑法所要求程度的社会危害,对此也就不能按犯罪处理。综上,伪造货币罪是目的犯,但其目的应限定为意图使其流通,只有此类伪造行为才会对国家货币管理发行制度乃至公共信用和交易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才有必要定罪处罚。同时,这样可缩小打击面,将那些基于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目的而客观上实施伪造的行为排除于犯罪圈之外。另一方面,那种将本罪目的进一步限缩为“营利”“牟取非法利益”等的观点,又会不当的缩小犯罪圈,不利于惩治犯罪的需要,于法无据,因而是不可取的。对于伪造有价证券犯罪,其主观方面除故意之外,应同时具备行使或者意图流通目的,其中的伪造有价票证罪,通说将其目的限定为牟利。对于伪造发票罪和伪造文书印章罪,通说认为主观方面故意即可,至于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不影响该罪的成立。
三、伪造罪的认定
(一)伪造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伪造犯罪,在认定其犯罪既遂的标准上,也有所不同。我国刑法伪造罪大多为行为犯,个别为情节犯。
1.表现为行为犯的伪造罪
以伪造货币罪为例,区分本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行为人的伪造行为是否实际伪造出了足以乱真的假货币。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实际伪造出了足以乱真的假货币,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伪造货币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原因,未能伪造出货币或者伪造出的货币不足以以假乱真,即属于未遂[7]。但同时要注意,本罪虽为行为犯,但作为经济犯罪,一般要考虑数额,如果伪造货币数量很少,即使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也应根据总则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2000年9月1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条规定,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或者币量200张(枚)以上不足3000张(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表明,伪造货币只有达到一定面额或者一定币量,才能构成犯罪,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则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故而对于本罪,不但要正确把握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也要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伪造有价证券犯罪、伪造发票罪、伪造文书印章罪包括的具体个罪均大多为行为犯,其认定既遂与未遂要结合其具体行为对象,参照上述标准来把握。
2.表现为情节犯的伪造罪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伪造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是其适例。情节犯是指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通说认为其最大特点是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只有成立与否即罪与非罪的区分。刑法第215条、375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伪造武装部队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才构成本罪。
(二)罪数形态
由于伪造行为与变造及其后的行使、持有等行为密切相连,实践中行为人也往往同时实施多种犯罪行为,此时就涉及到罪数的认定问题。对于伪造货币罪,如果行为人持有、使用、运输的假币是本人伪造的,则按伪造假币罪一罪从重处罚,后续行为被伪造行为所吸收;如果行为人既伪造了货币,又持有、使用、运输、出售了其他人伪造的另一宗假币,则应按伪造货币罪和有关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同时有伪造、出售两种行为的,也认定为一罪。对于行为人为实施其他犯罪如诈骗而伪造有价证券、文书印章作为方法或手段的,应按牵连犯原则处理。
[1][日] 大谷实.刑法各论(下)[M].东京:成文堂,1982:426.
[2]林山田.刑法特论(中册)[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9:521.
[3]柯良栋,莫纪宏.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5.
[4][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郑树周,译校.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576-603.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09.
[6]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362.
[7]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