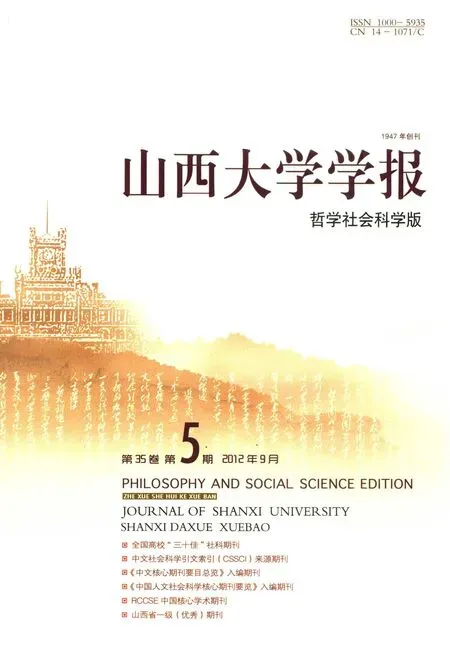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2012-04-13尚永琪
尚永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 130033)
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尚永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 130033)
古代所谓的魔法在内容上是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的一种专门化技艺或手段。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由“大秦幻人”表演的一种幻术就主要传自埃及亚历山大。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更是大量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虽以义学与翻译著称,但他所掌握的魔法或幻术知识相当丰厚,其获得此类知识的源头来自小乘学术体系中所谓的“杂学”。在西域龟兹时,鸠摩罗什就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来预言凶吉;到中原后,鸠摩罗什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他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法术,为我们认识鸠摩罗什与后秦统治者姚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迥异于传世主流僧史文献的说法。
魔法;巫术仪式;幻术;鸠摩罗什;芥子纳须弥
魔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全球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魔法在内容上至少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一种幻术就主要是从埃及亚历山大传来的。由幻术传入的情形亦可以推断,同幻术紧密结合的巫术仪式、医药知识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影响。
幻术及魔法的传播有两个途径,一是随西域诸国家的使者被进贡到中原,二是被传教的僧人带来。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就曾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面,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也不例外。
作为早期中国佛教传播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主要贡献是佛经翻译与中观般若学传播,如果把《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和《佛图澄传》相比较,就会发现,《佛图澄传》中几乎每一段文字都在讲佛图澄使用的幻术、预测等神异手段;但在《鸠摩罗什传》中,鸠摩罗什对于幻术、魔法等神异手段使用的记载就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其在凉州被吕光父子软禁的17年中。正是由于鸠摩罗什很少使用幻术等法术类技艺,因而学界历来不太注意对鸠摩罗什在幻术等神异手段使用方面的考察。事实上,鸠摩罗什所受到的这方面的“杂学”教育,不会比佛图澄更少。
一 对西域幻术东来的简单考索
中国通行的“幻术”不是土生土长的技艺,而是完全的舶来品。《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载:
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
此处所述的唐代幻术主要是在杂戏中表演,是一种娱乐方式,而非宗教手段。西域是中国中古时期幻术的主要传入地,尤其以天竺幻术最为繁盛。按此记载,幻术之初传,始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事实上,西域幻术传入中国,要远早于汉代。
据《金楼子》卷5《志怪篇》十二:
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能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为起中天之台,郑卫奏承云之乐,月月献玉衣,日日荐玉食,幻人犹不肯舍,乃携王至幻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鼻口所纳,皆非人间物也。由是王心厌宫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悦,肆志远游。
周穆王时期中原地区就有了“西极化人”,并且能表演“反山川,移城郭”大型幻术。至于这个“西极”西到了什么地方,至少也到了西域之西。
在《无能子》卷中《纪见》第八有关于秦代幻人表演的记述:
秦市幻人,有能镬膏而溺其手足者,烈
镬不能坏,而幻人笑容焉。
既然称之为“市幻人”,显然,秦代的这个幻人也是通过交换或贸易而来到中原的异域人。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之后,西域及其以西的幻人与幻术的东传,开始有了明确地记载,在从西汉到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一般都认为幻人是“犁靬幻人”。关于“犁靬幻人”的明确文献记载始自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按司马迁的记载,随西汉使者来到长安的幻人是“犁轩人”,他们是被安息国作为贡人献到中原来的。《汉书》卷61《张骞传》沿袭了这一说法:
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
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
《史记》及《汉书》中所说的“犁轩”、“犁靬”,指托勒密埃及王国,是其国都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的音译①参见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余先生指出,《史记大宛列传》的“黎轩”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国……盖黎轩即托勒密埃及王国,距汉遥远,直至前30年(成帝建始三年)沦为罗马行省时,还没来得及为汉人了解,仅知其大致位置而已,而当汉人有可能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已经不复存在,而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原黎轩国既成了大秦国的一部分,来华的黎轩国人又可能自称为大秦人,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合而为一了。。对于此次犁靬幻人东来,唐代杜佑在《通典·边防九》中的记载又有了“犁靬幻人”的数目及其相貌的生动描写:
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
那么,汉武帝时代来到汉都长安的犁靬幻人有二人,他们相貌奇特,是被犁靬的邻国安息作为“贡人”送来,是同“大鸟卵”一样的“奇珍异宝”。
在此后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段里,犁靬幻人一直被西域诸国作为向中原政权示好的“贡人”送到中原来。到东汉,文献中有两次西南夷贡献“幻人”的记载,并且所贡幻人都自言“我海西人也”:
(1)《后汉书》卷86《西南夷.哀牢》: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2)《后汉纪》卷15《孝殇皇帝纪》:
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国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则是大秦也。自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
海西,即是古罗马,那么在两汉时期,正史文献中记载的“幻人”,不论是安息国还是掸国贡献者,都不是该国家的本土人,而是“犁靬人”,即来自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犁靬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因而此后的“犁靬幻人”又称“大秦人”。早期文献谈及“幻人”,一般都认为是“犁靬幻人”,如《金楼子》卷4《立言篇》9下载:
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道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犁靬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若此者也。
此处明确将幻术定为来自犁靬的一种伎术,而“伎术”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册府元龟》卷997《技术》:
夫究技术之妙,所以事于上;通方术之旨,所以济乎物。中古而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蛮貊之邦,禀俊异之气,性识聪悟,讲习精笃。或作为幻戏,或研敫星历,或饵药以养命,或铸金而擅誉,以至留神书画,玩志博弈,莫不萃止中国,盛一时之观听者焉。
这个记载中将幻戏、星历、饵药、铸金这四者都归入技术,并且认为擅长于此类技术者,大多“生蛮貊之邦,禀俊异之气”。显然,幻戏等这些技术与来到中国的异域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除过以上列举的明确认定为是“犁靬人”外,文献记载中也有一些没有标明“幻人”的具体身份,而只是记载了是哪个国家贡献了幻人。如《魏书》卷102《西域传》:“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
文献中明确将善于“幻术”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性文化事象加以记录的,只有两个国家:大秦、条支。《旧唐书》卷221《西域传下·拂菻》载: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俗喜酒,嗜干饼。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毦举,足堕珠玉。
《史记·大宛列传》在记述“条枝”风土民俗时云: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
《前汉孝武皇帝纪》三卷第十二:
至条支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临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鸟卵如瓮。长老传闻条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尝见。
解读这三条文献可知,大秦是“居西海上”的国家,汉代来自安息或掸国的幻人都自言自己是“海西人”,海西是传统记载中一致认为的幻人的真正来源地,而条支不论是“国善眩”还是“出善幻人”,都与其“临西海”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可以推断,条支国的“出善幻人”是受大秦文化的影响所致。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的认识:
第一,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200多年的时段里,不论是从西域陆路来自安息,还是来自西南境外掸国的幻人,都明确记载是犁靬或大秦人。因而,据此可推断,周穆王时期的“西极化人”,在本原上也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人。
第二,从汉武帝到隋唐的近千年时段内,“大秦幻人”在中原表演的典型幻术未发生大的变化,大致是吐火变化、自支解等几个花样,颜师古将之总结为:“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1]卷61,《张骞传》注。《凉州异物志》也有相同的说法:“大秦之国,断首去躯,操钢刀屠人。”[2]卷828,引文这说明通过贡人而来的幻术在中原地区并没有得到扎根传播,而是一直处于不停地“外来表演”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一方面同幻术这种神奇技艺的技术封锁有关,也可能同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政府严格的控制之下,一般百姓很难得到学习机会;更重要的是可能与东西文化差异有关,传统中原文化体系至少在心理上不能接受这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幻术,譬如唐代就有过这方面的禁令,对于西域幻人的“屠人截马之术”,唐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3]卷92,《音乐志二》。
第三,通过“贡人”这个方式输入的西域幻人及幻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娱乐手段传入,可同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相提并论。
二 佛经中的外道幻术与鸠摩罗什的“杂学”知识
虽然中国古代正史文献中将“幻人”列入音乐技术类,但是幻人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精通魔法的巫师及各类宗教人员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幻术同魔法与宗教的亲缘关系,所以西域幻术在东传的过程中,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幻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佛教。
(一)佛经中的外道幻术
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在佛典中,有大量的关于幻师的记录,其中著名的大幻师有跋陀罗、阿夷邹、迦毗罗仙、斫迦罗仙、钵头摩诃萨多。
跋陀罗是王舍城最著名的大幻师,在佛典中又被称作波陀、颰陀、仁贤,生活在释迦牟尼传道的时代,是同大医王耆婆同时代的人。涉及跋陀罗的佛经主要有《大宝积经》、《佛说颰陀神咒经》、《佛说幻士仁贤经》。
据《大宝积经》卷85《授幻师跋陀罗记会》:
时王舍城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一切人民,皆於如来深生尊重,以诸上妙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恭敬供养。於彼城中有一幻师名跋陀罗,善闲异论,工巧咒术,於诸幻师最为上首。摩竭提国,唯除见谛之人及於正信优婆塞优婆夷等,诸余愚人皆被幻惑,无不归信。
由此可知,这个大幻师跋陀罗并不是那种属于音乐或百戏之类的“艺人”,而是同佛陀释迦牟尼一样的宗教性人士,在王舍城一般民众中拥有大批的信徒。他的目的是也要将释迦牟尼征服,所以就装作友善的样子邀请释迦牟尼去享受他的供养。释迦牟尼知道这个外道居心不良,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大幻师跋陀罗就开始运用幻术布置一个试图羞辱释迦牟尼的陷阱:
时彼幻师即於其夜,诣王舍城於最下劣秽恶之处,化作道场宽广平正。缯彩幡盖,种种庄严,散诸花香覆以宝帐。复现八千诸宝行树,其宝树下一一皆有师子之座,无量敷具,悉皆严好,为欲供养诸比丘故。而复化为百味饮食,并现五百给侍之人,服以白衣,饰以严具,作是化已。
当幻师跋陀罗在最肮脏的地方做好这个幻化陷阱准备羞辱佛陀时,“四天王”也以帮助跋陀罗为借口,在跋陀罗施展幻术的这个地方又大使幻法,让这个准备供养佛陀的法会场所更加富丽堂皇,跋陀罗非常吃惊,他发现他的幻术此时已失灵,变出来的幻象不受自己的控制。第二天,佛陀和弟子们都来到跋陀罗的这个供养法会,王舍城的各色人等都来观看,结果什么尴尬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幻象都像真的一样华丽庄严。随后,佛陀以各种幻化的长者之身点化跋陀罗,终于使得跋陀罗认识到佛法无边,深深悔罪,最后心悦诚服地说:“我愿出家作于比丘。”大幻师跋陀罗成为佛陀僧团成员。
跋陀罗皈依佛陀后,并没有放弃他幻术的使用,在遇到有人被蛇咬伤等非常之事时,也想施展自己的魔法咒术,据《佛说玄师颰陀所说神咒经》所载:
闻如是,一时佛游於罗阅祇国中鹦鹉树间,是时,有一异比丘,於竹园去罗阅祇国,适在中间为蛇所啮,复为鬼神所著,复为贼所劫。佛尔时即往到是比丘所,时玄师颰陀随佛俱往。玄师颰陀即白佛言:“我有术甚神,今欲为咒。”佛言:“止!止!颰陀。汝所咒,莫令有伤害。”颰陀白佛言:“后当国国相攻伐,贼贼更相劫。相增者复为相劫,鬼神更劫,毒毒更相害。若有比丘在山中树下坐,被五纳衣若露地坐,四辈弟子当令无有害我者,皆令安隐,无有病痛如是。[4]第21册,《密教部》4
从佛经记载来看,佛陀对于幻术是持贬斥的态度,在《佛说幻士仁贤经》中将跋陀罗的幻术称作“邪行之术”,所以就连皈依后的跋陀罗要运用咒术,佛陀也要制止。但是,咒术的使用在佛教僧侣中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如密教部典籍就充斥着大量的咒术、魔法的东西。即使帝释天(释提桓因)也曾有过向“阿修罗”学习幻术的想法,通过这个故事佛陀告诉他的信徒要“不幻不伪,贤善质直”[4]第2册,《阿含部》下,因而在追求最终智慧解脱的佛陀来看,幻术是一种邪行,是应该杜绝的技艺。
正因为佛陀的这个追求,佛教在其教义内核层面上是排斥幻术的。其实,直至明清时期,佛教思想中对于幻术还是视之为“邪见”的,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6《滦阳消夏录》云:“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汉已有,此盖其相传遗术,非佛氏本法也。”
既然如此,佛教僧侣应该不用幻术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传教的需要,佛陀涅磐后的天竺、西域佛教僧团普遍使用了幻术手段,汉唐之际的佛教文献对天竺幻术的盛行有所记载,如《阿毗达磨俱舍论》之《稽古》卷下:
西域之俗最好幻,亡论於梵志,虽女流亦慑焉。如摩登女之流也,其吞刀吐火则未也,扪日月驱风雨,出没变幻实出意表矣。
日本僧人的这个关于西域梵志、女子娴习幻术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佛经中提及天竺幻师做譬喻,都以“譬如幻师,善知幻术,住四衢道,作诸幻事”开头。可见当时的“幻师”是在“四衢道”这种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做幻化表演,其对于民众的影响力自然是非常大的。
(二)鸠摩罗什的外道幻术知识来源
在佛陀时代就有很多外道幻人成为佛弟子,那么在佛教文献与经典传授体系里,以幻术等为代表的一些神异知识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鸠摩罗什由一个小乘著名学者最终转变为一代大乘高僧,其知识结构中的幻术等神异知识的来源,就值得我们作以追踪。
鸠摩罗什是出身于说一切有部学派的小乘学者,因而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复杂。在他从7岁出家为僧到雀离大寺追随佛图舍尔大师学习经论开始,直到20岁受具足戒的13年学习岁月里,鸠摩罗什先后师事佛图舍弥、盘头达多、佛陀耶舍、须利耶苏摩、卑摩罗叉。现有文献的记载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鸠摩罗什追随这些佛学大师及在其后的自学中所学的主要经典和文献,大概有下列几端:
(1)从7岁到9岁的两年时间里,主要是跟随佛图舍弥大师在雀离大寺学习《毗昙》之学:
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口诵日得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解,无幽不畅。
“毗昙”即“阿毗达磨”,是基本的佛理论证解说技艺。显然,这段时间的鸠摩罗什主要是诵习基本的佛教经典,掌握如何理解和论证佛经义理的最基本方法。
(2)从东晋永和八年(352)到永和十一年(355)的4年时间里,鸠摩罗什在罽宾追随盘头达多大师学习:
什既至,仍师事之。遂诵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达多每与什论议,与推服之。声彻於王,王即请入,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幼稚,言颇不顺,什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服,愧惋无言。[5]卷中,《鸠摩罗什传第一》
盘头达多是著名的有部学者,他对《阿含经》的研究和讲授非常有心得,所以他首先向鸠摩罗什传授了《中阿含经》和《长阿含经》四百万言。
《阿含经》的“阿含”是“辗转传说之教法”的意思,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一般认为,《阿含经》的内容在佛教第一次结集时已经确定,至部派佛教形成前后被系统整理出来,公元前1世纪被写成文字,主要是论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善恶因果报应等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各部派所传的《阿含经》不尽相同,如南传佛教有“五阿含”、北传佛教有“四阿含”。《中阿含经》是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最初结集的四部经藏之一。这四部经依文字长短和内容特点,分别成为《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
鸠摩罗什学习了《中阿含》和《长阿含》,并且能让与他辩论的外道折服,那么他对于外道知识也肯定会有丰富的掌握①如鸠摩罗什的中原弟子道融同挑战的婆罗门僧论难,最关键获胜之处就在他对婆罗门文献目录的掌握,可见,同外道论难,对于外道所读经典必须有一定了解和掌握。,否则无法折服外道,外道知识中是否包含神异知识,如幻术等,也未可知。
(3)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到疏勒国,在须利耶苏摩的影响下,由一个小乘学者转变为大乘高僧。须利耶苏摩对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就是成功地扭转了罗什的小乘思想,并引导他深入研究了《方等经》,是否有其他“杂学”知识的传授,不是非常清楚。此后,鸠摩罗什回到龟兹,跟卑摩罗叉学习律学,而佛陀耶舍对鸠摩罗什的影响也主要是在大乘思想方面。
(4)在疏勒国,鸠摩罗什不但通读了大量的佛学论著,而且还自学了大量的外道文献:
什进到沙勒国……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于十门修智诸品无所咨受,而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问无所滞碍。
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吠)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后心,未尝介意。
疏勒国流行的主要是小乘教派,并且这里的人民似乎有着保存各类书籍、器物的热情,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书籍,罗什一面讲经,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知识。
显然,鸠摩罗什在疏勒读过的书籍,并不仅仅限于佛学著作,尤其是对一些所谓的“外道”的经典书籍的阅读学习,奠定了他庞杂的知识结构,这些知识可能就是他所掌握的“幻术”等神异知识的主要源头之一。
首先是同理解佛教经典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经论”,通过学习“经论”,他熟练地掌握了文辞制作和如何应对辩论问答等技巧。
其次是对《四吠陀》及《五明论》的学习。《四吠陀》是婆罗门教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经典,由《梨俱吠陀》、《裟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等四部组成,蕴含丰富的神学思想,包括了语音、语法、词源、韵律、天文、占星、医学、音乐、舞蹈、军事、建筑等方面的知识。《五明论》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声明(语言、文字之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历算等技艺)、医方明(药石、针灸、禁咒等治疗之学)、因明(逻辑学)、内明(即佛教自宗之学),这些是一个佛教僧人在传教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知识,它们既有利于帮助修道者理解经典,更有利于运用这些知识为民众服务,从而展开传教。
其三,鸠摩罗什还阅览了大量阴阳星算等方面的经典,这一部分可以称为“杂学”。学习这些知识,一方面巩固了鸠摩罗什所学到的医学、星占等知识,一方面也使得他在星算占卜等这些技艺上有了更加广阔的知识积累。据说当时人们请他算卦预言,他不但能预示吉凶变化,还能很准确地预料到事情的发生趋势和发展结果。
综上可知,从佛图舌弥到盘头达多、佛陀耶舍、须利耶苏摩、佛陀耶舍直至卑摩罗叉,所传授的知识里面肯定也包含了一些幻术等神异内容,但是鸠摩罗什在这方面的知识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其在疏勒国时对外道文献的学习。
三 鸠摩罗什在凉州所使用的幻术等神异技术
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的时候,也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如说他“妙达吉凶,言若符契”[6]卷2《鸠摩罗什》,这说明他在龟兹的时候就以善于预言吉凶而闻名。
到中原后,鸠摩罗什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较多,这些事例在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慧皎《高僧传》中都有记载。但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的时候也曾有过两例神异手段的使用,一是“纳镜于瓶”,一是“吞针”,后者在《晋书》有记载,而前者不见于早期文献,在敦煌卷子中有这方面的记载。
(一)鸠摩罗什使用过的幻术种类
下面我们先对鸠摩罗什在凉州17年中所使用的神异手段作一考察。
385年,鸠摩罗什被吕光掳掠东向中原,在吕光率军东归的途中,中原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建元二十一年(385)七月,在与东晋大军的淝水决战中,前秦王苻坚亲率的90余万大军被谢石、谢玄统帅的东晋军队打败,苻坚被擒。同年八月,苻坚被后秦王姚苌缢杀。九月,吕光的军队到达姑臧,听到了苻坚兵败被杀的消息之后,吕光一方面三军缟素,哀悼苻坚,一方面兵驻姑臧,自称凉州牧。到386年十月,正式在姑臧建立地方政权,建号太安,史称后凉。
鸠摩罗什在后凉京城姑臧施展的神异手段可以归纳为五类:相地、望风、预言、幻术、祥瑞。
(1)相地是对地理形势的判断,通过观察地理条件来决断人事,此事例发生在鸠摩罗什随吕光大军东行中原的途中:
光还中路,置军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徒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
这样的判断能力应该说算不上什么神异之术,但是能将地势判断与气象预测结合在一起,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尤其是在并不熟悉当地环境的情况下,这样的判断自然略显神异。也正是因为这次建议,吕光才对鸠摩罗什“密而异之”,一改对鸠摩罗什轻视、戏弄的态度。
抵达凉州后,由于吕光父子并不信佛,所以鸠摩罗什只能充当一个政治顾问的角色,通过他掌握的一些杂学知识来取得吕光父子的保护。
(2)望风跟观云一样,是一种古老的判断凶吉、预言人事的法术:
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梁谦、彭晃相系而叛,寻皆殄灭。
古代社会控制能力极差,一旦有自然灾害,动乱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姑臧地处沙缘,自然生态环境尤其薄弱,再加上吕光当政残暴不仁又刚愎自用,一贯赖于武力而无丝毫文治之策,手下的那些大将和凉州地区的土霸王们发动的叛乱时有发生,如386至389三年内就有张大豫、李隰、康宁、彭晃等叛乱,因而,鸠摩罗什根据姑臧一场大风就预言有叛乱,在事理上有其可以实施推断的必然逻辑。
不过,对于风的观察,其实也是术数之主要门径。在佛教经典中,对于风有各种分类,如佛经中对福地、宝地的描绘中有“香风”、“凉风”,而恶地、凶地则有“恶风”、“热风”、“暴风”。如《长阿含经》云:“阿耨达池侧皆有园观浴池,众花积聚。种种树叶,花果繁茂。种种香风,芬馥四布。”“阎浮提所有诸龙,皆被热风,热沙著身,烧其皮肉,及烧骨髓以为苦恼。唯阿耨达龙无有此患。阎浮提所有龙宫,恶风暴起,吹其宫内,失宝饰衣。龙身自现以为苦恼。”[4]第1册,《阿含部》上此外,尚有“寒风”“大黑风”、“随岚风”等名目,如《增壹阿含经》卷17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日空中有随岚风,设复有飞鸟至彼者,若鸟、鹊、鸿、鹄值彼风者,头脑、羽翼各在一处。”[4]第2册,《阿含部》下
由此可以判断,鸠摩罗什望风的这些知识应该来自佛教经典。
(3)预测术其实是一种综合性判断技艺,其准确与否同预测者事前所掌握的信息完备程度和经验有关,鸠摩罗什对于后凉的军事行动作过一些预测:
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梨。
后凉龙飞二年(397),张掖卢水胡人沮渠男成与从弟沮渠蒙逊起兵对抗后凉政权,并公推京兆人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在张掖(今甘肃张掖市)建立了历史上称为北凉的地方政权。吕光派遣庶子吕纂率五万精兵前往征讨,当时吕光的谋士、将军们都认为段业、沮渠蒙逊都只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没能力同吕纂的五万大军相抗衡。只有鸠摩罗什认为“观察此行,未见其利”,吕光没有听从罗什的建议,结果吕纂吃了败仗。
这种出兵打仗的事,如果事先对形势与双方的力量有所了解的话,还是能做出一些正确的事前判断来的。不过我们对勘《晋书》中的相关记载,证明罗什的这个预言并不那么准确,吕纂出兵平定沮渠氏叛乱,还是胜多于败的,至少罗什预言的397年的这次吕纂出兵征讨沮渠蒙逊,是取得了胜利的。吕纂与沮渠蒙逊战于匆谷(今甘肃省山丹县境内),结果蒙逊大败,引随从六七人逃往山中。
(4)烧绳成灰的还原幻术:
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系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而又治无效,少日资亡。
此为早期文献记载中鸠摩罗什所施展的最典型的幻术。
(5)祥瑞是通过某种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出现的现象预测即将发生的大事之成败凶吉,而谶言则是通过提前形成某种说辞以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鸠摩罗什在这方面有两个事例:
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什奏曰:“皆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棋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
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
以上5个方面,是《出三藏记集》、《高僧传》这两部时代较早而相对可靠的僧史文献中关于鸠摩罗什在凉州时期施展幻术等神异能力的所有事例。如果我们将之同著名的“神僧”相比,就会发现鸠摩罗什使用神异手段有其比较特殊的时代背景。
(二)鸠摩罗什本人对使用幻术的态度
在鸠摩罗什之前的时代,使用幻术等神异手段最多、声誉最著的是同样来自龟兹的后赵高僧佛图澄:
(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劾验。[6]卷9,《佛图澄》
《高僧传》中有佛图澄使用幻术、预测术及神秘医术的很多事例,但是最为主要的正是上面所概括的三点:(1)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2)能“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3)能“听铃音以言事”,即通过钟声来预测或判断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事情的凶吉与结果。
对于佛图澄的神化,可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添加放大的过程,如《后赵中书太原王度奏议序》云:“佛图澄者,得圣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灯炬之照。瞻铃映掌。坐观成败之仪。两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4]第52册,《史传部》4其中就比《高僧传》多出了“乳孔流光,不假灯炬之照”这种对佛图澄身体作神化的说辞,到了《晋书》中就成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佛图澄)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7]卷95,《佛图澄》
显然,像佛图澄这样一个从自己的身体机能到道术方面都充满神异的僧人,他使用幻术等神异手段就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鸠摩罗什则不同,鸠摩罗什在西域时,之所以能“声满葱左,誉宣河外”,主要原因在于他“广说诸经,四远宗仰,莫之能抗”[6]。这一点是鸠摩罗什作为一个义学高僧同佛图澄“神僧”的差别。
《高僧传》中鸠摩罗什的出场是被安排在记诵佛经“日诵千偈……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6]的这种知识接受与理解方面的“神俊”语境中的,因而他的整个形象的构建是基于“佛理”和“义学”这样的知识论层面的。
如果将鸠摩罗什和佛图澄东来传播佛教的趋向做个比较的话,佛图澄主要是基于“教”的方向,因而需要施展更多的幻术等神异手段来网罗信众,因而他也大量地建寺修庙①《高僧传》卷9《佛图澄》载:“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史传部》4《北山录》卷8亦云:“佛图澄建八百九十余所寺。洎天台三十有五。吾今不能兴弘一二。”僧史记载中佛图澄自言立佛寺893所,后代亦以此为据,但是这个数目,大概也跟佛图澄所说的自己弃家入道190年的说法一样,乃夸饰之词。不过从当时“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的情况可以断定,佛图澄所兴建寺庙应该不少。;鸠摩罗什主要致力于“学”的方向,因而他主要是翻译经典、教授学生,对于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是出于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一种无奈。
对鸠摩罗什神异手段的使用,要注意到三方面的情况,首先是他本人对幻术等神异手段极不认同②王铁钧先生指出:“鸠摩罗什认为指望借助神秘力量,如咒术一类得道升天,实乃修行误区,是为逃避艰苦修行之天真想法。”参见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如在《注维摩诘经》中他对维摩诘“降服众魔,游戏神通”的解释是:“神通变化是为游引物,于我非真,故名戏也;复次神通虽大,能者易之,于我无难,犹如戏也。亦云神通中善能入住出,自在无碍。”僧肇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为“游通化人,以之自娱”[4]第38册,《经疏部》6,这就把鸠摩罗什对神异变幻当做小游戏、小手段的认识说得清清楚楚;其次是他同佛陀跋陀罗的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佛陀跋陀罗运用了此类手段;第三是鸠摩罗什所处的位置和角色不需要太多的神异手段。另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鸠摩罗什来到中原地区是被武力劫持而来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个人的意愿,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醉心于理论探讨和新知识追求的鸠摩罗什,对于佛教之传播、信众之多寡,没有过多的激情,因而,一旦成为后秦政权支持的译场主持人,他就致力于佛经翻译与经义探讨,对于传教的辅助手段如“幻术”等神异技术,就基本上弃而不用了。
四 从“芥子纳须弥”的法门到“纳镜于瓶”的幻术
现有的记载中,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后使用的幻术手段有两端,一是“纳镜于瓶”,一是“吞针”,这两个幻术手段的使用,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前者是因为后秦国王姚兴不相信新译的《维摩经不思议品》中“芥子纳须弥”的法门;后者是因为僧团成员对鸠摩罗什破戒娶妻不满而引致。
可以说,鸠摩罗什是在传教与生存的生死转折关头迫不得已施展了这两个幻术法门。这样关键的事件,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都没有记载,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一)鸠摩罗什“纳镜于瓶”幻术之经义内涵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敦煌文献的有关记载来对此作一些探讨。
从传教的需要来看,鸠摩罗什真正用来验证佛理和折服信众的神异手段就是“纳镜于瓶”这个幻术的使用。对于此幻术,《晋书》等正史及《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早期佛教文献都没有记载,但是在敦煌卷子中有关于鸠摩罗什施展这种幻术的3个文本。
(1)拟题名为《鸠摩罗什别传》的 S.381号卷子,全文如下:
后秦鸠摩罗什法师者,其【祖】父本罽宾国辅相,到子鸠摩罗炎,厌世苦学,志求出俗。辞主东迈,至龟兹国。龟兹国王妹体有赤厌(黶),法生智子。诸国聘之,悉皆不许。一见炎至,遂即妻之。炎乃问辞,事免而纳。不逾岁月,便觉有胎。异梦呈休,母加听辩。后生什已,其辩还亡。母因出家,便得初果。年至七岁,日诵万言。母携寻师,还至辅国。便学经论,屡折邪宗,大小诸师,莫不钦伏。罽宾国王重加礼遇,凡是僧徒,莫敢居止。概乎进且志在传通,辞母东来,却至舅国。遭侣(吕)光之难,碍留数年。一一行由,事广不述。年三十五,方达秦中。什处欲来,嘉瑞先现。逍遥一园,葱变成薤。后什公至,即于此园立草堂寺,同译经律。后因译《维摩经不思议品》,闻芥子纳须弥。秦主怀疑,什将证信。以镜纳于瓶内,大小无伤。什谓帝曰:“罗什凡僧,尚纳镜于瓶内,况维摩大士,芥子纳须弥而不得者乎?”帝乃深信,顶谢希奇。
此《别传》的前面大半部分对于鸠摩罗什生平事迹的叙述,同《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吻合,所不同者是最后这几句:
后因译《维摩经不思议品》,闻芥子纳须弥。秦主怀疑,什将证信。以镜纳于瓶内,大小无伤。什谓帝曰:“罗什凡僧,尚纳镜于瓶内,况维摩大士,芥子纳须弥而不得者乎?”帝乃深信,顶谢希奇。
显然,鸠摩罗什把体积大于瓶口的镜子放进澡罐或净瓶,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移物幻术,也正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幻术所产生的效果,才使姚兴相信了《维摩诘经》中所说的“芥子纳须弥”的法门之真实不虚。
鸠摩罗什翻译《维摩经》在东晋义熙二年(406),此次译事之缘起始末,罗什弟子僧肇法师《注维摩诘经序》有详尽记载:
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独悟。弘至治於万机之上,扬道化於千载之下。每寻玩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滞於文,常惧玄宗坠於译人。北天之运,运通有在也。
以弘始八年岁次鹑火,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於兹显然。余以闇短,时豫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而为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庶将来君子异世同闻焉。[4]第55册,《目录部》
此次翻译《维摩诘经》,由后秦国主姚兴发起,他之所以命令常山公、安成侯等王公贵族与1200多僧人协助鸠摩罗什翻译《维摩诘经》,原因在于他对支谦、竺法护的旧译不满意,觉得译者没有把《维摩诘经》的真正玄义表达出来。既然姚兴有“常惧玄宗坠於译人”的心态,那么对于鸠摩罗什的此次翻译也不会完全放心。可以认为,僧肇所说的在翻译过程中的“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一定包含着姚兴本人对翻译出来的经文之质疑与探讨。
因而,姚兴对于《维摩诘经不思议品》中“芥子纳须弥”的这种无法用常理来理解的说法提出质疑,也就情在理中了。关于《维摩诘经不思议品》中“芥子纳须弥”之说,在三国时支谦的译本中是这样表达的:
维摩诘言,唯然,舍利弗。诸如来诸菩萨有八不思议门,得知此门者,以须弥之高广入芥子中,无所增减。因现仪式,使四天王与忉利天不知谁内我著此。而异人者见须弥入芥子,是为入不思议疆界之门也。[4]第14册,《经集部》
而鸠摩罗什译本则为: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将这两段文字加以对比,就发现支谦对于“须弥之高广纳芥子中”的解释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其中的“因现仪式”显然是不知所云的译语,“异人”一词所指不明,“忉利天不知谁内我著此”更是偏离经文原意甚远。鸠摩罗什将“应度者”同“诸天”之觉分开,翻译出了虽然诸天不觉“须弥入芥子”,而“应度者”乃见此不可思议解脱门,这就将“芥子纳须弥”之说解释的清楚明晰。
在支谦译本的基础上是无法讨论“芥子纳须弥”的,因为支译中涉及的所有主客体都是所指不明、彼此难分,“使四天王与忉利天不知谁内我著此”这句完全是一句错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鸠摩罗什译出“须弥入芥子中”后才引起姚兴的质疑。
鸠摩罗什对此法门的解释是:
须弥,地之精也,此地大也。下说水、火、风、地,其四大也。惑者谓四大有神,亦云最大,亦云有常。今制以道力,明不神也;内之纤芥,明不大也。巨细相容,物无定体,明不常也。此皆反其所封,拔其幽滞,以去其常习,令归宗有涂焉。[4]第38册,《经疏部》6
显然,这是用一种极端的逆向思维方式来破除“幽滞”的一种法门,将须弥这个最精最大纳入芥子之中,是要开示“物无定体”这样一个“不常”大道。庐山释慧远对“芥子纳须弥”所做的解释是:
一大小自在,须弥入芥;二广狭自在,海入毛孔;三身力自在,亦得名为运转自在。[4]第38册,《经疏部》6
这样一个很明显带有“譬喻”性质的启发性论题,不知道姚兴何以会将之具体化,一定要追究“芥子纳须弥”的实际可能性?
(二)“纳镜于瓶”幻术使用的知识背景分析
如果敦煌文献的这个记载确实可信的话,那么可以推断,当时的后秦国王姚兴虽然孜孜于佛理探讨,但是其理论水平还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鸠摩罗什不得不用“纳镜于瓶”这样一个幻术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实际可能性。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高僧传》、《出三藏记集》没有这个“纳镜于瓶”的记载了,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其间相差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
虽然如此,对于鸠摩罗什“纳镜于瓶”的幻术,在敦煌文献中尚有释金髻所作《罗什法师赞》两首。
(1)释金髻所撰《罗什法师赞》,敦煌卷子中有S.6631、P.4597、P.2680,其文如下:
善哉童受,母腹标奇。
四果玄记,三十辟交。
吕氏起慢,五凉运衰。
秦帝生信,示合昌弥。
草堂青眼,葱岭白眉。
瓶藏一镜,针吞数匙。
生肇受叶,融睿为资。
四方游化,两国人师。
(2)释金髻所撰《罗什法师赞》复诗,敦煌卷子中有 S.6631、P.4597、P.2680,其文如下:
诞迹本西方,利化游东国。
毗赞士三千,抠衣四圣德。
内镜操瓶里,洗涤秦王或。
吞针糜钵中,机诫弟子色。
传译草堂居,避地葱山侧。
驰誉五百年,垂范西方则。
释金髻的这两首赞诗,与前引S.381卷子《鸠摩罗什别传》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说在隋唐及其后的僧界,鸠摩罗什“纳镜于瓶”和“吞针”的说法在僧界是比较流行的。
释金髻“内镜操(澡)瓶里,洗涤秦王或(惑)。吞针糜钵中,机诫弟子色”的总结确实非常精炼,此处需要补充说明,关于鸠摩罗什“吞针”的记载。
“吞针”这个幻术类法术的表演,在《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中没记载,但是唐人所修《晋书》却作了生动的记述:
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正如释金髻所言,罗什法师之所以施展“吞针”幻术,目的就在于“机诫弟子色”,这是罗什破戒后为了维护长安僧团,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却以罗什向受业弟子的“检讨”来维护僧团:
姚主尝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房,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华,但采莲华勿取臭泥也。”
对比《晋书》与《出三藏记集》中的这两段文献,后人无法判断哪个记载更接近真实。
对于高僧事迹的记述,佛教史家、僧界流传与官方正史的记述选择的出发点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差距,我们从《高僧传》、《出三藏记集》、敦煌卷子和《晋书》关于“内镜操瓶里,洗涤秦王或。吞针糜钵中,机诫弟子色”这些幻术的遮蔽或不同记载,考察鸠摩罗什对于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鸠摩罗什东来传教作比较深入的理解。
佛教在中原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对于僧人的神化描写及传教僧人对于神异手段的使用,同佛学义理的探讨呈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讲,可以将这种趋势分作三个阶段:
(1)在佛教传播的早期阶段,由于经典翻译的不充分,所以幻术等神异手段被外来传教僧人大量使用,佛图澄即是一个典型代表。
(2)随着鸠摩罗什对佛经的大规模准确翻译,对于佛学义理的探讨在僧团与上层文化圈中兴盛起来,神异手段相对淡化。
(3)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对于经典的解释已经固化,僧人集团的神化趋势再次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大量的灵验记的产生及对于传教僧人的神化崇拜迅速形成趋势。
以上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同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密切相关。确切说,鸠摩罗什对佛经的准确翻译和对学问僧的培养,正好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宋)李 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大正新修大藏经[M].中国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5](梁)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梁)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贾发义)
Magic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Kumarajiva's Missionary Work
SHANG Yong-qi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chun130033,China)
Ancient magic is in content a specialized skill or means which is mixed with witchcraft ceremony,medical knowledge,magic and other factors.The general magic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is of bo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factors.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magic in the most fantastic“phantom”mainly came from Alexander of Egypt.Magic was often used for religious propagators to recruit followers.In the early Sangha of Shakya Muni,some members were the famous“phantom division”.In the medieval,missionary monk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especially used a lot more magic means to attract congregations,among their knowledge systems,magic occupied quite a large proportion.Although Kumarajiva was known for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but he had good command of magic or sorcery knowledge which came from the Hinayana academic system of so-called“variety knowledge”.When he was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Kucha,Kumarajiva used some magical means to predict fierce and auspicious;after he came to the Central Plains,the magic and magical means were used mainly when he stayed in Liangzhou for 17 years.Dunhuang documents recorded that Kumarajiva once used“Mirror in the bottle ”to verify the magicartds of“Mustard Nasu A”,which provides a quite different statement from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n the monk histor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o Xing,the later Qin ruler and Kumarajiva .
magic;witchcraft ceremony;illusion;Kumarajiva;Mustard Nasu A
B929
A
1000-5935(2012)05-0024-11
2012-03-16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汉唐时期来华西域胡僧研究”(10BZS011)
尚永琪(1969-),男,甘肃张掖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北朝佛教与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