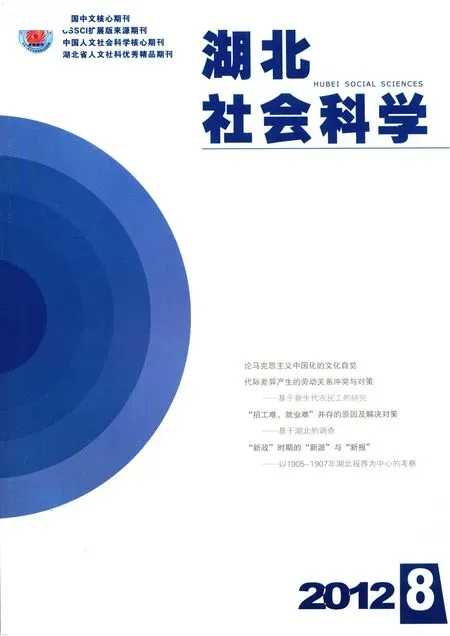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二维性探析
2012-04-12汪丽丽
汪丽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二维性探析
汪丽丽1,2
(1.山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意思自治原则加以重点规定,一方面大量扩张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又通过“直接适用的法”、弱者利益保护等原则对其加以限制,充分体现其二维性。这种二维性的价值根源正是当代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所致。然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继承法》中相关条文的协调问题、“直接适用的法”总括性规定问题以及具体把握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增加了意思自治原则二维性实现的困难。
意思自治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二维性
作为法律选择方法的意思自治原则,被认为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冲突法领域的延伸,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 《法律适用法》)明确规定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的有15处,既有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也有直接适用法的运用,充分彰显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与限制的二维属性。
一、《法律适用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二维性的介评
作为软化传统国际私法上僵硬冲突规则的有效手段之一,意思自治原则具备有效地调和法律选择中的灵活性和确定性、使私法主体得以平等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司法效率[1]等作用,在当代国际私法舞台上可谓是长袖善舞,自从1989年 《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继承、婚姻家庭等领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国相继跟行。现代国际私法上有关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已经随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阶段,其扩张与限制的二维性更加显现。
《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突出地位,从第一章的宣誓性条款,到第七章的知识产权(除了第四章继承),几乎每章都有意思自治原则的身影。
(一)《法律适用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
1.确定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总则性地位。
《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总则性地位,为意思自治原则在具体涉外民事关系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2.具体适用范围的扩张。
(1)代理关系中的运用。
对于代理关系的法律适用,通常区分代理种类与内外部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基于此,《法律适用法》第16条将契约自由原则运用于“委托代理”关系之中,不仅弥补了中国有关涉外代理关系法律适用的空白状态,同时在委托代理中运用意思自治原则充分体现当事人自主意思。
(2)信托关系中的运用。
在信托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日益成为趋势,根据1986年海牙 《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第6条规定,信托适用财产授予人明示或默示选择的法律。这种被选择的法律用来解决信托的有效性、解释、效力和管理。公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相对较少。但如果被选择的法律制度没有信托概念,可以不考虑当事人的这种选择。同时,如果适用选择的法律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或涉及法院地或某些情况下的其他国家的强行法,也可以不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2](p438)就此而言,即使在信托这种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仍然通过公共秩序、强行法等对意思自治加以限制。而《法律适用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表明我国借鉴国外信托法律适用的经验,为涉外信托业发展提供了法律适用依据,但同时也说明我国法律与《海牙公约》的规定相比仍存有差距。
(3)夫妻财产关系中的运用。
对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杜摩兰早在1525年就主张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将夫妻关系看成夫妻间的合同关系。许多西方国家采用这一做法,如瑞士、德国、奥地利、法国等,位于东方的土耳其、泰国等国家进一步在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问题上采纳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3](p141)但是,对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采取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有限制的,如1978年《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公约》把当事人选择的法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一般只支配夫妻财产契约实质有效性和效力,不支配它的形式有效性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2](p435)《法律适用法》第24条作为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将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确定夫妻财产关系准据法的首选原则,充分反应了目前我国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新发展,与国内婚姻法的规定相吻合。并且根据本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经常居所地法、国籍国法和主要财产所在地法中进行选择,给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自由,并没有体现法院地法的扩张适用,据此可知公正价值在本法中的充分体现。
(4)在离婚关系中的适用。
有关离婚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主要是荷兰于1981年的《国际离婚法》里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离婚的准据法。该法第1条规定:“配偶双方当事人就离婚的准据法问题,既可以协议选择适用荷兰法,也可以选择适用其共同的属人法。但是,如果配偶一方当事人依第1款第1项:婚姻的人身效力依夫妻双方所属国家的法律或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最后所属国家的法律。与其共同的本国法缺乏有效的密切联系时,则不能适用配偶双方共同的本国法。”[4](p567)由于荷兰以有利于离婚为理念,允许配偶双方自由离婚,故当事人很可能选择法院地法。因此,如果当事人的国籍国法拒绝离婚,配偶双方就倾向于选择适用荷兰法。[2](p435)《法律适用法》第26条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关于协议离婚法律适用的空白,并且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法律关系的分类越来越明晰,冲突规范中的分类与分段式方法运用的日趋成熟,已然不再局限于合同关系领域。
(5)物权关系中的运用。
物权领域引入意思自治原则,打破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物之所在地法一统天下的格局,当然在物权领域中“物之所在地法”仍是主要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仅限于与债权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主要集中于动产物权。如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8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运送中有体财产的物权的取得或丧失,适用支配法律交易并调整该物权创设或消灭的法律。当事人双方的此种法律选择对第三人无对抗力。德国1999年关于物权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也采用了意思自治原则。《法律适用法》第37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第3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输目的地法律。这些规定充分应合了目前国际上有关物权领域准据法适用的新形势。
(6)侵权领域中的适用。
第一,侵权行为发生后一般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
《法律适用法》第44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该规定既继承了《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同时扬弃了过去双重可诉原则的适用,将国际私法领域中有关侵权法律适用的新发展融入其中,并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时间加以规定。
现代国际私法上将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领域里的适用推到一个新的起点当属德国:1999年 《德国民法实施法》第42条规定:“产生非合同之债的事实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该债务的法律;第三人的权利不受影响。”[5](p242)而德国的非合同之债是指侵权之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故意思自治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之债中。
第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立法者运用了无条件选择式的冲突规范,《法律适用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但这种法律适用难免会落入扩张适用法院地法之嫌。
(7)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中的运用。
《法律适用法》第47条通过选择性冲突规范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准据法的确定中,并且作为首要确定方法,充分证明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地位,不仅填补了我国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法律适用的空白,同时还领先于国际。
(8)知识产权转让与许可中的运用。
知识产权拥有财产权的特征,其转让与许可使用与其他财产权的转让拥有同样的特性,故在知识产权的转让与许可中运用意思自治原则符合了合同自由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9条的规定正是契合了这种精神,与本法第41条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相吻合。
(9)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符合仲裁的任意性特征。
中国《法律适用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大规模扩张与现代国际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新发展相契合,既应合了国际私法的全球化趋势,同时不失其自身特性,如在一般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中,既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又对其选择时间加以限制,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二维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1.保护弱者的理念渗透到《法律适用法》中。
契约自由正日益成为强者的工具,借契约自由之名行强权之实,如各种标准化、格式化合同的运用往往造成对弱者的伤害,故法律应向弱者倾斜,以彰显法律的实质正义。
私法上的保护弱者,是指法律不是借助抽象人格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一体保护,而是根据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界定其居于弱者地位,再由法律予以特殊或倾斜性的保护。[6](p149)而国际私法层面上的“弱者”是指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7](p85)保护弱者利益是国际私法追求实质正义、国际私法人文关怀的体现[6](p148)。各国国际私法在扩张意思自治原则适用领域的同时,保护弱者的理念也渗透到冲突法中,如消费者合同、雇用合同等的法律适用规则对当事人的意思有一定的限制,朝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受雇人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也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我国作为新型法治国家,公平与正义是我国社会的本质体现,对弱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突出,《法律适用法》对此显有成就,第42条消费者合同和第45条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定,都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允许弱势一方选择适用法律,对意思自治的适用做出一定限制。本法对于弱者的保护远不止这两条规定(如第29条有关扶养关系的法律适用,第30条有关监护关系的法律适用,第43条有关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等),但是运用“有利弱者”原则来限制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主要表现在此。《法律适用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说明我国国际私法已经从传统冲突法的形式正义迈向实质正义阶段。
2.直接适用的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直接限制。
自从弗朗西斯卡基斯提出“直接适用的法”的概念,现代学者不但接受了此观点,而且提出不同的理论和名称,如警察法、必须适用的法、公共秩序法、国际公共秩序法、排他性规范、特定的硬性规范、地域限制性规范和自我限制性规范等[8](p196)。这些观点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得以体现,如美国法院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保护消费者免受法律选择条款伤害的方法:如果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违反《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187条第2款规定的根本性公共政策,就可以否定其效力。[2](p421)通常,这种强行性规范与一国的社会经济利益有重大关联。《法律适用法》第4条明确规定:中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纵观《法律适用法》,有关限制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强制性规定并没有多少体现。
综上所述,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有关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既与现代国际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相吻合,同时又有其特有的二维性。
二、《法律适用法》上意思自治原则二维性价值根源
《法律适用法》一方面大量扩张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多角度限制,这种二维性的价值根源值得深思。
(一)意思自治原则扩张适用的社会根源:个体利益发展、民主发展。
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9](p187-188)。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也逐渐接受了自由与民主的观念,对于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以及国家对其重视度都较前大有发展。
在自由主义看来,其根本价值在于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10](p25),如在夫妻财产领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约定财产制。作为私法自治精髓的意思自治原则,正好符合了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现代人对自由追求的法律彰显。在区际私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私法,其私法性质不言而喻,所以,在确定准据法时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是其私法自治理念的体现(但不能等同于国内私法上的私法自治,所受限制应更多,如公共秩序的考量)。故当代中国民主发展、个体利益的发展是中国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扩张适用的社会根源。
(二)现代国际私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二战后,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追求愈发明显,反应到国际私法上,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国际私法的价值,如莫里斯提出了“公平需要”理论,不再仅仅追求冲突法意义上的形式正义,对于实质正义越来越重视,关注个人利益,认为法律是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为此,现代国际私法上出现了各种有利于弱者的规则,如 “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受害者”、“有利于雇员”等,这都是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同时由于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选择性、灵活性的冲突规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到广泛运用,从一般合同领域扩展到婚姻关系、继承、财产、侵权等领域。[2](p290-293)国际私法上的这种变化也与国内民商事法律的变化相契合,与实体法的目的和政策相一致。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工、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其他格式合同中的非制定方、劳动合同中的受雇方等的关注,再如婚姻家庭中的弱者,近年来我国基于人文关怀精神、民生的考虑出台了大量有关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现了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正如李双元先生所说:“国际私法不应满足于法律适用形式上的公平和正义,而应该达到法律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适当国家’的法律必然是‘适当的法律’,这种适当性应该从法律适用的实质意义上,而不是从法律适用的空间意义上来界定”。[11](p415)而《法律适用法》就应是“适当国家”制定的“适当的法律”,为此本法中有关对弱者利益保护的法律条文正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反应。
(三)国际私法趋同化的现实基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化实行。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民商事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日益显现,各国私法正在进一步融合,而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也正走向趋同化。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提升了国家各项综合实力,同时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为这种趋同提供了现实基础。
基于以上几点因素考虑,笔者认为中国国际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二维属性有其必然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法律适用法》上意思自治原则二维性实现之困境
毫无疑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国际私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意思自治原则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意思自治原则的二维性作为矛盾体,如何落实将成为其难点。
1.与相关法律的协调。
由于《法律适用法》并不是唯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此需要调合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内容相互交叉,并不完全一致时,要理清关系,关键在于准确界定不同法律的法律效力。虽然《法律适用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条,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本条的规定暂且解决了一般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结婚、离婚法律适用和继承法律适用上的法律冲突,采取本法优先原则,但是并不说明其他法律失效,只是对《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47条和《继承法》第36条规定的补充。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的意义只是确定了其优先适用的地位,其他法律继续有效;当其他法律有不同规定时,本法就成为一般规定,适用特别规定,这种立法可不可行,还有待实践检验。
在笔者看来,目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大的问题是与最高院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按照《立法法》第八十三条有关法律效力位阶的规定,肯定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优先,但只有明确二者之间关系,才可能避免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已有司法解释的现象。
2.默示选择问题。
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中国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抑或是实务界,均不承认默示方式,即只能通过明示选择法律,不允许通过默示方式推定当事人的意思。为此,该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虽然本条确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在整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地位,起到宣誓作用。但是“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这种规定是否说明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可以选择。但作为私法能否适用“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即是否给“默示”选择留下了空间,这仍需要法律解释来完善。
3.有关直接适用法的规定。
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手段之一,《法律适用法》对于“直接适用的法”的规定主要限于第一章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作为“直接适用法”的总则性规定,其具体实施仍需要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运用(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直接适用法的规定——第8条)。
4.如何具体把握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法律适用》第24条规定对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优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但由于夫妻财产的约定往往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如若配偶双方利用本条款来侵害第三方利益,又将如何?莫非需要运用“有利原则”?
所以,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具体把握将成为法官与当事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1]王萌.国际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探析[J].科教文汇,2009,(21).
[2]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徐东根,薛凡.中国国际私法完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4]黄进,何其生,萧凯.国际私法:案例与资料(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6]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田园.保护弱者原则对国际私法基本制度的影响[C].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际私法改革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梅荣政,张晓红.新自由主义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李双元.国际私法正在发生质的飞跃——试评《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抑或倒退》一书的总报告[C].李双元.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丛(第5辑)[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DF973
A
1003-8477(2012)08-0165-04
汪丽丽(1977—),女,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 劳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