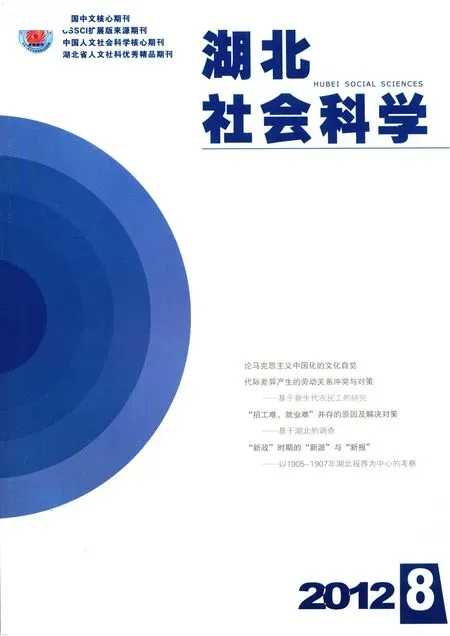从吴起的性格缺陷看其悲剧命运的必然
2012-04-12康清莲
康清莲
从吴起的性格缺陷看其悲剧命运的必然
康清莲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作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的吴起,最后被乱箭射死,其人生是悲剧的一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吴起的悲剧命运呢?可从个人原因,即吴起的性格缺陷、心理错位、品格低下等方面,探讨吴起悲剧命运的必然。
吴起;性格;悲剧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卫国人,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其用兵打仗之术与“武圣”孙武齐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所著《吴子兵法》四十八篇,现在流传下来的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 六篇, 其余亡佚。虽仅存六篇,却充分反映了吴起杰出的军事思想,被译为英、日、法、俄等文字流传海外,成为军事宝库的一朵奇葩,是研究吴起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吴起同时还是一位变法改革的急先锋,其变法甚至比商鞅还要早三十多年。当然,同大多数法家人物一样,吴起也为变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最后被楚国的保守派乱箭射死。
对于吴起,历来有不少文人墨客写诗歌咏,如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泣魏伤吴起,思赵切廉颇。”借泣吴起,抒发对贤才遭忌的悲愤之情。刘长卿《从军行六首》:“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歌咏吴起体恤士卒,慨叹今人不关心士兵生死。周昙《僭号公孙述》:“方知在德不在险,危栈何曾阻用兵。”[1](p323)讥刺公孙述虽有险可凭,却无德固国,最终败亡。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沿袭了他对法家人物一以贯之的态度,高度赞扬吴起杰出的政治远见、军事才干,肯定吴起在鲁国、魏国、楚国所建立的功勋,不过这方面司马迁着墨不多,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写吴起的刻薄少恩,对此茅坤感到无比遗憾。他说:“起之如楚多战功,太史公并为虚语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战之略,惜哉!”[2](p7)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成一家之言”,他要借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来表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司马迁不喜欢法家人物,对严刑酷法有切肤之痛,他认为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与商鞅因“天资刻薄”被车裂、晁错因“为人峭直刻深”而被腰斩、李斯因极度自私自利而被夷灭三族一样,都是自掘坟墓,不仅没有殉道的崇高感,反而为人所不齿。姑且不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是否偏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吴起的人生悲剧呢?目前从政治角度、社会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将从内因,即吴起的性格缺陷、心理错位、品格低下等方面探讨吴起的悲剧人生。
一、一个都不宽恕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主宰人生”。司马迁笔下的吴起虽才能出众,但他性格偏狭,心理阴暗,品格低下,这些致命的缺陷,使吴起失去了社会的美誉度,缺乏成功所需要的良性的舆论环境,最后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前有险滩,后无退路的洪峰巨浪之中。司马迁在为吴起作传时,一开篇所选取的几件小事就让人心惊胆寒,一是为了应聘鲁国大将的职位,杀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3]吴起之妻何其倒霉,碰到这样一个为了自己仕进不择一切手段的冷血动物,因为自己齐国的籍贯,被丈夫拿来祭刀了。又据《韩非子》记载:“起,卫人也,使其妻织维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2](p5)因为妻子织的布宽度不符合要求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吴起无情的休去,连国君出面说情也不能让他收回成命,可见吴起是多么的绝情寡义,同时也可见法家人物一贯的令出必行、绝不宽容的犀利性格。孟子也曾因为其妻在卧室坐姿不雅要去妻,被他母亲一顿数落“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孟子马上认错道歉。从这件小事的对比上,也可看出儒、法的代表人物有本质的区别啊!吴起最终休没休妻从上面文献我们推断不出,也许被休的和被杀的不是一人。此事之后,吴起离开卫国到了楚国,是不是休妻不成,愤然出走?不得而知。合二说见之,为人妻不易,为吴起之妻,难上加难!或被休,或被杀,简直是在刀尖上讨生活。对自己的妻子如此苛刻,对别人也不可能多么宽容。有史臣对吴起的贪残不仁写诗评论道:“一夜夫妻百夜恩,无辜忍使作冤魂?母丧不顾人伦绝,妻子区区何足论。”
二、睚眦之怨必报
吴起未成名之前,奋斗的道路充满艰辛。吴起生活的时代,没有科举可考,不能让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客卿制度需要读书人在外面去游学游宦。以吴起的为人行事,很难得到德高望重之人的举荐,于是只有用金钱铺路。在吴起年轻的时候,本来家道殷实,可经不住吴起的一再折腾,千金之家被弄得破败了。乡邻们的嘲笑,无疑将一心渴望成功、正面临重重打击、心理到了崩溃的临界点、性格中又有暴力倾向的偏执狂吴起推到了疯狂的巅峰,于是他砍菜切瓜般地把非议过自己的三十多人全部杀了。这样血腥的暴力无疑形成了恶性循环,在他人生履历表上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在后来的求职路上,他为此遭遇了一个又一个坎坷。比如,吴起用杀妻的代价谋得的鲁国大将之职,因为一鲁国人在鲁国国君面前的一番话,让他的大将梦断。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3]鲁君疑之,谢吴起。
常言道:“为天下者不顾家”,吴起将此推到了极致。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猎取功名富贵,拿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刀,用自己至亲的血肉垫起往上爬的阶梯,“杀妻求将”、“母死不归”,这种冷血行为,不仅违背了“亲亲为大”的基本人伦,甚至连禽兽不如。一个连母亲、妻子都不爱戴的人,怎么可能寄希望他是个忠臣、义士?这样的为人行事怎么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用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任何行为都会被人变味的解读。据《吴起列传》记载,吴起在魏国做大将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不仅身先士卒,而且与士卒劳苦与共。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共苦,是让人无比景仰的,如“飞将军”李广,“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3]李广自杀以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可同样的事由吴起做起来效果又如何呢?听说将军吴起为自己的儿子吮疽,“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这就是两个不同品格的人做同样的事,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效益。李广是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别人会认为是出自真心,而吴起因为他的极度自私自利,即便他是出于真心,别人也会认为他是“有心为善”,是作秀,是故意拉拢人心,是虚情假意的。这样的舆论导向,只会使吴起的奋斗之路充满荆棘,《史记评林》说得好“吴起在卫则乡党谤之,事鲁则鲁君疑之,将齐则公叔害之,相楚则贵戚射刺之,岂其所遭然哉?观太史公首著其杀妻一节与鲁人恶起者言,则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2](p5)
三、贪廉集于一身
贪与廉如冰炭水火,不可能和谐完美的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可别人对吴起却恰恰使用了这样矛盾的评价。由于鲁国国君不信任他,吴起只有另谋他路。听说魏文侯贤,吴起前往魏国。魏文侯向当时魏国的名臣李克打听吴起的情况。李克,也就是李悝,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平准书》)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和吴起由于都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他们应该属于同门,只不过由于吴起母死不归,被曾子逐出师门,成了曾子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李悝对吴起非常了解,对吴起的评价很权威也很公允,文侯问李克:“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肯定了吴起在军事才干方面超过了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但指出了吴起品格方面的一个致命缺点——贪而好色。好色与否,文献没有记载,但关于吴起的“贪”,似乎与下文‘魏文侯知起廉,尽能得士心’,又公叔之仆称赞吴起‘为人节廉’前后矛盾,难道李克故意在魏文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还是如董份所言:“李克谓起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节廉,岂其性本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矫勉耶?”[2](p6)吴起难道为了博取令名又在演戏骗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李克言起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产求仕,非实贪也;盖言贪者,是贪荣名耳,故母死不赴,杀妻将鲁是也。或者起未委质于魏,犹有贪迹,及其见用,则尽廉能,亦何异乎陈平之为人也。”[9]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公叔之仆说了吴起“为人节廉”之后,又说他“自喜名”,珍惜自己的羽毛,看重自己的名声,吴起并不愿意贪财,他的志向不在金银财富,他看中的是功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抛却身家性命也在所不辞。因此,说他贪,是贪建功立业;说他廉,是廉于克制物欲。尤其是他与魏武侯泛舟那一番谏言,简直可圈可点。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吴起用三苗氏、夏桀、殷纣王不修德政,虽有山河之固,最终却国破身亡的教训告诫魏武侯,广修善政、民心归附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史记集解》引扬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则太公何以加诸!”
四、骄傲自负,能伸不能曲,缺乏性格的张力
吴起性格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不能忍辱,而且喜怒哀乐形诸于色,这样的性格,于普通人无关大碍,但与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距离就相去甚远了。《史记·吴起列传》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魏置相,相田文。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此事中的吴起颇有点像廉颇,当蔺相如权位高过他时,马上就放话要羞辱蔺相如,当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传到他耳朵来的时候,廉颇马上就负荆请罪。这是一个军人、一个赳赳武夫的单纯可爱,吴起虽然也带兵打仗,但他更是一个军事理论家,一个政治家,“遇事便发”的性格显然是政治上还不成熟的象征。田文为相,吴起不服,于是找到田文“单聊”,无论统帅三军、镇抚百姓,还是防御外敌,田文都比不过吴起,但田文的一句话就点了吴起的死穴:国君年少,政局不稳,臣民对国君、对朝政疑虑重重,当此之时,天下之重,是放在你身上让人放心呢还是放在我身上让人放心?吴起自知声誉不如田文,得不到百姓的认同。从二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田文乃忠厚长者,虽然吴起来者不善,大有兴师问罪之嫌,但田文并未计较,反而以诚相待,据实相告,如果吴起面对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岂不是自找苦头?
另一件事是公叔为相之后,嫉恨吴起,想驱逐之而后快。他的仆人设计了一个现在看来很小儿科的计策,让公叔假意在武侯面前称赞吴起,说如此贤明能干的人必定不会长留魏国,可以用把魏国公主嫁给他试探一下,如果吴起拒绝,那么他肯定会离开魏国。这边厢,又安排公叔之妻——魏国的公主故意在吴起面前表现出对公叔的骄纵无礼。吴起果然上当,拒绝了武侯,武侯因此不再信任吴起,吴起被逼无奈,离开了魏国。如此拙劣的圈套,居然可以让吴起钻进来,主要是由于吴起能伸不能曲,缺乏张力的性格使然。苏东坡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4](p452)吴起还没有达到忍别人所不能忍的程度。
李贽《藏书》:“吴起料敌制胜,号知兵矣,而卒困于公叔之仆何哉?其废公族疏远以养战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杀身者亦以是也,其晁错之徒矣。任事者必任怨,虽杀身可也。”[5](p3823)在李贽看来,一个干大事的人,要对各种风险有预见性,任劳任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当然,吴起绝非等闲之辈,在自己最终无法免于一死的情况下,用楚悼王的尸体做挡箭牌,让射杀他的七十余家为他的死垫背,也算是快意恩仇吧,这也恰恰是吴起“一个都不宽恕”性格的鲜明体现。
五、结语
当然,作为改革的先锋人物,吴起的悲剧命运与别的改革家具有共同性,因为改革必然要动摇既定的社会秩序,冲撞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范围,比如吴起的“废除贵族特权,选贤任能”和“明法审令,裁汰冗员”,触犯的都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支持改革的国君活着,这些人不得不隐忍不发,一旦这个保护伞一去,他们必然疯狂的反扑;其次,吴起生活在嫉贤妒能、设奸计害人的小人包围圈中。这本身已让他招架不住,防不胜防,加之他自身性格的弱点,他成了一个君子厌恶他,小人陷害他,老百姓不信任他,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这么低的情商,这样缺少应有的弹性和韧性的处事方式,这样偏激峻切的性格,从事的又是那样高风险的事业,吴起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必然中的必然。
[1]宋嗣廉.史记人物诗歌选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2]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傅德岷.古文观止鉴赏[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
[5]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K244.05
A
1003-8477(2012)08-0117-03
康清莲(1967—),女,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