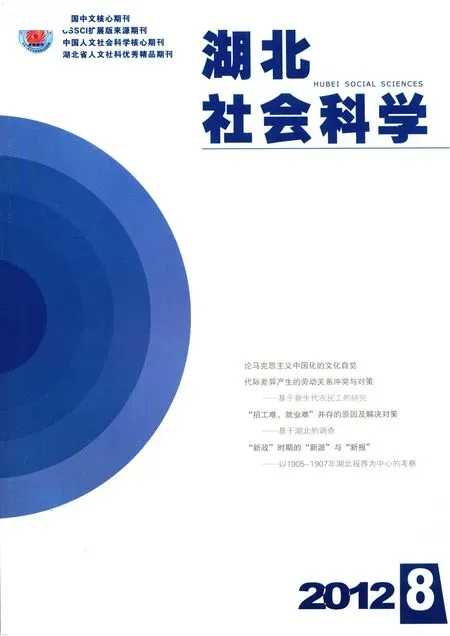论张君劢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2012-04-12王呈祥
王呈祥
论张君劢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王呈祥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张君劢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探索:其一,通过对中西哲学史上“唯心唯物之争”的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的探讨,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其二,在深入研究中西哲学的差异和相同的基础上,论证了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中国新哲学之创造;其三,在汲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掘和阐发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理,试图为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奠定学理基础。
张君劢;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科玄论战;儒学复兴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义理学十讲纲要》、《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思想史》等。他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探索方向和学术贡献。其一,通过对中西哲学史上“唯心唯物之争”的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的探讨,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其二,在深入研究中西哲学的差异和相同的基础上,论证了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偏重论证中西哲学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其三,在汲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深入发掘和阐发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理,为儒学之现代转型奠定学理基础。
一、“科学与哲学之携手”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了“科学无论如何发展,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1](p35)的观点,遂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撰文痛斥“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主张“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1](p55)一时,思想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张东荪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论战过后,张君劢通过对中西哲学作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的探讨,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
张君劢在《人生观》的讲演中,着重分析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差别:“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间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单一性。”[1](3p1-34)根据以上分析,张君劢断言:人类的意志自由非科学公理所能规定,人生观“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有反求诸己,而不假外求;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对于人生观问题的解决,总是无能为力的。张君劢还由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引发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故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1](p35)这一对中西文化的区分无疑是过于武断的,而且也不合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2](p641-642)
张君劢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中的两种传统——汉学与宋学的传统——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上唯物派与唯心派:“若夫汉宋之争,与惟心惟物之争,则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而不得以牵合傅会目之也。”他说顾炎武讲多学而识、王引之讲遍为搜讨、戴东原讲仁义礼智不求于欲之外,与培根讲事实之搜集、洛克讲一切意象由经验而入、唯用主义者讲意象之有益于人生者为真,都是属于唯物主义的思路,而孔孟下逮宋明理学家之言则与康德、柏格森和倭伊铿等人所代表的欧洲唯心派之言若符契。他认为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以欧洲唯物派和汉学家之言为长,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以唯心派和宋学家之言为长。[1](p104-106)这些说法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学理上的合理性。
他认为当今中国实在有昌明宋明理学的必要:第一,从理论上来看,宋明理学主张“心为实在”,故勤加拂拭,则努力精进之勇,必异乎常人,这既合乎最新的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之学说,也与我先圣尽性以赞化育之义相吻合。因此,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以及“克己复礼”的修省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第二,从实际上的必要性来看,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唯物主义是无能为力的,“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p108)他认为谋求现代化的“富强政策”、“工商立国”、“自然之智识”皆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主张冲决这“三重网罗”,回到以农立国、寡均贫安的传统社会中去。[1](p103-104)由于他的这些主张所具有的保守性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
科玄论战之后,张君劢对于科学和人生观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修正。他意识到现代化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转而深入剖析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他说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在于中国人对于宇宙的态度与西方不同:“一是对于人事兴趣特别浓,而对于宇宙事物现象公理之研究非常淡泊;二是中国人对实用方面非常注意,而不大注意实用之背后有理论,有纯粹科学。”[3](p369)而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之学与西方科学存在着一系列差异,“惟知向内不知向外,惟知有心不知有物”,[4](p10)于是导致了下列弊病:新知识来源窒塞,容易流于空疏而无裨实用,论理学不发达等。张君劢还指出:“要真正发达科学,不是在求人家已经成功的科学结果,而在养成所以产生科学的心态。就是说,这是思想的问题,而不仅是科学仪器科学实验室的问题。”[4](p70)张君劢认识到科学精神的真正确立或科学心理的养成比引进科学实验和科学方法等要更为根本,同时也更为困难。他似乎已经触及到民族心理或民族思维变革的重大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张君劢仍然认为,只要现象与物自体、机械论与目的论这类问题存在一天,那么,科学的效用就有界限,而义理学或哲学就由之而生。于是,他认为:“有各科学所解决不了之问题,亦即各科学所余剩之问题,又有哲学本身之问题如认识论、论理学等,则哲学自有其存在之价值。”[4](p46)更为重要的是,张君劢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与哲学既然是同源(理性主义精神)发生的,那么,两者的携手发展也是可能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是专门化,哲学是综合的,“有了分,少不了合;有了合,同时也不可不以分的研究为基础,这两方能合作,就是我今天所谓科学与哲学的携手。”[4](p72)二是科学家的哲学立场是量的观察、机械论和定命论,哲学家的则是性的观察、目的论和自由意志论,因此,“在科学家的立场,用不着排斥哲学家;哲学家当然也不必排斥科学家且引为好友。 ”[4](p78)
科玄论战后,张君劢重新界定了科学与哲学各自的学科范围,既限定了科学的界限,又维护了哲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他又敏锐地察觉到近代科学的显著特征如“立说之大胆、举证之精确、思力之无远勿届”等,在实质上与哲学思辨有着息息相通的联系,认识到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同源发生与携手发展的关系。
二、“与其求彼此之殊特,不如求彼此之会通”
西方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相关,为了科学在中国真正发达,那么,在西方近代哲学的观照下,辨明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和相同,进而谋求两者的会通融合,便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工作。张君劢认为:“今海外新智输入之机大动,凡欧美任何派别之学说,皆可供我取用吐纳之资,以浅者言之,则兼容并包,以深者言之,则融合各家之言,而自成一新说。”[3](p146)20世纪30-40年代,他主要论述了关于中西哲学异同及其会通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在西方哲学的观照下,张君劢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片断之格言,不相联贯而成为一种系统的著作;二是同意语之重复;三是中国语言由于缺乏印欧语的文法结构,意义含混模棱,不适于讨论哲学。另外还有:完全以书本为对象,忽略自然界;偏重直觉,忽视论理的展开因而缺少系统性;重视道德,忽视知识,只有道德论,未形成一种知识论;缺少为学问而学问的献身精神等。他还指出:“一、东方注重人生,西方注重物理世界;二、东方注重是非善恶,即西方所谓价值,而西方认为次要;三,东方将道德置之智识之上,西方将智识置之道德之上。”[3](p474)
在中西哲学相同方面,张君劢认为:“宋儒之基本观念,曰理性之自主,曰心思之体用,曰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曰致知格物之实事求是。此为东西古今思想之共同基础,而不可须臾离者也。”[3](p516)具体而言,在本体论方面,中国儒家哲学肯定天地间万物之有,反对释氏虚无寂灭之说,张载的气一元论就是显著的标志。张君劢指出:“宋儒之中,以‘有’为出发点者,莫过于横渠。”[3](p489)西方哲学家笛卡尔则主张“吾思故吾在”,认为万物之存在均在可疑之列,惟有以自己之思确定自己之存在一点为不可疑。这便与儒家“万物之有”的本体论思想大相径庭。不过,西方新唯实主义打破世间事物由于心识而后存在之论,直截了当地承认万物之存在,“此与儒家之态度不谋而合者。”[3](p489)儒家本体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认为形下、形上相通,必以形下为基,然后进而达于形上。《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君劢认为,器指物理世界中之有形可见有迹可求者言之,道指其中之义理言之。物质界与人心中之义理,二者不可分离,如果离而为二,“则一方有唯物主义,他方有唯心主义矣。更有但认物质而不知有心有人,则其为祸尤甚矣。”[3](p491)与康德把形上形下界化而为二不同,中国哲学“形上形下相通”的观点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相类似,都认为“限于形上界以讨论形上问题,诚哉其为无确实之答案可言,然以形下界之事实为张本,进而推定其有形上学问题讨论之可能。”[3](p491)
在认识论方面,儒家哲学不但承认天地万物之存在,而且以为天地万物之理,必经由心乃能知乃能通其理。这就是宋儒所提倡和阐发的格物致知之学。当然宋儒所谓的“致知穷理”,重于德性,轻于物理,所以,“其致知之方法,远不如西方科学家之知之精细,然其致知之心之真切,可与西方媲美。”[3](p489)张君劢指出:“处于今日,吾人深知数学之知与理,逻辑之知与理,物理世界之知与理,吾国远不如西方,然依伊川和朱子之说,足以见其对于知与理之不可忽视。自可与西方注重知识之点会通而为一。”[3](p490)
在伦理学方面,张君劢认为,康德讲“汝之行为应求其所根据之定则,经汝之意力而成为自然界之公例”与孟子讲“心之所同然”,虽然都是“求一种同归之原则”,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一则责诸一己,求诸一心,一则求诸人人,求其成为自然界之公例。”[3](p566-567)所以,西方伦理学与孔孟以来的正心修身之教,“一则由讨论以求其成为一门科学,一则求各人所当为者责之勉之。”[3](p554)
在辨明中西哲学彼此异同的基础上,张君劢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原则:“吾以为居于今日东西关系之密迩,与其求彼此之特殊,不如求彼此之会通。而其法有二,一曰知己,一曰知彼。知己者云,知己之所长缩短。知其所长,然后能择善而守之。知其所短,然后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知彼者云,知人之所长所短。知其所长,取其精者以为己。弃其短者,以期不陷于人之覆辙。”[3](p32)
在张君劢看来,为了促进中西哲学会通融合,首先需要全面客观地输入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早在科玄论战时,他就指出:“吾国学者若取欧美人门户以树之国中,行见其徒费口舌,而于学理一无裨益。然我默察国人心理所趋,倚旁门户之见解深入人心,故英德内外之争,先天后天之争,经验理性之争,环境与精神之争,恐亦不免在吾学术界上重演一过。”[1](p85)为了扭转此一不良学风,张君劢认为:一方面需要坚持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种种学说,固应同时输入,即以同一学说言之,不仅正面之言应输入,即负面(即反对者)之言,亦应输入,惟如是方能启人怀疑之心,令思想发达,人智进步。若仅仅推尊本师,则旧偶像虽去,而新偶像又来,决非吾国思想之福。”[3](p144)另一方面必须树立思想自主的原则,“惟有奖励吾国人之自主的思想,国族本位之学说,自然合此以国为别之学说而冶之于一炉之中。”[4](p5)因此他号召国内学界:“第一曰不随声附和,第二曰参互比较以求其正反两面之是非,第三曰敢于对外人议论为之折衷至当。”[3](p62)张君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除了他的老师倭伊铿的学说之外,还有柏格森、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杜里舒、罗素、怀特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郑大华先生指出:“就介绍西方哲学家之多而言,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5](p137)
另外,张君劢大力鼓励开拓进取的创新性。他认为:“学者之立言,不患采取他家成说,要其能自成一个体系而具有周遍性,乃成为一种宇宙观或人生观,不陷于偏激与一偏。”[3](p540-541)为了促进中国新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张君劢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哲学名著之翻译、哲学史之研究、哲学问题之分门研究、彼此之辩论等,此外,他还认为各个哲学家应该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并且建构自己的学说体系,一言以蔽之,“从事研究之者,贵乎博学、慎思、明辨,即有乐于信奉一家之言者,初不可盲从一派之言,应求其正反两面而知彼此长短。倘能更进一步,将其互不相容者而融铸于一炉之中,宁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一大妙事。”[3](p60)张君劢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唯实的唯心主义,即“以万物之有为前提,而其论心之所以认识与文物之所以建立,则以心之综合与精神之运行为归宿。”[3](p540)
在张君劢看来,只有在哲学研究领域贯彻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和独立自主、开拓进取的创新性这两个原则,中国哲学界才能逐渐脱离模仿时期,进入独立创造时期。而中国新哲学之创造,“将使中国贡献出两千年来以独特方式所得这一思想体系的优点。这种情形加上西方人丰富的知识原创性及方法,将使东西方之间有一新而更广泛的了解。 ”[6](p551)
三、“与其对于西方某派左袒或右袒,反不如以吾国儒家思想为本位”
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张君劢在论述中西哲学会通问题时广泛涉猎了古今中西哲学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并尝试着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可以看做是其学问“致广大”的一面,那么,20世纪50-60年代他对儒家哲学基本范畴的梳理、深微学理的阐发以及儒家哲学复兴的论证等,则属于“尽精微”的部分。
张君劢认为,儒家学说圆通广大,高明精微,是中国思想的主流。 《大学》首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一套大规模的思想,伟大的轮廓,足以吸纳西方哲学和科学知识。“我们当本此规模,更加以充实,则所包括者可无有穷尽。”[3](p57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实现了儒学的复兴,这一成功案例无疑会对儒学新一轮的融合西方哲学提供经验和借鉴。
在张君劢看来,宋明理学为儒学新一轮的吸收和融合西方哲学提供了以下经验:首先,宋明理学的程朱、陆王等学派在吸纳佛教思想的过程中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所以,现在便不应强调各个门派之间的差异,而应尽量阐发它们的相同之处来更好地吸纳西方哲学。张君劢认为,与其斤斤计较于程朱派、陆王派的这些差异,“莫若返于孔门创始时代尊德性、道问学之双管齐下,反足以息争而合于并行不悖之旨矣。”[7](p7)其次,既然宋明理学在更新和阐发心、理等儒家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成功吸纳了佛教思想,那么,为了吸取和融合西方哲学,便需要重新发掘儒家的基本概念和精微学理。最后,新儒家思想体系虽然是受佛家影响而建立的,但是,却从未失去中国人对世界及肯定人生的基本态度。“中国人不接受佛家空的观念,坚持其肯定道德价值的立场。他们以‘仁’和‘智’(此乃人生活动的本源)解释佛家所谓的大悲心和大智慧。 ”[6](p86)
今后儒学哲学发展之途,张君劢概括为“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具体而言,“其可以采择之地,或为西欧或为美洲或为印度,或为各回教国,或为日本,其来源各异,将成为一种多形结构。然其选择、决定与陶铸而成之权,操之于己,而不流于喧宾夺主。此所谓自主更生中之多形结构之要义也。”[3](p460)张君劢认为:“与其对于西方某派左袒或右袒,反不如以吾国儒家思想为本位,刷新条理,更采西方哲学中可以与儒家相通者,互为比较,互为衡量,互为引证。或者儒家之学说,得西方学者之助,更加明朗清晰。而西方哲学家言,因其移植吾国,更得所以发荣滋长。盖惟有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后吾国学说方能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亦惟有以吾国儒家思想为本位,而后本大道并行万物并育之旨,可集合众家之说,以汇为一大洪流,兼可以发挥吾国慎思明辨而加上笃行之长。”[3](p521)这样,儒学才得以有新血液之输入,而有其世界性的新生命,儒学才能真正复兴。
张君劢在《新儒学思想史》中列举并简要说明了“至善、道或理、物则、理与气、理一分殊、常与变、形上与形下、万物莫不有对、相反相成、礼与命、本体与工夫”等十一个中国哲学的主要观念,在《儒家哲学之复兴》一书中又重点论述了“万物之有、致知穷理、心之同然、形上形下相通、知德合一、道并行而不悖”等儒家基本范畴,他认为,这些范畴不但是中国儒家哲学推陈出新之基础,而且是中西哲学会通融合的基础。另外,只有儒家的“道并行而不悖”的气度才能涵容东西方哲学的精蕴。
张君劢对于儒家哲学精细学理的阐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万物之有”。这是张君劢对儒家宇宙观的高度概括。从孔孟以来的儒家对于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存在,从来没有怀疑否定之论,而是“对于内外之有,平等一视。”[3](p526)相对于西方学者或者主张唯物主义或者主张唯心主义从而陷入心物对立的困境,张君劢认为中国哲学的“物心并重之论”完整周密,当然其精密程度却不及西方近代哲学。一是“致知之心”,这是张君劢对儒家认识论的简明归纳。人之所以知外物,赖乎有心,心为知之管钥。这是儒家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孟子和荀子则分别代表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后世还有程朱和陆王的不同。张君劢认为,孟荀的上述不同和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不同类似,其理论各有长短得失,只有“承孟荀传统之后,更兼收并蓄西方两派学说,”才能“合其长而参互错综之,或者可以引而至于一条新路。”[3](p535)张君劢在发掘儒家基本概念和阐发精微学理的过程中,虽然仍旧使用儒家传统的概念,但已经把西方近代逻辑学等重要概念和方法融会其间,这表明他已经在中西贯通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和更新。
张君劢重新诠释了“现代”的内涵及其根源,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他说:“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的真正动力。这从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式中都看得出来。在宗教方面,它叫做良心自由;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它叫做理性论与经验论;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它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虽然在不同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它们却出于同一个来源,那便是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3](p581)既然作为现代标志的科学与民主和古代思想一样都是来源于思想的合理性原则,那么,现代或古代不过是区分一个时代知识趋势的一种表示,“现代与古代,不是像意义与无意义或者黑与白那样的分别,而是在准确程度上有差别而已。”[3](p579)
以“人的理智自主”或“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作为西方给予中国的“现代”启示,张君劢认为,中国固然需要从西方汲取“个人独立之精神”、“政治上之民主主义”、“科学上之实验方法”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经由中国传统的再生开辟出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途径。于是,张君劢断言:“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3](p596)张君劢在批评西方现代文明弊病的基础上,主张中国应该走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富有启示的思想。
[1]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3]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
[4]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郑大华.民国思想家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B26
A
1003-8477(2012)08-0095-04
王呈祥(1982— ),男,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06AZX003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