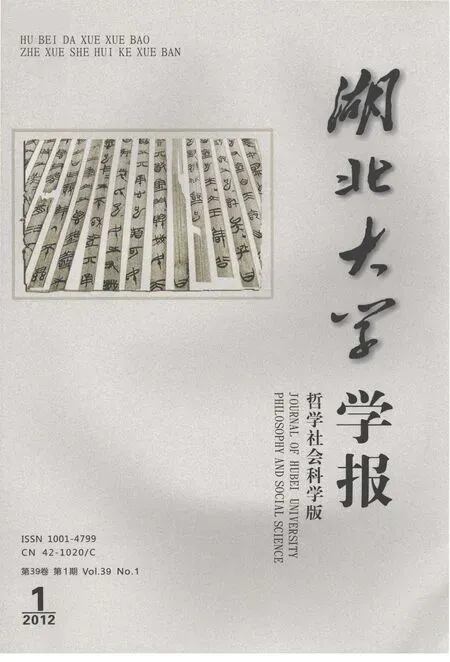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2012-04-09刘全志
刘全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刘全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大武》;《左传》;《象》;《酌》;用诗
《大武》是西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大型乐舞,学界关于其用诗的情况多有争议。遍览前贤的相关讨论,笔者认为《大武》的用诗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诸家之说的基点
《礼记·乐记》记载了《大武》的“六成”结构:“始而北出,再成灭商,三成而南,四成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依据诗乐舞合一的原则,演奏《大武》必然有相应的配乐诗歌。所以,依据《大武》的“六成”结构,来考索与之相应的配乐诗歌,成为学界讨论的问题。准确地说,此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实发轫于朱熹:他在《诗集传》中首次用《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载,来确定《大武》的用诗情况。朱熹所用的方法是先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与《乐记》的记载相链接,然后再依据楚庄王之语提到的《诗经·周颂》篇章与《大武》的“六成”相配,最终得出《大武》所用的三首颂诗:《武》、《赉》、《桓》。朱熹的这一方法,被何楷所继承,“在其《诗经世本古义》中,开始照着《左传》和《礼记》之《大武》‘六成’之乐的说法,向《周颂》按图索骥,以凑足‘六成’之数”[1]。其后,随着《诗集传》和《诗经世本古义》的流播,参与讨论的学者逐渐增多,而且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如庄有可、赵文哲、魏源、龚橙、王国维、孙作云、高亨、阴法鲁、王玉哲、张西堂、杨向奎、袁定基(以上学者的观点可参见任强的《〈大武〉章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姚小鸥[2]、李山[1]、张国安[3]、李炳海[4]、祝秀权[5]等,由此《大武》用诗问题变得众说纷纭。他们角度相异、观点不同,但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基点,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的《武》就是《大武》乐章。为方便分析起见,特引《左传》内容如下:
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帮,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2]1882
关于这段话,引起朱熹、何楷等学者注意的文字,无疑是楚庄王所引的四首颂诗,即《周颂》中的《时迈》、《武》、《赉》、《桓》。在他们看来,楚庄王之语中的“《武》”就是《大武》,而“其卒章”、“其三”、“其六”对应的就是《大武》的各部分。这种说法难以合符之处就是颂诗《武》,因为有“其卒章”字样,又被楚庄王首先提及,就是放入《大武》的最后一成也与《桓》相冲突。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学者们多认为“卒”为“首”之误,颂诗《武》便对应于《大武》的“始而北出”。至此,由六部分组成的《大武》有三部分确定了与之相配的颂诗。在此基础上,学者开始推测《大武》所用的其他诗歌。从何楷以来,学者针对《大武》“六成”用诗情况的讨论,虽然拟定的诗歌篇章不一、顺序不一,但其中都包括《左传》楚庄王之语中的三首诗:《武》、《赉》、《桓》,而且多位学者的顺序也是依据《左传》而定。显然,他们讨论《大武》用诗的基点就是楚庄王之语中的《武》即《大武》。也就是说,朱熹所运用的方法,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然而,值得怀疑的正是由朱熹、何楷所确立的这一研究基点:《左传》楚庄王之语中的《武》是否就是《大武》乐章?《乐记》中的《大武》“六成”是否与《左传》楚庄王之语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商榷。
二、《左传》之《武》非《大武》乐章
晋楚邲之战,楚国大胜后,潘党提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目的是“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就是针对潘党的建议而发,重在说明楚庄王对“武功”的理解。其中“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杜预云“著之篇章,使子孙无忘”,对此,后人颇有争论:孔颖达认为“不忘其章,谓子孙不忘上四篇之诗”;刘炫认为“武有七德,故子孙不忘章明功业”(《春秋左传正义》)。王念孙结合《国语·鲁语》“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晋语》“以德纪民,其章大矣”,认为:“凡功之显著者谓之章。‘使子孙无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经义述闻》)相比较而言,王念孙的考证最为切实,因为他的观点显然符合楚庄王之语与潘党之言的前后对应关系。可见,楚庄王之语都是在围绕“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而言,话语的关键词即“武功”。从全段的话语意义看,楚庄王之语又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即他从“武”字的组成结构来说“武”有“止戈”之意;第二层即从“武王克商”至“屡丰年”,他借用“武王克商”这件与晋楚之战相似的“武功”之事,举例说明自己对“武”的理解;第三层即从“夫武”至“使子孙无忘其章”,这是在前两层的基础上总结出“武功”所包含的道德意义。朱熹、何楷以来,学者引用楚庄王的这段话,多关注第二层举例说明,而忽略了对楚庄王之语真实意义的考察。
就楚庄王之语的第二层引诗部分而言,学界也存在众多的曲解。这首先表现在对“其卒章”的释读。马瑞辰说:“按《乐记》言《武》乐六成,《左传》言武王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以《桓》为《武》之六章,即卒章也,则《武》之诗当为首章。而《左传》引《诗》‘耆定尔功’以为‘卒章’者,‘卒章’盖‘首章’之讹。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武》之首章’,盖宋时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毛诗传笺通释》)马瑞辰的推测,很受后世学者的信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卒章”是否是“首章”之误,并不能依据《诗集传》,因为朱熹也是引用《左传》,而且并未明说《左传》“卒章”是“首章”之误。其实,早在朱熹之前的孔颖达就对《左传》之“卒章”做过解释,他说:“《颂》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谓终章之句也。”可见,不要说宋代的朱熹,就是唐代的孔颖达看到的《左传》也是“其卒章”,而非“首章”。另外,从楚庄王之语本身来理解,“卒章”根本不可能是“首章”。楚庄王之所以引诗,意在说明自己对“武功”传示子孙的理解。他引《周颂》中的《武》的最后一句,意在强调“定功”之于“武”的意义。“耆定尔功”本是《武》诗的卒章,所以《左传》记载“《武》其卒章”是对的,不存在错误之处。这一点前人也多有指出,如陈启源说:“《左传》以‘定尔功’《武》卒章,并不以《武》为《大武》之首章也。《周颂》篇止一章无迭章者,传指末句为‘卒章’,意以一句为一章。”(《毛诗稽古编》)简而言之,说“卒章”为“首章”之误,实是马瑞辰的“一厢情愿”。
当然,从本质上说,马瑞辰对“卒章”的曲解应缘于他对楚庄王引诗之语的整体曲解,即他没有把握住或者没有深究楚庄王引诗之语的话语内涵。我们可以把楚庄王的引诗部分简化为如下语句:
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其三曰……其六曰……
其中“武王克商”,是点明做诗的背景,而后面的“作《颂》”、“又作《武》”、“其三”、“其六”层次又如何呢?从立论基点看,何楷、马瑞辰等学者都认为“作《颂》”与“又作《武》”是并列关系,“又作《武》”与“其卒章曰”、“其三曰”、“其六曰”是从属关系,而“其卒章曰”与“其三曰”、“其六曰”又是小层的并列关系。由于这种层次划分的认识,何楷、马瑞当然就“一厢情愿”地设想“卒章”为“首章”之误了。然而,考察楚庄王引诗的具体语境,我们可知,楚庄王引诗的层次并非何、马所认为的那样。“作《颂》”、“又作《武》”、“其三”、“其六”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四首诗共同说明了武王克商的用“武”之意。即这四首诗是作为楚庄王举例说明的具体例证,从不同方面共同揭示了“出兵征战”(“武”)所代表的道德意义,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这一点也是《左传》的注解者所一贯主张的:“其三”、“其六”,杜预说“此三、六之数,与今《诗·颂》篇次不同,盖楚乐歌之次第”;孔颖达云:“以前此之三、六,全与《诗》次不同,故云‘楚乐歌之第’。今《周颂》篇次,《桓》第八,《赉》第九也。”杜预、孔颖达显然都认为“其三”、“其六”是《周颂》篇章的次第。这也再次证明了“其三”、“其六”与“作《颂》”、“又作《武》”属于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退一步说,楚庄王引诗部分的《武》就是《大武》乐章,那么用“其六”来称《大武》的卒章,与《左传》引诗的体例不相符合①《左传》引诗言及诗之第几章时,如果是最后一章,必用“卒章”字样,而不是标示第几章,如成公九年“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等。如果楚庄王所言《武》真是《大武》乐章的话,必不能称为“其六”,而只能称之为“卒章”。。
可见,如果把楚庄王所说的《武》理解为《大武》乐章,处处扞格不入,甚至还要篡改《左传》。这些现象显然都在表明,楚庄王所说的《武》只是《周颂》中的一首诗,并不包括“其三曰”、“其六曰”,更不能与《大武》的“六成”相对应。楚庄王之语也显然不能当作考察《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
三、《大武》是《武》乐与《酌》乐的组合
既然不能把楚庄王之语当作考察《大武》乐章的基准,那么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又从何入手?笔者认为,考察《大武》用诗应该从《大武》的组成部分或构成要件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掘出《大武》乐章的情况。以往,学者多将《大武》乐与《武》乐混同而谈,认为《武》乐即《大武》乐的简称,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这是《大武》乐用于享祭周之先祖。《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孔颖达云:“《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众舞之中,无能重于《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师说《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乐亡也。’”《武宿夜》,即《武》乐,是表现武王伐纣之乐舞。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来享祭祖先的《大武》,常常被各国诸侯所僭越,这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载的“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由于《大武》被各国诸侯普遍使用,它的名声逐渐超过了《武》乐,进而在有些典籍中《武》也成为了《大武》乐的简称。更为重要的是,《武》乐与《大武》乐的混淆,与《大武》乐的组成结构密切相关。
(一)《大武》乐的构成
《礼记·乐记》宾牟贾与孔子的对话,是我们经常引用的材料,他们谈论的“《武》”乐从表现内容看,显然不仅仅有武王伐纣之事,所以《乐记》中的“《武》”无疑是《大武》乐的简称。在孔子讨论《大武》的那段文字中,颇有争议之处就是《大武》所表现的具体内容,而争议的焦点又集中在对“南国”一词的解释。笔者认为,“南国”一词并不是只出现在《乐记》中,在《诗经》《左传》以及战国诸子著作中都曾出现。我们从一些实例可以看出,“南国”所涉及的地区正如郭人民所指出的那样:它“北起终南山、熊耳山、嵩山,南达长江北岸,东南至淮汝,西南至巴山以东的鄂北。包括今陕南、豫南、鄂北之地。正在岐丰洛阳之南,所谓江沱汝汜地区”[6]。由此,《大武》“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就不是对武王伐纣之事的表现。孔子说“《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史记·乐书》也说“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这些说明,《大武》除了表现武王伐纣之事,还要呈现周公、召公对天下的治理。无论“南国是疆”还是“周召之治”,事情都发生在周成王时期,而其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周公。所以,《大武》至少表现了两朝事功:一是周武王的伐纣灭商,二是周成王的治理南国和分陕而治。于此,《白虎通》“《礼记》曰:‘……周乐曰《大武》,[武王之乐]曰《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无疑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礼记·乐记》所载的《大武》乐大致是由武王之乐和周公之乐组合而成。
(二)《象》乐即《武》乐
武王之乐曰《象》,这一点也可以从文献中得以证明。《毛诗》曰:“《维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颖达云:“《维清》诗者,奏《象舞》之歌乐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可见,《象》是用于享祀文王。《礼记》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都有“升歌《清庙》,下管《象》”,把《象》与《清庙》相对。郑玄注《明堂位》云“《象》谓《周颂·武》也,以管播之”;注《文王世子》云“《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皆于堂下”;注《祭统》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乐也”。孔颖达云:“案《诗》‘《维清》奏《象》舞’,是武王作乐称《象》也。故《左传》云:‘见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纣乐者。”可见,《象》与《武》紧密相连,它们要表现的内容都是周武王伐纣灭商之事。《墨子·三辩》又载:“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春秋繁露》曰“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由此,把《象》当作《武》另一名称,显然是有根据的,即《武》、《象》、《武象》、《象武》都是指周武王伐纣灭商之乐,是同一乐舞的不同名称。“武象”、“象武”在文献中多有出现,如《荀子》“《武象》起而《韶护》废矣”,“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杨倞云“《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后乐,名《武》,亦《周颂》篇名”;《淮南子》“掉羽、武象,不知乐也”,《独断》“《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等。这些例子无疑说明《武》即《象》,《象》即《武》,是表现武王伐纣之乐。《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笔者认为,如果把时间只限定于周武王伐商胜利之时,周公所作“《大武》”无疑是《武》,内容是表现武王伐纣灭商之事,而非享祀先祖的《大武》乐。
有关《武》乐的结构,我们可以通过《国语·周语》伶州鸠的话一探究竟,即“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所以优柔容民也”。伶州鸠所说的“上宫”、“下宫”虽难以确指,但他无疑是从乐舞的角度来表达武王伐纣灭商的四个过程。“夜陈”、“布戎”、“厉师”、“宣德”、“布宪”,这些动作安排得如此紧凑,而又符合乐律;“羽”、“厉”、“宣”、“嬴乱”,四个部分紧密相承,昭示的意义又那么明确。这些现象说明武王伐纣的几个过程,早已被编排成乐舞进行了实地演奏。董增龄认为:“州鸠叙此曰乐,兼叙伐殷之事,乐以象事者也。《乐记》言‘《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与此同义。”(《国语正义》)另据专家考证,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磬上就有“厉”、“宣”、“嬴乱”等字样[7],这说明伶州鸠所说的武王伐商的过程,确实已被运用到了韵律的称谓上。于此,表现武王伐纣灭商四个过程的乐舞也一定在不断地演奏。从伶州鸠之语可看出,《武》乐所表现的时间是以夜为起点直至得胜而返,由此把《武》称之为《武宿夜》是十分恰当的。
(三)周公之乐《酌》
《大武》乐由《象》和《酌》组成,《象》又是《武》之别名,那么《大武》显然就是《武》与《酌》的组合。《白虎通》记载:“周公之乐曰《酌》,……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可见,《酌》乐乃颂周公之功德。《周颂》中也有《酌》诗,《毛诗》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注家虽多有美化曲解之处,但也肯定《酌》与周公之功有关。考察《酌》诗,首先赞叹王师之盛,然后出师征伐,进而取得天下太平,最后把功绩归于“尔”。全诗意义显然是与周公对东方以及南国的经营治理有关。傅斯年认为:“酌、勺本一字。”[8]160依据陆德明所说“酌音灼,字亦作‘汋’”可知,傅斯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于此,《酌》乐即《勺》乐。《礼记·内则》记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勺》即《酌》,是表现周公之治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张揖曰:“《象》,周公乐也。南人服象,为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乃为《三象乐》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据此,《三象》也是表现周公之功德的乐舞,它的制作背景也是周公对东、南两方的治理。结合前述《酌》乐之意,《三象》与《酌》乐表达内容和意义极为相近。因此,《三象》即《酌》也可通。据姚小鸥考索,“象”是指“效”“法象”之义,即表现后人以追步前王之德,以续先祖之功[9]。周家习惯把继承先人之功作乐而称之为“象”,如前述《武》乐称之为《象》乐,所以纪周公之绩的乐舞称之为“象”也是合理的。“三象”之“三”很难解释,大致意义可能是要把周武王之“象”与周公之“象”区别开来。郭沫若认为,“三象”,意为“本有三章”[10]83。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酌》乐有三成。《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勺》,《酌》乐;《象》,《武》乐。由前述伶州鸠之语可知,《武》乐有四成;按郭沫若的说法,《酌》乐可有三成,《武》乐的程序显然比《酌》乐复杂,这或许可以解释“十有三舞《勺》,成童舞《象》”的要求。
《大武》乐虽然是由《象》(《武》)和《酌》(《勺》)组成的,但绝不是两者的叠加。将《武》乐的结构与《大武》乐相比,可知在制作《大武》乐时,只是吸收了《武》乐中的主要部分,如《大武》乐中的“总干而山立、发扬蹈厉、夹振之而驷伐”等无疑取自于《武》乐“羽”、“厉”两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大武》乐在《武》乐和《酌》乐的基础上,更注重突出乐舞中的人物形象,如相对于《武》乐中的“藩屏民则”、“厉六师”等群体形象,《大武》乐更突出表现乐舞中的天子和将领,这可以从孔子在谈到《大武》乐时所强调的“武王之事”、“大公之志”、“周召之治”看出来。另外,《大武》乐制成后,《武》乐和《酌》乐仍可以单独使用,这也可以从“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的规定得以证明,其中《象》乐和《大武》乐并提,显然都用于典礼活动中,只是运用的时刻有差别而已①关于《大武》乐章在典礼中的运用程序,笔者将从《大武》舞容与颂诗的关系入手另文讨论。。
四、《大武》乐的用诗情况
明确《大武》的组成情况,显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大武》的用诗情况。既然《大武》乐是由《武》乐与《酌》乐组合而成,那么《大武》的用诗也必然与《武》乐、《酌》乐紧密相连。于此,先看《武》乐的用诗。《逸周书·世俘》记载:
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
《世俘》出于后世对周武王伐纣灭商行为的追述,其记载事件的细节免不了出现偏误,但从中完全可以提炼出周武王伐商胜利后进行祭祀活动的信息。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云:“‘谒戎殷于牧野’,谓设奠于牧野之馆室,以告行主也。”《史记》:“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可见,周武王此次在牧野的祭祀行为是正式告享文王的活动。乐人所奏之《武》,陈逢衡认为只有《武》之一成,所以此处的《武》,或曰《象》乐的不完整形态。至于“献《明明》三终”,《明明》即《诗经·大雅·大明》,虽难以确指,可知《明明》与文王之德有关。由前引可知,《毛诗》、孔颖达等都认为,奏《象》舞之时歌《维清》诗,颂文王之德。《礼记·文王世子》曰“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所谓“示德”是“示”文王之德,所谓“示事”是“示”武王伐纣之事,如此典礼仪式在后世频繁举行,这无疑是《逸周书·世俘》所载周武王祭祀行为的延续。可见,舞《武》乐,定有《维清》一诗与之相配。
《武》乐是反映周武王伐纣灭商之事,共有四成,且重在表现武王之功德。《毛诗》曰:“《武》,奏《大武》也。”孔颖达云:“《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于庙奏之。”虽然注家所说之“《大武》”只包括武王伐纣之事,“《大武》”即《武》乐,但认为《武》诗乃《武》乐之乐歌,显然是正确的。由此,《武》乐之用诗,能确定的只有两首即《维清》和《武》。至于周公之乐《酌》是颂扬周公之治,所用之诗即《周颂·酌》。考察《酌》诗之意,很符合周公之德。对于《酌》之“遵养时晦”,《毛诗》曰“遵,率。养,取。晦,昧也”,这与《左传》所言的“耆昧”即治乱相一致,其中暗示周公对东南两方的经营治理;至于“实维尔公允师”,“尔”指武王、文王,句意如郑玄所说“所以举兵克胜者,实维汝之事信,得用师之道”,即周公把取得天下光明太平的功劳,追述给文王、武王。
至此,由《武》乐和《酌》乐组成的《大武》乐,所用颂诗可确定的只有三首:《维清》、《武》、《酌》。
[1]李山.周初《大武》乐章新考[J].中州学刊,2003,(5).
[2]姚小鸥.《周颂·大武乐章》诸篇绎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3).
[3]张国安.大武乐章新辨[J].励耘学刊,2005,(2).
[4]李炳海.《诗经·周颂》大武歌诗论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5).
[5]祝秀权.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J].扬州大学学报,2009,(3).
[6]郭人民.文王化行南国与周人经营江汜[J].河南大学学报,1980,(2).
[7]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J].音乐研究,1981,(1).
[8]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9]姚小鸥.论《周颂》·《三象》[J].中州学刊,1991,(5).
[1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1998.
K204
A
1001-4799(2012)01-0051-05
2011-06-19
刘全志(1981-),男,河南鹿邑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