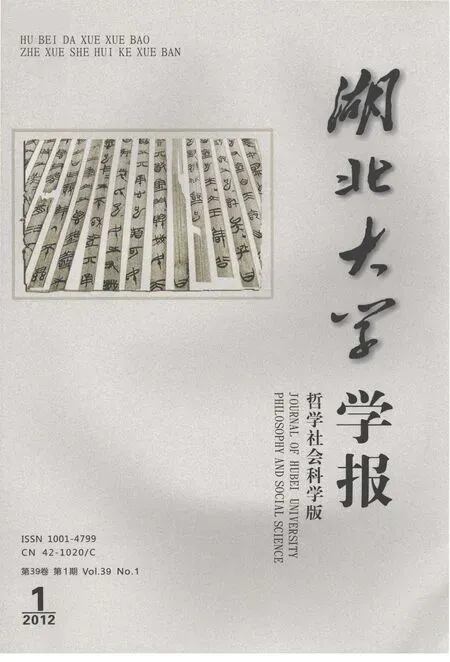屈原封号考论
2012-04-09龚红林
龚红林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屈原封号考论
龚红林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末五代封“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屈原;封号;神化;儒化;信仰
封号是古代帝王对已故的本朝或前朝忠臣烈士的褒崇典制之一。明代李奎《褒崇忠节疏》:“臣闻忠节乃万世之大贤,褒崇实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风伟节,足以感发人心,千万载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谊辟,举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谥追封,不忍使之泯没无闻于后。”[1]可见,三代以来即有封崇忠臣烈士之传统,其主要目的是以褒崇之典达到“正人心,厚风俗,扶植纲常,激励士类,为世道计”的政治风化效果[1]。朝廷褒崇贤臣功臣,可谓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文化天下”制度。
屈原作为历史文化名人,历代封赠及各地立祠祭祀不少。这表明屈原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学史,也影响及文化史。但是,关于历代屈原的褒封原因及演变,目前尚无专文论及。笔者详考历代正史方志、诗文笔记和碑刻庙记等相关史料,对晚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朝,屈原封号及用于庙额的情况进行梳理,或能祛疑。
一、敕封屈原始自晚唐
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唐哀帝李柷天祐元年(904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封屈原“昭灵侯”。
据考,历朝敕封屈原始自晚唐,应与唐末藩镇割据的动乱形势有关。屈原在唐代天祐元年(904年)封为“昭灵侯”时,正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此时,历史车轮已经到了唐朝历史的倒数第三年。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灭唐建立“梁”,史称后梁。值此乱世之秋,皇帝依从地方节度使的奏表敕封屈原。《旧唐书·哀帝本纪》载:“(天祐二年六月)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圯,臣复修庙宇毕,乞赐名额者。敕旨:……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2]593《册府元龟》载:“崇敕曰:楚三闾大夫屈原,正直事君,文章饰己。当椒兰之是佞,俾蕙茝之不香;显比干之赤心,蹑彭咸于绿水。虽楚烟荆雨,随强魄于故乡;而福善祸淫,播明灵于巨屏。名早流于竹素,功有益于州闾。爰表厥封,用旌良美。宜封为昭灵侯。”[3]1559
从封号及敕文内容,可以肯定,屈原正直事君的示范性触动了朝廷。在朝廷看来,敕封屈原,是继位之初提倡臣子赤胆忠心、舍身救国的契机;从地方官吏看,敕封屈原,既可利用屈原已有的民间信仰在乱世凝聚民心,护佑一方政权的稳定,又可向新君表白忠心,故而新官上任,常常奏请封赐地方庙宇和历史名人。
唐代首次封崇民间早已信仰祭祀千年的屈原,同样是唐朝祭祀典礼制度催生的结果。据考证,唐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始封各地祠庙:“诸祠庙:自开宝、皇祐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宋史》卷一○五《礼志·吉礼》“诸祠庙”)敕文称“播明灵于巨屏”,“明灵”指非阳间而又常护佑阳间生灵的天神或人神。古代楚地巫风甚炽,屈原流放沅湘之际曾根据当地巫歌,创编《九歌》;屈原投江后,湖南当地立祠纪念。今天汨罗端午于“屈原祠”内“龙头朝庙”,秭归端午唱“招魂曲”,均是奉屈原为神灵、相信屈原能主宰祸福的民间神灵信仰的遗迹。故,“昭灵侯”的封号,是民间屈原“神灵崇拜”的官方认同,是民间千年积淀的屈原信仰文化的第一次凝练。
二、后晋进封“威显公”
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937年)五月五日,屈原被进封“威显公”。《旧五代史》卷七十六《晋书·高祖纪》载:天福二年夏五月“丙辰……湖南青草庙旧封安流侯,进封广利公;洞庭庙进封灵济公;磊石庙旧封昭灵侯,进封威显公;黄陵二妃庙旧封懿节庙,改封昭烈庙。从马希范之请也”。北宋王溥撰《五代会要》卷十一“封岳渎”,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卷三四“崇祭祀第三”仍之。
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4]115天福二年夏五月壬子为朔,五月丙辰,即五月初五,端午节。在端午节封敕屈原庙额,表明五代民间、官方都已习惯将这一节日与纪念屈原相联系。正如唐代诗人所言:“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文秀《端午》)“磊石庙”即三闾大夫祠。考,今湖南省汨罗市仍设磊石乡,其地处汨罗市西北角,位于洞庭湖、湘江、汨罗江三水交汇处,地理位置接近今湖南玉笥山屈子祠。
“威显公”的封号首先将屈原的爵位由“侯”升为“公”,是屈原在朝廷推崇中的地位提升,也是马希范彰显自身政治地位的一种“隐形”方式。这从他呈请在其管辖境内的其他三庙有两庙封号均由“侯”升“公”可以看出。从谥号内涵看,“威显”是对屈原刚直弘毅的褒崇。苏洵《谥法》卷二记载追封为“威”有三种情况:“赏劝刑怒曰威。以刑服远曰威。强毅执正曰威。”在《离骚》等文中我们看到,屈原反复重申自己维护国家法度、不愿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九死不悔。这正符“强毅执正”的内涵。谥“显”表明,朝廷认为屈原德行品质可为后世楷模。《谥法》卷二:“显行见中外,曰显。”
马希范(899-947),字宝规。马殷第四子,继承其兄为“楚王”,都长沙。他为何要上表请封屈原庙等四庙?其一,与其继承父业有关。如前文所言,其父马殷曾向唐哀帝上表请封洞庭四庙。其二,与其自命不凡,发展继承“马楚文化”有关。《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后晋纪四》称其“喜自夸大”。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十八《文昭王世家》称他曾作九龙殿,“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龙也”。又载天福四年(939年)十一月马希范开“天策府”,选贤能做政治幕僚,倡导文学:“文昭以颖敏之姿,读书礼士,天策群英,几于梁苑邺下之选焉。”由此可见,屈原进封为“公”显然有地方官自显地位之“嫌疑”,而其请封为“威显”之功用,可能主要突出自己威加海内的政治企盼,取“以刑服远曰威”之“威”。但客观上则将民间对屈原神灵崇拜导向对屈原作为忠贞之臣“强毅执正”品行的褒扬。
三、宋神宗两次封屈原:“清烈公”、“忠洁侯”
北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封屈原为“清烈公”,见《宋史》卷一百五《礼志》、元·黄清老《清烈公庙记》、清《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祠庙附》等。
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三十日,敕封屈原为“忠洁侯”,亦即潭州屈原庙额,见《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宋史》卷一百五《礼志》。
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元年(1111年)七月二十七日后,屈原封号统一为“清烈公”。
宋神宗两次封屈原,封号各异,湖南称“忠洁侯”,湖北为“清烈公”。这给祭祀典礼带来混乱。所以,徽宗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秘书监何志同上书希望“取一高爵为定”。事见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九:“政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秘书监何志同言:详定九域龙志,内祠庙一门,据逐州供具到多出流俗……诸州祠庙多有封爵未正之处,如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如此之类,皆未有祀典该载,致前后封爵反有差误,宜加稽考,取一高爵为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宋史》卷一〇五《礼志》、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六《礼乐祭礼》、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三《吉礼·贤臣祀典》仍之。
南宋·范成大撰《吴船录》卷下:“(秭归)州东五里,有清烈公祠,屈平庙也。秭归之名,俗传以屈平被放,其姊女嬃先归,故以名。”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宋版集部”《楚辞(一函四册)》载:“是书刻于咸淳丁卯,系宋度宗三年,所绘汨罗山水图中,有清烈公庙及墓。”从文献记载和文物留存情况看,屈原封号的确在秘书监何志同上书后,以“公”比“侯”的爵位高而统一为“清烈公”。
元晋宗泰定(1324-1328年)初,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两次敕旨修葺秭归“清烈公祠”。元至正四年(1344年),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为其作《清烈公庙记》。
明清两代,湖北秭归屈原祠仍袭“清烈公”封号。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祠庙”载:“屈原庙,在归州东,一名清烈公庙。”清道光三年(1823年)熊士鹏《汉口丛谈序》云:“秭归为屈清烈公故里,旧有祠。”[5]1许印芳(1832-1901)有《归州屈原沱题清烈公祠二首》[6]219。这些均是明证。
1978年迁建后的秭归屈原祠,山门额题仍为“清烈公祠”。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湖北省》载:“屈原祠一名清烈公祠。……1978年迁至今地复建,计有山门、大殿、左右配房等建筑。山门为牌楼式,高14米,四柱三楼,正中门额题‘清烈公祠’四字。”[7]757今人李煌祖有诗《谒秭归清烈公祠》:“跋山涉水朝清烈,筚路临睨吊旧乡。千古国殇怜屈子,万方华裔唾怀王。”[8]185均可证“清烈公”封号至今犹存民间。
可见,“清烈公”是屈原封号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沿用时间最长的封号。为什么自宋以来千余年中,“清烈公”封号被如此看重呢?这里有什么历史文化原因吗?
先看“清”、“烈”内涵。何谓“清”?“清”与“浊”相对,本义指水碧绿无杂质,引申指人的品行高洁无邪念。如“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淮南子·原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书·舜典》)。《谥法》卷三云:“避远不义曰清。伯夷与其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而孟子以为清,故云。”《谥法》“清”指远离不道义的事情,如商末孤竹君之长子伯夷见人帽子戴得不正就离开远去,保持自己的清白。屈原远离不义的经典记述表现在与渔父的一段对话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屈原宁愿以死明志:“伏清白以死直兮。”(《离骚》)“清”是儒家君子品格的要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儒家圣哲以“不为不义”为“清”。宋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时期,褒封屈原“清”正是从儒家君子品格角度对其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远离不义的高洁品行的肯定和褒扬。
何谓“烈”?“烈”本义指火燃烧旺盛。《说文》:“烈,火猛也。”《诗·商颂·长发》:“如火烈烈。”引申义指光明、显赫。《国语》:“君有烈名。”《诗·周颂·载见》:“休有烈光。”再引申指功业。《汉书·王莽传上》:“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又引申指为功业而死难,或性格刚直之人,如“烈士”、“烈女”等。《谥法》卷二:“安民有功曰烈。秉徳遵业曰烈。”明·郭良翰撰《明谥纪彚编》卷二《谥法上》补充:“戎业有光曰烈;刚正曰烈。”屈原赞橘树:“秉徳无私,参天地兮”、“深固南徙,更一志兮”(《橘颂》),正是屈原自己秉徳遵业、刚勇正直品格的写照。
宋代封屈原为“清烈公”、“忠洁侯”,其“清”中寓“洁”、“烈”中见“忠”。“清刚”、“忠直”是人臣之高风亮节。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序》:“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朱熹《楚辞后语》卷二:“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於辩论而自显。”宋代学者和统治者从封建君臣伦理角度以儒家圣贤的标准来评价屈原,是屈原精神的“儒化建构”。这既是对汉代王逸“以儒注骚”模式的继承,又是中国儒家政治伦理制度日趋成熟的必然产物,是屈原精神在士大夫阶层的弘扬和传播。历朝对“清烈公”封号的沿用,彰显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屈原信仰文化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广泛认同。
四、元仁宗封屈原“忠节清烈公”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七月三十日,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载:“(延祐)五年……七月……戊子……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元纪十七》、清·徐干学撰《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五《元纪》十三“仁宗圣文钦孝皇帝”、清《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祠庙附”、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群庙考》仍之。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4]153元延祐五年(1318)七月己未为朔,戊子为三十日。
据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群庙考》可知,屈原是被作为忠臣名相予以敕封的,仁宗对已故名臣殷比干、唐狄仁杰祠都曾敕旨修缮祭祀:“仁宗皇庆元年三月,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延祐三年四月,敕卫辉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杰祠,岁时致祭。五年七月,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
作为封号的“忠节”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先看“忠”,《谥法》卷三:“盛襄纯固曰忠。临患不忘国曰忠。推贤尽诚曰忠。廉公方正曰忠。”可见,谥“忠”主要表彰四个方面的功德:努力为国,纯洁坚定者;面临祸患,不忘救国者;推荐贤才,竭尽诚意者;廉洁公平,耿介正直者。再看“节”,《谥法》卷二:“好廉自克曰节。谨行节度曰节。”即:对待外物,要廉洁,克制欲望;对待事情,要谨慎而行,不要过度。“忠”、“节”二字合用,表明对于国家忠诚不二、对自己要求严格,克己奉公,做人做事“心忠,行节”。
“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忠”置于封号之首,是元代以儒治国背景使然,亦是对汉宋以来就逐渐被认同的屈原信仰之政治道德价值的强化。其后,屈原之“忠”倍加推崇。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清老《清烈公庙记》说:“愚观屈公,事君尽忠,死而不二,卓然立于穹壤,如三仁、夷齐,千百载仅一二。”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
将屈原作为“政治楷模”加以祭祀崇拜,推崇屈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离骚》),推崇其“忠信”于君国的精神品格,固然是封建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屈原在民间和士大夫精神上的文化凝聚力在增强。
五、明太祖复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敕湖南汨罗屈原庙复号“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六十三“长沙府”载:“屈原庙:在湘阴县北六十里,原事楚王被谗见疎,投汨罗江以死。唐封昭灵侯,宋封忠洁侯,本朝复其号曰: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岁以五月五日。”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八十五“礼部四十四祭祀六”“湖广”亦载:“湘阴屈原庙,今称: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按,“湘阴”今隶属湖南省岳阳市。有明一代,湘阴汨罗屈子祠几经翻修。一次是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湘阴县事戴嘉猷重修汨罗屈子祠,其《重修汨罗庙记》未提屈原封号。一次是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年),余自怡任湘阴县事重建三闾祠,七年(1635年)秋立碑,所撰《重建三闾祠碑记》亦不提各代封号。
考,明代不再加封屈原的原因来自朱元璋。明代立国之后,朱元璋对历朝礼制封号进行全方位的整治,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声教不同。朕奋起布衣,以安民为念,训将练兵,平定华夷,大统以正。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定,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9]127朱元璋从元代统治失控中意识到礼制封号的政治功用——“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因而,立国不久即对自唐代以来各类祀典封号加以整肃。对山川河流、忠臣烈士的封号,去“后世溢美之称”,恢复“初封”。屈原亦在其列。
剔除前代加在屈原身上的“灵威”、“清烈”和“忠节”之号,恢复其作为臣民“三闾大夫”本初的身份并尊为“神”。好像是民间神灵信仰的回归,又似乎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屈子送还给了民间。而实际,“楚三闾大夫屈平氏之神”之号包含了宗国、官职、神位三个元素,巧妙地将朝廷对士大夫的忠君旨意与士人希望显宗耀祖、护佑百姓、青史留名的愿望有机统一,全方位地涵盖了屈原信仰的政治需求。真可谓“看似平常最崎岖”!
六、清代封号“靖楚江王”、“忠烈王”非“信史”
清代封屈原为“靖楚江王”,待考。浙江临海《屈氏家谱》之“临海屈氏家谱历代仕宦录”载:“‘平公’……号正则,仕楚,封三闾大夫,唐封昭灵侯,宋封忠洁侯,清封靖楚江王。’”[10]今安徽东至县“屈原纪念馆”陈列据说是清代帝王敕封的銮驾和“靖楚江王”牌[11]。
考《玉历钞传》载:丰都十王殿第二殿主管称“楚江王”,又称“初江王”,三月初一生辰。司掌活大地狱,下设十六小地狱。从秦广王殿解下来的罪鬼,按罪恶轻重,在此给予不同刑罚[12]439。故,在暂无其他材料证明下,屈原的这一封号有待进一步考详。
清封屈原为“忠烈王”,乃小说家言。一些资料称屈原“清朝又封为忠烈王”[13]164。考,此封号最早见《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三回“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其文曰:“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髯翁有《过忠烈王庙诗》云:峨峨庙貌立江傍,香火争趋忠烈王。佞骨不知何处朽,龙舟岁岁吊沧浪。”[14]886按,《东周列国志》原名《列国志传》,明余邵鱼根据元代话本改编,后经冯梦龙、蔡元放删改为《东周列国志》并加评点。“髯翁”在《东周列国志》有多处诗评,一般认为即作者冯梦龙,若是如此,他如何得知清代的封号?故,在无其他正史笔记可佐证的情况下,屈原“忠烈王”封号乃小说家言或民间传说,不足为信。
尽管有清一代未曾给予屈原任何新的封号,但是雍正九年(1731年)已规定地方县官春秋二季定期到汨罗屈原祠祭祀。
从历朝对屈原的封号可见,正统意识形态对屈原示范性的倡导主要着眼于两个价值层面:唐末五代封号“昭灵侯”、“威显公”,其核心元素“灵”与“威”吸取了民间屈原信仰的精髓,是屈原“神灵”化民间信仰的肯定与提炼,又促进了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宋代封号“清烈公”、“忠洁侯”,元代封号“忠节清烈公”,“侯”晋升为“公”,屈原被官方作为“政治楷模”的倾向明朗化,其核心元素“忠”、“洁”、“清”、“节”、“烈”挖掘了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从而奠定了屈原在士人阶层的伦理政治层面信仰的基石。这两个价值层面,即作为“民间灵威之神”的宗教价值、作为“士人清烈忠节楷模”的政治伦理价值,可视为在历史上官方正统意识对屈原信仰文化内在构成的理解。封崇屈原固然是封建皇权政治维系其根本的政治策略,但客观上,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屈原在民间和士人精神信仰上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1]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五[DB/CD]//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2]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校订本[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4]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5]范锴.汉口丛谈校释[M].江浦,等,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6]许印芳.五塘诗草:卷四[M]//丛书集成续编·一八一·文学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7]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名胜词典·湖北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8]李兴,蒋金流,等.屈原颂:下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9]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0]屈原后裔寻访之五:长沙城里论屈原——专访湖南“史学奇才”何光岳[EB/OL].http://www.zigui.gov.cn.[2009-10-28]8:9.
[11]余育章.第一座由屈原后裔建造的屈原纪念馆落成[EB/OL].http://www.sina.com.cn.[2001-12-12]16:57,合肥报业网-合肥晚报.
[12]曹英.中国神秘文化鉴赏大全:上[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13]郑土有.中国民俗通志:信仰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14]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蔡元放,修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I206.2
A
1001-4799(2012)01-0028-05
2011-03-29
龚红林(1974-),女,土家族,湖北五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