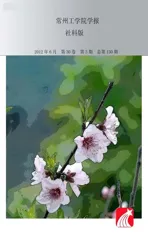论《亚瑟王之死》的世俗性与宗教性
2012-04-02陈莉
陈莉
(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 兴义 562400)
《亚瑟王之死》是马罗礼于1469年完成的一部巨著,属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是亚瑟王系列传奇的集大成之作。该作品围绕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们的冒险经历和感情纠葛展开叙述,反映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骑士“大体出现于公元8世纪初期,最终消亡于公元17世纪初期”①,是中世纪欧洲特有的处于统治阶级最低层的一个阶层。该阶层的行为观念有着较强的世俗性。由于中世纪是基督教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基督教将一切都纳入了宗教的范畴。因此骑士精神和行为规范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所以,世俗性与宗教性并行于骑士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之中,也集中体现于《亚瑟王之死》这部作品之中。
一
《亚瑟王之死》的世俗性首先表现在骑士强烈的荣誉观上面。骑士将荣誉看得高于生命,终其一生都在为荣誉而奋斗。但他们对荣誉的追求并非为了死后灵魂的得救,而主要是为了在现世生活中加以彰显。骑士获取荣誉的动力在于为自身,为国王或为情人而非为上帝。骑士们经常让降服的骑士去向国王或自己的情妇投诚而非向上帝忏悔。郎世乐就曾坦言:“我打了多少次战争,从没有一次专为上帝而打的,只不过为了获得尊荣,和赢得她更多的爱而已,以致我很少甚至不曾感激过上帝。”②郎世乐口中的“她”即指亚瑟王的妻子桂乃芬。郎世乐作为圆桌骑士中最有威名的一个,他为自身和情人去建立功名的观点代表了骑士普遍的价值观。骑士获得荣誉的方式也主要集中于冒险经历、比武、战争等而非禁欲苦修。亚瑟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大部分时间在外游历,以求获取奇迹,赢得荣誉。冒险经历伴随着惩奸除恶的正义性,也伴随着武力的残暴——骑士们杀掉对方或是被杀。例如郎世乐骑士在游历中遭到一位守桥骑士的攻击,“郎世乐骑士急忙拔剑,还回一击,这下正巧落在他的头上,因为剑锋太利,一直砍到胸膛。”③而为了获得荣誉,骑士们还经常举行大型的比武,赛场上,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战场上,勇武的骑士为了荣誉,勇往直前,直杀得尸横遍野。亚瑟王一生征战无数,在他与罗马皇帝的对战中,“亚瑟王觉得自己受了伤,立即举起截钢剑回击过去,不想正砍在了他的头上,由头顶一直劈到胸脯。这时罗马皇帝倒地身死……亚瑟王率着全体骑士在后追赶,当然沿途所经,凡能够消灭的人,绝不会放走一个。因此,亚瑟王大获全胜,而卢夏诗方面被杀的约计在十万人以上。”④这种血腥暴力场面的描述,不禁让人想起《荷马史诗》中的战争场景。古希腊时期文明较为低下,人们大都凭着自己的本性行事,较少道德规范制约。而《亚瑟王之死》中的骑士们虽处于中世纪,却仍旧表现出人性的残忍和对世俗权力的争夺,缺乏宗教文明的规约。
其次,作品的世俗性还表现在骑士对情爱的追求上。骑士们对贵妇的爱远远超越对上帝的爱。爱情是骑士获取荣誉的主要动力。巴乐米底深爱着马尔克王的妻子绮秀·婉儿,而后者又与崔思痛两情相悦。虽然,巴乐米底从未得到过王后的青睐,但他却一直将其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动力,“我爱绮秀·婉儿已经很久了,她是我一切成功的策动力,假若没有她,我在这世界上也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罢了。我受她那伟大的女性感染,正为了她的缘故,我才得以建树了以往的功绩。”⑤巴乐米底从未掩饰过对绮秀的爱情,并且努力去赢取这份爱情,除了在有绮秀观战的比赛中英勇表现之外,还找寻一切机会与情敌崔思痛比试,可最终他也未能得到绮秀的芳心。巴乐米底对绮秀矢志不渝的爱情令人动容,值得注意的是,巴乐米底在追爱的过程中饱尝心灵的煎熬,但他却从未因为此种情爱违背上帝的戒律而陷入矛盾之中,他痛苦的唯一来源在于他爱上了一个已经心有所属的女人。由此可见,在对情爱的追求上,巴乐米底并未将上帝的规约放在心上,他的心里只有爱情。在《亚瑟王之死》中,如巴乐米底这般令人叹惋的爱情绝非个例。崔思痛与绮秀、郎世乐与桂乃芬之间的爱情都堪称缠绵悱恻。崔思痛和郎世乐同为圆桌骑士中出类拔萃之人,并都爱上了王妃。在战场上,他们从未胆寒退却过,但在情场上,他们却为心爱的人而癫狂发疯。崔思痛和绮秀最后为情而死。郎世乐为救桂乃芬不惜背叛亚瑟王与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这种爱情并非所谓的“典雅”之爱即纯粹的精神之爱。除了巴乐米底之外,郎世乐和桂乃芬,崔思痛和绮秀之间都有肉体关系,这两对恋人除了平时偷情之外,更曾有一段时间公然住在一起,双宿双飞。而这样的行为丝毫不影响两位骑士成为公众爱戴的对象。郎世乐与王后的奸情败露之后对亚瑟王宣战,振臂一呼,居然应者众多,人数与亚瑟王的军队形成势均之势。马尔克国王力求除掉情敌崔思痛,却遭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差点引发国内叛乱。不难看出,人们对爱情是极其肯定的。整部作品所描写的骑士众多,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贵妇有染,当中有如崔思痛般真挚的爱情,也有仅仅是肉体关系的情爱。更可笑的是,在追寻圣杯奇迹中,骑士们居然想带上自己的情人同行。如此滑稽的举动,若非是宗教观念的淡薄,便可谓是对宗教观念的讽刺和反叛了。纵观作品,在对世俗情欲的强烈追寻中,上帝隐退了。
二
为荣誉而战,为情欲而死,这幅图景让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可《亚瑟王之死》毕竟产生于中世纪,人们不可能完全像古希腊时那样任人性自由流淌。中世纪宗教的巨大力量让骑士精神有别于古希腊时的英雄伦理,使骑士们的世俗追求中渗入了宗教精神。宗教对骑士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骑士规范之中。亚瑟王曾训示各位骑士:“永不得暴虐或谋杀,要远离叛逆;绝对不可残忍;凡向你乞怜的人,你要宽恕他……对于各等妇女,比如贵妇、名媛、小姐们,你们都要帮助她们,否则即处以死刑;而且,凡是违背律法,而由胡乱叫嚣所引起的战争,或是抢夺民间财富所造成的战争,你们之中,决不许有一人参与。”⑥这些规约是由各圆桌骑士公认并立誓遵守的。虽然这些规约中并未明确提出要信仰上帝,但其中所包含的仁慈、宽恕、忠诚、博爱的思想却明显具有宗教色彩。这些规约成为了骑士行为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的评判标准。例如葛汉利兄弟趁自己的母亲与拉麦若克偷情之时,杀掉自己的母亲,后又设计从背后偷袭拉麦若克致其死亡,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谴责。而卡文英杀掉了向他求饶的骑士,因而招致弟弟的责备。
作品中宗教色彩最为浓郁的地方在追寻圣杯一事上。圣杯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盛放其鲜血的容器。这是基督教的圣器,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治愈伤痛,可以带来美食等等。于是,能否取得圣杯便成为了骑士是否符合宗教规范的具体化的标准。因而追寻圣杯的过程便成为检验骑士是否具备宗教精神并努力向宗教信仰提升的过程。从追寻圣杯开始,骑士们便不断遇到幻象,而这些幻象都具有象征性,隐喻基督教的观念,例如禁欲、仁爱、节制等。它们加强着骑士们的宗教观念,并成为骑士们的内在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于是,郎世乐因为爱慕虚荣且有奸淫之罪,整个追寻过程便成为其忏悔的过程,薄希华、卜尔斯和高朗翰都受到女色的引诱,而他们都抵制住了这种诱惑。三人曾在一堡寨大肆杀戮,但之后立即觉得自己“万恶滔天”,直到得知这乃是上帝的意愿时方才安心。最终,郎世乐因其虔心悔过,得以目睹圣杯,但却不能接近。而卜尔斯终身只与一个女人有染,薄希华和高朗翰则始终保持着童真,尤其是高朗翰不仅童真而且完全无罪过。因而他们三人得以接近圣杯,高朗翰的灵魂还升上了天堂。可见,对圣杯的接近程度是以骑士对上帝的信仰程度为标准的。追寻圣杯的冒险经历已不同于骑士以往的历险,骑士行为的准则不再是世俗的追求而是宗教的规约。
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亚瑟王之死》对骑士的描述既包含了世俗的观念也有浓厚的宗教思想。而这两种观念几乎是并行的。在骑士的规范中有对基督教思想的肯定,例如仁爱、忠诚等。在对圣杯的追寻中,骑士们也有对上帝的虔信,将宗教规约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努力寻求灵魂的得救。但在骑士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更为看重骑士的荣誉和甜美的爱情。这意味着骑士的世俗性和宗教性并没有合二为一。宗教性更没有凌驾于世俗性之上。整个作品描写对圣杯的追寻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描写骑士的冒险和爱情。这也使作品带有更为浓厚的世俗性色彩。当然,在对世俗荣誉和情欲的张扬中,骑士也会将上帝挂在嘴上,以上帝的名义去冒险、复仇、打仗、比武甚至恋爱,而这些恰恰又与上帝的规约相违背。由此可见,上帝只是存在于骑士的嘴上而非心里。骑士只是假托上帝之名让自己的行为显得更神圣,而他们实际上却并非按上帝的戒律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摒弃上帝的,上帝对他们仍有一定的约束性。亚瑟王在平定内乱时,杀人无数,“他手拿盾牌,剑上染满了脑浆血迹,几无人能认出他了。”后魔灵警告他:“您向来杀人,不厌其多!您如今可杀够了!今日您把六万人杀到只剩下一万五,也应该停手了吧!上帝对您已经发怒了。”⑦正是忌惮上帝的怒火,亚瑟王宣布停止了战争。亚瑟王与自己的胞姐同床,生育一子,而这也触犯了上帝,最终导致了亚瑟王的毁灭。伯林诺王急于追寻奇迹而未出手救助一位骑士,造成骑士和妻子的双亡,上帝因此而给予其惩罚,让他被最信任的人所背叛。艾佛莱克国王因为过于靠拢圣杯而触怒上帝,因而遭受巨大的伤痛。在整部作品中,如此这般“罪”与“罚”的描写较多。也正因为“罪”很多,我们可以看到,骑士对于上帝的信仰并未深入内心,否则,他们会将上帝的规约作为内在的约束力,也就不至于屡屡触犯上帝,导致严重的后果了。事实上,作品中屡次写到,按照上帝的标准去衡量世人,真正笃信上帝的纯洁之人是非常少的。在追寻圣杯的奇迹中,所有的骑士中只有高朗翰能真正接近圣杯并升入了天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笃信上帝,完全纯洁无过错。在用杯子来检验女人贞洁的测试中,一百个贵妇只有四个人能喝光杯子里的酒,可见,真正对丈夫忠贞的女人是微乎其微的。而一个出轨的女人就对应着一个偷情的骑士。再以郎世乐为例,他是圆桌骑士中最了不起的骑士,一生赢得荣誉无数,并与亚瑟王的妻子桂乃芬有染。在追寻圣杯奇迹中,上帝因为他爱慕虚荣和通奸行为而剥夺了他获取圣杯的功绩,只允许他远远观望一眼。于是郎世乐深自悔悟,决心从此虔信上帝,开始了禁欲苦修。但回到朝廷之后,郎世乐“又同桂乃芬王后开始暧昧起来,把追求圣杯的时候,要保持身心纯洁的誓言,置诸脑后”⑧。奸情败露后,他揭竿而起与亚瑟王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他认为:“王上啊,若是我容忍您把王后桂乃芬烧死,即使她应该为着我的缘故被焚,那么我这骑士的光荣身份便丧失殆尽了。”⑨由此,他不仅背叛了上帝还背叛了君主,只为保有骑士的荣誉和自己的情人。在郎世乐看来,世俗荣誉和情人是高于一切的,为了他们,他可以完全挣脱宗教的束缚乃至于一切的束缚。
可见,《亚瑟王之死》包含了世俗性和宗教性,而世俗性似乎更为浓厚。宗教思想融入到骑士规范中,但骑士并未严格按规范行事。圣杯追寻与其说彰显了宗教的力量,不如说更清楚地反映出宗教的式微。骑士精神中更主要的是世俗的追求。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骑士是随着骑兵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而兴盛起来的,他们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会使其更为看重军人的荣誉,显得更为暴虐。正如约翰·赫伊津哈所说:“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崇高的尘世生活的形式可以视为一种带有伦理理想外表的美学理想。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其基础。但中世纪并不允许高贵的生活形式脱离宗教而存在。因此,虔诚和美德应当是骑士生活的本质。但是,骑士精神始终缺少宗教的伦理功能。它的尘世的起源摒弃了这一点。”⑩其次,骑士是在日耳曼人的长期征战中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更多继承了蛮族人的文化价值观:“蛮族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态度是所谓‘英雄式’的:好战、勇敢、忠诚、重视荣誉……等等。”再次,《亚瑟王之死》写成于15世纪末期,此时文艺复兴已经兴起,人们开始以人性反神性,肯定人的天然情感和欲望,“骑士叙事文学产生的时代,10世纪之前那种愚昧的信奉基督教,处处以基督教的戒律来严酷规范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增长了。”基于以上各点,《亚瑟王之死》表现出更为浓郁的世俗性色彩。
注释:
①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英)马罗礼:《亚瑟王之死》,黄素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87页,第215页,第183页,第679页,第112页,第30-33页,第898页,第1 004页。
⑩(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舒炜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