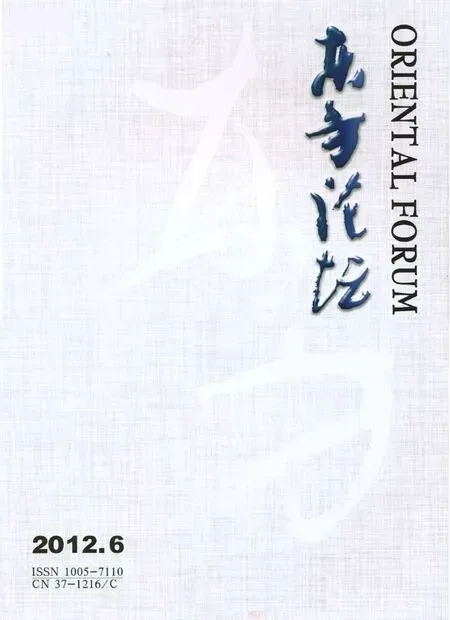李开先文学思想综论
2012-04-01刘铭
刘 铭
李开先文学思想综论
刘 铭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李开先是明中后期文学理论领域,尤其是曲论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综观其文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复古而不泥古、 强调文学的真情实感、 提倡南北文学风格的融合以及强调文学的自然、 通俗等。这其中包含有许多新的理论因子,对于明代中期的文坛,乃至影响深远的晚明文学思潮来讲,都具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李开先;文学思想;价值;影响
李开先是明代中期山东著名的文学家,其终生抱有“经世”的思想,没有在“立言”而不朽于后世上投入过多的精力,故其作品随笔挥洒者多,精雕细刻者少。而其文学思想一如其作品般散漫而不成系统,多在其序文中有零星的涉及。不过,我们却不可以因此而轻视李开先文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经过我们的爬罗剔梳,刮垢磨光,还是能够整理出其文学思想的大体脉络的。而其文学思想中也多有闪光之处。如《词谑》一书,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是明代从朱权《太和正印谱》以来第一部有关曲论的著作,承前启后的意义不可磨灭。李开先应当是明中后期文学理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
一、 复古而不泥古
李开先一生横跨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四朝。这一时期,文坛正处于复古思潮的笼罩之下,复古正是这一时代文人所倾心追求的审美风范。文坛上,茶陵派、 前后七子,唐宋派等主流的文学流派,无论主张如何,其实质都是在复古,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所学习的古人不同,程度不同罢了。
茶陵派的李东阳不满台阁体装点太平,内容空洞而技巧平庸的诗风,转而推重杜诗,提倡严羽的诗论,对诗歌的体制、 音律、 声调等形式技巧,颇为重视。然而,这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文坛的萎靡之风。李开先曾经批评道: “诗靡于六朝,而陈子昂变其习,文敝于八代,而韩退之振其衰,国初诗文犹质直浑厚,至成化弘治间而衰靡极矣。自李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材取软滑者,不惟诗文趋下而人材亦随之矣。”[1](集之十)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为了一洗文坛的劣习,更是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2](卷三百八十八)。这种更加彻底的复古思想,虽然对当时的诗风与文风有一定程度上的振衰起敝之功。但是,他们强调尺寸古法,对前人之法式亦步亦趋进行模拟的做法,又走入了泥古的极端,甚至滑向了剽窃古人的泥潭。这又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他们力图纠正这种现象。《列朝诗集》丁集上云: “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3](丁集卷一)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亦云: “大抵李何振委靡之弊,而尊杜甫,后冈则又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两浙以文擅天下,后冈乃两浙之首岀者也。”[1](集之十)“嘉靖初,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与罗达夫、赵景仁诸人,左提右挚,李、 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3](丁集卷一)可见,唐顺之、 王慎中、 陈束、 李开先等为代表的闻名明中期文坛的“嘉靖八子”中的青年才俊们,就是想用学习初唐之诗,提倡唐宋古文的办法,来“矫李、 何之习”[4](卷一百七十七),以救正李梦阳、 何景明等所提倡诗风中的泥古之失以及前七子文风之弊。
李开先与前七子中的康海、 王九思有忘年之交,对李梦阳、 何景明也是景仰有加,他甚至亲自为边贡编订诗集。而他与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也是关系颇密,唐顺之、 王慎中、 茅坤更是其好友。与这些人的交往,耳濡目染中,既使李开先文学思想中具有了较为浓厚的复古倾向,同时又能看到他们的不足,而使他不至于走上泥古的极端。
李开先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在其序跋作品中多有表现。《昆仑张诗人传》云: “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予应以‘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1](集之十)李开先赞同张诗诗作的拟古倾向,其说法与“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出,李开先诗文观念中的复古思想还是颇为浓厚的。
李开先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在曲论领域则更加突出和集中。《西野春游词序》云: “传奇戏文虽分南北,套词小令,虽有短长,其微妙则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资学力耳。然俱以金、 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何也?词肇于金,而盛于元,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乐于心而声于口,长为之套,短为之令,传奇戏文,于是乎侈而可准矣。”[1](集之六)
李开先推崇金元之曲,认为它们“辞意髙古”[5](P462),“乐于心而声于口”,可谓自然天成,直抒胸臆,表达真情实感,后世曲作以金元之曲为标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是毋庸置疑的。其又云:“或以为词小技也,君何宅心焉,嗟哉!是何薄视之而轻言之也。音多字少为南词,音字相半为北词,字多音少为院本。诗余简于院本,唐诗简于诗余,汉乐府视诗余则又简而质矣。三百篇皆中声,而无文可被管弦者也。由南词而北,由北而诗余,由诗余而唐诗,而汉乐府,而三百篇,古乐庶几乎可兴。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呜呼!扩今词之真传而复古乐之绝响,其在文眀之世乎。”[1](集之六)
这里李开先对轻视曲作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梳理了曲的源流,为之找到了正统的宗脉,即《诗经》之“三百篇”,并借用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的说法,将曲作拉上了儒家正统文学的轨道,对那些以曲为末技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又认为可以“扩今词之真传而复古乐之绝响”,通过继承和发展,曲作完全可以起到与诗文等正统文学一样的教化作用,起到扭转社会风气,让世风日下的社会达到所谓的“文明之世”。虽然李开先的这种复古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努力提高曲作地位的动机还是值得赞赏,有功于后世的。
李开先与前后七子、 唐宋派的骨干成员虽然有着密切的私交,而且他的文学观念中也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复古思想,但他又始终与他们极端的复古思想保持着距离。他对那些极端复古思想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对那种“于诗文犹少见本相”[1](集之十)的情况给予激烈的批评。《咏雪诗序》中其云: “我朝自诗道盛后论之:何大复、 李崆峒遵尚李、 杜,辞雄调古,有功于诗不小。然俊逸、粗豪,无沉着、 冲淡意味,识者谓一失之方,一失之亢。”[1](集之六)《对山康修撰传》亦云: “古人言以见志,其性情状貌求而可得,此孔子所以于师襄而得文王也,要之自成一家。若傍人篱落,拾人唾咳,效颦学步,性情状貌洒然无矣,无乃类诸译人矣乎。君子不作凤鸣,而学言如鹦鹉,何其陋也。”[1](集之十)又, 《李崆峒传》中云: “责备者犹以为诗袭杜而过硬,文工句而太亢。当软靡之日,未免矫枉之偏而回积衰,脱俗套,则其首功也。”[1](集之十)等等。
可见,李开先主张复古,是主张学习古人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精华,反对对古人语言形式的剿袭模仿。那种邯郸学步,桎梏于古人形式技巧,乃至剽窃古人字句,创作出的“粉装骷髅”式的作品,其是嗤之以鼻的。虽然,李开先的这种主张难以挽救极端复古思潮笼罩的文坛,但毕竟为之注入了一丝活力,如死水泛起的微澜,其作用和价值还是值得注意的。
二、 强调文学要抒发真情实感
明代中期,经济与政治都在发生着一定的渐变,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市民队伍逐渐壮大,市民的生活风气本已渐渐侵蚀着此时的社会风气与士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而王阳明“心学”对于主体精神的强烈提倡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中,尤其是文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以理限情”的思想也就遭到了许多文人越来越激烈的批评。他们主张文学应达到情与理的统一,这一古典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之一,从而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6](P8-12)李梦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李梦阳云: “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7](卷五十一)又云: “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7](卷六十六)可见其反对以理限情,主张情与理的统一的立场。而情与理的统一,就要抒发自己真实的情感。李梦阳向往唐调,就是因为他认为唐诗是古典审美理想的完美结合,是情与理的统一,可以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然而由于李梦阳太拘泥于对古诗的字袭句模,使其诗歌难以达到自己追求的古典审美理想,也限制了诗歌对真情的表达。后期的他也意识到了前作之失,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对王叔武“真诗乃在民间”的提法,大为赞赏,认为“若似得传唱《琐南枝》, 则诗文无以加矣”[5](P1276)。李梦阳对民歌的大加提倡,很重要的因素是其欣赏民歌的“真情”。诚然,能更好地抒发真情实感,则的确是民歌之长处。
在用文学抒发真情实感这一方面,李开先与李梦阳是一致的。《海岱诗集序》中其云: “而画亦有诗理焉,移生动质,变态无穷。蕴彩含滋,随心写象。纵横神妙,烘染虚眀,此画之大致也。诗则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声附气,调逸词雄,情幽兴远,风神气骨,超脱尘凡,非胸中备万物者不能为诗之方家,而笔端有造化者始可称画之国工矣。”[1](集之五)为画者,要用“纵横神妙,烘染虚眀”的多种技巧,来表现“移生动质,变态无穷,蕴彩含滋”的大千世界。最关键的是“随心写象”,即表现画家的真情实感。而为诗者,要做到“调逸词雄,情幽兴远,风神气骨,超脱尘凡”的美好境界,最关键的也是“感物造端,因声附气”,即表现真实的情感。
李开先进一步指出,“忧而词哀,乐而词亵,此今古同情也。”[1](集之六)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就是要直接表现人内心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西野春游词序》中,李开先更是将散曲分为“文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并表现了对那些只注重形式技巧,雕琢章句,而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的“文人之词”的不满。
李开先还积极响应李梦阳对民歌的推重,指出: “正德初尚《山坡羊》, 嘉靖初尚《锁南枝》, 一则商调,一则越调。商,伤也;越,悦也,时可考见矣。二词烨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篇》太平采风者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1](集之六)
李梦阳响应“真诗乃在民间”,李开先则进一步推进,认为“真诗只在民间”,而且李开先明确了所谓的真诗,就是要“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是作者最真实情感的流露。
这显然比之李梦阳的主张更进一步,与之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还没有人能有如此明确与具体的提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开先还第一个整理元代杂剧,第一个刊刻民歌集《市井艳词》, 第一个学习民歌经验来创作散曲等等。这样,身处明代中期文学观念嬗变之际的李开先,用自己的行动,为李梦阳等人提倡的向民间学习,文学民间化的运动推波助澜,这对当时垄断文坛的精英意识,有着巨大的冲击作用。仅从此也足见李开先之主张在明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三、 文学贵自然、 通俗
“自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这一范畴有着较多的论述。《原道》: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8](卷一)《明诗》亦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8](卷二)刘勰认为,无论是对自然万物的描写,还是抒发内心的情感,都要合乎“自然之道”,即做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学要“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要让内心真实的情感,自然地从胸臆中流出。文学不是不可以讲究词采,关键是不要因过分追求藻饰而使情感的表达不能自然灵动。
李开先主张文学以自然为贵, 《中麓画品·序》云: “事无巨细,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矫揉造作焉者。”[1](集之六)这种理论与刘勰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写物还是抒情都要从内心的真实情感而发,做到“情与景会”[1](集之五),“文意遇而自然成之”,“若出自信口,字句浑然天成,无雕琢之迹,有金石之声”,[1](集之六)“诗不必作,作不必工。或抚景触物,兴不能已;或有重大事,及亲友恳求;时出一篇,信口直写所见。”[5](P39)只有这样,作品“是则可传,传而可远”[1](集之六)。而对“后世拘声律,分门类,严偶仗,骈四骊六,抽黄对白,而自然之文意漓矣”[1](集之六)的状况,李开先提出了批评,“由盛唐而初,由晋魏而汉以至乎三百篇,质而不文”,而明代“初犹尚质,而后则渐文”,李开先则“独恶其日趋于文,而无用于世”[1](集之六)。
在李开先生活的时代,其好友唐顺之等为首的唐宋派,提出了“本色”的理论。唐顺之《与洪方洲书》云: “文章稍不自胸中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熔,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的字句。”[9](卷七)“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贱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9](卷七)“好文字与好诗,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见者与人自别,正不资籍此零星簿子也。虽古之以诗文名家者,其说亦不过如此。”[9](卷七)唐宋派所主张的“本色”,简而言之就是,重质轻文,提倡质直平易,直抒胸臆,反对藻饰虚浮。如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中所云:“其为文者,则应以始尊秦汉,继好宋唐,必须完养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经传,以愽其旨趣,独存本质,尽洗铅华,透彻光明,委曲详尽,虽从笔底写成,却自胸中流岀,如说家常话,而作家庭书,所谓见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1](集之十)又, 《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补传》: “识者谓其文理致精深,有发自自得者。”[1](集之十)
这与李开先主张自然天成,反对过分矫饰的理论,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难怪当王慎中写信说李开先: “新来独得为文之妙,兄虽海内报相契,而于此文①按,此处王慎中所讲的“此文”,指的是欧阳修、 曾巩之文。有不能共其味者矣!”李开先颇不以为然,认为: “然不知其正相同也。”[1](集之十)可见,李开先认为自己的文章和唐宋派并无根本上的区别。
但是仔细推究起来,李开先与唐顺之之文虽然在讲究自然天成方面有神似之处,但从内容取向与精神实质方面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唐文致力于性命之学,理学精神,其提倡的本色之论,也只是明道的一种方式而已,难脱道学的羁绊。而李开先认为自己为文之本色,只是他提倡的文学俗性,在语言形式上等方面与唐文契合,而其内容则随心所欲,多指向生活琐事,人伦之情,真挚感人,却难掩琐屑,与唐荆川弘扬道学的精神取向还是有相当距离的。而李开先这种为文之法实际上是对唐宋派本色论的一种发展。
李开先重视通俗文学,而且强调文学作品的“俗性”。其在《改定元贤传奇序》中云: “南宫刘进士濓尝知杞县事,课士策题问:‘汉文、 唐诗、 宋理学、 元词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1](集之五)李开先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没有能够给出答案。而陈宏绪在《寒夜录》中却引用卓珂月的话给出了答案: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 《罗江怨》、 《打枣杆》、 《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10](P6)李开先对这个答案应当是满意的,因为他对民歌一类通俗文学是非常重视的。而其所认为的俗性,不仅指为大众喜闻乐见,“明白而不难知”的形式,而且还与内容的表达有关,“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1](集之五)也就是说,比起那些虚浮雕琢,或者拟古不化的文学样式来说,其更利于表达真情实感。而这种真情,也不仅仅只是“男女相与之情”,而且“虽君臣友朋,亦多托此者”。用通俗的文学样式也可以传达君臣友朋之伦理大义,如同“《三百篇》太平采风者归奏”,这种民歌俗曲与《三百篇》实乃“今古同情者”也,又怎能有高低优劣的简单评价呢?
李开先喜欢通俗文学,一方面的表现是其努力搜集整理民歌。他不仅第一个主持编选了元代杂剧集《改定元贤传奇》, 而且将正德年间流行的《山坡羊》、 嘉靖年间流行的《锁南枝》等民间俗曲109首搜集起来,并对之加以润饰或改作,命名《市井艳词》进行刊布。这要早于冯梦龙半个世纪,他是明代最早收集、 刊布并学习创作民歌的人。
另一方面是其在文学实践中学习运用通俗文学的俗性,“予词散见者勿论,已经行世者,辛卯有《赠对山》, 秋有《卧病江皋》, 甲辰有《南吕小令》, 《登坛》及《宝剑记》, 脱稿于丁未夏。皆俗以渐加,而文随俗远。”“予独无他长,长于词,岁久愈长于俗。”学词者“初则恐其不文,久则恐其不俗。”[1](集之五)正是李开先在创作中注意吸取了通俗文学的俗性,才使他的作品为大众所喜爱,具有了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尤其是其仿效民歌创作的《中麓小令》一百首,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歌而和之者将遍东国,其仿效而作者,称中麓体。”[5](P1204)
李开先喜爱,并大力刊布民歌俗曲,更加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在当时来说是颇为大胆和前卫的。其行为曾遭到不少的批评,对此李开先不以为然,“至于《市井艳词》, 鄙俚甚矣,而予安之,远近传之。米南宫谓东坡:‘世皆以某为狂,请质之。’东坡笑曰:‘吾从众’。予之狂于词,其亦从众者欤?”[1](集之五)李开先所重视喜爱的通俗文学中还有小说,他在《词谑》中云: “崔后渠、 熊南沙、唐荆川、 王遵岩、 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 《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 史学之妙者也。”[5](P1276)这里李开先把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通俗小说抬高与《史记》同等的地位,而且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这种观点,是十分大胆的,后世的李贽也许就是受到了他的启发,才以与史传并列的做法来抬高戏曲小说的地位的。
这样看来,李开先在为文方面发展了唐宋派的本色论,其文章向日常化、 个性化方向的靠拢,实际上对唐宋派所坚持的义理至上,道统第一师道精神的一种消解,是对他们文学精英化路线的反动。而其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则是向李梦阳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民间化运动的回归与发展。李开先文学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新的因子理论价值是巨大的。具体来讲,他对冯梦龙、 袁宏道兄弟等的文学主张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对于影响深远的“晚明文学思潮”来讲,李开先也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能忽视的。
四、 提倡南北文学风格的融合
“在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中,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民俗风情的不同,反映在文学风格上,可能形成不同地域的特点。在中国文学史的地域划分上,最明显的表现是南方和北方的不同。”[11](P403)对南北文学风格的不同,古人早就有所认识, 《北史·文苑传》: “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2](卷八十三)而南北文学风格的不断融合,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常见的现象。
李开先对文学南北风格的不同,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乔龙溪词序》: “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有娀谣乎飞燕,肇起北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韵。北之音调舒放雄雅,南则凄婉优柔,均出于风土之自然。”[1](集之五)《市井艳词后序》亦云: “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锁南枝】亦有二,有南有北。一北一南,北简而南繁,歌声繁简亦随之,然而相类。”[1](集之六)这种南北文风的不同,使得文学具有了丰富多彩的美学特性,或“舒放雄雅”,或“凄婉优柔”,它们本身也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文学风格,而“不可强而齐也”。
然而,在李开先所处的时代,大行其道的极端复古派却是在墨守一种风格,李开先对此极为不满,“画宗马、 夏,诗宗李、 杜,人有恒言,而非通论也。两家总是一格,长于雄浑跌宕而已。山水、 歌行,宗之可也,他画他诗,宜别有宗,乃亦止宗马、夏、 李、 杜可乎?本木强之人,乃效李之赏花酣酒;生太平之世,乃效杜之忧乱愁穷。其亦非本色、 非真情甚矣!”[5](P1853)“世之为诗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纤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1](集之五)“诗贵意兴活泼,拘拘谫谫,意兴扫地尽矣。”[1](集之六)
李开先认为,固守一种风格,必然会使文学风格陷入单一与板滞,缺乏灵动性,造成多样性的缺失,必然会使文学吸引力降低,乃至窒息了文学的生命力。正确的做法应是“守法而酌量乎南北之间”[1](集之五),创作出融合南北的文学风格。而真正成功的作家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如乔龙溪“非惟能作而且善讴,南词时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为非其所长,是岂知词与先生者耶?”[1](集之五)又如康对山,“每赴席,稍后座间方唱南词,或扮戏文,见其入即更之,其所刻沜东乐府,南词亦参错其间,以为止长于北是岂知词与对山者耶?”[1](集之五)李开先主张,要想成为有成就的作家,墨守一种风格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如乔、 康那样博取众长,才能成就一代方家。
这种见解,在同时代的文人之中,可谓是真知灼见。李开先头脑中存在的对南北文风的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也是其避免走向极端泥古方向的原因之一。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论,李开先的文学思想在明代中期的确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价值。明中期的文坛被复古思潮所笼罩,在这种氛围下,李开先虽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复古思想的局限,但却对极端复古思想所表现出的流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力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挽救文坛的这种弊端。总体上看,在复古的问题上,其见解更为圆通,主张“师古人之心”,而非 “泥古人之语”。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与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可谓心有灵犀。
文学是人学,李开先是一个性格真实而情感率真的人,因而其文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对文学真情实感的反复强调。实际上,明代中期极端复古派所宗法的“秦汉之文”,“盛唐之诗”,从本质上讲,其优秀之处就表现于它们所反映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以及其独创性的艺术特色。而极端复古派并没有从这些方面学习古人,而是追求体制、 音调上的“形似”,走上了模拟剿袭古人字句的歧路。所以,李开先强调文学要表现真情实感的主张,的确点到了极端复古派的要害。虽然,李开先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扭转极端复古派的弊端,但他的创作和理论主张,依然如当时复古的“死水”中泛起的微澜,起到了一定的激荡作用。否则,罢官后几乎足不出章丘的李开先的文学作品也就不会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了。而且,李开先与唐宋派有很深的渊源,在文学主张上也与该派有诸多相似之处。其重视自然天成,反对矫揉造作的文学思想与唐宋派之主张,尤其是唐顺之的“本色”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难怪学术界有很多学者把李开先划分到唐宋派的阵营中去了。其实,李开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唐宋派,因为唐宋派的文学主张根本上讲是以“卫道”为宗旨的,而李开先更倾向于道学家所不屑的通俗文学,并将通俗文学的“俗性”引向诗文等正统文学,从而对后世的性灵文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外,李开先胸襟开阔,文学主张也颇具有兼容并包的度量。针对文学南北风格的不同,他主张融通南北,追求一种灵活多变,而非凝固板滞的文学风格。这对明代中期极端复古派主张单一文学风格的做法,有一定的反拨作用。
[1] 李开先. 李中麓闲居集 [M]. 明刻本.
[2] 万斯同. 明史 [M]. 清钞本.
[3] 钱谦益. 列朝诗集 [M]. 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4]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 李开先著, 卜键笺校. 李开先全集 [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6] 廖可斌.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7] 李梦阳. 空同集 [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 刘勰. 文心雕龙 [M]. 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刊本.
[9] 唐顺之. 荆川集 [M]. 四部丛刊景明本.
[10] 陈宏绪. 寒夜录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1]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12] 李延寿. 北史 [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Summary of Li Kaixian's Literary Thoughts
LIU Ming
(Colla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Li Kaixian is a very important man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y, especially the drama theory in the Ming Dynasty. His literary theory contents include: return to the ancient without following their traditions obstinately; emphasis on the true feelings of literature;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literary styles and emphasis on the natural and popular aspects of literature. His thoughts contain many new theoretical element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circles of the Mid-Mi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 Ming literary trends which have far-reaching impacts. Therefore, his theory thoughts cannot be ignored, which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of connecting the theories of different stages in history.
Li Kaixian; literary thought; value; influence
I207
A
1005-7110(2012)06-0092-06
2012-08-27
刘铭(1973-),山东宁阳人,文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近代文论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