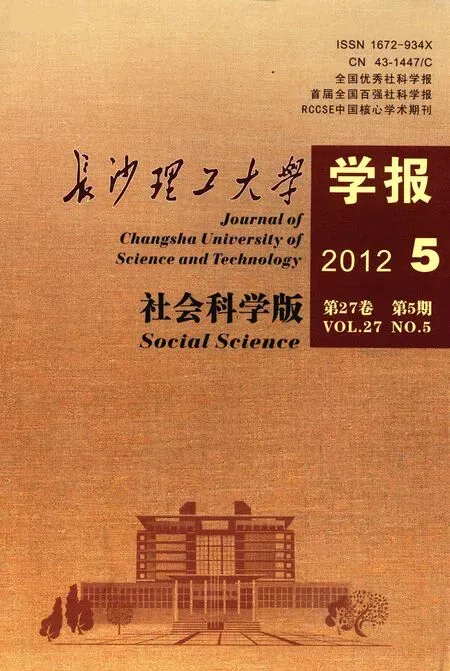美国当代印第安小说中的“灵性传统”
2012-03-31陈文益邹惠玲
陈文益,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美国当代印第安小说中的“灵性传统”
陈文益,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当代印第安作家以非西方的视角书写,在现代文学中发挥交叉道的作用,将印第安灵性传统和神话诗学想象注入文学作品.通过书写神话式的灵性传统,印第安作家们跳出了欧洲僵化单一的思维模式,不仅透过小说构建了一个在主流世界旁侧依然真实运作的灵性力量,也为当代印第安民族困境注入了新的信仰和希望。
美国当代印第安小说;灵性传统;幻象寻求;变形传奇;整体观
印第安文化源远流长,虽饱受种族灭绝、宗教同化和文化入侵等多重劫难,仍然迸发出不朽的魅力。灵性传统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了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以来的印第安作家群体的思维模式和谋篇布局。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将印第安灵性文化注入现代印第安故事,将本族传统与“西方”话语叙述形式进行结合,衍生出生动、逼真、极具张力的作品。正如佛比斯(Jack D.Forbes)所言:“印第安文学只能由印第安文化从内部视角和与土著文化相吻合的样式来进行评价。”[1]本文以美国印第安神灵诗学的角度来探讨美国当代印第安小说中体现的“灵性传统文化”,主要探讨对象为韦尔奇的《愚弄鸦族》、厄德里奇的《宾果宫》以及荷根的《太阳风暴》。
灵性,即个人在各种相处关系中达到平衡的最佳状态,而这些关系包含了本身个体、自然环境、神、他人等。灵性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超越外在世界与内在经验的分裂或互不相容”。[2]灵性传统是美国印第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美国印第安部族而言,灵性信仰渗透到他们神话故事、传奇、民俗以及各种歌舞典仪。Ridington曾在其论文《美国印第安灵性传统的诗学》中指出:“灵性是及其个人层次的经验,但同时又具有集体文化的背景……灵性传统结合了个人的灵性经验和部族的宇宙观。”[3]美国印第安著名学者Allen也讲到,“印第安人的信仰体系里,人、自然和宇宙有梦境相连的基础,因而和和谐,并形成各种灵性的力量,可治病,也可以与动物、植物等往来交通”。[4]因此,灵性经验虽然不符合物理常识,但是在美国印第安传统和文化中,它却如同梦一般真切,与现实世界一起织就了印第安人独特的意识体系。在印第安人眼中,宇宙充满情与知,而他们的灵性传统就是和宇宙中幻变出的各种灵力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一、《愚弄鸦族》:“幻象寻求”的现代文学运用
“幻象寻求”是美国印第安部族最具代表性的灵性传统,Benedict在其著作《北美守护灵》中说“‘幻象寻求’是美国印第安部族灵性信仰的中心。”[5]印第安部族的年轻人,通过离家远足、与他人隔绝和禁食等方式使自己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净化,以便更好地了解和获得自然和部落文化传统的力量。
《愚弄鸦族》是美国印第安作家詹姆斯·韦尔奇在1986年出版的小说,属于“喜剧性的历史传奇”。韦尔奇借助印第安口头叙述、历史记忆和记忆叙事,以“非常原住民”的方式和叙事想像呈现了白人尚未入侵时的印第安黑脚部族人经历的美好时光、再现印第安黑脚部族与白人的历史政治冲突。为了避免落入单一、呆板的历史事实叙述,韦尔奇将冗长繁杂的历史论述与主人公灵性成长故事交融在一起。一方面,韦尔奇借助“杂糅性”语言将黑脚印第安部族命名语言转化为英语,从而“引导读者进入部族语言意识并带出印第安作家写作的信心”。[6]另一方面,韦尔奇以印第安灵性传统文化贯穿小说叙事,打破了西方叙事中现实与想象、过去与现在泾渭分明的思维模式。小说中的人物不断讲述自己的梦境与灵性经验以及和“动物助手”(animal helper)或神话人物对话交流的故事。对于印第安作家而言,将“梦境之真实”与“灵性经验”写入文本是有其文化渊源的。对于印第安部族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源自于梦(the dreaming),……梦包含着对印第安风俗传统的阐述,但更重要的是还包含印第安祖先的故事”,除此之外,”梦也是印第安个人最神圣的财产,更是知识和力量的主要来源”。[7]
在《愚弄鸦族》中,韦尔奇以充满梦境和灵视经验来展示主人公的成长以及对印第安部族未来的种种预见。在描述主人公“愚弄鸦族”的“幻象寻求”时,韦尔奇融合了印第安神话故事和预言叙事(prophetic narrative)。他挪用印第安黑脚部族“羽毛女”(Feather Woman,So-at-sa-ki)的神话传说,把羽毛女的个人哀恸和黑脚部落的集体哀恸并置,一方面以此转化部族因白人殖民入侵而遭受的压力与悲痛,另一方面,借以寻求黑脚部族该如何面对历史灾难的新视野。小说中,当白人即将采取针对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主人公感到彷徨无助,“无助就如同黑夜的雪花一样降落在族人身上”;[8](P313)他也开始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当族人在受苦,当族人的思想如野马般四处逃窜,不再统一的时候,我的能力又有何作用?”[8](P314)就在主人公想以个人力量拯救印第安部族的时候,他得到了梦的助手(dream helper)尼叟康(Nitsokan)的帮助,继而展开了一段为了给其族人寻求方向和出路的灵视之旅。在这三天三夜的旅程种,主人公被引入危险的敌人领域,穿过亦真亦假、既熟悉又陌生的“梦境“,内心也饱受恐惧和自我怀疑的折磨。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动物助手(animal helper)的帮助:“他的马被堵在峡谷入口处的一片红色柳树绊倒,随后一只满脸斑点的狗和狼獾给他指明出路——巨石上的裂缝。匍匐着穿过这条狭长的裂缝,主人公来到一个“天与地之间的绿色圣地”[8](P360)。这是一处介于人类现实与神灵之间的神圣疆土,没有饥饿、羞耻和内疚感,也没有线性时间。主人公遇见正在歌唱的悲伤女子 “羽毛女”。主人公在羽毛女给他展示的“黄皮图画”里看到了黑脚印第安人即将面临的大灾难:白人入侵,野牛消失,天花蔓延,哀鸿遍野。正如里柯所言,“历史叙述虚构化的任务之一就是将过去受难者的惊恐再现,韦尔奇借助电影影像般的呈现印第安黑脚部族的灾难性的未来。主人公所见证的是其族人“将”如何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受难者。然而,面对“预言中”的部族灾难,主人公虽感到愤怒与哀痛,却也感到无能为力,最终以一种几乎是“认命”的态度接受了这可能即将变为现实的历史,“黄皮书中预言的真实远远超过了他个人微不足道的的力量所能改变,也远远超过了整个部族的能力所能动摇的”。[8](P358)对于韦尔奇而言,部族的历史似乎不存在与过去的记忆中,而是蕴藏在这”预知未来“的知识中。和许多同时代的印第安作家一样,韦尔奇认为对抗来自于白人殖民统治带来的摧毁性力量的唯一方发就是要自身挑起责任,从部族文化中寻找力量,树立传承部族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中,重建部族传统与尊严。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愚弄鸦族”参加黑脚印第安部族传统的“雷鸣烟斗典仪”(Thunder Pipe Ceremony)时所说,“他和羽毛女一样背负着有关他族人生活以及子子孙孙生活的知识,但他知道他们能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是被选的一群”。[8](P390)
由此可见,韦尔奇在《愚弄鸦族》中挪用印第安口述传统、神话故事以及印第安独有的灵性传统,构建听者与读者的文化历史意识,再现不同于西方认识体系的叙述模式,找回了陈述印第安部族历史的主体性。
二、《宾果宫》:人神互通的“化熊传奇”
在印第安传统文化里,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根据学者贝瑞的研究,北美印第安人崇敬熊,不仅因为印第安部族流传着许多的关于熊的神话,更重要的是熊灵是印第安药师(medicine man)入会仪式上不可缺少的角色,充当着世俗和灵性之间的桥梁,链接着身体和精神的两个层面。当新药师入会时,熊灵把守着通向可以获取医治疾病、致人死亡或起死回生的灵力的大门。在一些印第安作家的笔下,熊扮演者向导、巫师以及父辈等多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叙述的空缺,使得文本得以超越现实,实现具有“精神与物体结合”特征的“灵性写实”(spiritual realism),或者是巴赫金称之的“垂直时空体。”(a vertical chronotope)作为拥有最多读者的印第安作家,厄德里奇将印第安部族的灵性想象和神奇元素带进了主流文学。他的作品兼有世俗和超越的特征:纷繁复杂的现实与神秘莫测的时空接壤,跨越了想象和文字的界限。厄德里奇发挥了交叉道的作用,将印第安部族的传统想象融入现代印第安故事。在其1984年出版的《宾果宫》(The Bingo Palace)里,大量地运用了熊的意象,展现了人与熊灵的互通。
在小说中,主人公芙乐是守护传统的祖辈级人物,年龄接近百岁,人们皆称呼她为姥姥。虽然她不常在马奇玛尼托湖的祖地村落居住,但是年轻一辈对她害怕多于敬畏,因为其法力强大,联系着部族的过去,也联系着许多神奇的灵力。主人公立普夏为了追求修尼·瑞,趁着芙乐来村子采购日用品,硬着头皮向她求助。芙乐在教堂歇脚,穿着男人的工作靴,立普夏跟着她回到灵湖边的住屋,一路上偷偷打量沙地上有没有留下“熊的脚印。”[9](P132)当立普夏向芙乐提出要“爱情灵药”的时候,芙乐没有回答,继续忙着洗碗,突然转身,动作之敏捷丝毫没有老态龙钟之样。在昏黄的灯光下,“芙乐的身体开始膨胀,颧骨横展开来,脸色越变越暗。鼻子也开始往上拱起,变成黑色的长鼻,眼睛凹陷下去。灯火熄灭,立普夏恍惚之中听到一阵阵沙哑的声音”。[9](P136-137)芙乐身为“熊灵”的启示也体现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当失意的莱门在赌场机械般的投币玩“老虎机”的时候,赌博机的屏幕上浮现出芙乐的面孔。这时,赌场变成了野外,只听到芙乐的“熊声”对他说:“土地是唯一能够代代相传的东西,钱会像火种一样燃尽,像河水一样流走。”[9](P148)在小说的结尾处,芙乐拖着雪橇,走过结冰的马奇玛尼托湖,去往部族先辈埋骨的湖中小岛,准备以性命换取立普夏的安全。后来又目睹者如是说:“白茫茫的雪地上,一行足迹,脚印渐变成宽大的掌印,爪子深深印入血中……还伴随着热切的部族老歌。从那以后,就在也没有人见过芙乐。她的足迹早已被新雪覆盖,被风吹散。然而在晴朗灿烂的白天,或是星棋密布的夜晚,这些脚印又会出现。所以有人说,芙乐还在继续往前走。她不敲打我们的窗户,也不会在屋檐或门上留下任何她来过的痕迹。她只是轻轻咳嗽,让我们知道她来了。我们听到了熊的笑声。”[9](P274)小说中这些片段的叙述无一不证明芙乐与“熊”有着密切关系。她的“变形”,她的“熊声”、“熊思”、留下的“熊的足印”以及她自身具有的灵力都说明她就是印第安部族神话里“熊灵”的化身。作为为印第安部族后人心中的“记忆传奇“,芙乐不仅“给印第安后辈指明方向,还激发他们的潜能……使得印第安后人在接受传承部族文化的同时,还要为部族的将来寻找新的出路”。[10]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芙乐的模糊身影总是映照在现代印第安的时空里。
小说中,芙乐化身变为“熊灵”的书写正式印第安灵性传统鲜明而有深意的体现。这个精彩人物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印第安灵性文化的支撑,是人物个性加上文化集体性的综合。虽然这种“动物变形拟人化的书写”不时需要拐弯抹角才能表现,但是仍然极具张力,彰显了印第安文化中“生物的在场”以及“人与动物无法截然二分”的立场,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熊灵在印第安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批判了西方世界倡导的“人类中心论”。
三、《太阳风暴》:“印第安人的整体观
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万物皆有灵”,皆源自“大神秘”(The Great Mystery),或是宇宙所有存在共同形成的“大生命”(The Great Life)。印第安人信奉人与自然的平等性,认为自然万物与人类息息相关,把种种有关自然的神话看成是部族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可以视为是“整体观”(holism)的展现。“整体论”这一术语出自自然哲学家史马慈(Jan Christtiann Smuts)在1926年的著作《整体论与进化》,旨在表达“自然趋向透过创化性的进化形成整体,而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由此可见,整体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它肯定事物之间的一体性和相关性,反对僵化的二分法,这与印第安人的整体观不谋而合。相对于非印第安人和自然的片面关系,北美印第安部族和自然的关系是全面的,而非主体和客体的泾渭分明。正如在印第安人的意识里,自然和人一样具有“知情意”,人类世界与非人类(other-than-human)世界互相往来,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参与者,自然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举例而言,西方的观念和写作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独有,而自然是人以外的世界。如在爱德华·阿尔比书写自然的代表作《沙漠隐士》中,自然被定义为一片荒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然而,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荒野并不等于荒凉。荒野是他们活动的场域,充满了灵性。荒野中的一草一木均为人类的亲族,且充满动能。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印第安混血作家琳达·荷根,其充满诗意和神秘的作品洋溢着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跨越了人与非人的藩篱。从书写自然的角度来说,她的诗歌和小说都是印第安人与自然认同的最好写照。如在《祖母之歌》这首诗中,荷根用造物者的意象展现印第安祖母们是如何歌颂生命的诞生,而这个过程是依照大自然节奏的:“当雨开始下,当河流吟唱,水徜徉流淌汇至大海,水流经之处,土地发芽开花,祖母们沿袭这种创造,开启新的创,她们也在吟唱。”[11]在这首诗歌及其荷根的其他诗歌中,作者以土地象征血脉之源,强调土地是印第安人乃至所有人类的最后归属。在其小说《太阳风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更完美更淋漓地呈现。小说充满着印第安部族的自然想象和对自然现状的哀悼:大自然被巧取豪夺,野牛被捕杀殆尽,矿产资源被肆意开发,大型水坝的建设,这一切彻底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主人公安琪拉是一位十七岁的印第安少女,从小被母亲一起。长大后,为了追寻身世和文化身份而开始了一段朝圣之旅。在这个宛如印第安典仪般的旅途中,几位跨越数代的印第安女性以独木舟代步,跋涉没有国界之分的自然大地,与自然互动,领略自然的丰美与自由:“花粉飞散于风中,落于水中仿似片片黄色雪花。万物融为一体,分不清何为水,何为空气……小舟仿佛化作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皮肤……一切都成为了整体”。[12](P177-178)安琪拉跳入水里,石墙因为水坝工程而没入水中。水底下的石墙上刻画着鱼的图案,与周围的活生生的游鱼及水中生物共存。这个场景看似简单,却传达了人类和自然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情感。石壁上的鱼是人类的手笔,而与周围非人类的世界共处于同一个时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并不是“他者”,而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对于大自然对人类的洞察和知情,小说中由安琪的一段叙述展露无遗:老一辈的人都说我们生活的一举一动都被鸟儿、蜻蜓、老树和蜘蛛们看在眼里。然而,注视、打量我们的不仅仅是动物,甚至还有外太空深处的银行系,以及北风吹送的流冰。“[12](P80)在印第安人的意识里,甚至是蚊虫也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生物。小说中写道,当安琪拉一行人经过沼泽地的时候,安琪拉感到蚊虫正在凝视着他们:“(蚊虫)他们的祖先曾聆听过我的祖先的歌谣……当法国人经过这里时,他们在这里……当皮毛商人急速划船越过河流时,他们也在这里……。”[12](P175)由此可见,对于印第安人而言,无论蚊虫等等级生物多么渺小,生命多么短暂,都是这片水世界的古老居民,对这片土地拥有同样的权威。这种近乎神话的表现,扩展并丰富了知觉,补足了人类的自我观照,也再次表明人不是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生物,也不是唯一具有历史向度的物种。
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的自然诗学和印第安整体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想象达到了极致。主人公的曾祖母找到了一片周围满是蕨类植物的苔地,并以此作为她的临终之榻,人与自然的鸿沟也被再次超越,“天空下着流星雨,飘着宇宙尘……我(安琪拉)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死亡……我唱着一首召唤动物的歌。唱着,唱着,动物来到她(曾祖母)躺卧的所在,我们有看见你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都在那里。狐狸,又老又瘦,躲在我们,站在树后……还有目光锐利的老鹰、还有熊的声音,……还有一个黑影,是狼獾吧,也来(给曾祖母)送上最后的致敬意”。[12](P349)德瑞斯对此评价说:“荷根的作品就是神话、神秘与神奇;神话诗学想象是她作品的灵魂。”[13]
四、结论
印第安部族集体的想象力量,透过日常生活的超自然经验,再经由印第安作家的诗学转化,变成了文学的戏剧化表达。这种表达在呈现了印第安灵性传统独有的可感、可触与可知的同时,也展现了文化的创造力,打开了我们(读者)想象的大门,在异质的文化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身影。当我们回应他者、他族、他方世界的时候,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世界,我们不仅延伸了他人,更延伸了自己的认知与想象。在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延伸显得愈发重要。
[1]Forbes,Jack.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
[2]Deepskies,《灵性经验为中心的生物学观点》<http://home.kimo.com.tw/dipskies_4.htm>
[3]Ridington,Robin.Voice,Representation and Dialogue:The Poetics of Native American Spiritual Traditions.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20.3-4(1996):468.
[4]Allen,Paula Gunn.The Sacred Hoop: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Ed.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241.
[5]Ruth,Benedict.The Concept of the Guardian Spirit in North America.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23.
[6]Owens,Louis.Other Destinies: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2:26.
[7]Ashcroft,Bill.Post-colonial Transformation.London:Routledge,2001.
[8]Welch,James.Fools Crow.New York:Penguin,1986.
[9]Erdrich,Louis.The Bingo Palac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4.
[10]Barrr,Nora.Fleur Pilager’s Bear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SAIL 12.2(2000):33.
[11]Hogan,Linda.The Book of Medicines.MinneapolisL Coffee House,1993.
[12]Hogan,Linda.Solar Storm.New York:Scribner,1997.
[13]Dreese,Donelle N.The Terrestrial and Aquatic:Intelligence of Linda Hogan.SAIL 11.4(1999):8.
[责任编辑 刘范弟]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Novels
CHENWen-yi,ZOUHui-ling
(SchoolofForeignStudies,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China)
From the non-western perspective,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novelists serve as a crossroad in modern literature,infusing their literary works with American Indian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the poetics of myth.As such,they get rid of rigid unitary mode of thinking by creating dynamic spiritual power within the dominant world.Also,they bring brand-new belief and hopes for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s.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Novels;spiritual tradition;vision quest;transformation myth;holism
I13/7095
A
1672-934X(2012)05-0124-05
2012-05-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11BWW05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的身份主题研究(10WWB0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课题“创伤理论视阈下的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研究”(2012SJD750032)。
陈文益(1976-),男,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邹惠玲,女 (1957-),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