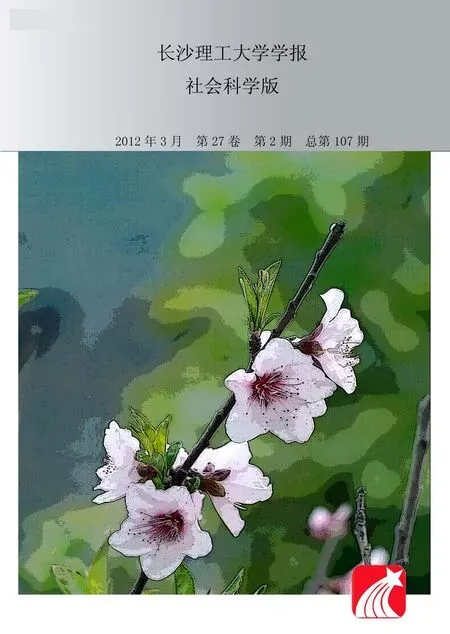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2012-03-31周仁政
周仁政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楚国是历史上南方文化的代表,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记载帝王将相之“事功”的历史荡然无存,而代表自身“有情”文化的“诗”则光芒万丈,这就是《楚辞》。屈原是这一文化的见证人,也是她的传人。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溯沅水而行,沈从文常能感觉到屈原及其文化的存在。沿河两岸自然的美与衬映着历史的“静”,带给他莫大的感动。他说:“自然使一切皆生存在美丽里,……任何一个活人,他都可以占有他应得那一分。一个‘诗人’或‘疯子’,他还常常因为特殊聪明,与异常禀赋,可以得到更多的赏赐。”①
这个历史上的“诗人”或“疯子”就是屈原。当年,这个“感情丰富作人认真的楚国贤臣”,由于“众醉独醒”的命运,被楚王放逐沅湘。当他“朝发枉陼,夕宿辰阳”时,面对高峻蔽日、幽晦多雨的溆浦深林,林杳冥冥、猿狖所居的沅水两岸,常是感慨系之:“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性情耿直的诗人矢志不移的是那份情感的坚守,文化的忠贞:“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忠不必用,贤不必以”的庙堂宫闱使他难于释怀,面对自然也平生怨郁:“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九章·远游》)
河道的激流险阻摧生了诗人的焦虑,多少年后沈从文把自己和屈原比拟,也不免内心激荡:
一只桃源小划子,……在一条清明透彻的沅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生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一丛丛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②
“静”的风景是沉默的自然,平息了心的波澜。沈从文愿意像屈原那样从自然接受教育。重新理解历史、现实,和人类的命运。他观察着且思考:“这地方的一切,虽在历史上也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人民担负种种不幸命运。……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②(P278)“静”与“动”,“常”与“变”,“事功”和“有情”——历史和文学,何更可贵?反复思索,他悟出:
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我感动得很!……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我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爱了世界,爱了人类。③
柔情似水,感动如风。稍纵即逝,回味永恒。当初“哀郢”沉江的屈原,他的政治理想与坍塌的庙堂俱去,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种感动和缅怀。但“诗”(文学)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楚文化。屈原所代表的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文化的生命。因而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所代表的也不是政治的“事功”而是文化的“有情”(即不由于恨而是由于爱)。走不出恨的历史就创造不出爱的文学。这是屈原及其“诗”留给后人的一份莫大的启示,沈从文悟出了它的真谛。
日本《楚辞》研究专家清川星孝认为,从文学史上看,先秦时代《楚辞》和《诗经》所代表的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范型。他分析认为:“拿《楚辞》和《诗经》相比,最显著的不同是其中各篇充满着神秘的思想。上古人中富于共通性的神话,独特而庄严的世界观,传承中透着苍然古色的传说等,能与这些丰富蕴含相匹敌的诗篇在《诗经》中一篇也找不出。”“其次,《楚辞》诗篇中具有的另一特色是浪漫的思想。……在《楚辞》各篇中,即指诗人因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苦闷而怀抱着对空想的世界——天界和神话之国——的憧憬,时刻思虑着死亡的精神状态下的思想倾向。不用说《诗经》中也有表达人生忧郁苦痛之慨的诗篇,也有浪漫的爱情诗篇,但却见不到如《离骚》、《九章》那样饱含激越情调的高昂的浪漫精神。”④
“神秘的思想”和“高昂的浪漫精神”昭示了《楚辞》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情感世界。作为诗人的屈原置身这一文化母体中正可以现身说法。西南联大时代的著名学者彭仲铎认为:“《离骚》者,屈原既绌后为巫之自序(叙)也。”⑤闻一多也认为,“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他说:“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分,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⑥日本学者藤野岩友视《楚辞》为“巫系文学”,“在巫者掌管的占卜、祝辞、神歌、神舞、神剧、招魂歌中寻求《楚辞》的起源”,划分出五大类别:“问卜系”(《天问》)、“占卜系”(《卜居》、《渔父》)、“祝辞系”(《离骚》)、“神舞剧”(《九歌》)、“招魂类”(《招魂》、《大招》)。他认为,“楚地自古与巫关系深厚”。⑦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⑧王逸虽并非认为屈原是巫,但承认其诗作(尤其是《九歌》)与楚地“巫文化”关系密切。
有研究者认为,《九歌》作为沅湘间少数民族的祭歌流传至今,其中:
《东皇太一》是祭祀沅湘少数民族始祖伏羲的(详见闻一多《东皇太一考》)湘西土家族、苗族均有《兄妹成亲》的传说,这与伏羲、女娲传说有关。《国殇》是祭祀沅湘少数民族牺牲的将士,歌颂的是战神。余下的四对神。《东君》和《云中君》为一对,是日月之神。至今土家族、苗族对太阳和月亮仍很虔诚,各有美妙的传说。《大司命》和《少司命》为一对,是司命之神,土寨、苗寨至今还供奉在神龛上。《湘君》和《湘夫人》为一对,是恋爱之神。《河伯》和《山鬼》是一对,是山水之神。这些神祇,都是沅湘间少数民族巫文化中所独有的。⑨
在小说《凤子》中,沈从文也认为,湘西苗地的谢土仪式,出演的仍旧是“九歌的本事”。他说:“什么敬神谢神,完全是一出好戏,一出不可形容不可描绘的好戏。是诗和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声音颜色光影的交错,织就一片云锦,神就存在于全体。……我心想,这是一种如何奇迹!……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二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纪录人罢了。……若有人好事,我相信还可从这口古井中,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⑩
二
当年,沿着屈原和苗族先民溯河西上的那条沅水,顺流而下,沈从文穿越“动”的历史走出了“静”的河流,下洞庭,过长江,北上故都,他踌躇满志:“问鼎中原”——不是军事的征讨,也不是功名利禄的建树,而是以个体的力量和文学的方式,为这个千年孤独的民族精神雪耻。因此,他选择了弃武“从文”,弃功用情,远人而近神。
历史上,无论是决战涿鹿的蚩尤还是问鼎中原的楚王,所欲征服的都不过是中原民族的躯体,获取他们的地盘,就像后来中原民族对“南蛮”们的征服一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争都是“南蛮”们发动的,无论是炎帝对黄帝的阪泉之役,还是蚩尤对炎帝和黄帝的中原大战——涿鹿之战,每一次战争的结果似乎都是中原民族稳操胜券。炎帝和蚩尤本来都是南方部落的首领,但由于炎帝最后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虽然他终为黄帝所败,但还是因此和黄帝一起博得了华夏始祖的称号。蚩尤及其九黎、三苗部落则以“蛮”称。多少年后,他们的后辈——曾经问鼎中原的楚王与雄极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等,又先后在与中原民族的军事对抗中折戟沉沙。何等横空出世的浩然霸气!那些肉体的征服、利益的征战付诸历史如歌如泣,令人叹惋。南方民族的强悍似乎注定了他们只能成为战争史上的悲剧角色。
面对这样的“历史”。 沈从文不愿如此延续自己的命运,他选择了新的道路。
进入20世纪,政治上战争与和平——攻略与共处,作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历史和时代主题,制造并加深着人文主义者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和裂痕,军事上的攻伐与政治上的控制日益为现代人文主义者所反感和拒斥。“在文化上,由于宗教时代神灵的退位,启蒙运动赋予人以自由的意志,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促使人们不再祈求集团或群体的权威(包括族群的力量)以维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而甘愿独来独往,自立于世。从楚、苗先民到汉、苗遗民,沈从文身上葆有的是一种近似于昔日三闾大夫的执拗而迥异于历代中原士人的奸佞圆巧的性格和气质。这就是他那种所谓‘乡下人’的倔犟和‘蛮’劲,从而使他仿佛先天地拥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现代人的文化觉悟。尽管他当初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寻梦人甫一踏上故都的土地,心中所秉持的那份期待难免是‘现代人’的,但奔涌在其血脉中的‘古老的品格’却最终把他从情感和心灵上留在了故里。他生活在了现代的都市,但他很快清醒于那份现代人的寻梦,而做着回向故乡和远古的梦——和同时代的人们相比,同样是梦想着的现代人,沈从文所作的不是生活的梦,而是情感和心灵的梦。从而,这也就是文化之梦。”
面对现实,他重新思考着自己的命运:现代社会和文化,从它的起点来看就恰似一场乌托邦式的梦幻,现代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这场乌托邦梦幻的寻梦者。只不过,有些人是向着“真”而做梦,或者以幻为真,重复着历史上那些由帝王将相演绎的“事功”的悲喜剧;有些人则是向着“幻”而做梦,或者以真为幻,执意要去“有情”的世界探寻人性的奥秘,用个人的方式证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前者寻梦于生活,后者寻梦于情感和心灵。沈从文属于后者。更为独特的是,饱含酸辛的楚、苗民族似乎在历经千年沉寂之后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托梦人。但此时,他们令沈从文所表达的那份梦幻般的憧憬和希冀,并非只是代表着他们自己,而恰好唤回了人们对不可重复的人类童年的记忆——童年的生活,童年的情感和心愿。所以,对沈从文来说,沉醉在这份历史和文化的旧梦中,他似乎成了一个真正为梦而梦的人。这对于每一个经历人类社会成熟期的文化汰洗的现代人,确乎不可思议。因此,或许只能说,沈从文犹如他所自来的土地和民族,那是一个仍停留在远古人神和悦时代的人类童年的神异之国、童话之都。以近乎“梦呓”的方式,沈从文作出的亦是童话或神话式的表达。这正如凌宇所说:“沈从文是在由湘西保留的楚文化余绪哺育下长大的。因此,当他二十岁那年,从湘西来到北京时,他跨越的不只是数千里的地理距离,而且也同时跨越了多个世纪的历史空间。他以‘乡下人’的眼睛看世界,便立即感到与社会一切现存观念与秩序不相适应。他早已意识到‘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但他执意走自己的路,写出长期受压抑的少数民族心坎里的沉痛隐忧。”
寻梦,使沈从文看待文学的作用与当初的启蒙主义者不同。他执意认为社会应该重造的是人的心灵,这是文学的责任。历史使“理性”扭曲了情感,恢复情感的本真就是重建联系古今民族命脉的自然人文,这须得借助那股来自人类文化源头的涓涓活水——从远古神话到近代湘西民族的生活,这股源头活水长流不断。照他理解,如果说历史上楚、苗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中的悲剧性不在“爱”而在“争”,那么,在楚、苗民族自身,恰好不是“争”,而是“爱”使他们联结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他要用这份获自自身文化历史的经验告诫和启迪所有执迷不悟的现代人。如其所说:
(我)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辞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
他不解:现代“年青人欢喜说‘学习’和‘争斗’,可有人想得到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争斗!”
因此,沈从文似乎要竭力使人相信,人类生命的真正粘合剂是情感,是爱;不是仇恨和斗争。早年,正是基于这一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他在自身生活中培育了对于艺术的领悟力:
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堆泥土,成为艺术与成为物件,谁更持久?一个艺术家或作家,比一位将军或斗士,谁更伟大?进而,一段历史与一篇神话,谁更真实——谁更接近情感的本真和更富于生命的瑰丽色彩?如此等等,难道不能令每一个对生命执着和对生活认真的现代人颇费思量吗?
确实,艺术似乎就是创造神话——犹如生活创造历史。历史和神话、生活和情感——实有和抽象,沈从文执意要从事的是一份“抽象”的事业,他要重造神话,以保留历史上楚、苗民族的生命本质和情感本真,与任何自封为“真实”的历史相颉颃。从文化上看,纵然仍体现了那种楚人“命定的悲剧性”,但和屈原相比,这在沈从文身上确乎已经改变了方向:
两千年前,当史官文学统治着北方文坛的时候,屈原以他的《离骚》、《九歌》诸篇烛照南天,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绚丽灿烂、别开生面的一章,与史官文学合成中华民族文学的南北二重奏。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学的主体精神,是南方民族特有的内聚生命力的爆发。而这种主体精神——厚积的民族忧患意识、炽热的幻想情绪、对宇宙永恒感与神秘感的把握、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又是与它独创的神话系统并存的。在这里,神的世界同时也是人的世界。但是,对人的世界的把握,必须经过神的世界的中介。
在艺术上看,屈原笔下的“神的世界”乃是一个外在于自我的力量之源,沈从文笔下的“神的世界”则是一个情感和秩序的自然王国。这个世界不是自我力量的外化,而是自我力量的本质化。就其思想基础而言,它源自近代的“泛神论”,却又与原始的“泛灵论”具有某种同质同构关系。其中,“敬畏自然”的观念不是某种无意识的外在恐惧,而是有意识的内在观照——自然之神是情感和自我力量之源,不是纯粹外在于自我力量的神秘客体。正如沈从文所说:创造于艺术,乃是他敬畏自然,信仰生命,要“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作为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却“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他决心“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其心目中的“神”不是宗教中万能的上帝,也不是拜物教文化中令人恐惧或敬畏的对象,而是人类情感世界中的自然和生命本体。在情感和艺术的世界里,生命是自然的存在形式。
“神即自然”——沈从文如是说。⑩(P123)对宇宙而言,生命是自然的存在形式;对人类而言,自然是生命和力量之源。自然的生命充满青春活力。个人的青春易得,民族的青春难再。在文化上,童话或神话的世界,代表着人类业已逝去的青春时代。沈从文要追溯并再现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近现代湘西社会正是人类即将或业已消失殆尽的青春世界的孑遗。他要创造一部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的神话,唤起乃至强化人类对于已逝青春时代的记忆与眷恋,让人类的记忆“永远年青”。
三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从沉睡的历史中唤醒,凝结在沈从文笔下,它是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
如果以泛神论(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理解现代文化(文学)的本质,透过一部人类文化史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一切之于‘神’的观念都与人的自然观及所反映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相连”。巫术文化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原始拜物教中的神灵主要表现为不同自然现象和各种可敬畏的自然物的象征体: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敬畏自然造成了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人们从自然中获取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方式也受到了相应的束缚,这有悖于人的主观愿望。
现代文化以泛神论和无神论为代表,反映了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其中,“‘回归自然’根源于人的自然本质化要求,‘征服自然’根源于人的社会本质化的要求”。前者是自然人文的目标,后者是科学文化的理想。所以沈从文在小说《凤子》中指出:“科学是在毁灭自然神学的。”“科学虽是求真的事情,他的否认力量和破坏力量,在以神为依据的民族上面所生的影响,在接受时,转换时,人民的感情上和习惯上,是会发生骚乱不安的。”⑩(P124)科学代表人类理智在物质世界的最高运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沿着“征服自然”一翼脱缰而出。那么泛神论呢?它只是代表了启蒙时代人们为着脱离一神论宗教观念的束缚,在思想和文学领域祭起的反叛之旗——回归人类童年时代的价值观的要求。泛神论并非无神论科学世界观的前奏,抑或成为它的对立形态。它作用于启蒙后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领域,把人类的成年和人类的童年关联起来。它无法认同人类历史只是在物质世界和政治领域的线性“进化”史,而将其看成一个永恒的生命过程——一种神化的自然本质和自我力量。无物不神,神即自我。“我”的精神跨越历史,穿越时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映证其本质的同一性。
在小说《凤子》中,沈从文写到,王杉古堡的人们依赖地下的朱砂、水银而生活,却并对自然的掠夺。千年开采,没有减弱地下蕴藏的丰富,也未破坏自然环境的优美。他们只是享用自然的丰厚赐予。付出也异常慷慨。因而在一个城市中人看来,这简直是对利益的“耗费”。但他们“耗费矿砂,可从不耗费生命。他们比我们明白生命价值,生活得比我们得法。他们的身体十分健康,他们的灵魂也莫不十分健康。在知慧一方面,譬如说,他们对于生命的解释,生活的意义,比起我们的哲学家来,似乎也更明慧一点”。⑩(P140)所以,沈从文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一切皆以一种迅速的姿式,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在消灭到过去一切”。⑩(P106-107)在王杉古堡,这一切尚未来临。“那个地方,地下蕴藏了如何丰富的矿产,人民心中,却蕴藏更其如何丰富的热情”。⑩(P108)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范例。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自然为神,同时视人的生命也是神圣的,这就要绝杀戮,少对立。因此,沈从文认为,“神在××人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的爱”。科学求真务实,难免与神对立。它是“否认力量和破坏力量”,“从别个民族进步上看来,已到了不能够相信神的程度”。但人的力量总是薄弱的,最终连自己也难于相信时,就不免发生一点“社会的悲剧”。⑩(P124)沈从文对此感到忧郁。
这种“社会的悲剧”就是人类的掠夺和战争。一个怯除了神的统治的社会,纯粹人的统治难免利益的争夺与冲突,乃至愈演愈烈。所以,沈从文认为,人必须在“神”的意义上保留一点纯粹的信仰。王杉古堡人的生活正是一种启迪和教训——人不能忘记了自己天真的童年,烂漫的童心绝非一无所值。纯洁的灵魂与对自然的敬畏互为表里。爱自然就是爱一切生命。这是避免掠夺和仇杀的基础。
屈原是否也看到了这样的景致?于是他开始厌恨人类的尔虞我诈,甘愿与民同乐,不问政治。沈从文的感悟更其“忧愤深广”——他不是面对一己遭遇或一族命运而发,而是面对人类的现实和未来而发。他思想中的浪漫主义不是一种指摄远古和虚幻世界的乌托邦,也不是仅为文学而文学的个人主义,而是要在“科学拜物教”指摄的现代社会,创造一种寄托深厚文化理想和历史基因的“自然拜物教”。
和沈从文一样,当年的屈原正是一个“自然拜物教”的信徒。当其流放之时,奔放的思想和情感曾上天入地,向祖宗和神灵追问,而生活上则简朴率直,与民同乐。同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一个矢志不移,感天动地的人臣和神子——尽管无法仍以“人臣”的身份祖述楚国的历史,却要以“神子”的姿态祖述楚国的文化。他崇拜祖先,因为相信祖先代表尊严;他崇拜自然,因为自然是神。他是一个生命的“拜物教”者。因此,我们看到了他在历史中记录下的情感世界和生命轨迹:
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緼亦脩,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桔颂》)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脩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在历史上,据《史记》所载,联齐与联秦的分歧及张仪等的离间是屈原和楚王失和及被逐的原因。这都是政治上的考量。然则战国争霸的政治与文化自存的理想更其表现了屈原与楚王不可调和的矛盾。若注意一下历史上屈原与楚国王室的不同身份及其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屈原的悲剧性及其根源。(唐)沈亚之《屈原别传》载:“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可见,屈原的外表及个性确乎与他(或家族)曾经为巫的历史有关。所着之“奇服”和所戴之“切云冠”也似乎不是通常的朝服和朝冠。他这样的外表和性情决非战国时代往来穿梭于诸侯间,舌战群儒纵横捭阖的张仪、苏秦辈所可比拟,也大略不会真正被渴望与中原民族在军事上一决高下的楚王(或楚王室)视为辅佐自己霸业的重臣——他的被逐,或许正是楚王视其为迂腐的表现。而一旦离开都城,屈原也不是如后世所拟想的那样关心朝政,而是“游沅湘,俗好祠,必作乐歌以娱神,辞甚俚”。这时的屈原与民同乐,仿佛又回到了远古与世无争的年代,至而乐此不倦。“晚益愤懑,披蓁如草,混同鸟兽,不交世务,采柏实,和桂膏,歌《远游》之章,游仙以自适。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可见,屈原并非如历史上人们所推测的,是以自己的政见不能见容于楚王,而主要是其文化品格和价值不再被楚王所赞赏和认同(反而楚王对别有用心的张仪等言听计从)。就政治意义上讲,楚王信赖甚至期盼张仪式的人才,疏远乃至驱逐屈原式的文化故旧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楚王的悲剧也象屈原的悲剧一样,终究还是文化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其文化载体的楚国人民并没有抛弃屈原。沈亚之《屈原别传》载:楚人相信,屈原死后,“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思慕,谓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贮米,投水祭之”。这正是虽被历史判定为不合时宜,却为屈原拼死捍卫的巫楚文化,在屈原身上及楚民族历史上的折射和投影。屈原成为楚文化和楚民族不死的精魂,是几千年来变易无常的政治的历史所掩翳不了。
因此,我们看到,在屈原身上楚文化的自然道德观最主要的表现为顺应自然,不苟同于流俗,执着坚韧,洁身自好,敬天畏命的个人道德操守及其独特的拜物教信仰。在屈原时代,人的道德观念并非依存于宗教上的服从意识或政治上的责任心与义务感,而是拜物教信仰中的泛神论或自然神观念,即以万物有灵而推定人(物)各自为神。屈原的“好奇服”、“性洁”、“濯缨”及“披蓁如草,混同鸟兽”等生活方式和习惯,无一不渗透了这种拜物教理想。显然,在屈原身上,人格或道德修养的基础与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圣经贤传中搜求“微言大义”,从而奉为圭臬完全不同。他的人格理想或道德观念深蕴在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体系中。其中,在人们对自然的观念中,除了普遍为人祀奉的神灵,一般自然物亦可充当各种人格目标的象征和载体,铸成人们特定的拜物教操守和信仰。因此,我们不能仅以“比兴”的修辞方法和作用看待屈原在《离骚》、《九章》等诗篇中一再提到的秋兰、辟芷、申椒、菌桂、杜衡、杜若、芳芷、芰荷、芙蓉、木兰、蕙、茝、桔等各种植物,实则它们在作者所赋予的象征意义上都具有着自然神的象征意义,即在“交感巫术”或自然拜物教体系中,万物有灵论导致人们将其不同的信仰(或信仰体系的不同方面)寄寓在不同的自然物上,或以其作装饰,或以其为信物、祭品,佩戴、珍藏或馈赠。对它们的珍爱和歌颂就是人格的表示,圣洁的誓言,正如巫术仪式本身的性质和作用一样。
上述屈原以香桔自比,蕙兰、芰荷自喻,无非说明他“独立不迁”的意志,“信芳”“好脩”的品德。这都化为日后沈从文在自身文学追求和生命活动中的宝贵营养。
在《金枝》中,弗雷泽曾以巫术——宗教——科学来规划人类文化或思想史的进程,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具有相似性,但他似乎只看到了巫术与科学在使自然力量对象化方面具有的同一性。如上所述,在“敬畏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思维方式上,科学自然观与巫术自然观有着明显的或本质的区别:科学使人藐视自然,巫术使人敬畏自然。倒是现代自然人文主义者继承了巫术自然观的思想传统,并在与科学自然观相颉颃中发展着这一传统,从而使自然本身不是在科学(或巫术)的对象化的视野里,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情感化视野里重新被“神化”,并以“神话化”的艺术创造重新去发现,去渗透和捕捉。因而,在泛神论的思维方式下,作为对自然或人的自然化生活方式的神话式——情感化的艺术表达,“回归自然”的文化(文学)理想就是一种现代“自然拜物教”。
心忧自然而目睹现代人性的困境,执意创造现代神话的沈从文,存在于其文化理想与艺术志趣中的惟一心愿,就是呼吁人们珍惜情感与“回归自然”。 经历过历史的洗刷和现代思想的陶冶——他跨越“历史”从远古走来,步履坚定地迈入现代社会却只能作为一个饱受生活和理想煎熬的卑微的“乡下人”,生活在情感源泉日渐枯竭的都市社会和现代物质文化中。因此,他要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验现身说法。对他而言,无边的勇气和无尽的激情确也来自那份与自然世界血脉相连的卑微者的决心和几千来饱受屈辱的民族泄愤雪耻的愿望。于是,他以略带戏谑而又不无夸耀的笔触描画的湘西社会,展现在人们眼中,确是一个珍藏在他记忆深处或情感世界中的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
[注释]
①沈从文:《由达园给刘廷蔚》,《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②沈从文:《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③沈从文:《湘行书简·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④(日)星川清孝:《楚辞の研究》,养德社(日本)昭和36年(1961)版,第214-215页。引文为笔者译。
⑤彭仲铎:《屈原为巫考》,《学艺杂志》第14卷第9号。
⑥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日)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韩基国编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⑧(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⑨彭秀枢、吴广平:《〈九歌〉是沅湘间少数民族的祭歌》,《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⑩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