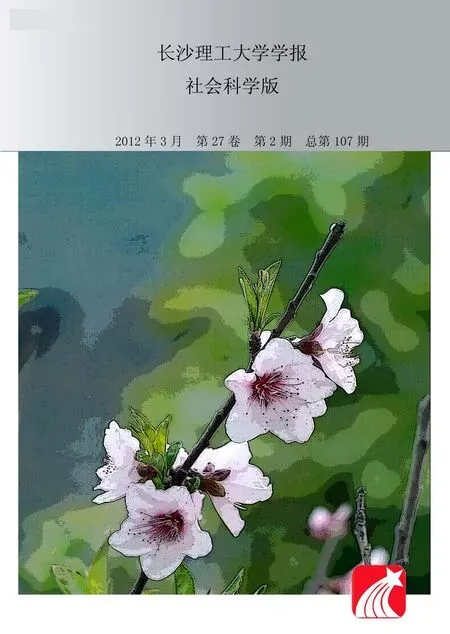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
——就钱学森之评价与叶永烈先生商榷
2012-03-31朱亚宗
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72)
我也是一位钱学森的崇敬者,小学高年级时适逢钱学森归国,通过师长和报纸的介绍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他于是成了我最早的偶像级科学家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后,在校园里能经常见到钱学森先生,有一次他作了一场才情洋溢、风趣横生的报告,对我影响甚巨,以至于从此一直关注他的文章和讲话,并悄悄去旁听他的讲课。1981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是钱学森先生推荐我到国防科技大学工作,我的一些论文、著作曾寄给钱先生请教,他也给我回过两封信。由于从事的专业是科技哲学,因而还从专业视角研究过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和思想,在教学中钱学森先生是我最喜欢讲述的科学家之一。虽然钱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却从未写过纪念他的文章,正打算为钱先生诞辰100周年写些纪念文字时,读到了叶永烈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2011.3.3)的长文,深受触动与启发,激发我也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基旨与叶永烈先生不太相同,不想写成为尊者讳的辩护文章,当然也不会写出求全责备的批判之作,而力求通过这篇短文,表达让钱学森先生的形象返朴归真的愿望。
一、自相矛盾的资料考证
叶永烈先生的长文《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以下简称叶文),一如既往反映出叶先生的勤奋与机敏,凡想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或研究钱学森的人均能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与启示,我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钱学森思想的一员深表敬佩与感激。但叶文在资料的运用及论证上却有自相矛盾之处。
叶文有一段关于走访毛泽东秘书李锐后的评论:“我说这么一来你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确实,史学界有孤证不立之说。问题是叶永烈先生接下来引用的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刊《风讯台》6期的报道,恰好是毛泽东本人对钱学森“万斤亩”文章的反映:“你在那时候敢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这表明毛泽东本人明确说出了曾受钱学森文章的影响,叶永烈先生的论证便自相矛盾,“孤证”之说不攻自破。笔者还记得,毛泽东与美国作家斯诺谈到1958年粮食亩产放卫星问题时,也曾说过受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影响。
二、割裂联系的思想方法
叶永烈先生长文的基旨,是为钱学森“万斤亩”的探讨、计算及发表的文章辩护。叶文认为,“钱学森是经过仔细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指亩产4万斤谷子——引者),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叶文并引用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看法,“钱学森一直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叶文还对钱学森在1993年继续改进计算结果表示赞同,“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由上可见,叶永烈先生是通过反复强调计算的正确性来为钱学森辩护的。但笔者看来,计算的正确与否是一个纯自然科学问题,可以通过各方专家的互相探讨,从长计议来解决问题。但是对钱学森先生在1958~1959年期间公开发表6篇宣传“万斤亩”的文章来说,就不能从纯粹科学的角度去评判,文章一经公开发表就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影响,因此问题也就从纯粹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乃至政治领域,因而必须结合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联系方可作出全面、客观、深刻的评价,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获得真正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叶先生的长文对细节的考察详尽而深入,令人敬佩,但恰恰忽略了整体联系的宏观视野,忘记了钱学森“万斤亩”文章发表前后“基本的历史联系”。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亩产2105斤的小麦高产卫星,时隔8天,钱学森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中指出根据科学计算,亩产可达4万斤。这篇文章的影响如何呢?叶永烈先生的长文已经为此提供了答案: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7日视察中国科学院时对钱学森说,“你在那个时候敢说4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跳出纯粹自然科学范畴而从历史联系来看,钱学森“万斤亩”文章的社会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其实叶永烈先生自己也是明白的,只是刻意回避评价中的这一实质问题。叶永烈先生又提出有人捉刀的理由来辩护,这也是难以成立的。问题在于文章的思想是否真实反映作者的思想,至于文章“捉刀”的情况,比比皆是,何足奇哉!更何况原作者说得很清楚:“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就署他的名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了。”叶永烈先生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是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由此可见,钱学森“万斤亩”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客观的负面社会影响并不等于主观动机的恶意,好的主观动机也常常会引出坏的客观效果来。相信钱学森先生是出于良好的主观动机来发表“万斤亩”文章的。然而历史的评价必须坚持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相统一的原则,不能因为良好的主观动机而抹杀负面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历史评价也必须坚持科学探索与社会历史视角相结合的原则,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探索性的东西,能否发表,在什么刊物发表,还必须预测其社会政治影响,真所谓探索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正如科学家无法从纯粹理论计算来预测粮食亩产一样,今日的科学家也无法从理论和观测的结合上预报地震。地震学家自然可以继续其地震预报研究,但在掌握其内在规律和预报方法之前,是不允许随意发布其预测预报的。
顺便要指出的一点也与思想方法有关。叶文对祁淑英和魏根发著的《钱学森》一书发起了尖刻的批判。祁、魏亦是资深记者和作家,写过不少有益的作品。二人撰写的《钱学森》属传记性作品,传记亦有不同风格。法兰西学院院士莫洛亚对传记所依史料要求极严,认为传记作品应该严格依照史料进行创作,不能加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莫洛亚如此要求,也仍有很多不确定性,难以保证所谓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首先,留存的史料不可避免有留存者的主观选择和描述;其次,莫洛亚也承认传记作品必须经过“创作”环节,而创作必然渗入主观因素。由此观之,对传记作品的纯客观要求是难以达到的,它的历史真实性必然是有弹性的。传记作品因写实成分多寡而千姿百态,在传记中根据史实而添加文学性情节也属平常之举,看看传记权威朱东润先生关于杜甫、陆游、张居正等人的名著就可知传记并非不能依据史实构造文学描述。祁、魏所写的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一事,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刊为史实,至于检讨的具体情节的描绘是有所异同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钱学森该不该向毛泽东检讨?叶永烈先生认为压根儿不需要:“钱学森倘若当面向毛泽东‘检讨’,这就是表明钱学森承认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他写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从历史联系和社会影响来看,钱学森应该作检讨,钱学森未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向毛泽东承认计算方法有错误,这是其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祁、魏根据史实设计检讨的具体情节,是善意的解脱钱学森之举,折射出来的正是对中国杰出人才的大爱。叶先生以“纯属瞎编”的激烈用词,对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定性,不仅态度失之于严酷,而且从客观上陷入了过度辩护的误区。平心而论,从记者和作家擅长的领域跨入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驰骋的天地,谁都有风险,本是同类,又相煎何急!
三、应该更新的评价基旨
叶永烈先生的长文涉及到一个更普遍深刻的问题——如何评价杰出科学家。
杰出科学家是古今中外极其稀缺的人才资源,在当今科技时代,杰出科学家还是综合国力竞争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许多杰出科学家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典范,如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人才评选中名列前茅的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就当代中国而言,一般科技人才相对富足,甚至过剩,而杰出科学家非常难得,钱学森生前就曾感叹杰出人才为何出不来。百年以来中国仍未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近1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十年六缺(仅2002、2003、2006、2009各一项),因此我们今天来评价、宣传杰出科学家有异常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围绕杰出人才问题,可以使公众提高认知能力,使有关机构提升人才管理水平,使社会形成有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文化氛围。
对于杰出人才的评价,存在一味拔高、刻意辩护或一味贬低、求全责备两种倾向,都有悖客观,而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我不知道叶永烈先生心中的杰出科学家是什么样,但我知道人类历史上杰出科学家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普遍反映在科学文化和政治方面,有的还会反映在宗教、道德等方面。
牛顿是彪炳史册的伟大科学家,然而牛顿曾因微积分、引力定律和反射望远镜的发明权,三次深陷发明权的争执,被20世纪的爱因斯坦称为“虚荣”;牛顿还将自己无法理解的科学动因归于上帝的力量。牛顿的这些问题,今人大多以历史局限性加以宽容,牛顿仍因创立第一个近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而位列头等科学巨星。二战期间,量子力学的创世人海森伯留在国内与纳粹政府合作,从事核物理和原子弹的研究,使人生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但是海森伯激动人心的量子力学创立史及其非凡的物理哲学思想,始终是人类科学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爱因斯坦是极少数能超越时代政治局限的伟大科学家,在德国法西斯刚刚兴起之时,便独具慧眼并挺身而出,从而成为在科学与政治两个方面同时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巨人,在世纪之交与千年之交的人才排名中,与马克思一起同登榜首。但是,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和哲学上仍然难脱时代的局限性。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科学遗憾是,没有发现本已隐含在自己宇宙方程中的动态宇宙模型,而提出了一个静态宇宙模型。当苏联年轻的弗里德曼第一个提出动态宇宙模型时,爱因斯坦不仅没有领会,而且著文批判弗里德曼。直到7年以后,哈勃红移现象的发现才使爱因斯坦醒悟过来。在哲学上,爱因斯坦因囿于经典决定论而排斥量子力学的统计性质,也因过度追求统一性而陷于终无结果的统一场理论探索。然而这些暗影并未遮掩爱因斯坦作为头等巨星的光辉。历史的评价是严厉的也是公正的,人为的辩护是不必要的,也是无用的。当年,牛顿为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曾在幕后操纵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企图证明另一位微积分发明人莱布尼兹是剽窃者。科学史最终公正承认了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共同发明权,而牛顿的过度辩护反倒成为自身的失误。
钱学森先生的功绩已牢牢地印记在历史的长河中。钱先生的功绩虽然难以胜数,但最重要且启人心智的三个方面是:科技创新与工程管理的杰出贡献,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胆探索,社会政治理念的与时俱进。前两个方面已有大量著作可作佐证,也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恕不多述。而“万斤亩”公案如果能从其政治理念与时俱进的框架中来解读,则能作出更客观理性的评价。依笔者之见,钱学森“万斤亩”公案的评判,不能将其定为纯粹科学探索问题,也不能认为钱学森在此问题上没有任何社会政治责任。客观的评价是以全局和动态的视角,将其视为钱学森归国后社会政治理念发展全过程的早期阶段——学习脱毛阶段所交的学费。回国后的钱学森正遇上新中国早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时期,也即社会主义模式探索时期,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和缺乏经验,当时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弊端,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当然也不具备看清其弊端的政治眼光。怀抱满腔热情、竭力报效祖国的钱学森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由于主观上缺乏真切的政治见解,实践效果毁誉参半:既为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等重大任务做出过重要贡献,又盲目发表“万斤亩”的多篇文章。这是难以避免的结果,要求杰出科学家都像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一样,在社会政治方面有超越时空的远见卓识是不现实的。但是钱学森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其政治理念随着社会实践和不断思考而与时俱进,其在中年时期多少带有自发性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在晚年时期转变为较自觉成熟的社会政治活动。转变的标志即是2005年发表的“钱学森之问”,并从杰出人才培养的视角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高度,重提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重大时代课题,对中国当代难以大量涌现杰出人才的深层次原因作出犀利的批判:“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
综上所述,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发生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模式的早期,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钱学森发表“万斤亩”文章,客观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叶先生完全否定其负面影响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也应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无须过分追究钱学森个人的责任,这一事件在钱学森思想政治发展全过程中,毕竟只是短暂一瞬。晚年钱学森大无畏的“钱学森之问”,向世人展示出一个不仅在科学、技术、工程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高度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且对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深层次问题有敏锐洞察力和责任感的杰出科学家形象。中国杰出科学家达到如此全面发展的境界,无疑为中国杰出人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杰出科学家的巨大功绩与历史局限同是客观存在,无须也无法为尊者讳,不能也不应求全责备。钱学森先生恰如一块天生的良玉,在中外优良科学文化的雕琢下,在重大国家需求和时代政治环境的磨砺下,终于玉成千姿百态的极品。纵然雕琢成极品,也仍有其独特的质、形、色、声、纹,当然也并非尽善尽美。后人鉴赏的艺术,不是大而化之的老生常谈,不是一味的膜拜惊赞,将其抬到吓人的高度;而是深入其质、形、色、声、纹,欣赏其精妙穷神的独特魅力,复归其质朴可亲的自然本色。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