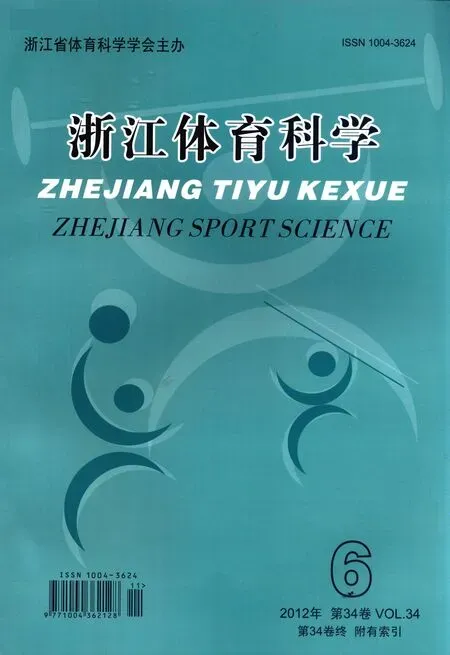国民政府(1924-1949)促进体育发展的措施及现代启示
2012-01-27李红英
李红英
(四川农业大学 艺术与体育学院,四川 雅安625014)
中华民国时期教育界、政界对体育的重视促进了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其中,民国时期仁人志士对体育思想的传播、国民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主动发展的措施,是民国时期体育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了“完善人格,首在体育”的观点,认为“有健全的身体,始有健全的精神”。毛泽东提出体育是一种有规划秩序的“养生之道”,其目的在于“养生”、“卫国”。由此可见,体育已经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当然,这与当时“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有关,在致力于改变民族危亡命运的仁人志士倡导和推动下,“体育救国”思想全面传播,并融入全运会。在国民政府的极力争取下,民国时期的第三届全运会开始收回了全运会主办权,国民政府体育发展以此为依托和重点进行全面辐射,对促进体育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国民政府对全运会的推动力度,旨在通过重新认识国民政府促进体育发展的措施,以期从中获得启示,为当代全民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 国民政府体育思想的转变
国民政府体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对体育价值认知的提升上,认为体育有助于增进国民健康、培养国家观念。中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对西方体育的接受既有不自觉成分,更有主动接受和吸收的成分。事实上“体育救国”并不是系统的理论思想,而将体育、将全运会视为“强国强种”的有效手段,则是吸收西方体育的内在需求,也是促进全运会民族化发展的强大动因。从历史视角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近代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灭亡在即,仁人志士深感振兴中华、救国家于水火,首先要改变国民的体质,即“强种”,才能促使国家强大,由此掀起了“体育救国”思潮[1]。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全运会完全超越了大型体育盛会的内涵,而成为“强国御辱”、“复兴民族”的一种手段[2]。民国时期全运会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了其必然会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与国家振兴联系起来。爱国人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救国的途径,因而喊出了众多的救国口号,而其中的“体育救国”是最为响亮的呼声[3]。他们认为,国民身体强健才能进行自卫,才有能力保家卫国,因而呼吁中国人都要主动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魄,捍卫民族尊严。基于对“体育”改变国家命运重要性的认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体育与振兴国家联系起来,旨在通过促进体育民族化发展来提高民族体育的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地位。体育界在各界爱国人士“体育救国”的呼吁下,积极探索如何以有效的方式进行体育宣传,推动民众体育锻炼的发展,达到强国强种、挽救国家和民族的目的。体育界一些人士认识到运动会的体育宣传过程能够对民众起到动员、示范、带动的作用。全运会就是基于这种体育民族化发展背景下进入转型阶段的,并因其参与对象的广泛性,而成为促进“全民健身”发展,增强民族体质、鼓舞全民士气、激发国民爱国热情、实现自强救国的主要寄托。中华民国时期的全运会在组织机构方面、竞赛规则方面的民族化发展,承担起了政治目标,被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得到不断推进。民国时期全运会的动态发展就是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体育救国思潮的作用下而得到不断推进的。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人起初对“外来体育”知之甚少,对西方传入体育的文化侵略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思想上也缺乏应有的觉悟。随着国际局势的恶化和内忧外患局面的日趋严重,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处在民族危难的境地,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有效措施,努力让国民在思想认识上提高。民国时期举办的第二届全运会虽然与清末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一样仍由外国人操办,主要工作人员和担任裁判工作的人员也都是外籍教士,文稿类资料和裁判用语都是采用英语[4],但第二届全运会与第一届全运会相比,已经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特别是从第三届全运会开始的五届全运会,中国不但完全收回了全运会的主办权,而且在赛事组织和项目设置等诸多方面都在不断提高民族化程度。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全运会民族化发展首先体现在国民逐渐认识到体育主权也是主权的重要一方面,尤其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全运会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三届全运会中国经过多方努力和多次辩论,积极争取并成功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主办权,就是对全运会主权的重要性认识提高的有力佐证。在举办第三届全运会之前,体育主权之争的原因是,人们认为中华民国的全运会应该是由中国人主办,全运会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体育盛会,而不能是外国主办的运动会,更不能全程使用英语,相反有必要融入民族传统体育,推进全运会的民族化发展。随着第三届全运会主办权的收回,从此改变了全运会完全由外国人操办的历史。与此同时,全运会思想认识民族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体育救国”思想的强化,认为发展体育有助于增强国民体质、强健国民体魄,可以挽救濒于危亡的中国,是推动全运会民族化发展的有效动力。面对民族危机,民国时期第三届、第四届全运会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注重体育,以应对危机,“体育救国”思想趋于高涨。在当时,大家认为体育只有走民众化道路,才能是就救国的体育,全运会要实现民众化,才能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可喜的是,关于“体育救国”与全运会发展,许多人不仅认识到体育可以使国民体魄强健,而且认识到通过体育运动可以形成一种“体育精神”,凝聚成为“服从、团结、合作、任侠、尚武、纪律、耐苦”的强大精神力量[5]。其中,体育的“团结合作”精神(Team work,Team spirit),有助于唤起全国民众团结合作精神,是中国的“急救品”,就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因此,促进全运会民族化发展,增强民族团结,挽救国难,成为民国时期全运会的重要历史使命。
2 国民政府体育促进措施
2.1 争取全民参与
国民政府发第三五0二号训令强调:“今后务求全国男女长可各有参加体育之机会”,“各校体育均应注重团体方面,务使其在各个学生身上为普遍之发展。各校尤宜为各当地体育之提倡者,唤起社会,使人民均能实行体育之锻炼以资普遍推行”。民国时期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改变了第一届全运会将参赛队伍分为华南、华北、武汉、吴宁、上海五区和教会学校代表队的模式,而将参赛队伍以全国地域划分为东、西、南、北四部,但所谓全国“四部”代表也只不过是个象征,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总共只有96人,其中南部参赛运动员只有2名网球队员。民国时期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将各参赛队按照区组进行划分,根据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五个区域来划分区组。从参赛队伍的组成方式来看,显现出全运会已经有了由教会系统范围向着全社会过渡的趋势。此次全运会首次正式设立女子竞赛项目,仅女子运动员就多达498名,参加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四个项目各小项的具体比赛。1930年第四届到1948年第七届,连续四届都是按省市与华侨团体参加竞赛。1930年在浙江杭州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竞赛开始改为以省市特区及华侨团体为单位,参加单位和参赛人数比以前大增,参加比赛的单位多达22个,男女运动员多达1 630人。此次全运会参赛对象与以前几届运动会的参赛运动员都是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次全运会运动员身份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提倡业余运动,因此赴这次全运会的比赛者由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员组成。第五届全运会参赛对象规模进一步扩大,参赛男女选手共有2 248人[6],较上一届全运会参赛人数有大幅度的增加,比民国时期第一次全运会即第二届全运会参赛人数的23倍还多。此次全运会的参赛运动员中,男子有1 542人,女子有706人,在增设了男子“国术”锦标的同时,还增设了女子垒球、游泳和“国术”3种锦标,并将田径锦标改为田赛与径赛两种锦标。第六届全运会共有来38个参赛单位的2 7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此次全运会一大亮点是,参加比赛的华侨特别多,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华侨、马来亚的华侨和爪哇的华侨队,其中,仅仅来自马来亚的华侨就达到了150多人,体现了中华儿女一条心。在此次全运会的开幕式上,东北五省的运动员身穿黑色丧服,以黑白两色旗示意白山黑水被日本侵略者践踏,警醒国人勿忘东北,增强全运会号召爱国救国的气氛,充分体现了民国时期全运会的民族化。第七届全运会参赛单位有各省、市及国外华侨和军、警,而且,由于台湾归还中国也参加了这次全运会。尽管此次全运会参赛运动员人数2 677人略低于第六届全运会参赛运动员人数,但此次参赛单位共由55个团体组成,形成庞大的参赛规模,进一步展示了全运会的全民性和普及性。
2.2 推进体制改革
由于前两届全运会都是外国人操办的,西方文化强权介入,竞赛制度移植于西方体育竞赛制度,完全体现出西方体育竞赛模式的特征。然而,这种对中国体育事业进行控制和垄断的企图被爱国人士意识到,并强烈地反抗。中国人不甘心外国人操纵全运会竞赛活动,积极寻求转变外国人控制全运会竞赛事宜的途径。因此,第三届全运会收回组织主办权,全运会制度由移植外生性开始转向本土化实践,田径赛的丈量由码制、英尺制一律改为米制,这是全运会竞赛制度民族化的初始阶段。从全运会民族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全运会主办权收回后,本国、本地、本民族的内涵、特征和特色得到不断深化,第四届、第五届全运会由全国体协负责组织,竞赛制度在第三届全运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规范,第六届全运会还颁布了《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对参加办法、比赛规则、录取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明细的规定[7],第七届全运会延续了第六届全运会的竞赛制度,并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相互切合更加紧密,进一步促进了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从筹办组织看,第一届全运会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并有该会美籍体育干事爱克司纳负责操办,民国时期举办的第二届全运会是由该会的名誉秘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候格兰德实际负责(名义上由“北京体育协进会”主办),也就是说,前两届全运会基本上全由青年会外籍干事操办,不但主要工作人员和裁判员都是外籍教士,而且文稿、公告、运动会秩序册以及裁判用语都是采用英语。第三届全运会前夕,提出“中国事当由中国人办理”,成立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组织,来管理国人的体育,组织全国运动会。这届全运会除了少数几个裁判员是外国人外,其余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担任,是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之始。第四届全运会由浙江省政府负责筹办,这次比赛的筹办组织较之以往的三届全运会有了较大的改变,首先是在全运会前全国各省市开预选大会,通过预赛选拔出代表赴杭参加全运会的正式比赛。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运会由中央政府主办。事实上,除去清末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民国时期实际上只举办了六届全运会。从竞赛制度方面看民国时期举行的六届全运会,可以发现,国民政府主要通过竞赛组织、参赛单位、项目设置、比赛规则、全运会目标定位、记分办法、录取办法等方面不断推进全运会的民族化发展。
2.3 丰富体育项目
全运会所设置的竞赛项目每届都有所不同,第一届全运会原名“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比赛项目只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项。第二届全运会于1914年在北京天坛举行,比赛项目增至六项,具体分类为田径赛、篮球、队(排)球、足球、棒球、网球。其中,田径比赛设立了17个小项,分别是“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英里和5英里赛跑、220码低栏、120码高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铁球、铁饼、半英里接力赛跑、1英里接力跑、5项及10项运动[8]”。第三届全运会于1924年在湖北武昌跑马场举行,不仅比赛项目再次增加,增至七项,而且项目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赛项目分类有田径、足球、棒球、排球、篮球、网球、游泳七项,此次全运会还将女子球术、童子军、国操、器械操等作为表演项目,初步体现了全运会的民族化发展趋势。第四届全运会于1930年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次全运会竞赛项目分为男子田径、全能、足球、棒球、排球、篮球、网球、游泳八种锦标,和女子田径、排球、篮球、网球四种锦标分别计总分[9]。在这届全运会上,男子自行车、国术和女子舞蹈等被作为表演项目,国术的进入说明全运会民族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第五届全运会于1933年在南京举行,由中央政府主办。这届全运会在上一届全运会项目设置的基础上,将田径锦标改为田赛与径赛两种锦标,此次全运会还增设了女子垒球、游泳项目。尤为突出的是,这一届全运会将上一届全运会国术表演提升为“国术”锦标,增设了男子“国术”锦标和女子“国术”锦标。第六届全运会于1935年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在原有的运动项目全部保留的基础上,此次全运会进一步融入了民族传统元素,增设了举重、竞走、摔角、马球、小足球、自行车等表演赛。第七届全运会于1948年在上海举办,这一届全运会竞赛项目再次扩展,增加了乒乓球、举重、摔跤、拳击等项目,增加了羽毛球和国术两个表演项目。通过以上梳理,仅就民国时期举行的六届全运会来看,武术、摔角、马球、小足球、乒乓球等民族传统项目的逐届增加,体现了全运会民族化的不断推进,为民族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思考与启示
国民政府促进体育发展的措施主要是争取全民参与、推进体育改革、丰富体育项目等,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国时期全运会因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对全运会思想认识的提高、主办权的收回、竞赛组织和项目设置的本土化、参赛对象的全面普及,无疑是国民政府体育促进措施有效性的具体体现。这一发展进程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发展,增进了国民体质,强健了国民体魄,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民族士气、增强民族团结、激发民族爱国热情的作用。
[1]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2-118.
[2]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69-77.
[3]刘勇.略论中国“全运会”演变史[D].南京师范大学,2007.
[4]张涛.民国时期的一次体育盛会[J].文史博览,2005,(19):41-43.
[5]李润波.民国时期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与体育专刊诞生[J].北京档案,2008(2):42-44.
[6]张建会,钟秉枢.1910~1948年全运会制度的历史考察[J].体育学刊,2010(8):71-74.
[7]史国生.对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开幕式的考证[J].体育文化导刊,2005(12):23-26.
[8]卢立菊,付启元.回首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J].江苏地方志,2005(5):54-56.
[9]开云.中国全运会述评(1910-2001)[D].南京师范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