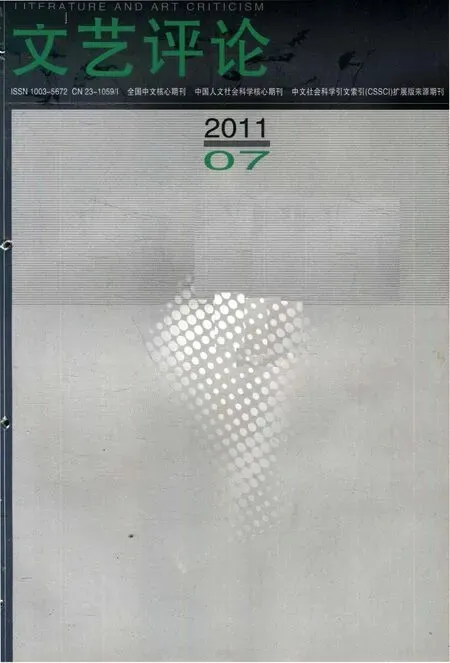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与反思
2011-11-25潘水萍
○潘水萍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与反思
○潘水萍
一、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
以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为视角的整体意识来看,古典主义作为一股重要潜在的文学思潮及一种至为显著的源远流长的审美理想,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展开广度的理论意蕴阐析、探微。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学界迄今对“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命题研究,因一直怀有戒心似的淡然处之以至人们对其几乎毫无所知。也许,当人们对刚刚过去的百年文学史或思潮史进行独树一帜的概观、清理、鉴照、反思、重审与评点时,亦甚少从历史视野的多维视阈或反思立场的价值向度自觉地意识到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曾经受的译介、传播、勃兴、误读、蒙蔽、冷寂、荒芜、衰微与敞开等起落沉浮的现代命运及演变论争,进行自成体系的源流考总结和理论根基意义的张力思辨。由此看来,“古典主义在中国”命题研究的整体性缺失、疏漏与架空,诚然成为当下学界研究领域亟待深入综述和认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古典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命题被低估、裹挟、轻视、疏漏与尘闭了,至今仍无以剔破其樊笼进行多元视阈的合理阐释而窥其底层堂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掀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叶维廉曾以一种略为温和的口吻却不失批判意识地指出:“科学和浪漫主义被同时移植到中国来是有着多重暧昧意义的。发生于浪漫主义前数百年欧洲的古典主义,发生于其后的写实主义,以及其他移植过来的意识形态和理论,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都具有不同时空的延展,其中还有不少是针锋相对的。这么多不同历史根源的思潮和文学运动竟会在一二十年‘同时’移植过来(有时全部集中在一个作家身上),这是耐人寻味的。”①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坛正逢中西文化彼此激荡与交融的时期。韦勒克曾尤为卓而不群地彰显:“对现代文学史中的各个主要时期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近来‘巴罗克艺术风格’等术语一直在界定,再界定,和争论。”②事实上,随着人们对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进行具体历史语境的透视时,却远远地把古典主义遗忘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应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理应受到学界研究者的重新审视、清理、勾勒与潜在性的解读。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却难觅其影响的踪影,这显然是学界研究领域的一大狭隘欠缺与盲视之点,实在不可思议。有学者意味深长地总结:“在考察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们显然很难找到法国古典主义传播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丰富史实……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古典主义关联问题的文章,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很久以来,我们在分析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时,常常在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做不厌其烦的阐述,却独独没有古典主义的位置,不管是有意地回避还是无意地忽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缺憾。”③因此,本着对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盛衰显隐等基本现象作一正本清源的概括导向对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探要和现代意义的思想展望,使人们对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认识的空白,可获得一些填补。
从社会思潮批判的思想史交叉渗透的理论角度看,刘永济于其《文学论》一著述中令人钦佩有加地述评:“古典主义Classicism一派,夙为文学之正宗,其要旨在注重中庸之道德,推崇高尚之理性,专写恒常普遍之人情,而一是于纯正。自十八世纪以还,久为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派所攻击,其势渐衰。”④针对古典主义之和谐美,周来祥则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与文化价值取向的述略:“古典主义的和谐美,有它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尚未见出深刻对立性的对事物直观的整体性把握,它突出强调的不是矛盾的对立,而是偏重于各种矛盾因素的统一,即对立的统一。对美的本质的探求是一个哲学问题。用朴素的辩证法把握美的本质,必然把美看成是各种因素的和谐,或者说和谐就是美。和谐美就是古典主义美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艺术的本质。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同意把古代艺术划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范畴,而是划归古典主义的美学范畴。”⑤简而明之,周来祥此段精辟而敏锐的文字所蕴涵的现代性省思理论剖析,无比有力地折射、点睛出古典艺术之“古典主义”和谐美的理念,给人予一种深刻的启迪。事实上,这也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韦勒克颇具智慧深度地指出:“新古典主义在历史上是权力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体,是一种保守势力,因此它要尽可能维持和适应古代的原始文学种类,特别是古代诗的种类。”⑥刘绍瑾教授则以一种沉潜而致远的气度极为明确地指称儒家传统文化就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文化。“即使就中国批评界来说,最早以源自西方的现代名词来概称中国文艺思想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而似乎是‘古典主义’……随着‘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界的传播和影响,以‘古典主义’来沟通孔子及其影响的儒家文艺思想的声音逐渐消失了。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美学热’的兴起,才重新出现了一些以‘古典主义’来说明中国文艺传统的研究取向,周来祥即是其代表人物。”⑦显然,这段颇具锐利锋芒的铿锵言论隐然地提出了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气势的重要性见解,即以“古典主义”而不是以“现实主义”来概观中国文艺思想更为贴切与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由此足见其别出心裁之见解的暗示性、辩驳性和深刻性,这倒是值得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做出反省与关注的。
回顾20世纪中国百年新思潮消长显没的文学现象及中西文化于“传统”与“现代”的独特的交互会通的文学现象印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重新发现与界定,诚然是近年敞开并渐趋勃兴探析与挖掘的文化表征。“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徘徊在文学的自主性和政治性之间,这种困境直接导源于‘文革美学’。‘文革美学’的实质是古典主义。”⑧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股被遮蔽于主流之外的古典主义,一度被学界有意无意地低视、排斥而迟迟未能得到人们的深层阐发与主导性的梳理而长期处于沉寂、尘蔽的边缘化境遇遭际的现代命运。实质上,古典主义无论是作为一股文艺思潮抑或是一种审美理想,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始终占有至为重要的一席之地。的确,“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被历史时代所低视的现代命题,显然亟待当下学界展开多元维度的综观、廓清、勾勒及解读。毋庸置疑,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展开探析与管窥,必然可以弥补“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论题亟待深入阐释这一不可逾越的遗憾。此外,透过被忽略和被遗忘的“古典主义”文艺创作思潮理论,从全新的视域勾勒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深层维系中所包孕着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介入、传播、接受、误读、遮蔽到敞开的消长沉浮命运,显得更为重要。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知识分子,他们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学说的认同、选择、吸纳、诠释与宣扬,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坛上激荡起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诚然,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显然与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被曾经一度的以偏概全的妄误解读、遮蔽而不可救药地滑向尘闭、沉寂有极大的内在因由。以下将对此问题症结进行多维度的简要综观、比照和考证。
二、欧文·白璧德学术批评新声的尘闭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缘起,理应上溯到20世纪早期留学潮影响下的吴宓、梅光迪、梁实秋等人对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古典主义现代性文化理路学说的历史时代认同、选择、接受与传播。“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正式通过‘学衡派’的译介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⑨众所周知,欧文·白璧德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是一位颇具争议的跨文化文学批评家,其思想学识与哲学基础有着多重渊源的文化元素。事实上,其文学理论着眼诉求的刻度及其开放的思维张力与其说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人文精神的理性批评镜像,倒不如说蕴涵着诸多新文学批评重构趋向的“潜在设想”和审美意蕴的现代价值内涵。此外,其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诸多的隐喻性思考、辨误、探略和考论,同样深深地淌荡着一股浓烈的古典西学的心性情怀和具有永久价值的传统秩序理想。有学者曾气度不凡地评述:“具有新人文主义之称的白璧德主义代表了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叶的一种自我调整与自我反拨。”⑩白璧德极为注重对时代经典所承载那种温润经脉、微言大义所显现的精神性学问光芒和经验价值进行纵横的断想、秉持、整合与新扬。他不失新意地强调“古典精神”有某种学术性的东西。(11)事实上,白璧德揉合了古典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文学批评思想之注意力所涵盖着的深刻指引,对现当代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依然有着遥不可及的甚至不可估量的特殊启示意义和影响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汇互渗的历史语境中,他以思力深厚的文学思辨力度、内涵,为现当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意蕴清新的批评新声并掀起了时代的回响。也许,他独特视角的高度阐发和强效的批判力量或多或少能给予人们某种暗示性的启悟与真诚的现代性思考。白璧德以一种具有现代开拓性思维信念与现状展望视野,认为20世纪学界对古典传统文化真精髓普遍存在一种只“弃”而不“扬”的低视与诘难的硬性态度是极为危险的。对此,他对20世纪现代文明暗藏的人文精神危机做出了富含历史意义的解蔽、批判、反思与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璧德古意盎然的文学批评思想走向的正是一种契合现代意义的“古典批评的勃兴”,其系列著述的思想内容不仅有着“不可埋没”的时代指引意义,而且也具有更高意义阐发与融摄的重要性及当代启示。
不必讳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对西方文化迎拒褒贬的迹象。叶维廉颇具思辨性意义地强调:“我们必须了解某种思潮进入中国历史意识时的复杂方式。当时知识分子所接受的部分,不一定是该思想大的部分,甚至不一定是重要、精要的部分,而是那恰好适合或接上当时历史、社会变化的相关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这些合乎历史需要的相关部分和外来模子中那些有助于巩固及创作中国传统的重要的文化层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文化和美学视境中的中国特征及其在过去运作时的原始力量有一个完全的把握;其次,我们必须探究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它在自己的时空中运作的原始力量,我们始可以明辨它们可否汇通与交配生长。”(12)具体地说,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具体历史时代因素影响使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受到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程度的迎拒、筛选与接受。毫无疑问,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于20世纪20、30年代,经由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为代表的学衡派及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推介与宣扬。事实上,他们对白璧德之文学批评学说的推崇,主要是以一种对抗当时文坛学界那种极端泛滥之浪漫主义之负面影响的姿态出现。然而,白璧德以捍卫古典传统文化为显要特征的文学批评主张在中国文坛并没有走运,甚至应者寥寥而成为历史时代有迹可循的缩影。这主要根源于当时主流文坛由于诸多的历史因素及思想立场之迥异使然,绝非白璧德文学思想缺失批评的力度和锋芒。作为一股抗衡着当时滥觞于文坛学界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新思潮负面影响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固然有其隐而不彰的历史现实贡献。俞兆平曾以一种足以澄清性的学术论调矢志不渝地认为: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坚持以人文精神的立场和一种警觉、反思的态度,批判、抗衡现代性负面效应,不仅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13)显然,近年来,俞兆平浓墨重彩地追溯、界定与探寻了古典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富含前瞻性的辩驳显然给人予一种登高望远的振聩与简劲有力的反思。
不容置疑,白璧德颇具抛砖引玉的文学批评眼光的表达与学术心得经验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具有最大说服力的比照和借鉴意义。他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反思所隐含的可能性批评路径的阐释和不受传统羁绊的周全论证。可以说,其文学批评不仅牵涉到文学创作审美维度的一种更高意义的指正、纠偏、矫枉、疏通与指引,而且其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持守着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境界和高瞻远瞩的气度,倾重于解构、发现、重建与导引某种文学批评理应持守而非迁就的东西。事实上,回顾五四新文化时期各种新思潮涌现文坛的境况,尤其是颓废派、浪漫派、唯美派等极端、空洞与泛滥,留学归国的学衡派知识分子如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正是从欧文·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中吸纳了一种稳健之文学批评观,从而尤为警惕、厌弃当时勃兴于文坛上的极端“抒情癖”。仍然值得指出的实际问题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叶维廉曾以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自然贴切地指出:“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沾染了一种爆炸性的情感主义。五四运动很难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14)然而,站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观照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诉求,学衡派知识分子对白璧德思想的推崇偏重于以文言文的形式从“道德感”的角度来进行译介、接受与诠释。这让当时学界大多数青年学者对其学说敬而远之甚至产生一种偏执性的先入为主的定见、误读,致使欧文·白璧德思想学说从一开始就受到某种历史时代的局促、狭隘性的定见,远远未能引起人们的青睐、拜读、诠释、回应而一度处于沉寂、尘闭的现代命运况味。这种境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们对新人文主义的阐发,白璧德思想学说批评之锐利性、洞见性才再次浮出水面渐趋为人们所体认、识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知识分子梁实秋后来更是紧随学衡派之后接触、选择、接受与发现白璧德文学思想学说之批评锋芒与力量。实际上,梁实秋从“浪漫”到“古典”的倾重之学术理路,诚然得益于白璧德思想理论对其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文学批评的历史角度看,白璧德对传统文化整体性嬗变的现代性转变做出了尤为值得信任的深邃解构、探幽和反省,而且他对当下文学建构之文化场的取向有着某种内在的更为合理的超然审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应透过其看似“复归传统”的繁复言论框架,洞悉到其倾心灌注的反向启悟和凸现性的揭晓。事实上,白璧德文学批评理论底蕴最为坚韧而显要的思想面相,足以引起人们的一些重要反思与重新发现。众所周知,欧文·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思想学说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学理存在诸多方面的相吻合的内涵积淀——即“中庸之道”文学观的持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有效地激发吴宓、梁实秋等中国留学知识分子于20世纪20、30年代初期,倾向于师承兼开启其富于可塑性与活力性魅力之批评理论经验在中国学界传播的因由。“白璧德的学说我以为是稳健严正,正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的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15)若以现代性视野来综观“学衡派”对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译介、解读与宣扬的迹象,则可发现其文学理论主张则更多地表现出其对“稳健”之古典传统文化之有益经验的肯定、接受,同时也折射出古典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和延伸。然而人们更应看到,学衡派颇具远见地指出古今中外文化的传统文化有着融会贯通的古典源流,即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为代表的现代性人文精神及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之“中庸”和谐哲学观,这正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需要参照与引起回响的真正文化之会通与启蒙。
简言之,白璧德文学批评尺度的学说旨趣与理念精神皆充溢着其敏锐谨严的思想精神和鲜明而特立独行的思想态度,其标举、凸显和昭示古典传统文化不仅存在着值得现代文学批评界借鉴与摄取的一面,而且恰恰彰显出其批评惊人的回应力与预见性的迹象无疑存在诸多值得追索与深挖的阐释空间。张源在译后记一文《“新人文主义”:美国与中国,历史与现状》中揭晓:“适度的法则——‘中庸之道’——成为最高的人生法则,强调‘人事之律’,就是要促使人们重视并运用这种令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庸适度的收敛集中之原理。”(16)白璧德恰恰是一位秉持着与时俱进的“适应变化需要”的不失信度的某种新范式话语的代言者。他以更高的透视力、以理性的崭新视角,着眼界定了“古典传统文化”明确的批判立场,这不仅给当代予缜密结实的入思维度与评判路向,同时也折射出文学批评渐趋走向一种自律性的审美价值标准与创作的理性自觉,凸现其理论思想力度的厚重与分量。他认为批评尺度应是“极端之间的调和物”的精神重塑。显然,白璧德的高瞻气度恰恰体现在他从古典传统文化中超然而坦荡地内视到一种完整系统的“常态人性”批评精神与使命。“适度的法则是最高的人生法则,因为它限制并包含了所有其他法则。”(17)他认为克制、适度是人性获得内在谐和的元素基调,合宜得体、温文尔雅的传统文学批评尺度和精神诉求,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依然有其先验性、可行性、可释性与合理性的内在意义蕴涵。事实上,他并不遮蔽而是以一种回溯源头式的方式澄清古典传统文化批评理论尚存的限度与利弊,而是把其纳入现代性语境中进行理性的批判与某种清新的论析。在现代视野思想中,白璧德思想学说最早以一股清新的批评审美精神之风被引介至中国学界文坛,这要归功与得益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梁实秋等新生代知识分子敏感的学术发现、选择、接受、译介、诠释及现代性反思。
近年来,学界对白璧德思想学说的探究渐趋呈示出一种重新阅读、重新发现的整体性势头。这无疑已应验性地印证了白璧德思想学说正如梁实秋早年“不可埋没”之预言,同时也暗示其学说所隐潜的思想力量之所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便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早期社会病象思考的产物……白璧德对西方社会的现代病感同身受,有许多深刻的反思。”(18)总而言之,白璧德古典温情而又锋芒毕露的思想学说应进入当下学界探究的视野,尤其是他明确坚定而又暗暗自得地重塑、发现到诸多言之有理的文学批评的独特思想视野。至少,一方面它给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一种厚重通透、温暖有益的思考力量,另一方面它深深地唤起并照亮人们对现代文学批评境况的警醒与反思。
三、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当下解读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因研究者缺乏对其进行自觉的学术反思与自省而长期受到历史时代的人云亦云的、歪曲如此熟悉的事实的陈述所造成的片面性之狭隘误读与滥觞之定见,远远未能引起学界文坛深度的正视与独特的丈量,同时也因学界文坛研究领域缺乏对其做出整体性深层理论的清理、勾勒、综观而一度处于明确贬低之暗处遮蔽的境地而显得沉寂无声。简而言之,学界研究尚且未能充分凸显出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误读、沉寂、遮蔽到敞开这个流脉展开新颖性的多维张力探究与纵观。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或隐或显存在,他们以时代相应的姿态对“古典主义”把脉会诊式的相关论析,也深深折射见证出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李怀亮、钱振文于《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古典主义倾向》一文中以先锋性的笔触姿态认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倾向主要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人文主义是其批评倾向的精神背景和思想基础。新人文主义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儒家传统渊源。(19)邓文华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一文中直探本心地知性断言:“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恢复文学史原貌的必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回答现代文学史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内涵,即用审美现代性质疑历史现代性;是现代文学之历史发展合力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几年来的史料发掘和梳理已经证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不仅不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排除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那么不仅文学史的原貌恢复无从谈起,而且一些历史问题也无法回答。”(20)古典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文艺思潮及一种审美理想,诚然有其存在的时代历史因素而绝非所谓的一抹辉煌的残照。刘介民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随着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在文艺上形成的某种思想倾向和潮流。(21)事实上,通过总结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锋芒,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廓清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某些彼此渗透且又相互影响的文学现象的密切关系过程,甚至还可以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艺思潮史的深层领域探究。
不容忽视的是,反思“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早期褊狭性的解读之现实失误,对全方位地鉴照、梳理其在整个新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中来龙去脉及承前启后,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由于政治和文化判断的偏失,一直被忽视或否定。”(22)有学者颇具前沿性地确认:对于学衡派来说,古典主义既然意味着精正和正宗,意味着出类拔萃的品质,他们服膺古典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23)显然,对白璧德思想学说的时代选择与接受,同时也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对“传统”与“现代”文化审视、守望、持衡背后之美学批评的意象姿态及反思立场。刘士林以独到的眼光不失深度地指认:20世纪美学思潮与当代现实中的文化思潮,都表明它应被命名为审美主义(或审美文化),而古典主义与审美主义本质就是联系在一起的。(24)叶岗则在《古典主义情怀与后新时期小说》一文中以颇为罕见的敏锐思辨力认为价值尺度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文学的发展,而现在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古典主义情怀,它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深刻回应。(25)毋庸置疑,古典主义是一股左右着现代中国20世纪新文学构筑的秘而不宣的文学思潮,同时它也是现代中国文艺创作可资借鉴的不可或缺的审美理想。“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由于文学的发展规律和文学的国际性,必然会对别国发生影响,然而在与别国的具体社会实际相结合时,又因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条件不同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和法国古典主义貌合神离。”(26)实际上,对古典主义在中国引介、传播、接受、误读、遮蔽、沉寂与敞开这一消长沉浮的阶段做出接力性与推进式的学术梳理,诚然要对它在20世纪的中国概况作一整体性的到位综观。
显然,对“古典主义在中国”之现代命运及当下解读的全面透视,同样应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清理、论析与比照。经由以吴宓为代表之学衡派及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古典”学说的肯定及对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的选择、接受、吸纳与借鉴,在中国文坛悄然产生一股古典主义思潮传播的文学迹象。杨经建给予了崭新的阐释:“考察、检视新古典主义话语产生、形成、建构的过程便不难发现,这一过程基本上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同步,而且以京派文学为圆熟、经典模式……从文化立场、审美理想和理论形态上最先体现新古典主义特征的是学衡派和稍后的梁实秋,他们的文学理念源于以现代美国学者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是力图复活古典人文精神以解救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如果说,学衡派的文学主张、理论诉求并不系统,也缺少审美经验和创作实践的印证,那么,较好地整合了新古典主义理论话语形态的人是梁实秋。梁实秋原本就稳健节制的文学倾向,赴美留学期间深受新人文主义影响,并由此最终形成了其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健康与尊严的文学观。”(27)事实上,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百年回顾、解读、述要与思考,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建构与批评走向有着毋庸置疑的当下启示意义和价值指引。一方面开启了人们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命题现代视野的重新审视与历史释读;另一方面拓宽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潮史重构的述评考察及审美阐释的空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显示了一种逐步深化的趋势。从学衡派的注重道德内容到新月派的注重格律,再到京派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走过了一个从片面到综合、从偏执到圆熟、从单纯的理论构建到介入创作实践的过程……古典主义以张扬普遍、常态、传统、秩序,彰显和谐、均衡为特征,秉承超历史的审美标准和伦理原则,适应了后发国家人民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对生存根基的追寻,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古典主义根本上乃是现代的产物,在追求文明和进步,在努力使中国成为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上,它和其他文学思潮没有什么不同。”(28)实际上,古典主义作为一股隐潜的文艺思潮影响在现代中国20世纪文学中仍然顽强存在。如样板戏、文革文学等创作中仍不时可见其潜在丝丝缕缕的影响力印痕。“新古典主义形成、发展,直到‘文革’推出‘样板戏’和‘三突出’原则而走向终结,新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文坛达半个多世纪。”(29)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古典主义文艺创作以其自身的独特性成为影响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力量。这一点也是当下学界文坛应引起进一步耙梳与透视的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古典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契机及“热”的根源,理应追溯至20世纪20、30年代学衡派、新月派知识分子对白璧德批评理论学说的审视、选择与推介。事实上,厘清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嬗变阶段的事实及其根源,考察中国作家学者对古典主义的现实借鉴与转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拓展性研究极具启示的鉴照意义。“学衡派与新月派于内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30)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持久的,它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潜在影响的思潮在中国的消长命运历程至今还没得到学界的整体审视,这不能不说是当下学界研究领域的一大纰漏和盲点。王富仁曾这样十分贴切的断定:“实际上,中国存在着古典主义,西方也存在着古典主义,并且东西方的古典主义原则都是在现实世界具有统治地位的原则。古典主义不是别的,它是人类求稳定、求规则的心理的反映。”(31)李钧对此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东西方20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学都是一种精神乡愁,是一种‘努力逃避现代生活的现代主义’,是积极反思和公开拒斥单一的市侩现代化的审美现代性,是反对虚无主义的文化守成的先锋派,是对极端未来主义的机器美学、机械芭蕾、高科技猜想和发展进化论的警惕……向传统寻求解救的良方、制衡的力量,从而发现了古典对于现代人的不可或缺性。”(32)白春超则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给予意蕴深厚的肯定。“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其他思潮相比,古典主义文学的传统情结和本土意识更浓重一些。”(33)学衡派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大力译介与宣扬,以致后来引发梁实秋对白璧德整体理论学说的重新发现,并在中国学界文坛掀起了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批评倾向。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虽然这些流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目,但是其总的倾向还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倾向。”(34)需要承认的是,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审美理想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存在着颇多可供“互释”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学界文坛传播的历史契机。
学界对古典主义在中国的重视不够可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颇多的学者抹杀、无视甚至遗忘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毋庸置疑,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古典主义”这股思潮不仅仅是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更为甚者则是对古典主义在中国这股思潮进行了某些致命的偏误性解读,蒙蔽了古典主义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这正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的消长沉浮命运一度无人问津的症结所在。“20年代,学衡派持守文化保守的自由主义态度,诗歌则有闻一多、梁实秋、朱湘等人的新古典主义运动……70年代末大陆朦胧的一支以及80年代‘寻根文学’,赓续了新古典主义的文化性、抒情性、象征性与含混性特征,成为中国文坛的重要一元;90年代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文化散文、生态散文及新历史主义小说都有着浓重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文学的目的并非要对抗社会进步,也并非哗众取宠的策略,更不是‘为王权服务’的帮忙与帮闲,而恰恰是一种艺术自觉,是对主流霸权话语的纠偏,是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现代性’刺激下的自我改造与再生,是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诠释。”(35)另外,李钧曾以一种敦厚内敛的口吻认为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此就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36)诚然,上述所论正可作为当下学界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研究命题的一种回响与对话。显而易见,以上学者不约而同的多重学术言论之理性分析,简劲果敢地凸显出古典主义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毋庸置疑的一席之地的暗示,而任何以有意无意的姿态机械地忽略、遮蔽、低视、冲淡、削弱或概念化、公式化地苛刻质疑“古典主义”在中国这股文学思潮和审美理想之现实存在的定性言论及偏激成见,都是显得稀薄乏力而微不足道的。随着人们以一种现代性视野的眼光对20世纪文学思潮的重新整合与勾勒,渐趋对曾一度被历史遮蔽的古典主义思潮做出了史料性考究的梳理与考察,使其流脉架构渐趋敞开。不难理解,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暗合。需要强调的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明显是一个极有必要敞开寻索、匡正乃至于参与充实的问题。显然,这与当前学界对此命题存在相对欠缺深层论析与理性介入探析的现象不无关系。
综而观之,从文学影响之接受的视阈看,从学衡派、新月派知识分子对白璧德文学批评理论译介、接受与秉承的学理渊源视角,深入梳通、验证古典主义与儒学传统文化内在暗合之喻示,这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命题的重新做出活性经验的厘定与阐发,将具有某种迥然而独特、厚重而丰瞻的学术价值和参照蕴涵意义。需要承认的是,当下学者诚然要以一种回顾与前瞻的眼量,对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缺失与疏忽做出合理的理论表述、揭示与阐证。值得珍视的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勃兴及各种思潮的概观,人们从学衡派、新月派的研究及其对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宣扬的现象把持中,渐趋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度被时代历史所误读、遮蔽的“古典主义”。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学衡派、新月派学术理路的掺入整合、清理的撺升而骤然升温。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梳理,还是对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抑或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重温,最终都要归结到“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或隐或显的深层反思与多元总结中。一言以蔽之,以上关于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论题的三方大面内容提出及论析,蕴含着现代中国文学史亟待进一步重新发现与批判性反思的学术命题。从文史结合的角度,结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考察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研究,才能使古典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获得深厚的文化背景依托。重要的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同样需要以一种开放的思想与审美的超然心境做出警惕性的定见、误读的剔除、消解与正视,同时也需要学者能从具体的时代历史语境探析中做出更富洞见的思想意蕴启示和理性之思的实质解读。
①(12)(14)[美]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②⑥[美]韦勒克,[美]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
③周冰心《京派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兼与西方古典主义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01).
④刘永济《文学论》,上海,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6.
⑤周来祥《论古典主义的类型性典型》,河北大学学报,1981(04).
⑦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长沙,岳麓书社,2006.
⑧邹华《文革美学与后古典主义》,西北师大学报,2010(02).
⑨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
⑩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11)[美]欧文·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13)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2004(06).
(15)梁实秋《雅舍谈书》,陈子善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6.
(16)[美]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and theAmericanCollege)》,张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17)三联书店编辑部,美国人文杂志社编《人文主义:全盘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
(18)庄锡华《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
(19)李怀亮、钱振文《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古典主义倾向》,人文杂志,1998(02).
(20)邓文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东南学术,2007(01).
(21)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0.
(22)叶红《古典主义的守成之路——古典主义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与探索,2008(06).
(23)刘增杰,关爱和主编《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4)刘士林《古典主义与审美主义批判》,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04).
(25)叶岗《古典主义情怀与后新时期小说》,当代文坛,1997(01).
(26)杨正和《法国古典主义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1982(02).
(27)杨经建《新古典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艺研究,2006(04).
(28)白春超《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河南大学学报,2003(02).
(29)杨春时《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04(03).
(30)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1)王富仁《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上),天津社会科学,1998(03).
(32)(35)(36)李钧《中和与重构,归心与返魅——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7).
(33)白春超《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6.
(34)李怀亮、钱振文《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河北学刊,1998(02).
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