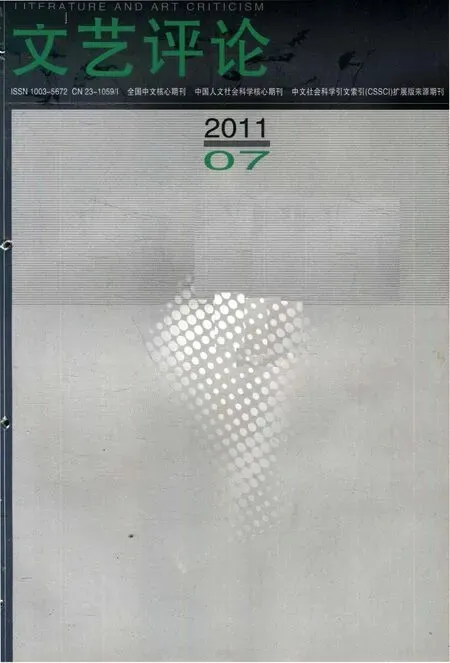中国古代吉祥图案“隐性”文化溯源
2011-11-25娄家骏
○宋 漾 娄家骏
中国古代吉祥图案“隐性”文化溯源
○宋 漾 娄家骏
中国古代“吉祥图案”中的“龙凤呈祥”、“双喜临门”、“鸳鸯戏水”、“比翼双飞”、“并蒂同心”、“因荷得藕”、“莲生贵子”、“多子多福”等等图案与露骨表现“性”内容的“春宫图”以及不表现“性”内容的图案相比,以“隐喻”、“双关”、“寓意”、“象征”等“隐”的方式表现“性”或“男女之爱”。这类图案可称之为“隐性图案”。“隐性图案”以“吉祥图案”最为典型,或者说这类图案大量集中表现在“吉祥图案谱系”之中。本文试就中国古代吉祥图案“隐性”溯源略谈一己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隐性图案”的哲理源头:“隐性文字”
中国古代先秦主流哲学思想高度重视“夫妇之道”或“男女之爱”。如:儒道共尊的“群经之首”《易经》中突出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并直接明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其中“天地”与“男女”以至“阴阳”,可以看得出是相互间的“异名”,意味着《易经》对“阴阳”的深刻意识首先是性别的或男女的,其次才推及社会、政治、道德和习俗的人际关系。“男女构精”(“阴阳相交”)具有构成意义的发生和维持的终极功能和地位。《中庸》强调:“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也。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也”;“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妇之愚”、“夫妇之端”在其中强调到无以复加的“中极”境地。用广义现象学或“身体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话说,所谓“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即意味着“有性爱和生育能力”的夫妇(男女)之间的“性爱”(“愚”)是一切意义和现象的源头(“端”)。《论语》中孔子讲“好德如好色”;“‘关睢’乐而不淫”;《庄子》说:“《易》以道阴阳”;《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凡此种种(以及各种以曲折隐含方式表达“性”或“性爱”的“文字”)都表明中国古哲看重“性”或“男女之爱”的首要性、起点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这些“文字”可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有性文字”(或“有性哲学”)。更深刻的是,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中国古哲认为,“爱情”与“性爱”之间并无鸿沟或硬性逻辑区分可言(不像西方柏拉图以至“传统西哲”那样严格区分“爱情”与“性爱”)。这意味着“男女之爱”或“夫妇之愚”都是指“相交生成意义上的雌雄区别”和发生意义上的“性”或“性爱”。
中国古哲的“有性文字”(“有性哲学”)显然不是以露骨的“显”的方式(张扬色情)而是以相对“隐”的方式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上强调“性”或“男女之爱”的根本性或首要性。因而,它和中国古代民间广泛流行的“吉祥图案”中(诸如“鸳鸯戏水”、“莲生贵子”之类)的“隐性图案”有相同之处,即都用“隐”的方式。由此可以称中国古哲的“有性文字”为“隐性文字”。有“隐性文字”必会有“隐性艺术”——中国古哲的“隐性文字”必然会“滋养”或“催生”出“隐性图案”。
“隐性文字”和“隐性图案”都以“男女之爱”为“意义发生机制”构成文字和图案。以现象学视野看,中国古哲的“隐性文字”无疑突出或强调的是前反思、前概念、前对象化的“实际生活经验世界”本身的“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语)——人类和思想之“根”的“性”或“男女构精”(或广义的性爱)。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以“隐”方式,而是以“显”方式(张扬色情)来言说或表达“性”,就意味着把“性”当成观念对象或物质对象。而“性”是发生于男女身体(身心合一的身体)之间的“居中产物”——“隐”的方式,意味着肯定前反思、前对象的“生活世界”中的“性”的重要性,避免“非关系”、“非发生”、“非境域化”地看待“性”,以至把“性”最终变成了“无性”——以“显”的方式(张扬色情)来突出“性”,其实根本上是“无性”,与“无性文字”(如西方传统哲学的“无性文字”)实质上是一样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只有“隐性文字”,也有大量“显性文字”(如张扬“床笫之欢”之类),也有大量“存天理,灭人欲”的贬抑“性”或不涉及“性”的“无性文字”。这情形和中国古代图案艺术中“显性图案”(如“春宫图”)、“无性图案”(如“抽象装饰图案”)、“隐性图案”(吉祥图案)三者并存的情形大体一致。但是,追溯“隐性图案”的思想源头只能是中国古代的“隐性文字”,而不会是“显性文字”,也不会是“无性文字”。因为,如果“隐性图案”来源于(张扬色情的)“显性文字”,就意味着“性”来源于人的对象化的生理本能或性器官,即来源于“身”(躯体),意味着“性”是无思想或理性的非理性行为。如果“隐性图案”来源于“无性文字”,则意味着“性”或“性爱”来源于人的意志、绝对意识或精神,来源于“心”,意味着“性”是人的意志完全可以主宰或操纵的“对象”。两者都是以“身心二分”为始终,因而无综合发生或构成的源头意义可言。
中国先秦古哲(如《中庸》、《论语》、《易经》)或“身体现象学”(庞蒂)所提示的是;“性”在根本上来源于生活世界中的“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灵肉合一”的“居间”的“身体”,而不是物质的“躯体”和绝对意识或精神之“心”。
总之,无论“隐性文字”和“隐性图案”,其“隐”实际上“彰显”或体现的是前理性(原理性)、前反思、前对象化的根源之“性”或“性爱”,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身心二分”思路中的抽象的或无思想的纯生理之“性”或“性爱”。这就是中国古哲中的“隐性文字”和装饰艺术中的“隐性图案”之所以具有永久生命活力的原因所在。
二、“吉祥图案”的胚胎、雏形:易象
《易经》以“阴爻”(--)和“阳爻”(—)为最基本的“象”或“象数”符号。阴爻和阳爻,皆为直线,仅是断与不断的区别,因而最具原本统一性或同类性、(有差异的)相似性,意味着它们与同出于一类(人类)的女性和男性极为相似,因而它们意味着代表“女”和“男”的符号即“隐性符号”为所有“卦象”的基本符号,因此《易》的全部“卦象”也就是“隐性”符号或广义的“隐性”符号。
《易经》的“阴爻”和“阳爻”代表的是“相交发生意义上的雌雄之别”的“男女之爱”,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两个”符号,而根本上是“一对互补”或“二对生”的符号,任何一方都无独立意义。因此《易》的所有“卦象”必须在“成对成双”的相交意义上来把握和运用。历代“解易”的原则,就是看阴阳是否“相交”,相交则“吉祥”、“吉亨”,则“能生”,“生殖”、“繁衍”,才有原发(源发、缘发)的构成意义或“生意”,否则,“凶悖”或“有咎”(吉祥图案中诸如“龙凤呈祥”、“和合二仙”、“双喜临门”之类的“双关构意”的图案及其各种变式,典型体现了《易》的“相交生成”的哲理)。可见,《易经》所“隐”之“性”或“性爱”是“可狭义亦可广义”地理解或解释。显然,这和《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夫妇”(“男女之爱”乃“修齐治平”之端之源)的道理,相通而一致。
《易》由“图”(爻象、卦象)与“文”(辞或文字)两种“互生会意”或“互补解释”的符号构成。但其中“图”(爻象、卦象)比“文”(辞、字)更原始、古老,更基本、稳定(辞历代可变,象历代不变),也就是说,《易》是先有“图”(“图几”、“几象”)后有“辞”(未必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指“依据”或“逻辑”上的先后),“辞”由“象”而来,是说“象”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图(易象)”,也就没有是中国古代几乎唯一的“图文并茂”、“图文互补”的《易经》。正如《易经·系辞》所言,“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言”,其中“象”与“卦”都可谓“图”,“辞”尽的是“象之言”。这表明“易象”本身的“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语)就是一种(隐含或暗蓄的)“辞”或“言”,乃《易》的“基因”,本身“能说话”,是一种(语言的)“身体”、直观可辨的“无声胜有声”的语言或“至简的文字”或“至简的寓意图案”。这表明《易》作者(或之前的古人)早已注重用可见的、时间化的空间的“视觉图像”(或德里达意义上的书写或文字)来表达终极哲理和“预言吉祥”。
《易经》和“吉祥图案”的相似之处或潜在共同点,可列出以下方面:
1、二者不同程度地运用“图文并茂”(“象辞结合”)的表达方式,并以可见性、空间性之“图(象)”为基本手法或方式。在《易》中即所谓“立象而尽意,设卦尽情伪,系辞以尽言”;在“吉祥图案”中则主要“以图为主”而寓意,同时也“系辞”,即以相应的文字题目配合具体题材的图案(尤其是那些常见的典型吉祥图案,如“龙凤呈祥”:图:龙、凤、祥云,文字题目:龙凤呈祥;“莲生贵子”,图:莲叶、莲花、莲蓬头,文字题目:莲生贵子。即使有些吉祥图案没有题目,但凭联想或直观也能领略其意,这和领会《易经》的人凭直观“卦象”就能知道其意,具有相似之处)。
2、二者都基于“阴阳关系”(“男女关系”)并以此显示“吉祥”之“意”。在《易》,即“阴阳相交”为“吉象”而体现(如遇“凶象”,则可据以“避凶变吉”或“逢凶化吉”);在吉祥图案,以隐喻“男女相爱”或“家庭和睦”的寓意图案来体现。《易》中“吉祥”的“卦象”,完全可以看作是后起的历代“吉祥图案”的“胚胎”、“基因”和微妙的“雏形”。
3、“易象”基于“阴阳关系”(“男女关系之‘基因’”),可以“随机应变”、“唯变所适”、“变通而用”,“广大配天地”。吉祥图案同样基于“男女关系”或“男女之爱”,同样可以创作出衍生或派生意义上的千变万化的各种题材的花样或样式,如与家庭家族、世代生命繁衍相关的各种图案,如“荷荷美美”、“多子多福”、“万代富贵”、“福禄寿喜”、“吉祥万年”、“美意延年”等等无数维护“生存”的图案
4、二者都有“忧患”意识和“图祥”意愿。“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系辞》),作《易》者因“忧患危殆”而“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系辞以尽言”,创造“与天地准”、“生生大德”之《易》;作“吉祥图案”者,也同样“忧患”于种种可能的“失源”、“无根”的不吉祥、不和谐、不和睦,而创作出“图祥”的吉祥图案,来营造生活世界的美好艺术氛围,以求“长生久视”。
总之,即使我们不追溯到与《易经》相关的“连山”、“归藏”、“先天太极图”、“河书洛图”之类以及彩陶等艺术上的“类易象符号”,也足以看出《易》是“吉祥图案”的雏形或“原始模板”。
三、吉祥图案“意义机制”与“隐性身体”
“隐性文字”和“隐性图案”之所以要“隐”或“隐性”,援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即意味着要“呵护”或“保护”有性爱能力的“意义发生场”的“隐性身体”——原本的“意义发生机制”。梅洛·庞蒂认为,“性爱”与“害羞”、“羞感”原本相关,二者是原本的“共谋”关系,“害羞呵护性爱”。
由此,无论“隐性文字”或“隐性图案”的功能就是“呵护人类性爱”或“呵护人类性爱的时机性”(不到“时机”,男女交往则不能成功)。“害羞呵护性爱”,在美术中就意味着作为“装饰”艺术的“隐性图案”具有“呵护”男女双方“性爱能力”、维护“身体——意义发生机制”、营造健康美好性爱氛围的一种艺术形式。
“男女之爱是人能经历的最自然、最动人、最有原本生成力的一种生命状态或这种意义上的思想状态”。但根据现象学的“时间”观,这种“原本生成力的状态”的“性爱能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出来。在不利或(像《易经》中所说的)“凶悖悔吝”情况下,人就会用“害羞”来呵护或保护它,以待时机成熟而实现之。也就是说,性爱有时机性。正如《易经》所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中国古代“隐性图案”和“易卦”在此“根源”功能上都可以说是“呵护(广义)性爱”的“隐性文化”。
“隐性图案”都“寓意”或“表意”,因此,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写意画”。创作“隐性图案”是以“身体执行”行为“写”——“在世界中的‘身体—意义发生场’”发出的可能性之“意图”(图案)。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隐性图案”正是人的“身体—意义发生场”绽放出的洋溢着真情、温情、至情、富有“原本生成力”的以“男女之爱”为“基因”的(或泛性爱化、泛生命化)的美丽花朵(“文饰”)。
“吉祥图案”植根于男女之“性”或“性爱”,“性”或“性爱”是“吉祥图案”的源头或起点。“吉祥图案谱系”中的那些表面上与“性”或“性爱”不相干的图案,如“长命百岁”、“松龄鹤寿”、“连年有余”、“美意延年”等等,都可以看作是“隐性图案”或“隐性”的“吉祥图案”,甚至其它画种如中国画中的那些追溯起来实际上是从“吉祥图案谱系”中借取或移植过去的诸如“岁寒三友”、“梅兰竹菊”乃至“花鸟鱼虫”、“青山绿水”等等,只要具有“吉祥感”或“吉祥味”的,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它们都是由人的“有性爱能力”的“身体执行”来实现或完成的,都与“阴阳组合”的人的“身体—意义发生场”原本相关。
与古代显赫地位的“主流艺术”的“中国书画”相比,“吉祥图案”在中国古代大多存身于日常人伦生活的“边缘地带”,是民间生活世界中的“边缘艺术”。但考察中国古代美术史,各种各样的“主流艺术”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吉祥图案汲取营养,受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表明吉祥图案是“主流艺术”的源头活水,而且表明吉祥图案作为“边缘艺术”,其“边缘”实际上是“无边”或“无界”的,各种文化艺术无不在“骨子里”与其有“缘”。究其“缘由”,无非在于吉祥图案的“隐性”“基因”或“特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装饰艺术符号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760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