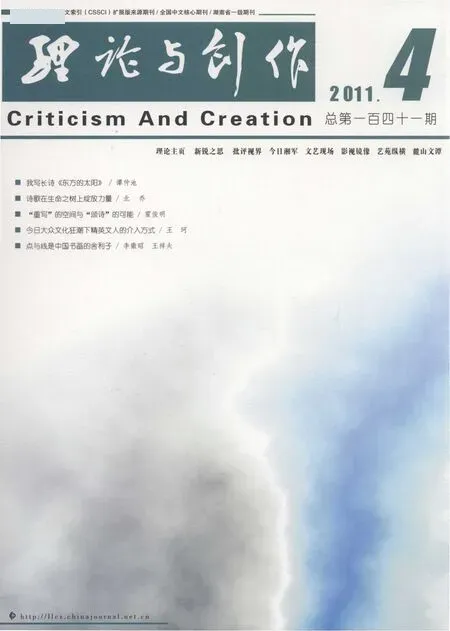田耳小说女性群像论
2011-11-24姚艳玉
■ 姚艳玉
当文坛闹哄哄崇尚“先锋”小说时,田耳说“别把先锋当成遮羞布”;①当文学也开始向俗流妥协之时,田耳仍专注纯文学创作。从1999年到2011年田耳“一不小心将小说写了10年”,“最跟自己过不去的事情,是我仍相信自己适合写小说”②。纵观田耳十年耕耘,女性形象光彩夺目、精彩纷呈。
一、苦难命运的湘西底层妇女
湘西自古属偏僻蛮荒之地。前现代社会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放蛊、沉潭、落洞等野蛮乡俗肆意流传,如桑女(《掰月亮砸人》,《西部》2008年第7期)等。即使进入现代社会,湘西仍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男权意识浓厚,妇女命运可悲,如梁晓雯母女等(《坐摇椅的男人》,《人民文学》2006年第4期),于心慧(《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2006年第 12期),吴妈(《风的琴》,《飞天》2007年第7期)等。
《掰月亮砸人》借湘西穷乡砍火畲村姑桑女的悲剧反思巫蛊盛行的丑陋民风。桑女相面不好,婚事一再耽搁。先是湾溪的麻家退亲,借口是“桑女爱蠕嘴皮子,不是好兆头”;“口不把门,长舌滋事,轻则败坏门风,重则罹祸事”。后来是本村的准公公杨吊毛嫌她长马牙,“搞不好以后那颗马牙会翻出嘴皮子外面,就成了一颗獠牙,撬掉了生的小孩也会长獠牙。”不准儿子夜猫娶桑女。桑女被迫用铁钉撬掉马牙但感染破伤风而死。其父田老稀认定是狗小放蛊所致。因为狗小被煤矿塌方掩埋90多天奇迹般生还,田老稀谣传他吃了死人肉,是不能碰的灾星。村民们几欲烧死他,还理直气壮说“是为民除害”。狗小最终复仇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桑女。狗小自是巫蛊谣言的牺牲品,他却把自己的不幸发泄到更凄惨的桑女身上,在此,巫蛊邪风及男人对底层女性的伤害双重而深重。另外,底层妇女苦难命运很多直接、间接与经济状况、家庭婚姻紧密相关。《风的琴》中铤而走险的人贩子吴妈贩卖人口罪不可赦,但同时作者以宽容、人性的目光巡视湘西苦难的子民:单从吴妈女性身份来看她就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作为妻子摊上个凶狠滥赌的丈夫本身就不幸;而沦为其挣钱工具,就更不幸;而儿子朱朋被警察诱惑大义灭亲举报母亲,使这个悲剧无以复加。《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现代市民于心慧的苦难叫人扼腕叹息。她不屈生活的困顿,勇敢追求爱情,以一个残疾人的心智自立于社会。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个弱女子。哥哥被杀情人亡命天涯,她一个人蒙在鼓里张灯结彩。田耳神来之笔描摹尽人生热闹中的凄凉感。
田耳的女性悲苦甚至触及精神层面的“惘惘的威胁”。《坐摇椅的男人》中受两代男人精神折磨的梁晓雯母女就是这样的代表。晓雯母女怕老梁、怕小丁,推而广之害怕所有男人。“晓雯和母亲成天忙个不停,老梁就会咳嗽一声,示意她(晓雯)走到跟前,帮他打扇子。”或是老梁冷不丁叫一声“晓雯!”晓雯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小丁小时候看着老梁作威作福的样子,感到愤恨不平。等自己做了晓雯的丈夫却无意学起老梁的样子,“虽然是第一次打她(晓雯),她马上就摆出逆来顺受的表情,仿佛生活原本就该是这状态”。晓雯不觉悟,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③小说叙述极端弗洛伊德化,但却勾勒出女性悲剧的轮回与宿命。“女人不属于任何人,属于她自己”,当晓雯60岁的母亲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之时,已本能地迈出了女性解放的一大步。
命运苦难的湘西妇女群像兼具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多重诉求,正如张昭兵所言,田耳一贯的主题是“弱者的抗争”。
二、女性意识萌动,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
田耳创作与时俱进,其笔下涌现许多独立、自强、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如《界镇》(《中国作家》2007年第1期)中的小林。《蝉翼》(《青年文学》2007年第7期)中的朵拉。《一朵花开的时间》(《钟山》2007年第6期)中的张莲花等。《界镇》较独特。小说以回忆的笔墨描写女主角小林“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深刻人生经历,塑造了一个独立有主见的现代女教师形象。小林投身山区教育事业非崇高志向或悲壮使命使然,而是出于善良的人性、自主的人格。其女性意识初步萌动又混沌。一方面其思维与时代“共名”,她觉得“当面赞美女人的男人大都是流氓”;一方面她又迷恋自身的女性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现强烈的女性意识;即或许扬言“你身上每一个地方我都看过很多遍了”,小林不像传统女性认命而稀里糊涂答应嫁给他。当中年小林结束与陈秋文无爱的婚姻后独自带女儿单过,活得自在淡泊。故《界镇》可视为一部女性的成长小说。
相比小林的浪漫、旷达,《蝉翼》中乡卫生员朵拉则世俗、精明。尽管她抱怨“马拉松式的爱情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她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在爱情与婚姻之间从不徘徊。她理性地选择了高学历的丈夫及其附带的干部家庭背景;对小丁的爱情“发乎情而止乎礼”。田耳塑造朵拉也理解朵拉——她何尝不象千万万个女人一样只不过是个俗女子?!
田耳多次表白其获鲁迅文学奖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属“无心插柳”之惊喜之作,最爱还是《一朵花开的时间》。后者解构《水浒传》中鲁智深故事。鲁智深是小说主角,田耳试着从女性心理学的细腻角度表现一下鲁智深这一定型化的人物,但几位分别命名为丁小莲、金翠莲、张莲花的女子却写得妖娆可爱。在“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佛教氛围中,女性不再是传统的贞洁、弱女形象,具有一定反叛传统,追求自主人生的现代思想。
如果说鲁达初恋对象丁小莲仍是传统女性形象,囿于“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婚姻既定规范的话,则金翠莲有一定反抗性,敢于再嫁。而林冲老婆张莲花则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林冲谎称张莲花自杀成烈妇,实际却养在高俅府上。鲁达潜入高宅搭救张莲花她并不领情。见鲁达一面只是为“去掉心头最后一点念想”,但“何必要走?何为搭救?要到哪里?这墙里墙外,又有多大分别?”张莲花之所以不肯逃离狼窝源于对所有男性的失望。丈夫林冲抱本守元一门心思放在武艺上;高俅被鲁达几个徒弟废身之后,沾着她的身子也是徒增苦闷;而最重情重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鲁达也未必靠得住,说不定哪天顿悟,立即就抛下一切独自走掉。张莲花在两性关系中具备清醒的现代女性批判意识,可谓是经典的“重构”。
三、消费爱情、游戏人生的后现代女性
1990年代后深化改革,中国社会步入典型的消费社会,在市场经济中一切成了消费品。田耳小说反映现实虽谈不上带露折花,但紧跟时代。其笔下的后现代女性们“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以无规则为规则”,折射出后现代文化的精神特质——对一切理性价值的怀疑。这些女性有风韵犹存的班花陈姐(《你痒吗》,《钟山》2007年第2期)、风骚婆娘花雉(《人记》,《钟山》2006年第6期)、企业董事长束心蓉(《环线车》,《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妓女葛双(《友情客串》,《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乃至“我为财狂”的普通老百姓吕大萍(《拍砖手老柴》,《人民文学》2007年第11期),大学生林小帆(《在少女们身边》,《红豆》2010年第8期)等。
《你痒吗》里的风流女人是老谭的后妻陈姐。她当年曾是班花,离婚后嫁了老谭依然故我:爱赌又养小白脸。有意味的是老谭在外面不断找女人,却说老婆养白脸总是吃亏的,典型的州官放火;但他又总是规规矩矩把每月工资交给花心的妻子。《拍砖手老柴》中老柴的老婆吕大萍嫌丈夫窝囊,为了钱先后和风流教授及抢劫犯老锯鬼混。《环线车》中的公司老总束心蓉,玩男人养面首,游戏人生。而长篇小说《风蚀地带》中江薇薇与表兄的乱伦、乱性可谓登峰造极。入选2010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的《友情客串》,主要讲述妓女的故事。省城姑娘苏小颖因男友在家公然嫖娼,她怀着失恋的心情到佴城散心,寻找六七年没见面的中学闺密葛双。但葛双已是一个妓女。犹如蔡大嫂受到妓女刘三金性启蒙一样,葛双独特的性体验诱惑情场失意的苏小颖彻底放松,“友情客串”一回妓女,“力比多”得到变态满足。也可用对妓女的“怨羡”心理解释苏小颖的沉沦。对葛双们而言,傍上公安何所长发家致富的三陪女“小三”正是其自甘堕落的源动力。人性、尊严、道德、爱情轰然倒塌,唯金钱阴谋游戏交织缠绕,美丑难分真假难辨不正是当下混沌的现世吗?《在少女们身边》笔墨尖锐指向一贯被视为“净土”的大学校园。林晓帆们个个是校园尤物,以姿色诱惑社会成功男人,甚至“慌不择食”。林小帆钻进半老头邹扒皮的奥迪车后才发现邹扒皮原来不是老板是个开车的。少女们个个会算计男友:看重的就是一个钱字。郭倩、林小帆、王丽萍三个闺密一个晚上使用一个“钱包”(男友)当跟班。王丽萍朝秦暮楚男友入狱马上转嫁大老板罗更。日后发达的小丁成为各路美女的抢手货,如师院毕业的小雨、移动公司领班小肖。而当他一文不名给报社打工时,女孩对他不屑一顾,和小丁交往的农机学院国贸专业的美女小梅不是半途失踪了吗?大学少女们性道德观念的集体哗变,深刻体现消费经济刺激带来的道德滑坡人性异化。田耳小说中的后现代女性可以在他的小说《人记》找到渊源。这类女人由来已久,但又有本质的区别。古代女性的风骚、无耻与性压抑有关;当代的则更多以追求享受刺激为目的。《人记》中野鸡坪被掳美女花雉她不爱丑丈夫,只喜英俊的土匪十一哥。十一哥破坏山规落得皮开肉绽一顿暴打,直接导致与土匪老大瘤子老韩反目。风骚的花雉似乎应证了“女人是祸水”的古老格言,实际却是女人感情得不到满足的变态行为。后现代女性消费爱情游戏人生就要复杂得多。
田耳十年对女性群像的塑造,体现了鲜明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同时折射出作家的审美情趣和思想价值观的变化,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镜像意义。
注 释
①田耳:《别把“先锋”当成遮羞布》,《山西文学》2007年第10期。
②田耳:《一不小心将小说写了10年》,《民族文学》2011年第2期。
③【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