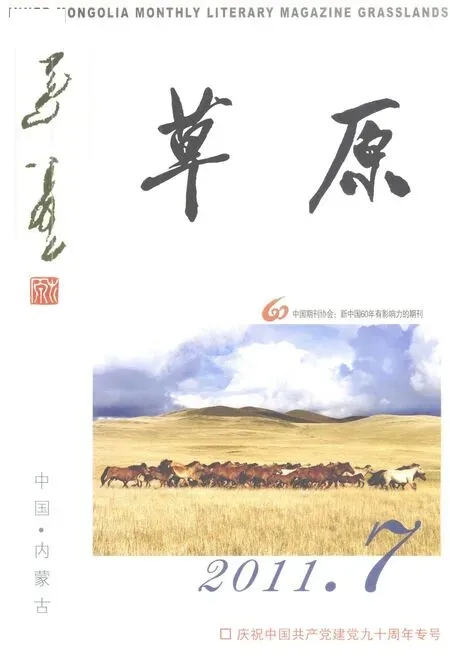历史不容颠倒——从有人企图改变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谈起
2011-11-21云照光
□云照光 贾 漫 杨 啸
历史不容颠倒
——从有人企图改变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谈起
□云照光 贾 漫 杨 啸
读了二○一一年四月八日《文艺报》上发表的李存兆的文章 《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我们才知道,关于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近来竟然有人挑起了事端。戈焰同志首先抛出出处可疑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一书之后,紧跟着我们又看到由陈建功同志和戈焰合编的 《重读邵子南》,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名义出版,其中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专章为歌剧《白毛女》剧本署名翻案加大了力度。
我们三人,一个作为一九三九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过的蒙古族少年,一个作为建国前亲自参加过《白毛女》演出的绥远省文工团团员,一个作为故乡就在民间故事“白毛仙姑”传说发源地附近、建国前解放区部队工厂的小童工,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我们对于歌剧《白毛女》作者的署名问题,也来表达一些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小事情,而是一个如何尊重历史,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严肃问题。
大家都知道,《白毛女》的创作及演出成功,在延安是轰动一时的。因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以及我们在延安的人们,都看过成功的演出。大家都称赞,贺敬之那么一个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竟以他为主要执笔者写出了那么好的作品,是很了不起的。该歌剧署名为延安鲁艺艺术学院集体创作,剧本执笔者为贺敬之、丁毅,这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任意改变的。
《白毛女》原是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奇故事,流传于河北阜平、平山一带。后来,在晋察冀边区几乎流传得家喻户晓。“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由延安鲁艺院长周扬同志提出的歌剧 《白毛女》的主题应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则是概括了不尽相同的各个故事的共同之点。
这个故事传到延安有两个渠道:一个是由周巍峙同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该团的作家邵子南将他收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带回延安;二是当时的 《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根据“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奇,写成一篇《白毛女人》的故事,于同年秋天托交通员带给了延安鲁艺的院长周扬。
周扬同志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他提出依据这个故事,写一个歌剧,责成张庚组织了包括邵子南、王滨、贺敬之和导演、作曲等七八人的创作组。邵子南执笔用秦腔形式写了《白毛女》剧本的第一场,并进行了试排。周扬看后很不满意,批评说:“这样写,这样排,怎么能把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内容表现得好呢?我们不要‘洋八股’,也不能不加改造地照搬‘土八股’、‘封建八股’。”
按照周扬的意见,《白毛女》剧本要重新结构,重写。周扬的意见,邵子南不同意,收回了他的稿子,退出了创作组。经领导决定,由贺敬之执笔重写。周扬和张庚等人,大胆地委以年仅二十岁的贺敬之来执笔,实在是有胆识、有远见的。贺敬之出身贫苦,亲身感受过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而且,在此之前,写出过全面反映农民疾苦的组诗《乡村的夜》,受到胡风的称赞,并在胡风主编的丛书中刊出。何其芳惊喜地向周扬推荐说:“诗里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周扬完全赞同。因此,周扬起用贺敬之执笔写歌剧《白毛女》,不是盲目的。贺敬之不负重托,全身心地投入,内心里汹涌澎湃,波涛激荡,激动不已。由于太激动、太投入、太劳累了,没等写完,他就病倒了,所以,最后一场是由丁毅执笔的。
这是一次大胆地创造,《白毛女》一举成功。全剧彩排后,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赞扬。我们延安民族学院的同志们看后,更是十分称赞。因为蒙古族奴隶、平民深深感受到王公贵族的残酷欺压,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黄世仁是一丘之貉。不推翻旧社会,各民族是翻不了身的。
在当时的延安,非常民主。不论演出多么成功,也可以有不同意见发表。贺敬之、丁毅的本子全剧彩排后,邵子南同志张贴墙报发表由他主持的批评这个本子的座谈会发言摘录,说这个本子是失败的,“是不健康的猎奇”;“主题思想不统一,情节不统一,内容和形式不统一”;更有人发言说表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破坏统一战线”等等。他自己在墙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他无关”。这是铁的历史事实,当时在延安的人,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
奇怪的是,六十多年以后,由戈焰主编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一书中,竟然提出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的剧本,署名要加上“邵子南原作”或者“根据邵子南原著改编”的字样!
众所周知,邵子南同志写的初稿试排一场就被周扬同志否定,其中的情节、人物、唱词以及整个的格调,都和贺敬之的重写本完全不同 (详见 《文艺理论与批评》二○一一年第二期)。除此之外,质疑者谁也拿不出邵子南的可以与贺敬之、丁毅的本子对比的本子,能够证明后者只是改编而不是重写。对此,解放前在延安、解放后在内蒙古以及国内其他地区,我们已不记得多少次看过《白毛女》,我们也亲自演出过《白毛女》,大家全都知道执笔者是贺敬之、丁毅,从来没有疑义。怎么《白毛女》作者署名如今突然成了疑案,这不明摆地是无事生非吗?
至于对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本子的评价,它取得的成功,这里无须我们多说。无论是情节和细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运用以及主题意蕴的把握和开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早就为众多专家、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称道。
这里我们仅从语言方面来说就可见一斑。无论是道白还是唱词,完全是用通俗的、大众化的、农民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剧中多数农民人物的思想感情,生动、深切、又富有诗意地表现了不同的人物个性和心理。特别是喜儿的一些著名唱段,打动了千万人的心,几十年来在广大人民口中传唱不衰。这位反抗到底的女子,随着她性格的逐步成长,从“北风吹,雪花飘”开始,发展到“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最后到“太阳底下把冤申!”充分表现出,喜儿的命运,就是从受剥削、受压迫到翻身解放的亿万农民的共同命运。这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新歌剧中,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第一次登上舞台,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人,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独占舞台的一统天下。这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从戏剧到音乐、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全面的创新,是集体的智慧与作家、作曲家、艺术家(导演、演员等)个人才能的结合,是六十多年来经过群众评定和历史检验的一部成功的民族的、人民的新歌剧。
作家在创作中,对于民间故事素材,有着提炼升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也就是源于民间故事,却又高于民间故事。这就体现了作家可贵的创造性,从中充分展示了作家的天才和凝注了作家的心血。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创立了集体创作与个人执笔相结合的模式。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歌剧,如《王秀鸾》、《赤叶河》、《刘胡兰》、《翻天覆地的人们》、《小二黑结婚》等等。这是一场戏剧史上的革命。回忆峥嵘岁月,我们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亲身参与过,我们可以算得上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
当年,内蒙古的军队和地方文工团曾多次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内蒙古文工团,由陕北公学来的周戈、鲁艺来的陈清漳同志分演杨白劳的A、B角,舞蹈家贾作光扮演黄世仁;绥远文工团,由冼星海武汉时的学生理为民扮演黄世仁。他们都熟知《白毛女》的创作过程。陈清漳就是与陈强、王昆等同志,一起从延安到达张家口的。他们都是歌剧《白毛女》诞生过程的见证者。从一九四六年以来的所有版本,署名都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编剧:贺敬之、丁毅(执笔);作曲: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也有的版本,作曲家由于参加先后的不同,因而早期的名字少一些,但剧本执笔者贺敬之、丁毅,主要作曲者马可、张鲁等,始终是不变的。
当年,延安的民主气氛是令人怀念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如前所述邵子南同志能够对大家一致叫好的歌剧《白毛女》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公开声明:这个歌剧《白毛女》与他无关。他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歌剧《白毛女》公演之后,为了表示与歌剧《白毛女》的区别,他自己另外写出了同名的一首长诗。他的这种文学家的个性,是应当被尊重的。我们想,如果邵子南同志在世,要是有谁竟然在歌剧《白毛女》的署名中加上“邵子南原著”,那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应该是邵子南同志。
历史是不容颠倒的。历史的真实是不能任意改动的。在那指鹿为马的“文革”时期,有人硬把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改为毛泽东、林彪会师,当时便遭到国人的唾骂;在表现南昌起义的油画上,把朱德、贺龙去掉,而加上林彪,更是被天下人耻笑。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妄改是白费力气的。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的前述《重读邵子南》一书,其中《邵子南与<白毛女>》专章,正是要对歌剧《白毛女》的署名进行妄改的一例。该丛书主编陈建功同志所写的 《总序》中写道:“本丛书所含所有书籍的出版,惟以我馆认识到的参考价值为取舍。”这是明显地在告诉读者,提出要改变歌剧《白毛女》的署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太独断专行、太不顾历史事实了。前面已讲过,此问题早已被当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反复肯定,大批的文章也提出了不可辩驳的证明。戈焰同志企图改变署名的难以成立的 “理由”已是不攻自破,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陈建功同志是否应责无旁贷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取舍”呢?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涌动面前,是理应要求我们在对待革命文艺史和红色经典作品的问题上分清是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向曾经把“白毛仙姑”故事带到延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同志以及邵子南、李满天同志,向创造了不朽歌剧《白毛女》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已故的和健在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