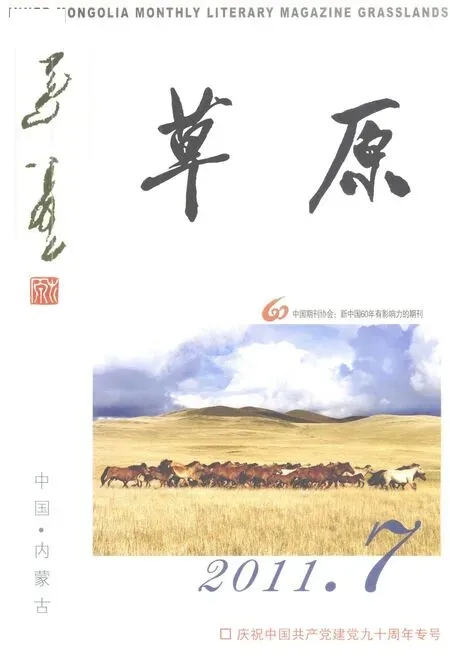乡村细节
2011-11-21关俊利
□关俊利
乡村细节
□关俊利
麻雀
童年的家乡有好多好多的麻雀,飞起来像云彩一样在村子上空与周围庄稼地里盘旋。群起群落,尤其在冬季落在一棵大树上,仿佛突然间长满密密麻麻的叶子。这些无以计数的麻雀自下而上活动的范围与空间是和我们这个村有关的,几乎一生也不离开我们的村庄。它们从不迁徙,生活在人们的屋檐下,墙缝里,柴火垛中。麻雀是村庄坚实的守望者,也可以说是村庄忠实的守护者。麻雀把村庄当成自己永远的故乡,他和村庄一同经历四季,经历岁月的沧桑。
其实,那时麻雀是被人尊重的。因为没有华丽的外表,又没有动听的歌喉,有时还和人类争吃谷类、小麦、高粱等作物,就因看见这些小小的过错,没有看见它们每天要吃多少害虫,竟被列入“除四害”行列,国民共除之,以至于遭到“满门抄斩”的奇冤。那时,我们小伙伴把麻雀称之为“家贼”,是我们捕捉的对象。因为麻雀肉既肥又香,我们用弹弓打、下夹子夹、用筛子扣、到屋檐里掏等手段来对付麻雀。
在夏季里,常常几个顽皮的伙伴,以人为梯,去屋檐下掏麻雀,把收获的带有黄嘴鹅的雏鸟连同褐色纹路的麻雀蛋引以为豪,还常常用麻绳拴着一只麻雀玩。记得有一次在家的屋檐下掏出几只还没有出飞的“雀油子”,放在家中的窗台上,雏鸟凄厉叫着不停,引来大麻雀。当时我家窗户分上下两扇,只有下扇是玻璃的,上扇是纸糊的。玻璃和窗户纸把它们隔成阴阳两界。那两只大麻雀爆发着所有的愤怒,有一只撞在玻璃上,企图冲破防线,结果撞掉的羽毛在风中飘舞,另一只竟把窗户纸撞一个窟窿,飞到屋里叽叽喳喳的和他的孩子亲近,这个场面把我们几个小伙伴吓得惊呆了,坐在炕上的奶奶把窗户打开,放走了大麻雀,我们几个小伙伴又小心翼翼把几只雏鸟放回雀巢里。这个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当想起麻雀救子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自责和内疚着。
捕来的麻雀不管用什么方法,它始终不吃不喝,气愤到极点,忧郁到极限,总是在绝望和绝食中死去,我对麻雀产生了敬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性格,有着用生命捍卫自由活泼的天性。
还有一个场面叫人忍俊不禁。进入春天,麻雀欢呼雀跃,因为进入繁殖期,通过春、夏、秋、冬辛苦劳碌,麻雀数量成几何倍数增长。进入八月,谷子、黍子快熟了,麻雀满天飞,争着与人吃谷粒,村里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人们总是拿着树枝吆喝着轰赶麻雀。那是轰不过来的,有的在木杆绑上红布像旗幡一样在田野舞动,有的树起稻草人,再戴上一顶草帽,端着枪,并且装模作样的披上一件衣裳,稻草人不分昼夜,不吃不喝,不躲风,不躲雨,忠诚的监守着。麻雀躲了几天,又折了回来,对于麻雀的伺机行动,稻草人充耳不闻,无动于衷,麻雀识破诡计,和稻草人成了朋友。吃饱了,它们便落到稻草人的肩上亲昵、唱歌。农人不得不说“年景好了,老家贼能吃多少……何况老天爷还饿不死瞎家雀呢”,不得不对麻雀进行了妥协。这是几十年的事了。
我已居住在城市里,但城市的麻雀和农村的麻雀没什么两样,仍然是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仍然是鸟类的“平民”,仍然是飞鸟类“大众”,但是每天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像音乐,像晨钟呼唤我起床。听见叽叽喳喳的絮语,看一跳一跳啄食的姿态,有一种回忆幸福地流动。经过迷雾,经过风雨,经过磨难,我突然感悟到:其实,我们的幸福和那几只悠闲地一跳一跳的麻雀没什么两样。
煤油灯
夜幕降临,时常徜徉于广场。面对万家灯火初夜,面对光明闪烁的霓虹灯,面对车水马龙在大街飞舞穿梭,面对天空长穹的星光灿烂,“花市灯如昼”、“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愉悦和幸福常常涌上心头,给人以追求和振奋。但此刻儿时那一盏灯,昏暗而又深远的光芒随即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消失的煤油灯,那是形状各异的煤油灯烛掌乡村的夜晚。
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我走过快乐的童年。
昏暗的灯光凝聚浓浓亲情,揭示着过去的贫困,更是我思念家乡走出暗淡的一个亮点。
一块薄铁皮卷成钉粗细的圆筒,插进废弃的墨水瓶盖,穿入棉花捻子,倒入煤油将瓶盖拧紧,“哧啦”划亮一根火柴便点燃了,这就是记忆中简易的煤油灯。有的人家连煤油灯也舍不得用,而是将蓖麻籽用土办法榨出油来,把蓖麻籽油倒进一个浅一点的瓷盘中,用棉花搓出一根捻子,放进油里浸泡一会儿,然后把其中一头拽出盘沿,用火点燃,简易的油灯就这样做成了。条件好的人家用马灯,因为马灯有玻璃灯罩,可以把屋照得很亮,有的人家为提高照明效果,还给油灯做一个高脚的大头灯台。“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不下来,吱吱吱,叫奶奶,奶奶打它一烟袋,灯翻了,油洒了,耗子跑了,盘儿打了……”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歌谣。
那时的夜,尤其冬夜又黑又漫长,哪家点亮一盏灯火,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见,这灯光是有诱惑力的,小伙伴们总是涌到这户人家的院里借着灯光玩各种游戏,直到灯光消失。
在油灯下聊天、吃饭、做作业,伴随摇曳忽闪的煤油灯静静的恬静的依偎在奶奶的怀里,听老人家讲故事,讲《杨家将》、《封神演义》、《小人书》,讲黄仙、狐仙的故事。听得痴迷,有时是欢快兴奋的,有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有时围着火炉取暖的同时,把黄豆粒、玉米粒埋进火盆里,伴随着噼啪声响,一股股灰烟随着豆香一起升腾起来。寒冷中,我们的喜悦和谗相都写在脸上,尽管晚上的油灯是昏暗的,并且第二天人的鼻孔里有一层黑渍,但儿时伙伴觉得却是那样快乐与温馨。
煤油灯是乡村夜晚的星星,冬天长夜借煤油灯的光亮把白天拉长,把白天的琐碎家务排列在油灯斑驳的光芒中。编炕席,绑笤帚,穿盖帘,搓玉米,整理白菜,蒸粘豆包,做鞋缝衣,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奶奶做针线活时拿针尖挑下灯芯的灯花儿,昏黄的光即刻就亮了一些,将针尖伸进额头的发丝间擦一擦,便使锈钝的针尖更利一些,也把期待与淡淡忧伤搁在这一瞬间。
那一片光亮把一家人团结在一起,把暗淡的乡村岁月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这一豆灯光永远是童年故乡的标志,是希望之光,我是带着这一豆灯光进入这灯火辉煌的城市的。
土豆
土豆是不可少的食物,又是美丽朴素的鲜花。把珍贵埋在土里,美丽留给人间。土里越珍贵,上面鲜花越灿烂绚丽,越让人赏心悦目,越让农人笑逐颜开。面对那盛开的呈穗状金钟般紫、粉、白一眼望不到边的鲜花,真的有亲亲土豆的感觉。
立夏前后,伴随春雷惊醒,选好土豆种子,圆圆的土豆身上,有多少芽眼,就有多少种子,把牙眼切成三角状,伴着草木灰,铧犁划开沉睡一冬的黑土地,农人上有阳光普照,下有令人陶醉氤氲泥土的芳香,无比愉快和细致地把土豆扔进土里,埋好,踏实,那里有草木灰、粪肥、水、养分、地气、阳光辐射的温暖。于是就像盼望所有庄稼发芽一样,盼望着土豆的深绿色芽芽,早些破土而出。
薄薄的、硬硬的一层板结土面顶破后,白嫩嫩的幼芽探出来。几天后一片一片,伸开绿绿的、嫩嫩的、翠翠的秧苗铺盖整个地面。
深藏于泥土的土豆,通过粗壮的枝杆向田野昭示:有茂盛的叶片飘散的清香,或白或紫的鲜艳花朵,闪烁太阳雨露一样的晨光,给土豆送去乳汁,白的、红的土豆生长在大地温暖的怀中。
秋风吹起时,到了收获土豆的季节,蹲下细看,一道道地皮开裂着,露出白的或被太阳晒绿的土豆。这时人们纷纷带着喜悦,出现在田野上。沿着土豆秧的边缘一铁锹插进去,后压前挑,翻起散开,便潮流般流出鲜亮白嫩、硕大的土豆来。车载的车载,马拉的马拉,人扛的人扛,把收获与希望运到家中,运到城市,运向国外。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