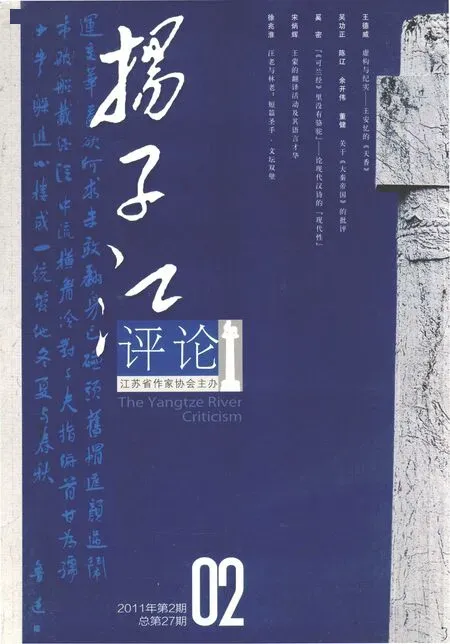与人共舞中的对峙与和谐——论1980年代以来动物生态小说主题分类
2011-11-20刘晓飞
刘晓飞
纵观中外生态文学创作,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动物题材上大做文章。据我目前所及的阅读视野,中国当下文坛涉及动物、表现动物的生态小说占所有生态小说的二分之一还多。中国的动物生态文本不仅数量多质量高,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独到的书写领域,也就是说,动物生态小说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重头戏,可以代表中国生态文学的整体水平。
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澄清,那就是动物生态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动物,能呼吸,会跑跳,有感觉,是与人最为相似的物种,言说动物的故事,相当于描绘通常意义上认为弱于自己的同类的境遇,动物是被分析的对象,但通过动物折射的是人,落脚点还是在人。重新认识动物,特别是在动物与人既争斗又共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认识动物,可以矫正人类一向自傲的自然观。“动物与人的关系,原来是一个如此敏感并充满挑战的话题,它所涉及的现实社会、道德伦理,以及历史、科学、心理、行为、情感、常识等方方面面,从广度上来说浩如烟海,从密度上来说盘根错节,从深度上来说直抵世道人心。”①也就是说,动物生态小说体现了普世性的价值尺度,表现更为深广的人道主义。
在这里,我想依据文本内容和作家表达重点把中国动物生态小说分为四类,当然每一类或许有交叉或重叠。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梳理总结当下动物生态小说创作,以期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以及规律。
一、动物王国中的情趣
第一类,发掘动物世界的情趣。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动物生态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比比皆是,实际上这也是动物生态小说的最基本主题。当作家们注视动物世界的时候,发现它们的经历竟也是如此丰富多彩,它们的喜怒哀乐也是如此扣人心弦,于是生态作家们的眼光中不仅有居高临下的怜悯、惊奇,还添加了感动和钦佩。动物既不像我们人类想象的那么弱智和混乱,它们的世界里充满情趣,充满温情,甚至在动物的身上表现了令人刮目相看自愧不如的灵性、智慧和才能。曹文轩说过,“动物小说的不断写就与被广泛阅读就是一个证明。它显示了人类无论是在潜意识之中还是在清醒的意识之中,都未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注意与重视。那些有声有色的,富有感情,情趣与美感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文字,既显示了人类依然保存着的一份天性,又帮助人类固定住了人本是自然之子,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员,并且是无特权的一员的记忆。”②
1993年,李传锋把自己之前创作的动物小说编为一本专门的集子——《动物小说选》,在这本书中,退役军犬黑豹和偷鸡的老狐狸斗智斗勇、带领小黄嘴(鸡)和巴克夏(猪)逃出人类暗算;山鸡破坏庄稼为所欲为,小雄鸡毛栗球出落成鸡中间谍,成功引诱母鸡上钩;原本骁勇善战的猎狗狮毛居功自傲、好吃懒做,结果成了一只大腹便便、臃肿肥胖、走路都困难的痴肥狗;母鸡来亨儿在乡间的广阔天地自由游荡,大叫报火警,反被误解的主人打瘸一个星期……动物出于本能,发挥它们自己的秉性,在自己的世界里懵懂努力地生活着,趣味盎然。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小小生物圈,有天敌也有朋友,它们用行动确认了自己作为生态系统成员的身份。
动物小说家李青松致力于发现动物世界里的乐趣,他说,“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讲述一段自己与动物有关的故事——动物之趣是我们记忆深处无法抹掉的东西。动物与我们许许多多的遥远的往事相伴相随。我们对人类自身的敬畏、对生命的同情和惊异、对自然的至美至善的体味,很大程度上,是从我们最初接触和认识的动物开始的。”③他所主编的《大鹰高飞》是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特别推出的“人与动物丛书”之一,这本群众集体创作的小说类似于动物的趣闻汇编:大黄鼬和大刺猬相斗棋逢对手、山狼绕过人成功偷袭山牛、水鹨佯伤调虎离山护雏、行义黎鸠翅扇聒噪喜鹊、秃嘴巴野猪被蒙头顽童吓跑、猪场母猪张生逾墙、野猴子自任牧羊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些发生在动物身上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让人会心一笑,一向为人类所忽视的动物角落里原来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这个对人类来说阴暗的角落里兀自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当真正深入动物凝视动物时,作家们就拥有了一双童话般的眼睛。原来它们的生活一点也不比人类乏味。“所有的动物,不管它是何等渺小,何等不引人注目,都有发出莹光的能力。”④动物在自然中活出了自己的生命乐趣,作为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它们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猪在烂泥中打滚,鹰在高空中翱翔,鱼在水中吐着泡泡,鼹鼠在地下挖掘,它们乐在其中,人类不懂也不会享受这些乐趣,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以狗熊、长虫、黑鱼等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女作家叶广苓在谈自己创作动物生态小说的经验时,曾经说要学会用动物的思维和角度来看问题想事情,“到山里来,我换了一肚子狼心狗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来理解自然,解读生存。存在着就是合理的,我们要尊重并且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生命”。⑤以这种眼光看动物,它们就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源”成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拥有独立价值地位的生命。真正的生态眼光就是尊重每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它们应该是人类道德的对象,也具有自己的道德地位,而且不以人的价值观为衡量标尺。“我们必须以动物自身是什么来加以评价,而不是用只适合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它们部分是什么、部分不是什么而予以评价。……拥有最小脑子的最小动物难道不会思考吗?尽管那只是最细微的思考?……必须有强有力的、自信的、心胸开放的、气度恢宏的、温和的人类,才能精通这些思想,将之吸收到他们的生活里。”⑥
二、动物对己对人的感情
第二类,刻画动物的深情厚谊。动物的感情是动物生态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动物丰沛的感情。中国古代就有相关的故事说明动物是有感情的,比如感恩报德就既有“衔草结环”的美丽传说,也有“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的谚语。当代生态作家们复活并且更新了自我的创作视野,注视着老牛被宰前的大颗眼泪,感动于义犬追随主人的一片忠心,也为母狼舐崽浓嗟叹,不同的情节共同支撑起了有情有义的动物形象。从198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作家们一次次讲述着一个个足以让人悄然动容甚至潸然泪下的有关动物感情的故事。
动物对同类有着深深的爱。狼一向以残暴嗜血著称,但是在诸多狼题材小说中却不约而同地描述了狼夫妻伉俪情深、共同面对灭顶之灾、双双赴死的情形,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邓一光获得《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的短篇小说《狼行成双》,另外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天出血》中的公狼也是明明知道人类用狼崽引诱其上钩还是自投罗网,高贵地放弃逃脱。刘晓滨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废墟狼嚎》中,大难中失散的母狼残耳和狼崽肥肥执着地互相寻找对方,隔着遥遥的距离母子俩真诚的呼应让人几乎落泪。2003年,北京晚报“人与动物”专栏从来稿中选出一些精品编成了一本集子《我的动物朋友》,这里面的《母子情深》讲述了“一只年迈的瘸着腿的老狼牵引着一只瞎眼的小狼,在旷野里奔波着、寻觅着,它们在顽强地寻找着生命间的亲情与永恒”。
狼且如此,其他动物更不用说了。早在1988年,寥润柏在《广西文学》发表了《血崖》,崖顶的老鹰一次次被人端窝,鹰崽被人掏去,因为觅食已经累得瘦骨嶙峋的老鹰护崽心切,一次次地被人的铁扫扫及,“身背上已经重重地吃了老头子一下狠扫,一只眼睛被钩伤了。血顺着落毛冷飕飕地飘下了山崖。于是,老鹰不得不草团似地落到远远地树梢上,眼巴巴地看着老头子”。著名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1999年初出版了小说集《狼妻》,在其中的《熊母》中,身负重伤、明知人类拿熊崽诱杀自己的母熊却仍然在陡峭的山路上留下长长的血痕,用生命开辟出一条辉煌的寻子血路。陈俊2006年的小说集《母狼新月》中讲述了包括狼在内的许多动物之间的真挚情感故事:胡狼亚当和夏娃眼看逃生无望,在狮群中交颈而卧,微笑着走向死亡;剑齿虎兄妹在困境中相依为命;母象盖娅放弃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进入象冢和濒死的伴侣一起面对死亡等等。2007年《当代》第一期发表了李克威的长篇小说《中国虎》,雄虎交配成功后,把盘踞多年的风水宝地留给妻子和未来的孩子,自己重返已被人类破坏的出生地,结果活活饿死。2008年的《兽部落》中,动物呈现的是“美丽的兽性”:不畏人类冒着生命危险挖洞救同类的旱獭、自己主动选择死在伴侣身边的母鹿、让自己的孩子踏着自己的脊梁跳到安全地方自己却坠入悬崖舍生救子的黄羊……在这些作家类似主题的高密度写作中,面对灾难,在伴侣之间、同辈之间、父母和下一代之间,动物表现了丝毫不逊于人的真挚情感。沈石溪在《狼妻》的封面上写道,“动物的高贵情感,足以打动哪怕最冷酷的人类的心灵”。
动物有的时候甚至跨越种属界限,对其他动物特别是弱小危难中的动物也不分“种族”、“物种”地施与“大爱”。新时期文学开始不久,王凤麟就在《人民文学》1984年第9期发表了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彪猛的猎狗在围捕黑熊时,见到小熊崽竟然能够产生犹豫;邓一光的《飞翔》(2000)中,健康漂亮的红嘴蒙关心体恤孱弱残疾的暴风鹱;李传锋2004年创作发表的中篇小说《红豺》中的黄狗则与豺王产下了小崽;2005年1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狼王传说》中,狼从铁夹子下救出母豹,母豹到危机关头也为狼解围助阵;董立勃2006年的长篇小说《烧荒》中的家狗黑风和独耳母狼产生不伦之恋,黑风怜悯产子的母狼,向自己的主人为母狼求情,大火中,母狼放弃逃生回到黑风的墓前守候;差不多同时出版的陈俊的小说《母狼新月》中的鬣狗抚育小花豹;同年初赵剑平的小说《困豹》中被人追捕的豹与被人打伤的狗互舐伤口,相亲相爱“错欢喜”。在2008年出版的新疆作家王族的《兽部落》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狼与带领幼崽过悬崖的雪豹狭路相逢,它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主动让路;一只雪豹和牧场上的牛羊成了朋友,每天遥相呼并与对鸣。2003年出版的《鹰屯:乌拉田野札记》类似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笔记,在其中的《伊尔根觉罗氏》中,助残扶弱的喜鹊竟然与自己的对头——受伤的花鹰嬉戏,“鸟、兽都有对病残同类主动帮助照料的天性,有一天天性越过了界限,便使得它俩成化敌为友。自然界中不同种类的动物成为朋友、互相依存的例子很多,如青蛙会在危机时刻跳进鸟类的地巢中,与雏鸟一起躲避敌害;猛兽来临,乌鸦会给森林里所有的动物报警;母狍子会给失去妈妈的小鹿喂奶:甚至母狼和母豹也会哺育掠来的婴儿……”
对人,动物也是表现了深深地眷恋,特别是对主人和真诚对待自己的人类朋友。同样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的“人与动物丛书”之一的《三只狐狸与一个人》(1993)和《驼铃悠悠》(1994),其选题着重点就比《大鹰高飞》多了情感的成分,文本中有许多情深意长的动物特别是狗的故事:三条腿的狗为了救主人,自己被狼撕成碎片;家犬黑豹和主人形影不离,被送给别人后绝食而死。《野狼出没的山谷》(1984)和《狼狗之间有条河》(2006),不同的作者相隔二十多年不约而同地都表现了“狗变狼”对旧主人旧情难忘,同样的还有陈永松《太平狗》(2005)中的赶山狗对主人执着的追随,张永军在长篇小说《狼狗》(2007)中也描述了勇猛机智的大狼狗对主人忠心耿耿的追随,并且在主人死掉很长时间后终于为遇害的主人复仇。2005年引起轰动的杨志军的《藏獒》试图塑造“比人类更珍惜人性”⑦的灵透勇猛的狗,藏獒对人的忠贞不二、绝对服从让人感动不已。《兽部落》中的狗“从不背叛主人,无论主人怎样对待它都毫无怨言,从始至终都忍耐着,并对命运表示出一种柔顺的样子。主人的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见它回来了便宽容了它。它走到在自己身上击断的那根木棒前,伸出舌头舔了起来”。这样的忠诚让人动容。
除了家养的狗,一些本来凶残嗜血的野兽甚至也收敛了自己的野性,与人和睦相处。红柯的长篇小说《大河》(2004)中熊和人类孩子的嬉戏让人感动,那悲怆的《熊之歌》催人泪下。狼和狐狸是郭雪波的生态文学中两种最重要的沙漠灵兽:《狐啸》(2002)和《银狐》(2006)中,白狐姹干·乌妮格和年轻媳妇珊梅如影相随,《狼子本无野心》(2002)中的被奶奶收养的狼崽黑子和老人、《沙葬》(1993)中的狼白孩儿和云灯喇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于《红豺》(2004)中的土家族女人冬月来说,“红豺是她的狗、她的猫、她的鸡、她的猪。”,她的儿子小时候则与山上野物交朋友,人兽不分。《烧荒》(2006)中,被人手下留情放过的独耳母狼和它的狼群与人怡然相处,“问阿布,咋会和一只狼那么好。阿布说,狼也和人一样,身子里,也有一颗心。将心比心,你对它好,它肯定也会对你好。”京夫的《鹿鸣》(2007)中,老人收留产崽的母豹,人与豹从撤消设防到互相默契,牙牙而语蹒跚而步的人类婴孩“攀圈栅而立,看豹仔在圈舍嬉戏。当豹仔有吓婴孩时,母豹便以爪击仔,以训导幼仔。孩与豹仔,无异于人与家犬,几近形影不离”。此后,豹子还从老狼爪下救人,当人类的牛群受到侵害或者遇到蟒蛇等野物时,豹子总会适时地从天而降解救人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的动物,无论是温顺的猫狗羊还是野性的狼豺豹,只要人稍微表示一点善意,那么它们就会对人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眷恋;而作为对方的人大多数却对动物保持了极大的警惕、提防甚至虐待。人性真的本善吗?
三、动物的多才多艺
第三类,展示动物的突出才能。其实,动物身上有着诸多人所不及的秉性,它们的一些灵性、智慧和才能令人叹服。人是万物的灵长,可是面对动物,人不一定拥有绝对的优势,从动物身上,人类可以赞叹大自然的造化神奇,也更能准确地定位自己。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狼》中,狡黠的狼几乎使人成为其口中物,在和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显示了高超的智慧。“莱布尼兹坚称,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问题,而且动物拥有不朽的灵魂。休谟虽然不认为平等与公平适用于动物,却认定它们具有那些很容易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心理特色:意志、热情、理性、自尊、谦虚、爱、恨及合群。卢梭主张:基于知觉能力而非理性的基础,动物有权利得到保护而不受人类的糟蹋。”⑧
乌热尔图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中,尽管有人类中心主义和前现代的写作倾向,但是勇于和狼搏斗的公鹿以其威武雄健的身姿和“不可阻挡的、奔向自由天地的神力”博得了人类的钦佩。一向“新写实“的女作家池莉1994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沙漠为背景的人与狼》,狡猾的狼芎一箭三雕:借围攻人推翻了原来狼王的统治,又借狼消耗了人的力量,还借人的反抗消化了狼内部的老弱病残。沈石溪的《血染的王冠》(1997)中,被赶下台的麻尾巴猴王为了整个猴群的安宁和整体的利益,拒绝救援选择了死亡,不啻于辉煌的就义。贾平凹一向对动物抱有敬畏,在他最新的小说《古炉》中,被视为弱智儿童的狗尿苔亲近动植物,与之交流沟通,于是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玄妙无比的宇宙,特别是动物,比如猫狗鸡大聚会,给一只冒疙瘩鸡过生日,颇有百“鸟”朝凤的气势;其实在他更早的作品《怀念狼》(2000)中,动物更是大显神通,金丝猴幻化女人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谢恩、狼变人赶着猪过河和调包变猪以及变成老头逃命,相比之下人反而显得有些狼狈不堪。文本中的动物虽然有些虚幻色彩,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是作家的意图在于展示这些动物令人不可小觑的灵性和智慧。《鹰屯:乌拉山野笔记》(2003)中,熬鹰的过程其实就是鹰和人比毅力和决心的过程,人要驯化鹰桀骜不驯的野性,鹰要对抗人对它的改造维护自己原本的特性。杨志军的《藏獒》系列(2005—2008)、还有黑鹤的《黑焰》(2006)、《鬼狗》(2006)更是充分显示了狗中神类惊天动地的“狗迹”,在杨志军的眼中,“比人类更珍惜人性”成了人类应该学习的榜样。《狗村》(2007)的作者认为“狗是世上最聪明的动物,狗是人世上最懂生活的动物”,作品中被人残暴虐待的黑狗像韩信一样含垢忍辱等待报复时机,一旦成为狗王它竟然能统帅万狗部队对人类进行报复,逼迫人类逃离家园。《鹿鸣》(2007)中的头鹿峰峰在岩石上摔碎了自己为人类所觊觎的美丽绝伦的珊瑚状巨角,然后“它侧身回头,面对着大个子原副局长的枪口,等待着,等待着最后在东方大地上的生命涅槃。它是那样从容,高贵而自尊。大个子原副局长手中的枪垂下去了,全身有一阵在战栗,他慢慢跪了下去,向着这尊无角的鹿神塑像跪了下去”。《黑焰》(2006)中的铁红色藏獒和《中国虎》(2007)中的老虎奎奎则因为失去自由,宁肯绝食而死。鉴于此,乌热尔图的《你让我顺水漂流的》(1996)鄂温克最后一任萨满卡道布老爹说:“人——早就比不过林子里的动物了。你看——你不如它跑得快,也不会比它听得远,连你那鼻子也只能闻着两步之内的臭屁。可不管你变成什么模样,还得向它们学点什么……”庞天舒在《白桦树小屋》(2002)中这样评价动物,“其实动物全是鬼精灵,狐狸有一套与野兽捉迷藏与小兽套近乎的手段;家母猪有本事自个儿招郎君;猫狗蹲在人类的屋檐下,佯装一无所知,其实却把人类的事情打探得一清二楚;而军犬忠于职守,严肃的样子一如最优秀的士兵。”
其实不仅在这些方面,即使在人性和道德伦理方面,人有的时候还真的说不上就比动物高贵。塞顿对人和动物作出了这样的对比性评说,“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但是在这里,我希望有人可以找到像《圣经》中所强调的古老的道德观——我们和四条腿的动物是一家人。人类没有的东西,动物也没有;而动物没有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⑨
但是,在此类主题的生态写作中,出现了一种对动物本领夸张失真描述的倾向:与《狼图腾》把狼夸大成人的军师、教官、升天阶梯、精神图腾等的做法如出一辙的是,《藏獒》、《狗村》等写狗小说也同样把狗超拔到了类神的高度,特别是《藏獒》(二),狗会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甚至未卜先知,而且具有无敌的勇猛和对人的无限忠诚,同时还具备宽广的慈悲胸怀,竟然放过天敌的狼崽和怀崽的母狼。《狗村》中的黑狗不仅会察言观色、叼柴火、点火、做饭、洗衣、给人塞被角,而且还能统帅一万多只狗的精锐部队,向人类发动进攻,逼得人逃离家园。这是超越了人的智慧和能力从而像神似妖的狗或者藏獒,看起来痛快淋漓,精彩纷呈,但是在紧张喧闹的荒诞背后,是否意味着一种力不从心的虚张声势?无论是公开提倡藏獒精神反对狼性文化的《藏獒》还是标榜“继《狼图腾》《藏獒》后的新生态写作”的《狗村》,似乎都没有找到准确有力反驳“狼性”的关键点,这种以夸张对超拔、以荒诞对奇诡的策略,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阻击狼性哲学的乌烟瘴气的蔓延与扩散。相比之下,同样是表达生态主题,在《狼图腾》之前出现的《怀念狼》中虽然也有“妖夭奇遇”、“诡事异象”,甚至狼不可思议地会变成人,但作者对狼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狼拥有让人惊讶的本领,狼是吃人的,但因为狼是生态平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我们要怀念它,这就不失为一个好的姿态和好的借鉴参照。
四、动物的辉煌传记
第四类,为动物立史作传。书写某一动物的成长史或奋斗史,长时段多方位地展示此动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习性,多角度勾画其心灵轨迹,揭示它与“非它”特别是人类的错综复杂关系,是动物生态小说的一个近期热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动物生态小说,大多都是此类。这类题材一方面是上面三类的综合,既可以展示动物世界的情趣,也可以表现动物的感情,同时也显露了动物的才能;另一方面,为动物立传作史,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动物从以往小说中人类脚边的模糊物或者山林中的人类威慑物耸立为作品文本中的主人公,它占据了主体地位,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决定了事件的后续发展,甚至人类都只能退到幕后成为陪衬或者背景。精彩绝伦的山野故事连绵不断,动物相对短暂的一生,可以作为多面镜折射出许多东西。动物生态作家们“假语兽言”“衣冠禽兽”,身份的错位还原了动物,也通过动物的眼睛还原了人类。
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是长篇小说《狼王传说》(2005),讲述了“一部狼中的成吉思汗故事,一段关于激情和永不停息的奋斗经历”。在母亲的庇佑下快乐生活的小狼崽贝利,在人类的围猎中随母亲仓皇逃命,死里逃生却发现最终失去了母亲,不得不告别了凄伧的狼窝,当它离开呼伦贝尔草原开始流浪生涯、开始捕猎各种野物填饱肚子时,狼崽已经独立,已经长大。贝利从人类的铁夹子下救出母狼小茸茸,随后和她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并最终成为头狼。狼马大战血雨腥风,展示了贝利的智慧,确立了其草原狼群之王的地位。解救被铁夹子夹住的母豹显示了贝利的博大胸襟,舐崽情深说明英雄同样儿女情长,几次报复偷猎者“红中带青”又显示了它爱憎分明,捍卫自己和狼群的生存权。这个荒野中的狼英雄尽管最终被人烧死,但是其起伏跌宕、高歌猛进的短暂一生尽情挥洒了作为天地间生命的光彩,一些赞颂人类的词汇用在它身上毫不过分,所以作者引用《动物记》作者塞顿的话感叹道,“他们像人类一样聪明,有人类一样的小小的狡猾,会用计谋挫败敌人;他们有感情,有对家人的爱和对朋友的爱;他们身上强烈的英雄气质令你肃然起敬”。
另外相类似的作品还包括《藏獒》、《狼图腾》,以及蒙古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黑焰》《鬼狗》、张永军的《雪国—野狼的海》(2002)等,与《狼王传说》中贝利主要在荒野中的成长不同,这几部作品更多的讲述这些动物在人类中间的生活和成长过程,或者动物在与人类的对峙中互为对照,彰显了动物的英勇和智慧,在《雪国——野狼的海》中,女侠狼姑说狼王闪电是一个“豪杰”,“它才是真正的长白山十万大山中的大当家的”。
发表于2007年的《红毛》则从一只雄鼬与人的关系中描述其成长过程,着重描述在动物眼中的人类行径,特别是人对其他动物及生态环境破坏性的影响。“躲在一个角落里,它暗暗想:从记事起,它的家族就和那个猎手争斗,确切地说是和人类去争斗,最终只剩下它孤单一个了。人类的强大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凭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想毁灭任何一种动植物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人类的荣耀和伟大!但让它不能理解的是:人类干嘛不利用其特有的优势去与其他生灵和睦相处、共享其乐呢?尤其是那些对人类没有任何危害的生灵!”《中国虎》(2007)则讲述了一只从出生开始就处在人类虎视眈眈之中的、被人类保护和反保护的珍贵华南虎祖祖的坎坷一生。幼年的它亲眼目睹了母亲被带毒土箭射中痛苦挣扎,死去后又被剥皮的悲惨一幕幕,在和偷猎者的周旋中自己学会了生存的策略,积累了生活的经验,但是它英武的“丈夫”和两只可爱的小虎崽仍旧没有逃过人类的暗算,或深陷囹圄或被毒死;当然它也享受到了动物保护者小心翼翼的呵护和做母亲的甜蜜。泥石流中,它拼尽最后的生命热能救出了一直真诚帮助它的专家斯蒂文。其实在1989年,敏锐的李传锋就发表过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讲述了南渡江边的最后一只白色华南虎在人类的步步紧逼之下,生存地盘越来越小,后被人抓住,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最后逃回老家,也最终被偷猎者打死。浓厚的悲剧色彩弥漫其中,已经表达了相当可观的生态意识。
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2004)和《狼王传说》在内容结构上很相像,但是,从这只身负灭族血仇对人类怀有刻骨仇恨的豹子眼中,更多的看到了人类互相算计的龌龊行为和贪婪的欲望:“别看他们会微笑,他们的眼睛深处闪烁着嗜血的渴望。母亲说,有一年,她看见人类相食,而我们这些豹子,就是饿死,也不会去啃啮另一只豹子的肉体。”人类歹毒地杀死了母豹在大火中产下的幼仔,美丽的母豹红果也被人射杀。不光对动物心狠手辣,人类还卑鄙无耻地对待同类甚至亲人:孙子按照爷爷的形象做了一个木头人,每天扎一针,还用土铳向木人射击;侄子给叔叔酒里下毒;嫂子设毒计把小叔子撑死……相反,动物之间反而能够相亲相爱:豹子受重伤后几乎饿死,它的情敌为其捕来林枭果腹,自己却因为吃了剧毒的鱼死去。在动物的对比参照之下,人类显得如此的渺小,人类的行径如此黯然无光。“我们假定除人以外的某种动物暂时具备了与人一样的智力,有机会来随心所欲地观察人的生态。那么这位虚构的观察者一定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所谓人类的尊严不过是徒有其表,其实和别种动物没有很大差别。然而人类却要用隐瞒这个事实的习惯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尊严性。”⑩
就动物生态小说总的情况来看,虽然数量众多而且质量看来也相对比较高,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某些细节虽然跌宕起伏但是看上去总和某些国外作品比较类似,比如就狼和它的猎物一块逃命这个情节,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已经描绘了狼和羚羊同样被人追赶,混成一堆一道逃命的场景,在中国的动物小说中,几乎相同的情节也一再出现,有的不过是把羚羊换成野马等其他动物而已,类似的还有狼马大战,马被狼掏出肠子后带着狼飞奔,蹄子踩踏自己奔涌而出的肠胃的血腥场面。这一方面可能因为狼的生活中确实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有待发掘。而且就总体结构和场面描写来说,中国动物生态小说作品互相之间也颇为相像,有的时候几乎把小说中老虎豹子互换就成了另外一部作品。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内作家对于动物的关注范围只是限于某几种类而且是相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老虎、豹子、狗等,作家的视野略显狭窄,还不够广阔,“人类对生命的尊敬不仅仅包括那些有着卓越名声的动物,如长脚的牡鹿、黄色的狮子和棕色的大熊,或者甚至是古老而忠诚的斑头鸽等,还要包括那些令我们厌恶的臭虫们”。诚如斯言。
【注释】
①蒋子丹:《双向的沉重》,《天涯》2007年第1期。
②转引彭斯远:《中国当代动物小说论》,《重庆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③李青松:《编者的话》,《大鹰高飞》,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④[美]S.R.凯勒特:《生命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王华、王向华译,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⑤张兴海:《山野的精灵(代序)》,叶广芩《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⑥[美]福克斯:《深层素食主义》,王瑞香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⑦杨志军:《藏獒是一种高贵的存在,狼不是——我写〈藏獒〉》,《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1日。
⑧[美]福克斯:《深层素食主义》,王瑞香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⑨[加]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致读者》,《动物记——我眼中的野生动物》,段丽华、刘娟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⑩[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