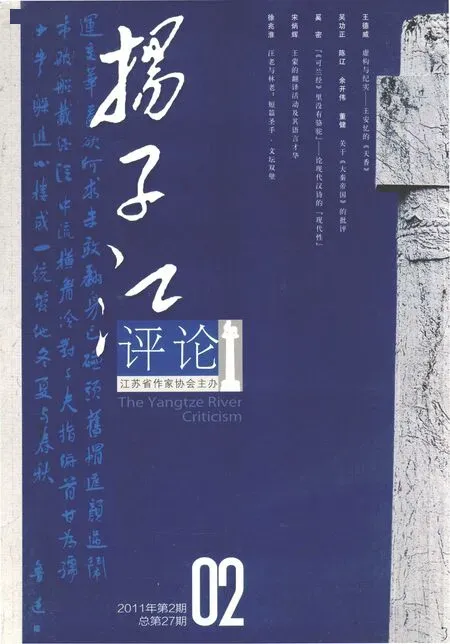在“检讨”与“颂歌”中迷失自我——老舍1950年代的另类文字
2011-11-20商昌宝
商昌宝
回顾历史可知,当1948年革命形式急转之下和1949年革命注定胜利之时,远在美国重洋的老舍并没有及时赶回来参加新政权的建设,而是借故拖延到12月12日才回到北京。当然,作为远道归来的客人,他得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高规格待遇:公款入住北京饭店;第二天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享受专车待遇;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贺新年暨欢迎其归国的大型联欢茶会;文联第四次扩大常委会上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受命筹建北京市文联被内定为文联主席;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纵观老舍回国后的生活履历,可以说,“革命不分先后”、“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的说法在他身上得以应验。然而,面对如此礼遇,与革命胜利本无多少贡献的老舍,自然难免产生一种“擎现成的”的心理。于是,如何满足和回报新政权,便成了老舍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一、自觉检讨“旧作”、“旧我”
既然皈依了新政权,老舍自然就要顺应时势改造思想。在1950年文联的新年联欢茶会上,老舍谈了自己归国的感想,表示自己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很早就愿意回来。同时,他也检讨自己没能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很觉得惭愧,愿意学习,希望利用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技巧,对革命有些贡献。①从形式上说,这可以算作是老舍的第一次公开检讨,只是其中礼节性的成分掩盖了应有的严肃。1950年6月,老舍在开明版的选集“序言”中开始了正式检讨。文中,他批评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特别是在革命文学兴起时,自己虽受普罗文学的影响,创作了《黑白李》,不过“没敢形容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他还处心积虑地说,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自己“居然还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月牙儿的女主角的继父”。他承认自己的作品“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为此他检讨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最糟糕的,是我,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关于《骆驼祥子》,他承认自己“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他还“披露”说,自己在原稿文末写过:“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指祥子——引者注)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可惜“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被删去了”,他继而说:“我管他叫作‘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最后,他不无诚恳地说:“以上,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不过,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②从这篇“序言”看,老舍一方面竭力给自己的作品“涂脂抹粉”,以增加和突出其先进性;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诸多落后思想,老老实实地检讨了自己的温情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选》的“后记”中,老舍再次检讨说:“在思想上,十三篇中往往有不大正确的地方,很难修改,也就没有修改。人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的,今天能看出昨天的缺欠或错误,正好鞭策自己努力学习,要求进步。”③
1951年6月,老舍撰写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文。在极尽感谢之余,也对自己的思想做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检讨。他说:“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我没有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共产党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艺里的重要性,和文艺是为谁服务的。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缥缈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的‘赶任务’。”④随后,他在《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中着重检讨了自己的幽默风格。他说:“我没反对过革命,可是我的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并进一步补充说:“假若我自己承认: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进,岂不是倚老卖老,越来越没出息么?……专凭卖老字号,而不充实自己,不久一定会垮台。字号越老,才越须改造,老的东西不是更容易腐坏的么?”⑤在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他撰写了《毛主席给了我新生命》。文中,他再次检讨了自己的幽默趣味、不敢革命、自得自傲等问题,还明示说自己回国后首先读的便是《讲话》,明白了文艺为谁服务和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也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文艺家。因为自己二十多年来“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在坦诚了自己的诸多错误思想后,他总结说:“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最后,他表态说:“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⑥1954年,他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再次检讨道:“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⑦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中,他一边批判一边检讨说:“在我解放以前写过的作品里,因缺乏共产主义思想,……所以那些作品很肤浅,甚至于有错误。”⑧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了更深刻的自我批判。他剖析说:“我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争名夺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弃名利。这就是说,在旧社会里,我虽没有无耻地往高处爬,可是也不大明确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⑨看得出,无论是个人的思想还是文学创作,老舍在否定自我方面已经比较全面、深刻了。而这样的检讨在他看来是一种进步、高尚、忠诚的表现,而不是丢脸、有失身份,正如他所说:“面子不过是脸皮那么厚薄,掩藏不住肮脏的灵魂。”⑩“勤于学习,勇于接受批评是光荣,而不是丢脸,是勇敢,而不是自卑!在一个新社会里,有什么比急起直追,争取吸收新知识新经验更可贵的呢?”因此“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干净,重新作个干干净净的人”。老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可见他进步之大、态度之诚了。
二、检讨“新作”和“新我”
在检讨“旧作”和“旧我”的同时,老舍也开始检讨起“新作”和“新我”。1951年元旦,老舍在抒发自己回国一年的感想中,检讨性地表态说:“在这一年以前,我已被称为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对得起那个称呼吗?我不敢说。……只要我肯向人民学习,而后为人民写作,我便可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文艺,对得起文艺工作者这个称呼。啊,我能在短短的一年内,明白了上述的道理,这一年不是等于五十三年么?”一贯以幽默著称的老舍,竟以如此夸张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心情,真是其情可感了。不过,检讨“新作”并不像检讨“旧作”那样容易,毕竟他还不能完全通晓新的写作规范,为此他诚实地说:“在学习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有时候,我想不通;有时候,想通了而不肯那么写出来,怕别人笑我,说我鼓着腮帮子充胖子。没想通的,写出来,自然要受批评。一受批评,我就觉得丢了脸,心中老大不高兴。想通了而不肯写出来呢,又使我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使人坚定与坚强的利器。……我要抱定这态度去作人,去作文艺;我相信,我已摸到门儿。老舍虽说“想通了”、“摸到门儿”了,但那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样的体认并未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可,这一点从电影剧本《人同此心》的流产遭际中可以看出。老舍虽不知其中详情,但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因此,不久后他便撰文剖析说:“必须要求自己写得‘对’,而后再要求写得‘好’;道理说错,文字越漂亮,故事越有趣,才为害越大!……在这个新社会里不准有胡说八道,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自由’;也不准利用漂亮的文字,有趣的故事,偷偷的散放毒气!”他接着结合自身的实际说:“在这二年里,我写了不少东西。其中有的写得很对,有的不很对,有的大体上对,而细节不对。在第二届国庆节这个好日子,我愿意坦白的说出来:写得对的,我引以为荣。写得不很对的,我并不灰心;我知道只要我肯虚心的接受批评,社会上就允许我改过自新。”他还针对“勉强”和“不痛快”的质疑回复说:“追求真理是必定有痛苦的,怎能不勉强?难道真理能像买个烧饼那么容易么?至于痛快不痛快,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假若你肯和人民立在一条线儿上,写出足以为人民服务的作品,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呢!”当然,他没有忘记强调自己的转变还需要时间和过程,并解释说:“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是,假若真有自信心,也并非绝对办不到的。即使一时办不到,不是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帮助我逐步前进吗?我愿意下决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总有一天我会走到一个新社会文艺工作者该走到的地方!现在看来,老舍如此委曲求全似也必要,据齐锡宝回忆,当时江青正要组织召开1952年电影创作题材规划会,便指示说:“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从事后老舍讳莫如深的态度看,他的上述检讨是有针对性的。
老舍虽然没有因为《人同此心》的流产而一蹶不振,但在此后不断创作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作品的检讨。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在我的近五年来所写的东西,也因为思想学习不够深入,所以思想性还不很强,作品也就软弱无力,不能“成为阶级斗争中的精神食粮”,是“可有可无”、“不疼不痒的东西”。他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对新社会的生活,工农兵的生活,都体验得不够”,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内容不够丰富,感情不够饱满”。其次,他认为,即使“有了生活,而不懂马列主义,还是不中用”,自己就“吃了这个亏”。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听别人唱歌,和自己唱歌,自然是两回事。打算描写歌唱的乐趣或困难,顶好是自己唱唱。不参加革命斗争,就不会得到应有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经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薄弱无力。”老舍的分析和判断,不能说不深刻,但是,他没有想到,即使参加了革命斗争实践,也还是写不出好作品。巴金便是明证。
三、热烈歌颂
既然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自然要根据集体的需要履行自身的职责。作为人民代表,老舍热心为百姓分担解忧,忘我地投入工作。据作家林斤澜追忆,“老舍当年作为市文联主席是积极参加解放初几项政治运动的,天天来机关上班,连编辑部发稿时间都管,还在机关吃顿午饭。为了亲身感受控诉恶霸大会,他拖着病躯的腿老早就到了天坛,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群众”喊“该打!该打!”为了响应全国文联关于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号召,他带头捐献了《龙须沟》、《方珍珠》的上演税800万(旧币)。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他积极表态,“勇敢战斗”,先是“看穿了胡风的心”,然后要求“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进而呼吁大家“都来参加战斗吧”,最后提醒说:“别光说‘真没想到’啊”。1957年夏,他率先嗅出“反右”的味道,接连撰写了《三邪》、《心中有了底》、《个人与集体》、《为了团结》、《树立新风气》、《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旁观、温情、斗争》、《勖青年作家》、《首先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等批判文章。
老舍出身的家境决定了他的仔细、老成持重和世俗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没有诗的天才?……我缺乏着诗人的明敏犀利。但是,1949年后老舍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满含激情的颂歌诗人。他歌颂他所热爱的北京,因为他说他“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和发展”,“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所以他满怀憧憬地写道:“这人民的古城多么清爽可喜呀!我可以想象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他歌颂伟大领袖,因为“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在第一届人大会投票仪式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毛主席……我们投您的票不是一种什么形式或手续,我们是向您表示拥护您的决心!我们将永远跟随着您,听您的话,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当被毛泽东接见时,他兴奋地写道:“最使大家欢喜的是毛主席非常的健康,精神非常的好。这是大事:他老人家健康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他还说:“我要告诉我的儿女并嘱咐他们将来告诉他们的儿女:我选举了毛主席,并且和毛主席握了手!”老舍的感情是充沛的,也是永不知疲倦的,所歌颂的内容也尤其丰富:“中苏同盟”、“中苏伟大友谊”、“英雄的平壤”、“和平会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抗美援朝、宪法诞生、五年计划,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他歌颂的对象。通俗文艺创作上,老舍更是尽展自己的才华。仅1950年上半年他先后创作和发表了《别迷信》(京津大鼓)、《生产就业》(鼓词)、《谈相声的改造》、《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大众文艺怎样写》、《中苏同盟》(太平歌词)、《维生素》(对口相声)、《金喜翻身》(单弦)、《改编绕口令》(对口相声)、《从技巧上说》(文艺杂谈)、《“现成”与“深入浅出”》(文艺评论)、《假博士》(对口相声)、《通俗文艺》、《铃铛谱》(相声)、《鼓词与新词》、《相声改进了》等。老舍在剧本创作上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据舒乙不完全统计,老舍1949年后共写了三十多部剧本,其中发表的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京剧三部、翻译剧一部。一些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量则无从计算。可以说,在1949年后的颂歌中,老舍的声音最洪亮,音质最动听。
自然,这些作品如老舍当时说:“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自然,这样的作品自然难免人物虚假、语言生硬、情节牵强等公式化、概念化的结局。唯一的例外是《茶馆》第一幕。当然,如果将《茶馆》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三幕话剧——来看的话,它也仍逃不出“运动戏”、“观念戏”的宿命。从1949年后老舍的创作实际来看,他明显背离了前期的剧作主张,而走向另一个“审美领域”。不过,老舍虽然在主观思想上皈依了主流政治,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却未能把握如何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要领。因为他虽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却极少真正介入实际政治,对主流意识的政策把握的不够,所以在文艺图解政策上常常要求助于具体业务干部。而且,因为腿疾他也很少走到工农兵中间,对一些新兴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缺少切身的体认和感悟,一些现实取材常常是由助手或帮手来完成,而他也只能立足于这种二手资料,所以闹出了不知“车间”是“装机器的大房子”而以为是“两个车轮中间”的笑话。老舍对生活的不熟悉是显见的,但为了政治的需求,他不得不采取“现用现抓”、“临时抱佛脚”的投机手段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客观地说,在这种创作方式和状态下,老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文化官僚”和高级写作“打工仔”的角色。如果联想到“文革”中的所谓“集体创作”,可以发现,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紧张、忙碌地唱和了几年后,老舍明显意识到,这合唱队伍虽然庞大,但是真正有分量的声音并不多。一些“老”作家早已经放下笔墨,连短小的诗文也写得很少,这让他很有一种寂寞之感。不过他给大家找的理由竟然是:“老”作家们因为会务多、工作忙,才扔掉了笔。因此,他现身说法道:“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但是我仍能“手不离笔”。因此他希望:“上自全国‘文协’,下至各地方的文联‘文协’,都从现在起,有一种学习与创作的空气,把老的少的新的旧的作家全动员起来,一边学,一边写。老舍的确是热心的,他为文艺的不繁荣而担忧,不理解作家们为什么不拿起笔。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之际,他倡言说:“作家们必须参加这个斗争,好好地打几个漂亮仗!我们深信胜利必属于我们的,好,就写吧,教全国人民都深信胜利必是我们的!时隔一周,他再次撰文倡议:“同志们,忙起来吧!写吧,画吧,唱吧,表演吧!我们越忙,就越快乐,就越光荣……我们要抢到前边去!我们要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去配合、鼓舞前无古人的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与超额完成!这之后,老舍又先后撰写了《文艺工作者都忘我地劳动起来吧》、《文艺界要马上全体动员起来》、《“将军”》、《前进,前进,再前进》等诸多应景文章。从这些极尽夸张的号召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老舍的拳拳之心。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老舍如此声嘶力竭地忘我工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抗战时期,他就曾为号召文艺家抗战而奔走呼号,并写作大量短小精悍的动员文章。但如果作以比较,可见其中的不同点:前一次他扮演的是一个文化战士的角色,更多地带有悲壮意味;后一次他扮演的则是一个文化小丑的角色,更多地带有滑稽意味。正因为这样,当时就有人写匿名信咒骂他:“我希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北京大中学生也在私下讥讽他是继郭沫若之后的“京城四大不要脸”之一。
1949年后,老舍这样虔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阶级和集体的乌托邦事业中,同时也能够那样完整地放弃自己的幽默、沉郁、悲观和改造国民精神及文化的自由追求,一切都是那样自然,那样协调,那样顺理成章,甚至在赴死前还不忘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只是后来1966年8月24日他的“纵身一跃”,将这一切全搅乱、打破了。他能眼看着“胡风集团”2100人被整肃,“反右”运动中55万人被打倒,却独独受不住“革命小将”的皮带和拳脚。老舍死得悲壮,但也死得脆弱,死得不够明白。对于死者不应有任何苛求,那样有大不敬之嫌,但对于生者,还应该思考:假如皮带和拳脚出现在1957、1955年,或者此前十七年的任一年,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他还会紧跟吗?假如1966年没有出现皮带和拳脚,又会怎样呢?
【注释】
①参见甘海岚:《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②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
③《老舍短篇小说选·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④《光明日报》,1951年6月26日。
⑤《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1951年12月10日。
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
⑦《生活,学习,工作》,《北京日报》,1954年9月20日。
⑧《好好学习》,《学习》第六期,1955年6月2日。
⑨《八年所得》,《新观察》第十九期,1957年10月1日。
⑩《为了团结》,《文艺报》第二十号,1957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