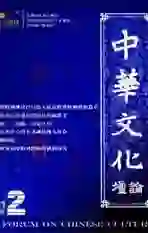东晋义解僧人对于诗风转变的影响
2011-10-21李斯斌
李斯斌
[摘要]东晋佛学兴盛,对于清谈以及玄言文学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历来东晋诗歌研究少有从其义解僧人的政治地位角度分析对于诗歌的影响。实际上,东晋义解僧人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其与文人相交过程中,文人多有附和于僧人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新的影响势力,影响了诗风的转变。
[关键词]义解;玄言诗;石门诗;退寻;山水诗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63-7
一、义解僧人的出现与地位提升
佛教最重经译之功,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以译经为首,而义解居次。义解僧人,慧皎谓“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实谓偏于佛经义理阐发,杂通儒道之僧人。佛教自西汉末传人中土,虽历经汉、魏,而终不脱“道教”习气,实有义解不足之因。大法西来,即有经译,北方以洛阳为中心,
译经:汉魏7人,附12人西晋2,附4人
义解:汉魏0人西晋2,附2人南方以建业为中心,经译虽艰辛而佛法传阅不广译经释子多汉语不精,诗文无作,其必影响与文人相交,义解之僧不足可见矣。佛教义理难为中土帝王、士族所接受,其僧人政治地位可想而知。西晋祚短,义解之僧只有少数与文人相接触,虽至永嘉渐盛,又遇典午政乱。由此,义解僧人之兴,实盛于江左。以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为例,足可见汉魏两晋之时,释子译经与义解之差距:
东晋13,附10人
东晋40,附,43人
东晋义解之盛,一是南土文学有偏理寄之风。《世说新语·文学》有记: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南方学识偏于义解,正与永嘉风气相接。东晋之时,佛理大兴,北方文士僧人纷纷过江,多有以义解而谋食者。支愍度立“心无义”可为典型。《世说新语·假谲》: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饯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由此可见,过江之人,多有以迎合南学之风而立新说,此为东晋义解一大特色,谓之“拨新”。孙绰《愍度赞》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拔新”之评,非为贬词。支道林为东晋清谈第一流人物,寻微之功,不减辅嗣,亦评品之“拔新领异”。《世说新语·文学》: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世说新语》中多处可见拔新之谈。东晋佛教经义义解“拔新”之盛,鸠摩罗什未到之前,南土即盛行“六家七宗”之说,皆以《庄》《老》之法以解般若。
东晋义解之盛。不仅有南土文风有关,实亦为佛教传播客观之需要。自东汉以来,译经虽多,而影响不大。一来经译手法还不成熟,更大问题是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存在差异,若没有很好的手段加以传播,则中土之人很难理解。由此,虽译经功高,实佛教传播之功,皆在义解僧人。义解之僧,重在圆通佛理与中土文化,加速文化异质的融合。纵观佛教中土化历程,义解之功,实不减译经。早期义解,用所谓“格义”之法以适应中土文化的理解。“格义”虽早,竺法雅为之完备,《高僧传》曰:
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成附咨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
以中土《老》、《庄》思想比附于佛教大乘思想,由此两者便相互融合,互有所取,《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慢慢汇合。这种义解之法至鸠摩罗什至后,实则也没有改变。罗什东来,虽大斥此法,但此风已盛,似难弥净。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言:
按晋代以玄学、《般若》之合流,为学术界之大宗。南方固为士大夫清谈之渊薮,而北方玄理固未绝响。什公有名之弟子来自北方,均兼善内外,博通诗书。且在什公入关以前,多年岁已大,学有成就。吾人虽不知其所习为外学何书,然僧睿、僧融早讲《般若》,慧睿、慧观来自匡山。匡山大师慧远并重《老》《庄》,而罗什以前之《般若》更富玄学气味,则吾人即谓什公门下多尚玄谈,固无不可。
汤先生所言甚有道理,玄学之盛,积习已深,非罗什之力所能革新。佛教之理偏于义理思辨,非中土之人思想所长,政治集团以及文人又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要,佛理之解,多汲不害儒法之处,又改佛法有违儒法之处,诸多变通,印度佛教思想已汇入《老》、《庄》而加以简化,此正应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此可谓佛教传人中土之境况。吕潋先生在《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提出:
不妨可以这样看,佛学传来中国,原是在玄学基础上接受并发展起来的,以后双方分了开来;到了禅学的后期,却又重新归到与玄学结合的方面。
佛学与玄学之结合,此为中土佛学之特点。而东晋之时,佛经义解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激烈的时期。正是由于此时佛理义解大兴,义解僧人政治地位更值得重视和研究。东晋义解之僧的政治地位、文学影响实则都远高于译经之僧人。
三国时期,未见僧人与文人相交的记录。而西晋之时,《高僧传》载“支孝龙”与庾凯等人相交,史称“八达”。
支孝龙,淮阳人,少以风姿见重。加复神彩卓荦,高论适时,常披味小品,以为心要。陈留阮瞻、颖川庾凯,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支袈裟,释胡服,被绫罗?”
西晋类似支孝龙与文人相交的僧人记录并不多见,僧人多不以宏法、义解佛经为第一要务,反而更效嵇、阮之流。研习佛理而不崇佛律,多狂士之举。《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叔兰传》:
(竺叔兰)性嗜酒,饮至五六斗方畅。尝大醉卧于路傍,仍入河南郡门唤呼,吏录送河南狱。时河南尹乐广,与宾客共酣,已醉,谓兰曰:“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曰:“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问侨旧?”广又曰:“饮酒可尔,何以狂乱乎!”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广大笑。时坐客日:“外国人那得面白?”叔兰曰:“河南人面黑尚不疑,仆面白复何
怪耶?”于是宾主叹其机辩,遂释之。
西晋清谈之风虽盛,然僧人与文人相交,少玄理之谈而多标人生畅达之举。从西晋僧人的此种行径来看,亦可理解为与文人相交之中,政治地位上实则处于弱势而多效文人林下风流。这也能
解释慧皎所收西晋高僧寥寥无几。其《高僧传序》所谓“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
但到了东晋,这种风气便有了微妙变化。东晋之时,文士与僧人交往频密,其清谈又多研佛理。今存《世说新语》之中东晋文士与僧人相交记录甚多,多集中于《言语》《文学》《赏誉》《品藻》之篇。东晋义解之僧纷然成群,实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南土崇佛,君臣同好。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法。《世说新语·方正》引《高逸沙门传》载:
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
哀帝之后,其清谈更盛于前期。崇佛之心大臣亦甚,何充等人则侍佛以巨资。《世说新语》注引《晋阳秋》:
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久在扬州,征役吏民,功赏万计,是以为遐迩所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僧人地位显赫,甚至影响到了政治的决策。梁宝唱撰《比丘尼传》中记载了简静寺支妙音尼传:
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问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云。
东晋僧人获得了政治君主、门阀士族的支持。竺法潜出身于王氏家族,而支遁亦曾淹留亦师三载,甚至还出现了以慧远为首的僧人集团。依《高僧传·慧远》所记:不仅有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依远游止;秦主姚兴钦其德,赠珠献像;桓玄入山相敬;晋安帝遣使相问。诸多事迹可见慧远地位之高。义解之僧政治上取得优势,实与其当时文化传播有关。义解僧人,处于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相融这一层面,一方面他们深识佛教,又善立新说,著书以释佛理;另一方面,他们三教皆习,善于融通,又兼擅诗文。游走于政治集团、门阀士族之中,又与文人游宴酬唱,故而名高一时。东晋义解之僧其名望与政治地位实非译经之僧所能比。
正是君臣与文士对于佛教的支持,实得东晋义解之繁盛,义解僧人的地位亦很高。但义解之僧亦不失弘法之宏愿与独立之精神。东晋僧人多有康法朗、于法兰、智严、智猛等西土求法之士。成帝成康之时,庾冰起沙门敬王者之争,何充复疏辩之。安帝元兴之时,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亦据理以辩。沙门竞不致敬,一见其僧人地位,亦见佛教教义的独立精神。东晋义解僧人这种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得在与文人的交往心态中,僧人也并不再处于弱势,而渐成为了文学创作新的影响势力,从而影响到了东晋诗歌风格的转变。
二、义解僧人对于玄言、山水诗歌创作的影响
西晋之时,与其说佛理影响文人,更不如说文人之行径影响僧人更为贴切。就其诗歌创作,葛晓音先生在其《八代诗史》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解的观点。认为西晋之时,玄言诗风未盛,实与清谈之士多不擅诗文有关。其言:
永嘉前尚未大量出现玄言文学的原因,首先在于:西晋尚玄,多在模仿阮籍、向秀、刘伶放达的行迹,或讲究风度言谈,却很少对玄理本身进行探讨研究。所以后来戴逵说:“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放达为非道论》)同时,王衍、乐广虽为天下风流之首,但并不擅长诗文创作,因而玄言文学尚不可能大行于世。
西晋玄言诗风不盛,确与清谈之士不擅诗文有关。实则,西晋司马氏多崇儒法,门阀士族亦多习之,虽然清谈风气,多为人物品评,少放达行径。佛法本符切《老》《庄》,西晋义解僧人自不受君臣亲睐,与文人相交,亦多效其放达,实见政治地位不足。东晋之时,僧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许多文人都试图与僧人相交,而附和声名。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孙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孙绰写《名德沙门题目》涉及诸僧,而著《道贤论》又以僧七子比附“竹林七贤”,更著《喻道论》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这些现象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对于佛教教义的笃信与僧人佛法高深、仪止不凡的赞扬。实则,其背后可以看到其文人与僧人交往之间微妙的政治利益。孙绰非士族门阀,许询为徵士,唯有交往于当时名流才能在玄风之中获得政治、名望的收益。而对于诗歌的创作,文人必是投其所好,而加以推波助澜,玄风在佛理的推动下,更是繁荣之至。《高僧传》有载:
(道安)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
僧人地位尊崇,文人自有相附,此南北皆同。檀道鸾《续晋阳秋》有载:
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
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
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
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亦言:
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
询极其名理。
从义解僧人地位背景再来理解檀道鸾所说“加以三世之辞”“自此作者悉体之”,可以看到孙、许此风所倡并为文宗,非仅为孙、许所作诗其艺术性而言,实与佛法义理遍于江左,且僧人地位崇高,文人多相附和而至。
对于东晋玄言诗研究中,我们都会提到佛教义理对于玄言诗的影响,但是如何影响玄言诗风格的转变,则比较模糊。大多从其义理层面来看待这种转变,言其佛教义理符切《庄》《老》等。实则,佛教对于玄言诗的影响,不仅需要从其义解方面来解释,更重要的是从其义解僧人的角度来解释。玄言诗在东晋前期,实则还可以看到郭璞“游仙诗”一路,追求绮靡风格的诗歌创作,这一风格是继承了西晋太康潘、陆之风,但到了东晋中叶之后,玄言诗出现了另外一种“辞简旨达”的佛偈化诗风。为什么文人热衷于这类诗歌的创作,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实事上,从其以上对于义解僧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义解僧人与文人的接触增多,不仅有助于文人佛理修养提高,同时,义解僧人当时地位的显赫,使他们摆脱了西晋之时与文人相交的方式与心态,成为了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势力。
东晋之时,诗歌创作中虽渐有山水诗句,然真正大规模进行山水诗歌创作却是在僧人集团确立之后。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山水自然,僧人居隐山林,亦有畅游山水之兴,犹比羲之兰亭诗会。虽然,僧人亦同文人山水之游,但僧人对于山水的本质认识,自东晋般若学兴盛之后,便有了细微的变化。庐山慧远等诸人在隆安四年仲春,便有一次石门之游的记录,并有《石门诗·并序》:
石门在精舍南十馀里,一名障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辟三泉之会,并立则开流,倾严玄映其上,蒙形表于自然,故因以为名。此虽庐
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皆传之于旧俗,而未睹者众。将由悬濑险峻,人兽迹绝,迳回曲阜,路阻行难,故罕经焉。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馀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
《序》中不仅有对其所见山水之感,言“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而且提出对于山水之游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退寻”说。
若玄音之有寄,虽仿佛犹闻,而神以之畅。虽乐不期欢,而欣以永日,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寻之。
僧众纵情山水而却不耽于此中,山水有味而不易言,需“退而寻之”,此所谓“退寻”。“退寻”这一概念前人并非无人重视,明代钟惺对于“退寻”之说便大加赞赏。其《古诗归》卷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夹批中就讨论到“退寻”之法:
(“退而寻之”)每对山水,思理不属,必欲当境成诗,非唯诗未必佳,且亦有妨游趣。过去补作,又似不情。读“退寻”二字豁然。匪徒便门,自是至理。
(“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而未易言也。退而寻之。”)“退寻”,妙,妙!游后追忆,胜于游时领略。
(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大悟人语,退寻之妙,于此想得出。
“达恒物之大情”,实表明“退寻”乃僧人对于山水的另一种态度。“退寻”不仅强调了山水之“游”,同时更强调了“退”而寻之。目之所见山水非自然之真,是为自然之理的外在表现。山水之游,当达于自然之理,而非纵情于山水本身。正如《序》中所言:
夫崖谷之间,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间邃笃其情耶?并三复斯谈,犹昧然未尽。俄而太阳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
山水之游,不应以情而开兴,纵山水以为乐。物之大情虽寄山水,而又不止于山水。“神趣”之悟,非在山水而已。需以山水为接引,而悟自然之本理。这正是僧人山水之真谛的理解。僧人对于山水之观念,使得僧人对于自然山水的表达区别于西晋文人与郭璞的游仙诗。一方面,他们纵情山水,怡情自然,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山水并非“真趣”之所在。总观其序,僧人对于山水之情的领悟,总是由景及情,由情及理的表现。由此,僧人的山水诗中,总是有其“点理”之笔,就是强调了山水本旨的目的。其《石门诗》可见: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物化”语出《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陈鼓应指其为“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依僧人看来,虽然神仙达至物我消解,但这种消解,只是把主体置于自然之上,实仍为有“物”有“待”的表现,并不彻底。“未若两俱冥”不仅表明山水与自我同一,同时强调了并非归之于物,而是归之于理。僧人对于山水观照,强调物我两者皆弃,以便悟识人与自然的至理。钟惺《古诗归》卷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夹批中对于僧人山水之诗点评可谓独到: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山水说理字,浅人不知。
“退寻”强调了对山水本质的认识方式,而不是对于山水一种外在形式的适性把握。它不同于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物我同性观照,也不同于道家所谓“逍遥于天地之间”畅游,更突出了主体与山水的理悟层面上的关系,强调了主体对于山水的觉解。
“退寻”的山水诗作是玄谈说理在诗歌中的运用,讲究“游”与“理”契,自不免染上玄言辩理的习气。与陆机《文赋》中“心游万仞,精鹜八极”的意象自然的观照相比,更进一步要求山水之“游”后对于自然本真的刻画,并不强调繁缛的意象渲染,而是更多思虑自然山水“理”的启示,从而使山水更多展现出主体对于人生哲理的领悟。山水诗中所营造的意象不是简单的自然世界的对应,它往往要求出于自然而超于自然。总之,僧人山水观完成了对早期屈原《离膝》山水的虚幻漂渺、郭璞游仙的坎咏怀的蜕变,而直接呈现山水自然,从而引发人与自然更深层次的人生体验的思考。就其对于诗歌的影响,可概之为二:其一,“退寻”强调对于山水自然的本质领悟,摆脱了传统诗歌创作中“托物言志”的创作手法。一方面直呈对象,另一方面又凭藉对象领悟其本质,这种本质的核心是“理”。其二,这种从“诗缘情”到“诗言理”的改变,形成了中国诗歌审美中的境界雏形。“理”的表达实则是主体对于人与自然的人生哲理领悟,随着中国诗歌发展,“理”亦被纳入到了“情”的范畴,“至理”之大情亦在为诗歌人生境界的表现。这样来看,“退寻”之法可谓影响诗歌境界的早期形成。
“退寻”的山水观念,在其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也得到体现。谢灵运是刘宋山水诗兴起的代表诗人,与僧人交往甚密,著《辩宗论》以宣佛旨,其诗歌创作也受到僧人山水诗的影响。钟嵘《诗品》列之上品,认为“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谢灵运诗歌是对屈原《离骚》、郭璞游仙诗的借鉴,但又是一次革新。其摆脱了对于自然的寄兴创作手法,直面山水本身而求其理。谢灵运的山水诗,一方面具有其“游”山水特点。罗宗强先生认为“谢灵运山水诗的叙述部分写法上常常是流动的,大处落笔。记行程、时间和空间,在行进中变换,并非写一个固定的画面。”但同时,谢灵运山水诗在“游”之中,大都有人生之“理”的概括,这一点体现了“退寻”之法对于他的影响。
“退寻”之法,不仅影响山水诗的创作,同时对于当时绘画理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宗炳《山水诀》中所表现的自然观,就是“退寻”创作的体现,其《山水诀》中有:
圣人含道哄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
在《宋书·列传五十三》中: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宗炳所言“饱游卧看”的山水创作与审美就是“退寻”之法的体现。所谓“澄怀味象…‘应目会心”就是要求对于山水的领悟,不能止于山水的形式而必须对于山水自然的意象进行高度的概括,通过对于意象的玩味,领悟山水自然之“理”。
总观东晋之时,其义解僧人对于东晋文学影响可谓巨大。东晋义解之僧,亦颇有宣扬佛法之宏愿,显有几分独立精神。道安力排格义,慧远法性之论,道生顿悟、阐提成佛,肇公《肇论》,皆以求佛法真要为务,比之西晋游僧风流,实为可敬。而齐梁之后,佛法虽亦盛,然其义解之僧政治地位远不及东晋,又儒法再兴,僧人多依附于政治集团、世族门阀而失其独立精神,宫体艳词,实首发于僧人之作,以真俗二谛圆融,佛教方便法门而附和冶艳之词,虽佛事尤盛,亦可叹其宏法精神不存。唐宋以后,虽僧人多有与文人相交,而其诗作多效文人诗法,与东晋之时别为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