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给了郜元宝什么
2011-10-13江苏鲁正杰
[江苏]鲁正杰

重新回到“不安”
在郜元宝先生的北大版《鲁迅六讲》(增订本)“附录一”中,《竹内好的鲁迅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独特的有些古怪的论辩方式,迫使他在这本小书中用心探索一种竹内好式的模糊、幽深、本质上几乎不能完全表达的语言。”(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如果这也算是“批评”的话,那几乎是稀有的。
他接着说:“正如鲁迅的诞生主要是文学家的诞生,鲁迅的死,也主要意味着一种执拗的文学沦亡。对那种看不到鲁迅的文学却自以为能够‘发扬鲁迅精神’的买椟还珠的做法,竹内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第160页)同页下注很有意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恐怕只在于胡风、冯雪峰一致秉承鲁迅的作风,目光主要在国内文化与政治,而慎谈甚至不谈国际(比如中日之间)的政治,因为问题一旦国际化,中国自身的问题就有可能失踪——不管这中国自身的问题在当时已经多么国际化了。”我们的问题是,胡风、冯雪峰秉承的“鲁迅的作风”是不是那种“执拗”的作风?如果是的话,那么说明还没有“沦亡”;如果不是的话,就说明那二位还没有秉承鲁迅的什么作风。结果是怎样的呢?答曰:为了防止“中国自身的问题”“失踪”。
虽然“在《鲁迅》一书中,我们确实往往很能够看到竹内忠实于自己的‘无法理解’。正是用这种方式,竹内将他的‘不安’传给了他的读者”(第164页),并且“他许多关于具体作品的观点完全照搬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大可省去不说。当然,他的表述仍然有其强烈的个性,和常识无论怎样总有距离”(第163页),但是,“我觉得,必须尊重这种无可奈何的闪烁其词,就像大家同在黑夜里走路,宁愿听到姑妄言之的相互提醒,而怕听到一定要走某条路的绝对命令”(第168页)。
至此,已经完全可以看出郜先生对竹内好是怎样的态度了,并且我们也多少知道了竹内好给了郜先生一些什么东西。而郜先生给我们的解释就更加高深了:“当一个人的思想开始进入宗教的无边无际的空虚之际,任何对他在此之前的演说的指责顿时都将成为盲目。任何可能的指责所面临的问题倒是:你是否也愿意和你所指责的人一起落入那个空虚?”(第169页)在此,我们又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认识”,即宗教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如此说来,如果竹内好在世的话,也一定会用他的“模糊”来和郜先生争辩一番的吧?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郜先生将他的“空虚”的宗教观强加给了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头脑里罢了。另外,我们也不能再去说竹内好什么,因为你将要“落入空虚”。
这篇论文的末尾,郜先生这样说:“他只是提出来,自己却躲开,站在作品的一旁,像鲁迅经常所做的那样,站在作品之外没有明言的黑暗里面,让你感到‘不安’。”(第169页)实际上,竹内好是没有那样高的境界的,他自始至终都是在“想象”中对“鲁迅”进行解读的——在某种意义上连郜先生也承认“和常识无论怎样总有距离”,扭曲和捏造之处自然也是避免不了的,并且,竹内好也确乎是在“不安”中匆匆结束了他的工作。
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郜先生也是在这种和竹内好一样的“不安”中又重新回到了“不安”,到底为什么“不安”则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三个疑惑和最大的继承
在第二篇文章《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中,笔者对郜元宝先生西方文论的功底深表佩服。从“疾病的隐喻”(第189页)到“身体化的呈现”(第183页),几乎用得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然而,笔者有三个非常大的疑惑,在此斗胆提出来。
第一个是“小引:鲁迅与中国文学身体诉说的传统”的开头,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和孔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中的两个“身”到底该作何解?难道它们指的都是“肉身”吗?我们也都很清楚“三省”(与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传不习)是什么,它们和肉身的联系紧密吗?而老子的“身”也许更多是强调“欲念”方面吧。
第二个是“《野草》:身体书写的自忏之书”,这个观点实在很新颖,在笔者看来简直不啻于“如雷贯耳”。问题是,鲁迅曾经明确表示过“一个都不宽恕”,这该作何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过度阐释”。
第三个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在对“身体禁忌”的论述中郜先生这样说:“将阿Q式的情欲的愚蠢发动与四铭、高老夫子式的曲意掩饰作为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加以无情地暴露。”(第196—197页)笔者和阿Q一样没有太大的优越感,因此也就很想为他抱不平:世间有哪个人情欲的发动是“不愚蠢”的?为什么就偏偏说我是愚蠢的?窃以为,在关乎情欲方面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愚蠢和明智之区分的。看见 “无情地”这几个字眼,马上就又想起李长之先生的话来:“可是一般人之对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郜先生最后的结论是:“肉体不能离开精神而获得独立的意义,精神也无法出离身体而直接说出自己的话来。鲁迅的文学就这样不断消解着精神与身体任何一方的片面的自足,从而充分验证了现代中国身体和精神在语言中的命定与纠缠。”(第197页)这也许是对竹内好最大的继承吧。
“赎罪文学”不成立
首先必须严正声明,这一小节是在郜元宝先生完全采取竹内好判定鲁迅的“赎罪文学”的基础上来“读《野草》”的,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与竹内好有很大的不同,郜先生认为《野草》是很难懂的,而竹内好曾说过它“比《呐喊》《彷徨》好懂”之类的话。
《读〈野草〉》这篇论文的第二个小标题是“《题辞》所示:忏悔‘过去的生命’”,由此可以看出郜先生是以“赎罪文学”的标准来解读《野草》的。“弥漫于《野草》的怨毒之气有多重指向,由‘过去的生命’而来的‘我的罪过’则是主要的内容。这就暗示着,《野草》首先将是关于‘我的罪过’的一部忏悔之书。”(第203页)更进一步的论述是:“《题辞》预示着《野草》将既是独锁心底的对‘我的罪过’的忏悔,又是针对‘地面’的咒诅”(第205页),“营造一种并不彻底的自我怨怼的忏悔气氛,引逗阅读的兴趣,好比庭院深深,门口一无所陈,唯见烟雾弥漫,诸物掩于其中,神秘莫测”(第205页)。笔者最想说的是:华丽的辞藻遮掩不了空虚的思想。试想,在忏悔的主体和客体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怎么就可以认定有“忏悔”的存在呢?况且郜先生已经界定了一种“宗教”:“无边无际的空虚”。因此,“忏悔”的说法不能成立。
“《野草》的失败感和罪过感,是作者对自己从1907年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直到1920年代中期正式从事文学创作期间近二十年的一连串的失败的体认”(第206页),这活脱脱就是一副“竹内好式的论腔”。郜先生曾经指出竹内好是把作品论和作家论混为一谈了,而现在他自己是不是把这两者也同样地混为一谈了呢?
第四个小标题“‘大阙口’内外的‘游魂’”下写道:“‘过去的生命’既然‘委弃在地面上’,托生为‘野草’,怎么还有一个依然思维着的现在之‘我’跑来讲述过去之‘我’,并为过去之‘我’承担‘罪过’呢?”这也是我们每个读者共同的疑惑,而这个疑惑完全是由竹内好,更是由郜先生自己制造出来的。也许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产物”吧。“托生”和“罪过”是两种不同的信仰,而郜先生硬是要和竹内好一道,让鲁迅或者“鲁迅”来忏悔,真不知他们是什么用意!这又一次证明了忏悔意识不存在,“赎罪文学”不成立。
但,郜先生依然执著:“抓住这个飘荡着的‘游魂’对‘过去的生命’的罪感体验,以及对未来的筹划,是解读《野草》的关键。”(第213页)“所以,‘游魂’不仅‘无心’,也‘无信’。这就暴露了《野草》所潜藏的一个绝大的问题:行动的主体可以‘无心’亦‘无信’吗?‘无心’亦‘无信’的主体义无反顾地投入行动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第219页)“无心和无信”的说法是郜先生自己虚构的,根本没有回答之必要,因为建立在虚构基础之上的论证,最终的结果不过还是“虚构”。
除了“美”之外……
此前曾听说过郜元宝先生的文笔多么好多么迷人,现在是真切地领略了一番。可以肯定地说,郜先生是竹内好忠实的信徒,他和竹内好一样,信奉鲁迅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李冬木译,第44页)。可是当他们开始立论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了这些?竹内好是结构了一个“想象中的鲁迅”,而郜先生则在竹内好的基础上再次“结构”了一个“鲁迅”,并以这个标准来重新解读鲁迅的作品,因此他的解读除了给人以新鲜感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了吧?
同时佩服的是郜先生那极强的“理论自觉”(不得不承认,这是受了他的影响的缘故),能够随时造一些概念性的术语,涵义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吧:“自审意识”、“现代心学”、“中国‘心宅’”、“心学历史”、“‘天地’之境”等等,都是很“美”的词语,除了“美”之外却还真不知道能给我们什么。
另外,笔者对在第184页和第214页出现的几段非常相似的文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认真地比对了一下,也许注意力在“比对”上面,对它们的高妙也终于没有看出个究竟来。那是对《复仇(其二)》的分析,前者是《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后者是《读〈野草〉》,当然它们毕竟是有联系的:都是鲁迅的作品。
最后,后人如此理解鲁迅,实在还不如忘记他更好一些。其实,鲁迅本人最有自知之明倒是真的:“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我的这些文字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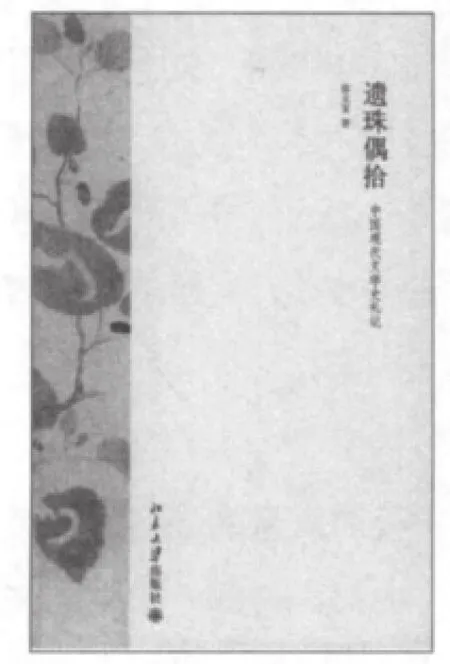
《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郜元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定价:4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