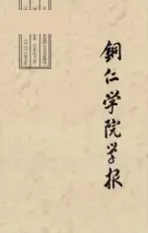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上)
2011-08-15吴国柱
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上)
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被人们称为考证派新红学的“集大成者”,但周先生的红学考证却不是真正考据学意义上的红学考证。真正的考证是视证据为生命,一切从证据出发,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周先生却发明了“悟性考证法”,只讲“悟性”不重“证据”,专做“证据不够的推求”,把那些属于史学范畴的实证问题,强行演化为“见仁见智”的学术是非之争。
考据学; 考证方法; 法官断狱; 学术规范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周汝昌先生似乎是胡适考证派新红学的“集大成”者,是将胡适红学考证成果推向“巅峰”的红学考据大家。然而,周先生的红学考据,究竟是不是真正考据学意义上的红学考据,也还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这就颇有值得议一议的必要。
一
周汝昌先生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考据的代表性著作。这部著作曾经根据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基本框架,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身世、家庭状况、时代背景以及《红楼梦》的版本演变流向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具体考证,为人们提供了较为丰富而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对红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应有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从表面上看,周先生似乎的确不愧为深深洞悉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的红学考据大家。可是,洋洋数十万言的《红楼梦新证》,究竟为我们“考证”清楚了多少重大历史事实,又为我们解决了多少红学中的疑难问题呢?周先生说过:考证的功能很多了,非止一端,大致说来,一是纠谬;二是辨伪;三是决疑;四是息争;五是抉隐;六是阐幽;七是斥妄;八是启智;九是破腐;十是发现![1]
周先生概括出考据学的十大功能,确实是非常精辟的。然而《红楼梦新证》是否真正体现了考据学的这些功能呢?恐怕得打问号。别的不说,单看“息争”一项:所谓“息争”,就是用确切的文献史料证实、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止息人们的争论。就像周先生说的:“考证使人们只以为是‘仁智’的看法不同的错觉,变为正误是非的严格界划,而不容以‘各存己见’来‘相提并论’。”[1]这就是说,考据学以确凿的证据所证实的结论,是就是,非就非,决不是“见仁见智”的“各存己见”,因而丝毫没有争辩的余地。然而《红楼梦新证》出版以来,究竟是从此“止息”了红学中的论争呢,还是挑起了更多、更大、更尖锐的论争?实践证明,周先生的“考证”并非是从此“止息”了红学论争,相反是挑起了更多、更大、更尖锐的论争。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周先生的红学考据,可能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考据学意义上的红学考据。
那么,周先生在红学考据中所运用的“考证方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考证方法”呢?周先生对于传统的考证方法本来是十分明白的。他说过:所谓“考证”,“就是‘考’而‘证’之,不考无从证,得证皆由考”。[1]但是,周先生在其具体的红学考据中,却没有按照这种方法办事,而是加进了自己的“私货”,那就是“悟性”。他说得非常清楚:
考证之事实非容易。它需要学、识、胆、诚、义……而更需要有悟性。[1]
悟性——比“考证”更重要。[1]178
周先生在他的红学考据中,特别强调“悟”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反复说,考证“需要悟力”。又说:“治学不易,要有才、学、识、德、勇、毅、果、静、谦……也要能悟。”而所谓“悟”,指的是“领悟”、“感悟”的能力。正如所言:“悟有顿、渐之分;顿是一见即晓,当下即悟。渐就是涵咏玩味,积功既久,忽一旦开窍,洞彻光明。”[1]172
统而言之,在治学过程中讲求“悟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或不对。例如在“见仁见智”的意义阐释领域,那的确是需要“悟性”的。但这种所谓“悟性”之能否适用于史实还原领域即考据学领域,则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周汝昌先生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将所谓“悟性”广泛运用到他的红学考据中,以至形成他的一种“奇特”的“考证方法”,这就是所谓“悟性考证法”。正如周先生自我总结的那样:他的“考证方法”就是“边证边悟、边悟边考、证中有悟、悟中有考”[2]。周先生的红学考据,基本上就是采用这种“悟性考证法”来解决问题的。例如他“平生在红学上,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就是“脂砚即湘云”,亦即曹雪芹之“续弦妻”。他颇为自豪地说:“这种考证,与其说是靠学识,不如说凭悟性。”又说:“这种考证,只靠死读书、形式逻辑、书本证明……那种常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1]187换言之,所谓“脂砚即湘云”即“雪芹续弦妻”这一结论并非实证的结果,而是全凭“悟性”所“悟”出来的。这不能不说是“悟性考证法”的“特异功能”。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悟性考证法”有时也可能会出现“奇迹”。例如周汝昌先生一再所说的关于“曹荃和曹宣”的“考证”就是如此。早在《红楼梦新证》中,其第二章“人物考”就有“曹宜曹宣”(初版题“迷失了的曹宣”)一节,对曹宜、曹荃二人进行了“推考”。书中说,史载曹寅兄弟二人,弟名曹宜;其实曹宜并非曹寅之弟,而是另有其人。曹寅之弟名荃,字子猷,号筠石,但这“荃”字也非本名(或因音误,或因避讳),因为“寅”字是宝盖部首,“荃”字却不是。那么这曹寅之弟究系何人耶?周先生说:要“考”清此人之真名,“已不仅是学识的事情,就要一点儿悟性了。”[1]180于是他提出三个条件进行“逆推”:第一,曹寅是单名,其弟也应是单名;第二,“寅”字是宝盖头,其弟之名也应是宝盖头;第三,这个宝盖部首的字必须和“猷”字“有经典字句上的关合”。据此,他们很快查出《诗经》中“秉心宣猷”之句来,从而得出结论说:曹寅之弟名“曹宣:字子猷,号筠石。”[3]事后周先生颇为欣喜地总结道:
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秋问世后,受人注目的一个小小“考证”乃是考出曹寅有弟,实名曹宣(而非曹宜)。宣北音犯帝讳“玄”,有同声之嫌,方又改名“荃”。这“宣”的考证先受讥嘲,而后获证实,群以为“佳话”。[4]
直到后来,李华先生发现了康熙本《上元县志》的曹玺传,果然载明长子曹寅,次子曹宣。于是反对、讥讽者闭口,我们的奇特的“考证”胜利了![1]181
从这段“佳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第一,周先生对曹宣的“考证”,所采用的是“逆推”法。他说,这种方法不仅仅只是靠学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悟性”。这就是所谓的“悟性考证法”。第二,“悟性考证法”碰巧也有可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充其量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猜测”,就算“蒙”对一次,也不能证明每次都能“蒙”对。周先生一生从事红学考据,“考”了那么多问题,就只“蒙”对一个曹宣,也不值得特别加以吹嘘和炫耀,因为这“奇特的考证”并非是次次都能“胜利”的。第三,曹宣的“考证”之所以取得“胜利”,全在于最后发现了《上元县志》曹玺传的史料记载。如果没有“曹玺传”的发现,周先生的“考证”结论就只能永远是“猜测”。由此可见,“考证”的结论终究还是需要用可靠的文献史料和事实来证明的,没有取得文献史料的力证,任何凭借“悟性”而得出的结论都不能算作定论。那么要“反对、讥讽者闭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证据来”,而不是炫耀自己的“悟性”功夫。在学术考据中,绝对不能随便提倡“悟性考证法”,相反应该拒绝“悟性”。
二
已有学者严肃指出:考证全凭证据,不需悟性。然而周汝昌先生却不以为然,奚落说“将‘证’与‘悟’对立起来是个治学史上的笑话”。[2]281他讥讽道:
其实,“考证”包涵了学、识、悟多个层次方面的研究进程,三者互相渗透,缺一不可。听说有位史料工作者公然向学界宣称:史学靠证据,不靠悟性,云云。这种话让真正的史学家听了,只好窃为解颐。[4]75
史学靠证据,不靠悟性,就管见所及,这话很可能是张书才先生说的。张书才先生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是一位长期从事历史考据工作的资深专家。他根据自己的学术实践和深切体验,在批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考证不是靠‘悟’,而是靠证据”的观点,[5]实在是一位诚挚的史学工作者深谙考据学规范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我也曾拜读过张先生的几篇红学考据文章,认为他论证问题时全凭史实说话,给人一种极为厚重的历史感,令人心悦诚服。然而阅读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据著作,其感受就大不相同了。周先生的红学考据,大抵属于“随笔”性质,不讲求可靠的文献根据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凭借“悟性”的翅膀,纵横翱翔,驰骋想象,犹如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虽让人感到五光十色,眼花缭乱,而最终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大概就是周先生执意推崇“悟性考证法”的必然结果吧。
最近一个时期,主流红学家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就是讲究“学术规范”。“考据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究竟有无“学术规范”可言?换句话说,作为史学范畴的“考据学”,究竟是应该讲究“实证”呢或是讲究“悟性”?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极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
什么是“考据”?《辞海》解释说:“考证即考据”。所谓“考证”,乃是“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蒐集整理”。《辞源》解释说:“考证”就是“根据文献资料核实说明”,“考证也称考据。指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而“考据之法,大致以校勘厘正本文,以训诂贯通字义,以积累资料供研究的应用”等。由此可知,“考证”的核心内容就是根据可靠的史料和确凿的事实来证明命题。而“考证”的方法则主要是指训诂、校勘和资料蒐集之类。对于“考据学”来说,最关键的是证据,而不是其他。
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论述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风”时,曾概括出“朴学”的十大特色,其前四条就是:“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6]这四条的核心问题,就是讲求“证据”,可以说也正是考据学的精髓所在。梁启超在总结乾嘉考据学兴衰的经验教训时,还深刻指出“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6]64其所说的“实”字,主要就是指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证据确凿可靠的“务实”、“求实”精神,有它则盛,无它则衰。由此可知“证据”在考据学中的极端重要性。
新红学的开山宗师胡适先生,尽管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主要采用西方自然科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并不完全符合传统考据学的规范,因而其考证结论也就并不完全科学。但是,他在探讨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和治学特点时,却对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有过大量极其深刻而精辟的阐述。胡适对考据学的论述,大致有三个要点:
第一,胡适着重指出,考据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全靠证据说话。他说得非常清楚:“考证的方法是立一说,必有证据”;又说:“考一物,立一说,究一字,全要有证据,就是考证,也可以说是证据,必须有证据,然后才可以相信。”[7]他的名言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7]304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态度,这“科学态度”就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8]他还说,他作《红楼梦考证》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8]118当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客观上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是否做到了“处处让证据说话”,是另一回事;但他主观上却是想尽一切办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种治学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说明他很重视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第二,胡适明确提出,学术考据与法官断狱具有同样性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治学原理。他曾尖锐地指出:“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应该相同。”又说:“做考证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务有法官断狱同样的严重,他的方法也必须有法官断狱同样的谨严,同样的审慎。”[7]280-284我们知道,古代的考据法实际上是源自法官断案的证据法。把学术考据与法官断狱联系起来思考,等同视之,是我国古代学者的一种传统治学思想,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一条重要治学原则。从表面上看,学术考据与法官决狱似乎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一个是“治学”,读书人的笔墨纵横;一个是断案,事关人的身家性命。但实际上二者从责任到方法都是完全相通的,即都用证据说话。所以胡适反复强调:“考证学在今日还应该充分参考法庭判案的证据法”,“把考证书传讹谬和判断疑难狱讼看作同一样的本领,同样的用证据来断定了一件过去的事实的是非真伪。”[7]282法官断狱靠的是证据,即所谓人证物证俱在,方可量罪定刑;学术考证同样靠证据,即所谓内证外证或本证旁证具备,才可做出结论,断定事物的有无、真伪和是非。可见证据不仅是法官断狱的生命,也是学术考据的生命。
第三,胡适一再强调,考据家必须严于律己,自觉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干性,做到证据的确凿可靠。胡适非常清楚,法官断狱,由于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明白自己的责任,弄不好就有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可能,所以特别注重证据的翔实、准确和可靠,对证据的调查与核实取绝对“敬慎”的态度。文人就不同了。学者治学,自以为无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往往容易忽略证据,出现“信口开河”的弊病。所以他批评说:“文人做历史考据,往往没有这种敬慎的态度,往往不肯把是非真伪的考证看作朱子说的‘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因为文人看轻考据的责任,所以他们往往不能严格地审查证据,也往往不能敬慎地运用证据。证据不能敬慎的使用,则结论往往和证据不相干。这种考据,尽管堆上百十条所谓‘证据’,只是全无价值的考据。”胡适认为,“考证方法所以远不如法官断案的谨严,主要原因正在缺乏一个自觉的驳斥自己的标准”。有鉴于此,他大声疾呼:“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要问,我提出的证人证物本身可靠吗?这个证人有作证的资格吗?这件证物本身没有问题吗?第二要问,我提出这个证据的目的是要证明本题的哪一点?这个证据足够证明那一点吗?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干性。”因此,考据学家首先必须严格驳问自己,自觉排除“假证据和不相干的证据”,努力使自己提出的证据真实、确凿和可靠,这样“才能担负为千秋百世考订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大责任”。[7]285
从以上三个方面不难看出,胡适对考据学的“学术规范”了如指掌,相当推崇。尽管他的《红楼梦考证》未曾严格按照考据学的规范办事,但他要求人们做学问随时不忘“拿证据来”四个字,并把这四个字当作“小小法宝”和“防身工具”赠送给自己的学生,[7]28足见其对证据的重要性是何等重视的了。
三
我们在上面花去不少篇幅,观察国学大师们对于考证方法的论述,目的无非是想说明:证据是考据学的生命。所谓“考据”,其实也就是考察证据;无证据即无所谓考据。胡适还说过:“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用材料”的方法。其所用的材料“始终是文字的”,而“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因此“考证家若没有证据,便无从做考证;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7]217而“顿悟”的方法,绝非考证的方法。胡适就说过:“禅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顿悟”[7]167可见“悟性”是“禅宗的方法”,而不是史家的方法。然而号称胡适的“好徒弟”的“红学考据家”周汝昌先生,却竭力倡导“悟性考证法”,这无疑是对考据学方法的背离。周先生在他的红学考据中,不讲求证据的重要性,更未曾自觉地驳问过自己所凭“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干性;而是运用“悟性”对那些不确切的历史材料进行想象、加工和发挥,引申出一些荒唐的虚无缥缈的结论,让读者深受其害。我们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例一:周先生的“高鹗伪续论”没有实证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红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有人说它是“一无足观”,“令人见之欲呕”;当然,认为它写得相当优秀,出色完成了伟大的悲剧结构者,也大有人在。这些“见仁见智”的审美评判,都属于正常现象。天地间任何事物莫不如此,有人说好的东西必然有人说坏,有人喜欢的东西也必然有人讨厌。任何人都可以赞赏后四十回,认为它“好得很”,是《红楼梦》有机艺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任何人也都可以鄙视后四十回,认为它“糟透了”,不屑一顾,这是各人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人说后四十回因为它是“高鹗续书”,所以才是“臭狗屎”,这就超出“见仁见智”的范围了。道理很简单,后四十回是否“高鹗续书”,这已经不属于意义阐释的范畴,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还原问题。换言之,确指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书”,根本不是什么“一般认为”的问题,而是要像胡适所说“拿证据来”加以证实的问题。所谓“一般认为”是绝对没有作证资格的。
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从胡适确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无论是胡适的“考证”,还是其“集大成者”周汝昌的“新证”,都未曾提出过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证实,其惟一依据不过就是张船山诗注的一个模棱两可的“补”字,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持否定意见者必然越来越多。然而作为“红学考据家”的周汝昌先生,几十年来不仅从来不去认真审查该说所持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干性,反而在“一般认为”的基础上强行上纲上线,迅速升级到“高鹗伪续论”的高度,硬说后四十回是乾隆指派和珅“重金延请”程伟元、高鹗“删改抽撤”之后又进行“伪续”的结果。他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长文中所提出的主要“证据”,就是赵烈文《能静居笔记》的一条记载:
竭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据《献芹集》第 411页所引,中华书局2006年新版)
这条记载于同治九年(1870)的传闻,能证明后四十回为乾隆指派和珅“重金延请”程伟元、高鹗“伪续”的吗?宋翔凤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程甲本出版时(1791)才十几岁,他亲眼见到过和珅操办此事吗?对于这种根本不具备“证据”资格的道听途说,周先生却津津乐道,敢于在这种完全靠不住的小道消息上建构自己的“高鹗伪续论”,并吹嘘是他的“奇特考证方法”即所谓“悟性考证法”所创造的“奇迹”之一。他在《考证之乐》中颇为得意地写道:
原来,《能静居笔记》同治九年一条,记载亲闻老学者宋翔凤言说《红楼梦》是乾隆末年和珅“呈上”的,我立即想到:和珅就是那位“名公巨卿”无疑了,其时绝无第二位能向乾隆呈上一部小说——那是他主持《四库全书》时为了篡改有“妨碍”的一切古书今作而出的坏主意:抽、撤、换、改、销毁等手段中的一招,伪续四十回是阴谋(也偷改前八十回原文)。所以“全本”一出,士大夫“家置一部”,天下风行——是官方的事啊![1]183
这就是周先生从《能静居笔记》中“引出”的“一悟”。他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中剖析这个问题时,曾反复使用“悟出”、“领到”、“想来”、“推断”等词儿,展开丰富的联想,左右逢源,终于“悟”得程本《红楼梦》的出版,乃是乾隆与和珅玩弄的“偷天换日”的“政治阴谋”。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如果法官都按照这种“捕风捉影”的方式断案,岂有不制造冤假错案之理?而周汝昌先生的所谓“高鹗伪续论”,恰恰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全靠“悟性”凭空捏造出来的!
例二:周先生的“脂砚湘云说”没有实证
自从20世纪20年代脂砚斋亮相红坛以来,一直是人们追逐的热点和时尚。胡适首先提出“大胆的假设”: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大概”是“堂兄弟”之类“亲友”。[8]164当然,胡适的考证用词谨慎,他反复使用了“也许”、“大概”、“疑心”等等字眼,说明他不敢妄下结论。但周汝昌接过胡适的“脂砚至亲”说,却将其坐实为作品中的史湘云,曹雪芹的“亲表妹”——李煦的孙女儿“李枕霞”,亦即曹雪芹的所谓“续弦妻”,在红学史上真可谓“独树一帜”。早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周先生就通过脂批“余二人”、“一芹一脂”等称谓,玩味出脂砚斋和曹雪芹有着“不即不离,似一似二的微妙的关系”,只有脂砚斋“是一个女性,一切才能讲得通”。于是他找来一条脂批作证:
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庚辰本第二十六回朱侧)
这条批语,本来就是脂砚斋的“自作多情”,或者说“调侃”、“玩笑”之语,当不得真;而周先生却信以为真,说脂砚斋“自居女性”,“以爱人、妻子的关系相比”,其中的“老货”是特指“女人”的。但这条批语能证明脂砚斋是个“女人”吗?胡文彬先生已经指出,在《红楼梦》文本中,“老货”既有称“老妇人”的,也有称“老男人”的,[9]足见“老货”特指“女人”之说不确。
更妙的是周先生对“脂砚斋”与“畸笏叟”为一人的“考证”。他在《红楼梦新证》中就曾提出:“畸笏之人,恐怕还就是这位脂砚,不过是从庚辰以后,他又采用了这个新别署罢了”。而在《和贾宝玉对话》、《红楼夺目红》等著作中,则对“脂砚斋就是畸笏叟”这个命题做出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说:
脂砚是个女的,时至中年,自谓年岁已大,不复少女年华,人们也就以嫂待之,叫他脂砚“嫂”。等到他批书,却怕惹出是非,连累雪芹,就不愿让人晓知是女,故将“嫂”字去了女子旁,自号为“叟”以为笑乐。
脂砚是个性情朗爽,爱说爱笑的人,她开小玩笑,常逗人乐。大家称她嫂,他就顺水推舟,说,是呀,我几乎要成“老爷子”了!逗得众人都笑——于是她就编出一个“畸笏”来,其实是“几(ji)乎”的谐音。[10]
笏,是砚形的代称变词……这古砚就变称为“笏”了。
畸(ji),是脂(zhi)的音转。“咬舌子”“大舌头”如幼儿,不会说“脂”“支”“知”,只会说成ji——“不机道”,“一机铅笔”……皆 zhi、ji的“纠结”也。
这证明脂砚是个“咬舌子”,自己读为“机砚”——然后才换“砚”为“笏”,为的是搭配词义而已。
总之,畸笏还是脂砚,名变人未变。[11]
在周先生的意念中,“畸”即“脂”,“笏”即“砚”,“叟”即“嫂”(所谓“女叟”是也),故“畸笏叟”即是“脂砚嫂”的“变称”。按照此等“思悟”,我们同样可以说脂砚斋(史湘云)是“老广”。有一则笑话说:有位广东老板对一个青年说:“你到我公司来,我每月给你两千工资。”青年懵了,回答说:“你每月给我两千公鸡,我怎么养啊!”原来“广普”说“工资”为“公鸡”,“资”“鸡”不分。这岂不可以“证明”操“广普”的史湘云(脂砚斋)是“老广”吗?这当然是玩笑,不过也可以略见周先生的“考证”是何等随心所欲,是怎样在“编故事”。
脂砚斋究竟是谁?周先生说:“有人说他是雪芹自作自批;有人说是雪芹的‘舅舅’;有人说是‘兄弟’;有人说是‘叔叔’……这都是揣测、猜度,并无实据,所举理由也很稚弱甚至滑稽”,[1]184而且全是“笑话,神话,梦话,糊涂话……因各人都有信口开河的权利”。[11]292周先生批得极对,什么“叔叔”、“舅舅”、“兄弟”、“自己”……,的确全部都是“信口开河”,都是“揣测,猜度,并无实据”。那么周先生为何不反问一下自己:你自诩为“平生最得意”的“凭悟性”得出的“脂砚即湘云”即“雪芹续弦妻”的结论,不同样是“揣测、猜度,并无实据”,同样是“笑话,神话,梦话,糊涂话”,其“所举理由”不也同样“很稚弱甚至滑稽”吗?
例三:周先生的“脂本真本观”没有实证
现今可见的所谓“脂本”,几乎都是民国时期及其以后才陆续出现的。我们当然不能说,脂本的出现时间较晚,其形成时间也必然较晚。但是,脂本出现以后被红学专家确指为曹雪芹的“原本”和《红楼梦》的“真本”,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证问题,是需要“拿证据来”加以证实的。作为红学考据家的周汝昌先生,当然明白古籍版本(特别是手抄本)鉴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然为什么会撰著《石头记鉴真》呢?就以《石头记鉴真》[12]为例,其“鉴定”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三:第一,“三真本”的“先后次序”是:“《甲戌》的形式最早,《庚辰》已在稍后,而《戚序》……形成时间居最后”。第二,甲戌本是“雪芹、脂砚二人共同经营,到乾隆十九年甲戌,已经成就了一个定本,如现今尚残存的十六回所示的那样。”第三,“《甲戌本》之可靠与可宝,因为它是芹、脂自己的定本。《庚辰本》之不可尽信,更不可迷信,是因为它是经过别人妄加改动的一个本子”。以上三点结论归结为一句话:甲戌本“最真实”,其“文字是原始的,是雪芹初稿”,为“芹、脂自己的定本”,也是“一部珍贵异常的乾隆旧抄本”。
问题不在于这个结论本身如何,而在于用什么证据来证实这个结论。胡适曾说:“我提出了一个假设的结论:依甲戌本与庚辰本的款式看来,凡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8]297胡适说得明白,他的这个“假设的结论”是从脂本的“款式”上“看出来”的,并未获得文献史料的力证。而脂本是否“乾隆旧抄”,是否“曹雪芹原稿本的过录本”,本身就是一个严格的版本鉴定问题。在当今主流红学家中,惟有刘世德先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现存的各种《红楼梦》早期抄本,无论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还是彼本、蒙本,本身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杨本的两个影印本的书名,都题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那“乾隆抄本”四字,只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个别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支持。[13]
既然脂本本身没有抄写时间的可靠证据,那么周汝昌先生又是如何进行“版本鉴定”的呢?他在《石头记鉴真》中主要采取三种途径:首先是文字鉴定。他说得明白:“我们的目的是鉴真,鉴真的核心是文字,文字指的是文笔的是非高下。”不难理解,所谓“文笔的是非高下”,乃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无客观标准,根本不能构成“脂本真本论”的确证。其次是脂批鉴定。他说:“读书考鉴素重题跋”,而“《石头记》也有一种极为重要的题跋——这就是脂砚斋的批语。”将脂批当作“题跋”使用,可说是周先生的“独创”。但尽人皆知,脂批是一个历经不同时代、不同人士之手而拼凑起来的大杂烩,真正称得上“来路不明,面目不清”!就连批者的真实身份都无法落实,他的批语就像“匿名信”一样,有作证的资格吗?再次是笔迹鉴定。周先生罗列出甲戌本上不少“异体字”(实际上大都是低水平抄手书写的错别字),认为这种“特殊写法”就是乾隆时代的所谓“太监体”(即所谓“乾隆字”),它绝对“忠于原著”,是“从原稿本清抄录副的”;这种抄手“不会擅改一笔一划,不用说妄改一字一句了”。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曹雪芹的“原稿本”也就必然跟甲戌本一模一样,通篇错别字,这谁会相信呢?总之,周先生“鉴”甲戌本之“真”,实在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证据,他从头至尾靠“悟性”进行主观臆测,并在这个基础上强行循环论证,从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种结论,显然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以上所举三例,主要是用来观察周汝昌先生红学考据的基本状况。因为这三个问题,不仅都是周汝昌红学思想的“命脉”问题,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实证”问题。考据家面对这类实证问题,只能像法官决狱那样,必须拿出确凿无疑的可靠证据来才能定案。正如胡适所说,“考证学的正路是多寻求证据,多寻求最直接的,最早的证据”;而“证据不够的推求”则“不是考证学的正路”。[14]此乃是考据学的基本规范。但周先生却未严格按照考据学的规范办事,不仅没有出示有效的证据,反而运用他创造的所谓“悟性考证法”,专做“证据不够的推求”,把那些属于史学范畴的实证问题,强行演化为“见仁见智”的学术是非之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1]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179.
[2] 周汝昌.红楼别样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281.
[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5.
[4] 周汝昌.解味红楼周汝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73.
[5] 张书才.是谁误解了红楼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15.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4.
[7] 胡适.读书与治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57.
[8]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94.
[9] 胡文彬.读遍红楼[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62.
[10] 周汝昌.和贾宝玉对话[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84.
[11]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93.
[12] 周汝昌.石头记鉴真[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3] 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4.
[14] 朱洪.胡适与红楼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210.
Zhou Ruchang and Redology (VolumeⅠ)
WU Guo-zhu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an 650031, China )
Zhou Ruchang is known as “master” of school of textual research on new redology. However, Mr Zhou’s research does not belong to a real textual research on redology according to the textology meaning. The exact textual research focuses on evidence. It draws scientific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demonstration. While Mr Zhou proposed a “perception research method” which focuses on “perception” rather than “evidence”, and inferred without enough evidence, which forces the historical empirical problems develop to be an academic matter of “opinions differ”.
textology;textual research method;settle a lawsuit;academic standards
(责任编辑 朱存红)
I20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3-9639 (2011) 03-0029-07
2010-07-15
吴国柱(1936-),男,重庆市铜梁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高级教师,业余从事红学研究,曾发表红学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