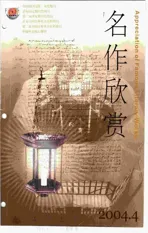复仇(节选)
2011-08-15重庆巴一
/[重庆]巴一
复仇(节选)
/[重庆]巴一
一九七七年,于天成十九岁,他的弟弟于天良九岁。天成刚刚初中毕业,天良正读小学三年级。
八月的一天下午,雨下得很大,当于天成淋得浑身湿透从学校跑回家时,突然看到母亲和弟弟正在他家门前的红芋地里逮猪呢。天成知道他家的猪又拱圈跑出来了,便急忙追了上去。
“天成,快来抓住它!它把生产队里的红芋趟得不像样子了!”母亲气喘吁吁,见天成赶了过来,才停下脚步擦着满脸的汗水和雨水。
于天成一个箭步冲上去,俯身一把抓住了猪腿。这百十斤的猪拉在天成手里,前爪连着地,“哇哇”地刺耳大叫着被拽到了堂屋里。天成娘赶忙从屋门后找来细麻绳,在左腿上紧紧地系上。“不行不行,这样会把猪腿勒肿的!”天成大声对他母亲喊着,任嗷嗷直叫的猪在他们兄弟俩手里挣扎。天成娘又急忙把系成死疙瘩的麻绳解开,在堂屋的床底下抓出一块破布来,缠在猪腿上,然后再将麻绳系在破布上,死死扎上,说:“天成,松手吧。”天成、天良都松了手。天成娘紧拽着手中的绳子,无论喘着粗气的猪怎么挣,也是不会跑掉了。他们兄弟都笑了。天成娘也笑了,说:“你们俩赶快在门外洗洗手,把衣服都换了吧。”她把绳子的这头系在屋门头的木栓上。
回到屋里,天成娘来不及擦手,就急着给天良脱衣服,并找来干衣裳给天良穿上。她还没顾得上天成,就听天成“哇”一声大哭起来。他从兜里掏出被粘成糨糊般的纸末子叫道:“娘,我的通知书没有了!”天成娘急忙抓着他手里的纸末子说:“这是啥?这是啥?”天成急得跺着脚说:“这是通知书,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娘。”天成娘连连“哎哟”着,无可奈何地把碎末子凑到一块,呆呆望着唉叹着:“这可咋办哩?这可咋办哩……”
天成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摊水渍慢慢浸湿开来。
弟弟天良说:“哭啥哭,明天再到学校补一个就是了。”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天成娘。她蹲下来,安慰儿子说:“对,明天再去要一张。咱是自己考上的怕啥,学校肯定有底根儿的。明天娘去学校给你要。别哭了,赶快换衣服吧。”天成娘爱抚地给大儿子解着扣子,鼓励儿子说:“要不是你回来,俺跟你弟弟到天黑也追不上猪。好了,猪也逮住了,等过年的时候够磅重了,卖了就够你们兄弟俩的学费了。”于天成不哭了,站起身,遗憾地叹息着回里屋换衣服去了。
天色黑尽的时候,雨停了。凉凉的晚风吹过,屋前的田地里传来细微的响声。大片葱绿的红芋叶子摇摆着,抖动着晶莹的水珠儿,绵绵的红芋藤蔓盎然地翘动着稚嫩的芽须,如饥似渴般等待长大。收获红芋的季节要在农历八月间,眼下七月初,正是红芋长出淀粉的时候,可眼前这片的红芋,被踏踩得一塌糊涂。有的红芋藤蔓被踩断,冒着白色的汁液;有的红芋藤蔓被踩得露出根须来,哪能结得出红芋?这可是全生产队的口粮啊!
天成娘看在眼里,心疼地蹲下身来,一个个扶起被踩坏的红芋秧。她担心着明天一大早被生产队里的人看见了。挨骂挨打不算,她们家肯定要赔生产队的损失的啊!说不定,生产队长还会把她家这头猪也要牵走作为赔偿哩……天成娘嘤嘤地哭了。她越想越感到后怕。她气这头该死的猪不该跑出来,她后悔只顾撵猪而忽略了脚下的庄稼。想着想着,她想到了她的丈夫于自海。
她比丈夫小三岁。她今年整整三十九岁,于自海今年四十二岁。她和他结婚那年她才十八岁。当年嫁来于围子村时,老老小小都夸于自海有艳福,找了个虽不识字但却俊秀得出众的好媳妇。于自海是个初中生,字也写得好,一直是生产队里的记工员。有了两个孩子后的于自海,便被区政府抽到县兽医站学兽医去了。对村人们而言,能在县里学兽医就是有了铁饭碗。给生产队里的马、牛治病,给猪治病,村人们都尊称他为“先生”的。一晃几年过去了,于自海学会了给牲畜治病的技术,也吃上了“商品粮”,可恰恰没有分配到他们村所在的兽医站,偏偏分到了离他们家三十几华里的另一个区兽医站。
这样一来,于自海便不能经常回于围子村家里照顾老婆和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天成娘既当娘又当爹,家务活地里活,全包揽在她一个人肩上。白天,她要忙着挣工分,中午和晚上她又要给两个儿子洗衣做饭,唯恐耽误了孩子的学习。仅有的三分四厘的自留地里,天成娘种的萝卜白菜大葱,也十分茂盛,这已足够他们娘儿仨改善生活了。另外还喂了一头猪,省吃俭用下来的几块钱除了给孩子买些作业本子,三角板之类的用品,就买些盐巴,还给那头猪买些麸皮、豆饼之类的精饲料。天成娘想得明白,给孩子上学买用具也好,给他家的猪买饲料也罢,都是“零攒钱”,总有一天都会收回来的。日子虽然过得不如有的人家,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要两个孩子学习好,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
唯一让她失落和遗憾的,便是遇到阴雨天。别的一家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而唯有她一个人在屋里转来转去,空旷寂寞,徒生惆怅,有时还衍生出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来:如果有个男人在身边说说话儿,该多好啊。丈夫于自海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呆不了三两天又走了,让她刚刚燃起的美妙一下又变成了失落。有几次夜里,她望着两个熟睡的儿子,焦盼着的心情折磨得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叹息着: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啊……
眼下,又遇到了这件事,明天一大早上工的社员见了这么多红芋被践踏,肯定会惹来大祸。如果丈夫于自海在身边,也就有了依靠,可偏偏他又不在家,该怎么办呢?
天成娘满怀心思地给孩子蒸红苕面饼子,愁眉不展的她只顾拉风箱,往灶膛里填柴火了,以至于锅被烧得干焦,冒着青烟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天成娘朦朦胧胧中,就听到窗外的红芋地里一片嚷嚷声。她一骨碌爬起来,让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谁不讲良心毁坏大家的粮食?”
“瞧瞧吧,这鲜水水的红芋都被踩毁了。”
“叫他赔偿!咱生产队里的人都去他家吃饭去!”
你一言我一语的愤怒里,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谩骂。天成娘心里一阵比一阵难受。可当她走进人堆里的时候,面对这一双双凶神恶煞的眼睛,她没勇气承认是她家的猪糟蹋的。她心里想,只要她不承认这件事,又没哪个人看见,瞎吵吵一晌午就过去了。
突然有一个说:“赶快报告队长去,这事得追查到底。不管它是咱们生产队里的猪还是外生产队里的猪,非抓住它杀了不可!”
几个人附和着,一会儿把生产队长于庆喊来了。
四十岁出头的于庆,人高马大,体魄健壮,扛粮食布袋,一人顶得上两个三个。这个人性子粗野、暴躁,所以在生产队里说一不二,再加上他大哥是区政府的副区长,别说本生产队里人怕他,就连全村的人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于庆仗着他大哥的威风,在村子里算得上个头面人物。无论哪家和邻里闹了矛盾,只要于庆出面说和,就百事大吉了。如果哪家不听劝阻,于庆的两个大眼珠子一瞪,说两句威胁你的话就让你听得做噩梦。
有一年,邻村的几个小青年偷了于庆生产队里的几棵大白菜,根据线索抓到他们以后,于庆硬是用绳吊着那几个小青年的脚脖子,挂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其中有一个小青年被打得吐血住院后,他们家人到乡里告状,不但没告赢,自留地里的庄稼反而在夜里全被偷个精光。
因此,于围子村男女老少,都对于庆既畏惧又恨之入骨。
天成娘看到生产队长于庆在红芋地里察看猪蹄印,禁不住全身哆嗦起来。
快吃早饭的时候,于庆通知全村生产队社员开会。一家来一个人,任何一家都不准缺席。
天成娘给天成、天良兄弟俩一人一个红芋片子馍,催促他们去学校。她一个人急忙来到杨树下的“会场”,等待着队长于庆发号施令。
于庆先是就生产队里的红芋地遭破坏一事给大家作了个“通报”,之后,要每家人“坦白交待”。每家每户的人都表了态,声明不是自家的猪造成的。轮到天成娘表态的时候,天成娘两腮通红,心里狂跳着,结结巴巴地说:“这事绝对跟俺家没关系。”
于庆看着她不自然的表情,再三追问她:“到底是不是你们家的猪吃的?”天成娘抬起头发誓说:“要是俺家的猪吃的话,天打五雷轰不冤枉!”天成娘心想,你是问谁家的猪吃的,俺家的猪是撒野没拴好才跑进去的,又不是故意的,所以发个“毒誓言”、“赌咒”也骂不到俺自己。
争论了很久,议论了很久,也没查出到底是谁家的猪惹的祸。于庆急了,他拍着大腿说:“日他浪娘,我不信查不出来!明天晌午扎个草人子,全队里的人都来浇水,非咒得他家里死绝死光不可!”
于庆这一招可真够狠毒的。在农村,“草人子”便是指用稻草扎成的有胳膊有腿的人的虚拟形体。头部用一个葫芦瓢安在上边,画上鼻子眼睛和嘴巴。肚子部位扎着一把刀子,绑在树上。到了中午太阳最火烫的时辰,男人们女人们轮流对着“草人子”骂,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谩骂指向那个做坏事的人。每当路人见到“草人子”被刀子扎得龇牙咧嘴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天成娘听到了于庆明天就要扎“草人子”,心里比吃了苍蝇都恶心。她浑身发痒,两眼发黑,脑子要爆炸一样痛不欲生。
“俺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平平安安地让他们长大成人,千万不能遭别人的诅咒。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俺这做娘的死也不咽气啊……”天成娘独坐在堂屋里,泪水婆娑地自言自语着。想来思去,她决定今晚就去找队长于庆求情,干脆自己承认算了。她把两个儿子安顿好,披了件衣服往外走去。
刚出屋前,她便一眼望见了于庆挑着尿罐子往自己家的菜地里“呼扇呼扇”地走着。
“于庆大哥,你去菜地呀?”天成娘笑着,主动跟于庆搭讪道:“俺这正想上你家找你哩。”
于庆一看是天成娘,放下钩担挑子便走了过来,嬉皮笑脸地问:“天都昏黑了,找俺有啥好事?是不是于自海没在家,你想痒痒啦?”
天成娘和于庆是平辈的,平常大伙在一起时也经常开开荤玩笑。
“于庆大哥,俺找你真有正事。”天成娘没有在意他的荤笑话,有些为难地说。
“啥正事啊?”于庆板起脸来,压低着嗓门问。
天成娘一五一十地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给于庆说了。于庆故作惊讶并有些为难地说:“兄弟媳妇呀,这事咋不早说呢?今上午我都把扎草人子的事在会上说了,你说叫我咋办呢?”他抱着两个胳膊,在地上转着圈儿。
天成娘哭着说:“于庆大哥,你是队长,啥事还不是你说了算?俺俩小孩都还小,东一咒西一咒的,万一有个好歹,俺这做娘的还咋活呢?”
天成娘又嘤嘤地哭起来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天都黑透了,回去明天再说吧。”于庆看着她伤心痛苦的样子,就没再说吓唬的话了,两个眼闪动着邪恶的淫光说:“我要是帮你这个忙,你该怎么样谢我?”
天成娘擦着眼泪说:“你说咋谢都行,要我给你下跪都行。”说着,她马上准备下跪。于庆一把拉住了,说:“算了算了。你让我想想办法,明天咋给社员们解释。”
“于庆大哥,俺们全家人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以后等天成他爹回来了,一定请你喝两盅。”天成娘的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轻松起来,对于庆答应帮忙的事感激涕零得词不达意了。
果然,第二天,生产队里没有扎“草人子”,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提这件事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天成娘吃完饭,正在厨房里洗碗刷锅,于庆提着几个大白萝卜走了进来。天成娘一看是于庆,急忙走出来了。
“是于庆大哥啊,你怎么有空过来了?”说着,天成娘忙迎他往堂屋里坐。
“我从菜地里回来,顺便串个门。”于庆拎着白萝卜放在屋门口说:“弟媳妇,你看俺家的萝卜大不大?”
“哎哟,这真够大的,你看多水灵!”天成娘从地上拎起白萝卜,端详着,恭维着于庆。
于庆满脸的兴奋。
“你们的小孩呢?”于庆环视了一下,关心地问。
“大儿子去镇上读高中了,住在学校,到星期六才回来一次;二儿子一丢饭碗就去上学了。”天成娘一边唠叨着一边拿着白瓷碗给于庆倒水喝。
于庆坐板凳上,眼睛上下打量着忙来忙去的天成娘。
天成娘也坐在了他对面的板凳上,说:“于大哥,俺真不知道咋感谢你才好。上回那个事多亏你帮忙。”
于庆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女人,贪婪的笑容里埋藏着阴险。
“兄弟媳妇,你说你该咋谢我呀?”于庆说。
“谢谢,真谢谢你啦于庆大哥。”天成娘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表达由衷的感谢。
“兄弟媳妇,我就直说吧。你要是真想谢我,那就趁小孩都没在家,咱俩睡一觉吧。”说着,于庆向天成娘这边走过来。
天成娘一下子脸色吓得焦黄,连忙说:“于庆大哥,你是俺孩子他爹的大哥,也是俺的大哥,你,千万使不得!”
“自海又没在家,怕啥,就这一回!”于庆两手把门合上,扑上前去,捂住她的嘴巴把她抱到了东屋的大床上……
天,不知不觉间已经亮了。
车厢里一个个离开铺位的旅客急于去厕所,殊不知厕所的门口早已排成了长队。就连肩上搭着毛巾急着洗漱的人也只好又回到铺位上。上铺和中铺的乘客见过道里特别拥挤,抬着头,侧着身子,往厕所的方向张望着。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
陷入往事回忆中的于天成,这时才记起自己一夜都没合眼了。
他不想睡。站在窗前,他的眼睛张望着窗外推车售货员忙碌的身影,心里却被一连串的“假如”二字否定着过去的一切。
假如他的母亲在众人面前承认了是自己家的猪惹的祸,又能怎么样呢?扣她的工分?赔偿所有红芋的损失又能值多少钱呢?
假如他的母亲不去找队长于庆求情,任他在树上扎“草人子”,又能怎么样呢?他真的能把我和弟弟“咒”死吗?迷信,那是封建迷信呐!母亲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你怎么没想到找我商量,或者去找父亲商量呢?
……火车又开动了。
于天成的心被一个又一个的“假如”折磨得阵阵灼痛,但是,事情发展的后果,都是于天成不堪回首的啊……
第二年三月的一天,队长于庆组织生产队里的妇女,都去村南边麦地里薅草。傍晚时分,收工后的妇女们挎着满满粪箕子的草去称重量。
轮到天成娘称重的时候,于庆悄悄地对她说:“今晚上留个门,我上你那去。”天成娘一脸的愤恨,看也没看他一眼,把草倒掉就走了。
自从那次被于庆强行奸污以后,她变得心事重重起来。每晚天不黑就关门,就怕于庆说不定哪天再闯进来。晌午,她没事就往菜地里去。如果老远看见了于庆走这条路,她会折回身走另一条路。
丈夫于自海有时回来,往往做完了那个事后便呼呼大睡,她便一个人静静地躺着,仍在为于庆强奸她那一时刻心惊肉跳。她在心里一直骂他:狗日的于庆你也太欺负人了!可是,这些事只有她一个人埋在心底,她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跟她的丈夫说。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于庆今日又向她提出了这件事。吃了晚饭,她把小儿子床铺铺好,把门板插好,吹灯睡了。大半夜的时候,她听见窗棂在砰砰地响。她忽地坐起身来,几乎是屏着呼吸在静听着响声。她心里知道,这肯定是于庆来了。
“砰砰。”窗棂又在发出响声。她就是不吭声,两眼盯紧窗棂口,全身吓得每个细胞都抽搐着。
“兄弟媳妇——”于庆的声音轻微而拖着长腔。
天成娘很想把睡在西间的儿子叫醒,可她的两腿像灌铅似的,在床上的被窝里一动不动。
“兄弟媳妇——”于庆又在窗外喊。
天成娘的喉咙里像塞了东西似的,连一声咳嗽都冒不出来。好半天,她才鼓足勇气挤出声来:“你快滚!俺睡下了。”她欠了一下身子,木床发出一声脆响。恰恰是这木床发出的响声壮大了她的胆量。她一下子又坐起,大声说:“你再不走俺就喊人了!”
反插着的木门被于庆用刀子一下一下拨开了。当天成娘听到屋门“吱扭”一声的时候,她“啊啊”地叫了起来!于庆将一柱电筒灯光直射着她。缩成一团的她被压在了他身下。
在西间屋的二儿子天良被惊醒了,连声叫着:“娘!娘!”
于庆紧卡着她的喉咙。
天良走了过来。他擦亮火柴,点亮了小油灯。当他看到娘被于庆骑在身下时,他冲出屋门,便在院子里大喊起来:“赶快来人啊!俺家里有一坏人——”
于庆慌忙跳下床,夺门而逃。在院外边看到天良还在使劲地喊着,他飞起一脚踢向天良。
天良“哇哇”地哭叫着,静谧的乡村夜空里回荡着她们母子的呼叫。村民们陆陆续续跑来了。当知道于庆欺负她们母子时,便不敢再说什么。几个妇女把天良和他娘一起劝回了屋。
“于自海的媳妇被于庆强奸了!”这种桃色新闻在农民的口中,几经创作和演变,成了有头有尾有故事的趣闻。田头间,杨树下,饭场里,三五个一堆,无不窃窃私语着于庆强奸未遂的“惊心动魄”。
天成娘在屋里睡了一天了,也没吃饭。猪在圈里饿得直叫。几个妇女坐在她床沿上,说着一些劝解她的话。
天黑的时候,于庆的大嫂来了,披着一件蓝呢子褂子,手里夹着烟卷,身后还跟着两三个妇女。
于庆的大嫂在区供销社卖化肥,听说她是专门从区上回来的。天成娘听说她回来,便下床走了出来。
于庆的大嫂望着天成娘红肿的眼睛,用心疼的口吻说:“兄弟媳妇,吓着你了吧?”
天成娘拢起头发,看到屋里大人小孩来了这么多人,连忙说:“你们坐啊,你们坐啊。”她到西间里又拉出两条板凳来。
于庆的大嫂弹了弹指间的烟灰,说:“这事我和他大哥都听说了。今个晌午俺们也都训了于庆一顿。他是昨晚上喝醉了酒,正好路过你们家,想寻碗茶水喝,谁知道你误会了。咱们都是本乡本村的,你可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
于庆大嫂的语气里,听起来是责怪于庆,而实际上是恐吓着天成娘。
“俺那大兄弟也没在家,你一个人在家也够辛苦的,昨天你和俺弟弟于庆的那场误会,以后就别再提了,俺那个大兄弟回家来,你也别提这事了。谁愿意给自己的男人戴绿帽子啊?再说,你要是一直闹下去,对谁的名声都不好听。俗话说,母狗不浪,公狗不上!”说到这儿,全屋子里的人都笑了,有的男人还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天成娘委屈地厉声道:“大嫂,于庆真不是人!去年吧,他弄俺一下子,俺都没吭声,吃个哑巴亏就算了;今年吧,他又来老一套。这不是欺人太甚吗?啊?!俺又不是没男人,你又不是没女人,你这叫骑在俺头上拉屎啊!”
“话不能这么说!”于庆的嫂子打断了她的话,说:“你说他强奸你了,有啥证据?拿出来化验化验。裤裆里的事啊,说不清楚。我看就这样算了!你大儿子都读高中了,说出去让人家笑话你啊!你和于庆都是平辈分的,他日你一驴屌,你日他一棒槌,两够本。哈哈哈……”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又到了冬天。
天成娘心里明白,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她和于庆那件事,唯独她丈夫于自海不知道。谁也不会当面告诉他,可纸里包不住火啊,迟早他都会知道的。有几次,她下决心想告诉他,可话到嘴边,又难以启齿。
他能相信自己吗?
他一旦知道了这些事后,他会怎么样呢?打我一顿?骂我一顿?跟我离婚?天成娘整天在心里想象着丈夫的态度。如果像这样继续瞒着他,让他蒙在鼓里,有朝一日突然知道了这些事,他会受得了这种打击吗?
天成娘想通了,这事不能再瞒他了。等他再回家,一定要给他说清楚。
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于自海骑着自行车从兽医站回来了。刚在家里坐下,就被一个老年人招呼去给他家的猪看病去了。
“腊八腊米饭,越腊越喜欢。”这是一句流行在乡村的土话。意思是说,腊月初八这一天一定要吃米饭,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天成娘知道丈夫回来了,便舀了一碗米,准备照每年的老规矩,做一顿“腊米饭。”
腊米饭做好了,在大锅里蒸着,她正要炒个菜的时候,丈夫满脸发紫地冲进了厨房。
他喘着粗气,两眼怒视着天成娘。
天成娘知道事情败露了。有着思想准备的她愿意任他骂。可是,他却就这样痴痴地伫立着,一语不发。
天成娘说话了。她说:“反正事情也过去了,你知道就知道了吧。要杀要打,俺随你的便吧。”说完,她蹲在他面前,等他随意发落。
于自海没有打他的老婆。他心里啥都清楚,根本就不怪她,完全是他于庆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没把我当人看!他一把抓起案板上的菜刀,就往外走。
天成娘死死抱着他的腿,苦苦央求他不要干傻事。他还是不说话。
天成娘又说话了。她说:“孩子他爹,这事都怪我,好不好,啊,快要过年了,算了,啊?再说,于庆狗日的有钱有势,他大哥是区里的官,咱弄不赢人家呀……”
“老子不过年了!”于自海终于说话了,牙齿咬得咯嘣响,“他是个石磙,老子是个鸡蛋,也得跟他碰!”
“又何必呢!咱两个儿子都这么大了,再闹的话,对他们也有影响。就算了吧,俺求你了……”天成娘在他的男人面前哭得无遮无拦。
于自海放下了菜刀,把天成娘搀扶起来,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要叫他于庆知道老子也不是好欺负的!”停了停,他对天成娘说:“今儿个是腊八,做米饭去吧。我出去买盒烟去。”
天成娘看丈夫消了气,便到厨房炒菜去了。
出了家门,于自海没去买烟。他坐在河边,怔怔地望着厚厚的冰溜,任呼啸的北风卷袭着他,把并无一丝寒意。他想不到好的办法去报复于庆。一股男人强烈的冲动激励着他站起身来,迫使着他与于庆鱼死网破。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还算什么男人?他要问清楚于庆为什么这样欺辱他?
他赤手空拳地向于庆家一路狂奔。
于自海刚刚跨进于庆家大门口,一条黄狗汪汪地叫了起来。他并不害怕。兽医什么样的畜生没见过呢。径直往前走,那黄狗便往后退着继续叫。他弯下腰。那狗扭头就跑,继续叫着。
“谁呀?”屋里走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
“是我。你爹在家吗。”于自海一眼便认出了于庆的女儿玲玲。
“是自海叔啊,你啥时候回来的?”玲玲很是懂事地跟他应声着。
“今天上午回来的。我找你爹。”于自海望了她一眼,又问:“你爹呢?”
“俺爹赶集还没有回来呢。”
“你娘呢?”于自海的话音刚落,从厨房走出于庆的媳妇来。
“你找俺啥事?你老婆勾引俺汉子的事,俺还没找你算账哩,你主动上门来找事是吧?”于庆的媳妇也不是省油的灯,两句话让于自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于自海用鄙夷的目光瞪着她,气得不知从哪儿说起了。
于庆的媳妇个子不高,头发像是很久没梳过一样,又脏又乱,可说话的嗓门并不和她的身材成正比。在同生产队里的妇女当中,她的个头算是最矮的一个。可就是说话声音特别响亮,和她的男人于庆走在一起,一个太高一个很低,构成了十分显眼的差距。因为她说话时大都爱抢在别人前面,所以生产队的妇女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喳拉鸡子。”农村的早上,树林里有很多鸟儿鸣叫,最嘹亮的一种黑色的鸟就叫“喳拉鸡子”。喊于庆的媳妇为“喳拉鸡子”,于庆一家人并不生气,这个绰号并非贬义,相反,他们一家人对这种女人们推崇开来的“借代”词还挺乐意,那是女人羡慕她才给她取外号呢。
于自海虽不常在家,但知道她的外号。听着她这么一连串的不着天不着地的啰嗦,于自海根本不愿理她这种胡搅蛮缠的泼妇。他说:“我找的是你男人,又不是来找你,跟你说不着话。”
“喳拉鸡子”在她家院子里转着圈,叉着腰大声说:“你不是来找我?!你那个熊样的找我的话,我还嫌你那东西没本事哩!”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于自海一下,嘴角撇向一边,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你不就是个兽医吗?天天X骡子X马累得不舒坦了是不是?你想来X我给你的浪娘报仇吧?我跟你说兽医,你浪媳妇子是找着俺们家的男人于庆去X她的,不是俺男人于庆找她。”
“喳拉鸡子”振振有词,说得兴味盎然妙语联珠,两个嘴角边都泛出了白沫。她的女儿玲玲在屋里听不下去了,跑出来拉她母亲说:“娘,你这是胡说什么呢?自海叔是来找俺爹说事的,你乱骂什么?”
“骂,骂,我就是要骂他!”“喳拉鸡子”寸步不让。她女儿越是用力拽她,她越是用力挣脱着朝于自海身边跳过来。
于自海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十分冷静地说:“你嘴里不干净地骂人,瞧瞧你那样就叫人恶心。你女儿在这儿看着的,是你先骂我的对不对?”
“我不光骂你,老娘我还打你哩!”说着,“喳拉鸡子”便扑了上来撕打着于自海。她女儿在大门口大声喊着:“快来人啊——!”
听到喊声,饭场里不少人端着饭碗都跑来了。一看见“喳拉鸡子”正用头顶于自海,就纷纷劝说,并对于自海说:“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快走吧!”
于自海在众乡亲的劝说下,正要离开于庆家时,“喳拉鸡子”又猛扑了过来,抱着他的小腿就一个劲地狠咬。于自海疼得“哎哟”着,坐在了地上。“喳啦鸡子”顺势压住了他的下身,两手紧紧揪住他的裆部。这可是男人的致命部位,弄不好完全可以致人于死地的。于自海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像个“小钢炮”的农村妇女会使出这么一招。他本能地揪着她的头发,用力重重一拳打在她脸上,才挣脱着站了起来。他捂着阵阵作痛的裆部,一瘸一拐地走出了于庆家的大门口。“喳拉鸡子”破口大骂着又要追上来,被众乡亲拦住了……
于自海啊于自海,你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怎么那么不冷静呢?你怎么就不听老婆的劝阻,非要这么着急来找于庆“算账”呢?这下子可好,找于庆报仇没报成,反被他老婆臭骂了一通,差点儿还被她揪裆部揪得半死。你说,这叫什么“报仇”啊?这是偷鸡不成反又蚀了米,这叫“打不住黄鼠狼反惹一身骚”啊……
于自海坐在自家屋里的板凳上,越想越气,自己太鲁莽太感情用事了。他有点后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个大老爷们儿,今天这样做不是无效劳动吗?“嘿!”于自海叹着气,到处在衣兜里找烟抽。
天成娘心里想,这下丈夫闯祸了。当时丈夫和“喳拉鸡子”厮打时,于庆赶集还没回来,等他下午回来了,他那狗日的暴性子,肯定要找丈夫算账的。她想着想着,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庆肯定会来他们家找事儿的。
她把她的担心跟丈夫说了。于自海一拍大腿说:“他娘的敢闯进咱家的院子,我就砍断他的腿!”他在屋里踱着步,又对倚在门旁的天成娘说:“怕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过,我是鸡蛋非碰碰这个石磙不可,我看他于庆狗日的能对我怎么样?”
农村的腊月间,因为没有什么农活,村里人大都是三五个一团,围在挡风的墙根边,东拉西扯,开着玩笑,议论着一年的收成,议论谁家比谁家富裕。村人们叫这种闲谈为“闲嗑牙”。一些性格开朗的男人,聚到一起分析着某某的名字,上溯八代,下至子孙,把姓名连成一串,你骂我,我骂你,嘻嘻哈哈。村人们叫这种笑骂为“吃小名烩”,又叫“骂大烩”。而今年的腊月间的人场里,村人们“闲嗑牙”,“吃小名烩”的内容,全离不开于庆和于自海两家的“寒门艳事”。当然,“闲嗑牙”、“骂大烩”的人场里,没有他们两家的人在场,若有他们两家亲戚路过人场时,刚才还是妙趣横生加油添醋的笑谈,便会戛然而止,待他们两家的亲戚过去之后才能继续着谈笑……
天成娘的担心和忧虑,和村人们预感的一样:于庆果然真要找于自海“算账”来了。
黄昏时分,刺骨的北风刮个不止。天阴沉着,眼看是要下雪的样子。于庆纠集了他家族里五六个年轻人,每人拿着铁锹、抓钩、扁担等农具,浩浩荡荡而又不声不响地来到了于自海家的墙头外边。
于庆在最前面,他用脚不停地踹着大门。
天成娘和于自海都听到了踹门声。“谁呀?找谁呀?”天成娘把饭碗放在锅台上,于自海也紧张地放下了饭碗,随天成娘一起从厨房里走出来。
“是我,于庆!你男人今天晌午不是找我没找着吗?现在我来找他。”外面很静,就于庆一个人的声音。
听到于庆的声音,于自海顺手从屋门口拎起了铁锹,两手紧紧地攥着木把。
“他没在家。回兽医站去了。”天成娘对着大门喊着。
她的话音刚落,从大门口的土坯墙头上,“噌噌噌”跳下五六个人来,每人手里都拿着家伙,吓得天成娘目瞪口呆。
“你想干啥?”于自海把天成娘挡在身后,紧紧攥住铁锹。
于庆手里拎着的木棍,有三尺长左右。那是他家的“开棍”,专门用作支撑架车负重的车把下的木棍,也相当于汽车用的“千斤顶”。他一个人走到于自海面前说:“听说你要找我是不是?”
醒过神来的天成娘急忙从丈夫身后走出来,冲着于庆大喊:“于庆,你别仗着你大哥是个官,就这样欺负人!要打就打我,不关俺男人的事!”
“滚开!”于庆飞起一脚,踢在了天成娘的肚子上,天成娘打了一个趔趄,大哭大叫起来。
还没等于自海抡起的铁锹砸下去,他已被一拥而上的帮凶打得鼻青脸肿,倒在了地上。于自海恼怒地从地上爬起,又去抓铁锹时,于庆轮起手里的木棍,对准他的头部,“砰砰”两下,于自海再也没有爬起来……
鲜血淌得满地都是。天成娘在血泊里抱着死去的血肉模糊的于自海,在漆黑的夜空里呼喊着:“老天爷啊,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啊……”
天成娘的哭声震动着村子。
当她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了眼泪的时候,她才知道她的面前已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乡亲们。
(原载《红岩》2003年第1期,小说原题为《旋转的火光》)
作 者: 巴一,本名巴毅,作家,出版有中篇小说《淮北往事》《复仇》和散文集《故乡在晚风中》等。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