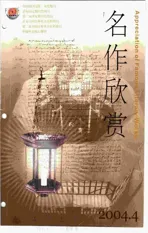唐宋体诗例话:胡适
——“后唐宋体”诗话·之五
2011-08-15浙江王尚文
/[浙江]王尚文
唐宋体诗例话:胡适
——“后唐宋体”诗话·之五
/[浙江]王尚文
胡适倡导白话新诗,可以说是掀开了我国诗歌史崭新的一页,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厥功甚伟。所谓“倡导”,表现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两个方面。就其诗歌作品本身而言,往往阳刚之气不足,时代气息不浓,或失之平易浅白,其价值主要在新诗史上的开拓地位。而其诗歌理论,除了历史影响,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当然也有矫枉过正之处。
诗有文言旧体与白话新诗,文言旧体要变革,实乃历史必然。这一点,胡适的论述颇为透彻。他说:“吾辈既以‘历史的’眼光论文,则亦不可不以历史的眼光论古文家。《记》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及乎身。’(朱熹曰:反,复也。)此言复古者之谬,虽孔圣人亦不赞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吴奔星、李兴华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说到明代文学,他指出:“及白话之文体既兴,语录用于讲坛,而小说传于穷巷。当此之时,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于汉魏以上,则罪不容辞矣。”(第173页)
但按他的逻辑,文言旧体必当也必定演变为白话新诗。而在我看来,却是未必。白话新诗固是康庄大道,但白话也可以化入旧体而成新的旧体,也就是我所说的由唐宋体变而为后唐宋体,质言之,旧体并不在完全扫荡、打倒之列。
而且,必欲坚守唐宋体者,我也绝不以之为罪,还相信并期待能够写出好作品来;只是认为“坚守”越来越难,富于时代气息的好作品也将越来越少。据知,当前从事旧体诗词创作者数以百万计,希望能够大胆尝试后唐宋体的写作,以迎接旧体诗复兴之真正的春天。
柳亚子曾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对此,胡适反驳道:“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第176页)胡适此问,也是一味排斥后唐宋体者所应思考的。
胡适断言:“用死了的文言绝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第187页)对此,我们似乎没有不信的理由。
胡适下面一番话,也说出了唐宋体的病症: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 ,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是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驌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第153-154页)
唐宋体诗未必每首都有此病,尤其未必都有如此严重,但许多作品都难逃“陈言套语”的羁绊,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适的文学革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白话”。他曾有专文《白话解》解释这一关键词,说白话之义约有三端:
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字眼。
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第180页)
其实,在文学的范畴内,白话就是与文言相对的书面语体,并非“俗语‘土白’的白”,不能把它和“俗语”完全等同起来。再者,由于现代白话乃从近代白话发展演变而来,而近代白话与所谓浅近文言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汉界楚河,彼此并不泾渭分明,因而现代白话自然会有文言成分掺杂其中,用白话写作,所追求的是“自然”(这也是胡适所一再提倡的),所谓自然,就不必提出“夹入”一说。夹入者,是从另外一实体中取出而有意夹入其中也,难免就不自然。只要不碍白话之大体,能把语言的表现力发挥出来,做到“明白易晓”,夹入多几个、少几个,原可以在所不计。
唐宋体用的就是典雅的文言,以与其所表现的精神相匹配,若夹入白话,难免会被讥笑。后唐宋体追求的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化合,并非在文言中“夹”入白话,或在白话中“夹”入文言。所谓“化合”,就是追求自然,追求把语言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后唐宋体不是白话诗,用的基本上是浅近文言,由于白话的化入,就使它的整个精神风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和时代精神相吻合,因此唐音宋调具有了现代意味,既继承了唐宋古近体诗的独特魅力,又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语言既非一仍唐宋体之旧,又非全是白话诗之新。这是艰难的创造,这是使中华诗歌传统生命力得以重新焕发的异卉奇葩。
胡适对某些律诗(包括杜甫的名作在内)遣词造句勉强拼凑的指责,颇有见地,如说“‘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实在不通。‘拟绝天骄拔汉旌’,也不通。”(第192页)但说“白首(应作“日”——笔者)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有点做作,不自然”,未免就委屈了杜甫。这是诗人喜极之时的想象之辞,即使有点“过”,也十分自然;依我体会,此“过”正是老杜天真可爱处。他又说:“‘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一笑。”(第192-193页)这回胡博士是真正闹了笑话!他为了打倒律诗,连诗起码的常识都不要了。照他这样说来,他所推崇的“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也是“极坏”的句子了:一定要有钱才能“对菊花”吗?难道无钱就不行吗?真是岂有此理!
胡适对律诗似乎深有偏见,一再说“律诗总不是好诗体,做不出完全好诗”,“不配发议论”等等,甚至还说“律诗是条死路”。贬得如此之低,终失公允。他自己所赞赏的杨杏佛《再送适之》就是一首律诗,而这首诗真正值得称道的又恰恰是夹带议论的中间两联:
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鸟满树林。
他和周作人1934年相互唱和的“打油诗”,实为后唐宋体的开先河之作,也都是难得的律诗佳构。
胡适关于新文学的八点主张,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纲领。其中关于精神(内容)的三点:“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可以说正是为后唐宋体量身定做的;从反面看,唐宋体最易犯这三种毛病。形式方面的五点中之“不用陈套语”,后唐宋体当然也无异议。至于“不用典”,“不讲对仗”,后唐宋体万难从命,只是力求不用僻典,用典而能出新,绝不为用典而用典——唐宋体往往为炫博而用典,用典因此而成为目的,以用典多而僻相高;“对仗”,该用处一定用,而且可以说这是后唐宋体体现汉语特有魅力的主要平台之一。“不避俗字俗语”,当然举双手赞成。所可讨论者是他紧跟着的括弧里的说明:“不嫌以白话作诗词。”后唐宋体不是提倡以白话作诗词,当然也不反对。问题在“不嫌”两字所表露出来的语气,似乎用文言是正道,以白话为之不应嫌弃而已。其实,“以白话作诗词”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诗词本是文言的产品,用白话来作,就好像用牛奶代替水来煮稀饭一样,相互对不上号。
后唐宋体所追求的是白话与文言的有机化合,而与所表现的精神、内容融为一体。他自己曾“戏以白话作律诗”:
眼前风景好,何必梦江南?
云影渡山黑,江波破水蓝。
渐多黄叶下,颇怪白鸥贪。
小小秋蝴蝶,随风来两三。
(《江上秋晨》,《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节所引其诗除另注明者均出此书)
这怎么算得上是白话诗词?他的朋友当时就“不认此为白话诗”。首联(还有“小小秋蝴蝶”)和王熙凤她们的“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一样,只是比较接近白话而已,但整首诗仍是十足的文言味。而且,我还要说,这首诗还是典型的唐宋体。何以故?其精神格调是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陈套语”、“死文学”,一点新意也没有。他辩解说:“古人皆言鸥闲。以吾所见,则鸥终日回旋水上捉鱼为食,其忙可怜,何闲之有乎?”这有强词夺理之嫌,难道内容与古人所见不同就是白话诗?
关于新文学的八点主张,他在日记中说:“能有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话。”(第116页)这话,我以为反映出了胡适早期不很成熟的地方。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苛责前人,他在那个时代提出这样的主张,了不起!但就事论事,也不能不指出它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大学课堂上听到了“现代文学史”老师批判他的有关新文学“八事”的主张是形式主义,当时觉得挺有道理,后来发现这帽子并不合适。他由此反对旧文学、死文学,极有见地,他的“文学革命”也因此比黄遵宪他们的“诗界革命”高明多了,成效也显著多了,但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所见却是仍有所谓时代的局限性。
打油诗本来只是形式有点像诗的游戏之作,原不是诗,只是由于以前的一些文人借打油诗之名以自谦,逐渐就模糊了诗与非诗的界限。唐宋体一般与打油诗的区别比较明显,而后唐宋体多讽刺之作,有时很像打油,其实它们是“含泪的笑”,是极其严肃的幽默,是好诗。胡适关于诗的言论也涉及打油诗,我们正好借此进行鉴别。
《胡适诗话》有《湖南相传之打油诗》一节,录大家熟知的“张打油”的开山之作(与前文引用的文字有异,参阅《简说“后唐宋体”》,《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第13页):
上天老懵懂,打破石灰桶。
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由于流传甚广,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尽相同的版本。《白话打油诗一束》中,胡适说:“打油诗何足记乎?曰,以记友朋之乐,一也。以写吾辈性情之轻率一方面,二也。人生哪能日日作庄语?其日日作庄语者,非大奸,则至愚耳。”(第131页)且录其最短者以为例:
纽约城里,有个胡适。
白话连篇,成啥样式?
所谓“记友朋之乐”者,乃友朋相互取乐之乐,如他的《戏题杨杏佛的大鼻子》,故谓“性情之轻率一方面”,非“庄语”也。与“庄语”相对的是“谐语”,即诙谐风趣之语,是用来玩笑的戏言。足见打油诗和我们通常说的诗,确实是两码事。
但“谐语”又和“幽默”相关相联,因此打油诗和诗的边界就模糊起来了,极大部分的打油诗一望而知其为打油,有的看似打油,实则诗也,而且是好诗。苏东坡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轻率”,亦深刻,非打油也。
胡适1916年有一段话“从旧体诗词看清末民初文学之腐败”: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盫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
(第135页)
在此不拟对其所涉及的人进行评论,只想指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八个字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时效,虽然时间已过去将近一百年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警醒起来,推陈出新,更上层楼。
还是要当文抄公,为此,心里不免感慨万千,怎么胡适近一百年前的批评仍然适用于今天呢?他说:
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
(第135页)他举老杜《北征》《石壕吏》《羌村》《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为例,认为“以用典见长之诗,绝无可传之价值”。(《胡适文集》第2卷第3页)瞿髯师(即夏承焘,字瞿髯,为笔者恩师,故称——编者注)有一首《感北省近事》:
衰衣自合从高勋(遗山句),衮衮筹边腹负君。
快意犹能堕郈费,寒心岂但失燕云。
未招朱喙归千里,又见苍头哭一军。
翻被药师笑张珏,汴京此局昔无闻。
我年轻时觉得是一首很好的讽刺诗,但《天风阁诗集》却未收,仅见于附录所引《石遗室诗话》中,陈衍以“用事精切,非精于史学者莫办”誉之。我想,一定是瞿髯师也不以用事胜者为好诗。《浪淘沙·过七里泷》(《夏承焘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我以为是瞿髯师最好的词作:
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 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
就未用一个典故。不是没有典故可用,也不是典故无用武之地,诗人就是愿意来一场“肉搏战”,而使“境界全出”——当然,我们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绝不用典。若非僻典,又能出新生色,为什么就一定不能用?
胡适的诗歌创作由早期的唐宋体而白话新诗,轨迹分明,尽管“尝试”时期难以完全摆脱旧体影响,“新”得并不纯粹。早期的唐宋体追求“清顺达意”,其实和他的白话新诗风格是一致的,只是前人的影响更为明显罢了。如作于1911年的《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见街头有推小车吹箫卖饧者占一绝记之》:
遥峰积雪已全消,泄漏春光到柳条。
最爱暖风斜照里,一声楼外卖饧箫。
一、二两句平平,三、四两句有点意思,但马上让人联想起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们当然不可能起作者于地下而问之,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陆游的这名句早已在作者的潜意识里,为他这首诗的发酵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唐宋体作品全无新意,而是说由于前人的作品已烂熟于心,只要你一开口一下笔,就只能是那个腔调,更可怕的是你只能是那种眼光、那种思维。这是唐宋体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后人难以有所突破的困难之所在。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说:“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第209页)这话自然是对的,曾被朱自清奉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我想补充的是,唐宋体对人的束缚甚至使人逃避新内容和新精神,它从根本上阉割了人的创新能力,只能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上蹿下跳、左冲右突。
1934年周作人写了《五十自寿诗》,同年1月17日胡适依韵作《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啥袈裟。
能从古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吃肉应防嚼朋友”,来自周作人所说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一日,他谈及一个忘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鲁迅祖父的骂人、著作和姨太太》http://hi.baidu.com/bpzxlqc/blog/item/0121b025d13c716334a80f94.html)
翌日胡适意犹未尽,又依旧韵和了一首五律: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读书偶得——周作人自寿诗》http://10758268.blog.hexun.com/35018489_d.html,以下所引胡适的诗及注均出自此)
末句是《红楼梦》里的话,他说:“用典出在大观园拢翠庵。”其实不知末句出典也无关紧要。总之,周作人与胡适的这几首诗称之为后唐宋体的开山之作,可以说当之无愧!胡适另外还有两首也颇出色。一是《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不可著袈裟。
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
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但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不用典”的规矩。二是1935年《和周岂明“二十五年贺年”打油诗》: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
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
羡煞知堂老,萧闲似散仙。
中间两联平易而深刻,尖锐不亚鲁迅,历时而弥新,自是后唐宋体的佳作。
胡适虽不是个优秀的诗人,但他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却有着特殊的贡献。
诗曰:
披荆斩棘勇尝试,革故鼎新举帅旗。
天火盗来烧腐朽,俨然普洛米修斯。
作 者:王尚文,学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