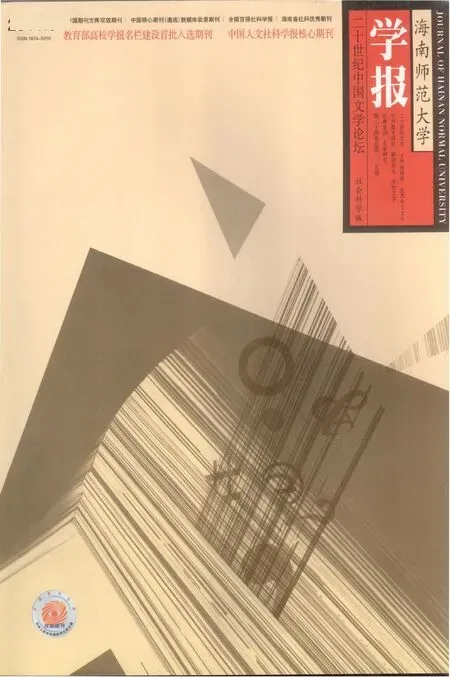明代海南文化的发展及原因新探
2011-04-13李勃
李 勃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明代海南文化的发展及原因新探
李 勃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明代是海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有十:一是各类学校多;二是科举考试中式人数多;三是“鼎臣继出,名满神州”;四是两位海南人分别掌管明代全国两所最高学府;五是九位海南人入选《明史》;六是各种著作多;七是俗尚礼文和读书风气浓;八是许多家庭妇女都有文化,并出现冯银等五位女诗人;九是各种楼亭、坊表和名胜古迹及名人墓葬多;十是海南岛被称为“海滨邹鲁”或“海外邹鲁”。明代海南文化之所以获得高度发展,主要原因有九,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明王朝对本岛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成因
明代是海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明代海南文化,对于对外宣传海南岛的古代文明,提高海南的国际地位,让世界了解海南,使海南走向世界,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进程;对于深入发掘海南传统文化,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对于提高海南各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帮助某些人彻底改变传统偏见,无疑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的表现
以往经常有人说“海南岛是文化沙漠”。意谓海南岛完全没有文化,像沙漠一样苍白。其实,这既是对文化概念的无知,又是对海南历史的无知。“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一般指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因此,从广义的“文化”来看,历史上只要有人类居住过的地方,该地区就一定有文化。因为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适应环境,创造出一些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石器工具和茅草房都是原始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或物质文明。而原始宗教、象形文字和符号文字或结绳记事等,则是原始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或精神文明。虽然这些都是较为粗糙的、低级的文化,但它们毕竟是原始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世界上的各个古代民族一般都能创造出这些较为低级的文化。这些低级文化是与人类早期低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文化有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分,如计算机和手机等都是较为高级的物质文化,这些高级文化是与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我们不能苛求原始人类或古代人类都能创造出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高级文化。由此可知,历史上海南岛只要有人类居住,那么,岛上就一定有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海南岛不是荒岛,自古以来岛上一直有很多居民。考古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岛上已有人类存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踪迹已遍及全岛各地。[1]海南岛是个移民岛,秦代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在海南岛设立地方政权,祖国大陆各地的汉人纷纷迁入本岛。据《汉书·贾捐之传》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二郡,“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2]经考证,这些被编入西汉政府户籍的居民都是汉人。[3]可见早在西汉时期,汉族已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因而使中原文化或汉族文化成为海南文化的主流,如海南岛历代科举中式者都是汉人和本岛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汉文著作等。
海南岛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在明代,海南文化曾出现昌盛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表现之一,各类学校多。据海南旧志记载,明代海南岛曾设立众多学校,计有:府学(亦称府儒学)1所;州学(亦称州儒学)3所,即儋州学、万州学、崖州学;县学(亦称县儒学)13所,即琼山、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乐会、昌化、陵水、感恩、宜伦、万宁、宁远县学;社学(由官府或乡绅建于乡社间的初级学校)201所,其中琼山县82、澄迈县19、临高县 11、定安县 3、文昌县 8、会同县 5、乐会县13、昌化县6、陵水县2、感恩县3、儋州19、万州12、崖州18;义学(由官员或乡绅捐款建的免费学校)17所,其中琼山县9、澄迈县2、乐会县1、儋州5;卫学(亦称卫儒学)1所,即海南卫的“卫学应袭书馆”;所学(明代设于千户所一级军事编制单位的军队子弟学校,属于社学)9所,其中清谰千户所1、万州千户所1、儋州千户所2、昌化千户所2、崖州千户所2、水会千户所1;书院(由私人或官府所立讲学、肄业之所)21所,其中琼山县8所(桐墩书院、同文书院、奇甸书院、西洲书院、崇文书院、石湖书院、粟泉书院、乐古书院),澄迈县2所(天池书院、秀峰书院),定安县2所(录漪书院、尚友书院),文昌县1所(玉阳书院),会同县1所(应台书院),乐会县1所(安乐书院),临高县2所(澹庵书院、通明书院),儋州3所(振德书院、图南书院、东坡书远),万州1所(万安书院)。此外,琼州府及其所属三州十三县均分别设立阴阳学(培养天文历法人才)和医学(培养医学人才)各1所。以上参见 《道 光 琼 州 府 志 》、[4]309-374,711-729《正 德 琼 台志 》、[5]299-319,335-359,361-384,385-395《 万 历 琼 州 府志》。[6]143-162,285-314
表现之二,科举考试中式人数多。据海南旧志记载和本人详细统计,明代全岛共有进士64人(其中琼山44,文昌8,定安2,万州 4,海南卫 1,陵水1,崖州 2,澄迈 1,临高1);举人614人,其中文举人599人(琼山303,文昌60,定安 48,会同 17,乐会 18,万州 32,海南卫 3,澄迈 30,临高 18,儋州10,宜伦20,陵水3,崖州19,宁远7,昌化5,感恩7),武举人15人(琼山 9,澄迈 2,崖州3,文昌1)。进士和举人合计 678 人。[4]1190-1235
此外,明代全岛还有荐举64人(其中举贤良方正2,经明行修17,举茂才1,举人材41,辟荐3),其中琼山25,澄迈3,临高1,定安3,文昌9,乐会5,昌化3,万州3,崖州 9,海南卫 3。[4]1187-1189
正途出身的各类贡生(包括岁贡、恩贡、选贡、拔贡、副贡等,即府、州、县儒学毕业的学生经考试合格选拔到中央国子监读书的监生,监生毕业后的待遇与举人相当)共有2,439人,其中琼州府学315,琼山县学144,澄迈县学179,定安县学185,文昌县学168,会同县学146,乐会县学179,临高县学152,儋州学220,昌化县学114,万州学197,陵水县学103,崖州学225,感恩县学112。(非正途出身的例监、纳监和荫监,不包括在内)[4]1241-1273
那么,明代海南岛进士、举人所占人口比例及其与省内外比较情况如何呢?据《万历琼州府志》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琼州府有户 5,6892,口 250,524。[6]231按此,则平均每位进士所需人口3914.4人,平均每位举人所需人口408人,平均每位进士和举人所需人口369.5人。
据清代有关《通志》记载和本人详细统计:明代广东省有进士 903 人,举人 6,977 人,两项合计 7,880 人。[7]明万历六年(1578年),广东省有戸 530712,口5,040,655。[8]1133按此,则平均每位进士所需人口5,582.1 人,平均每位举人所需人口722.5人,平均每位进士和举人所需人口639.7人。
明代广西省有进士223人,举人4,677人,两项合计4,900 人。[9]万历六年,广西省有户 218,712,口 1,186,179。[8]1149按此,则平均每位进士所需人口 5319.2 人 ,平均每位举人所需人口253.6人,平均每位进士和举人所需人口242.1人。
明代浙江省有进士3,805人,举人10,390人(其中文举人 10,126人,武举人 264人),两项合计 14195人。[10]万历六年,浙江省有户 1,542,408,口 5,153,005。[8]1101按此,则平均每位进士所需人口 1,354.3 人,平均每位举人所需人口496人,平均每位进士和举人所需人口363人。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知,明代海南岛平均每位进士所需人口数,分别少于广东、广西省同类的1,667.7人和1404.8人,而多于浙江省同类的2,560.1人;明代海南岛平均每位举人所需人口数,分别少于广东、浙江省同类的314.5人和88人,而多于广西省同类的154.4人;明代海南岛平均每位进士和举人所需人口数,少于广东省同类的270.2人,而分别多于广西、浙江省同类的174.4人和6.5人。远处南溟的海南岛能够取得以上科举中式比例,可谓成绩辉煌!
表现之三,“鼎臣继出,名满神州”。明代海南岛人才辈出,在朝廷和地方当大官的很多。如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的,有邱濬(琼山人);官至尚书(正二品)的,有薛远(琼山人)、廖纪(陵水人)、①廖纪原籍是明陵水县,这在明代广东和海南诸旧志里都有明确记载。《明史》卷202本传记作河北“东光人”,系以其户籍所在地言之。王弘诲(定安人);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的,有海瑞(琼山人);官至侍郎(正三品)的,有唐胄(琼山人)、钟芳(崖州人);官至布政使(从二品)的,有胡濂(定安人)、梁云龙(琼山人);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的,有夏升(海南卫左所人);官至按察使(正三品)的,有林士元(琼山人);曾任翰林院学士(翰林院之长)的,有丘浚;曾任巡抚(明代临时委派的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的,有邢宥(文昌人,江南巡抚)、唐胄(山东巡抚)、海瑞(应天巡抚)、梁云龙(湖广巡抚)等。至于在中央各部门担任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给事中(从七品)、监察御史(正七品)以及在地方各省任参政(从三品)、参议(从四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知府(正四品)的,则不计其数。[6]因此,明代海南岛有所谓“鼎臣继出,名满神州”之誉。见万历《广东通志》、[11]446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2]555对此,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曾赞叹不已,他说:“成化二年(1466年)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邱公濬翰林学士,皆在一月。虽天下望郡亦希觏,洵海外衣冠胜事也。”[13]284-285明代海南人在朝廷当官的不仅人数多和职位高,而且几乎每个都是为政清廉,有学问和有作为者。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有四位:一是著作等身、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思想①明代邱濬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里说:“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卷21)“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于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卷27)意谓一切财富虽然来源于自然界,但必须经过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由人付出的劳动大小而决定产品的价值多少。这就所谓“劳动价值论”。比英、法学者提出同样观点约早180年。的大学士邱濬;二是被明代年青进士称誉为“当代伟人”的著名清官海瑞;[8]6034三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睁眼看世界和主动接受西方外来文化、于万历二十六年率领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北上北京准备谒见明朝皇帝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王宏诲);[14]四是被《明史》作者称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8]5359
表现之四,两位海南人分别担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和南京国子监祭酒,掌管明代全国两所最高学府。国子监是明代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太学。明初先后设有三所国子监:即南京国子监(设于1365年)、中都国子监(设于1375年,在安徽凤阳)和北京国子监(设于1403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罢中都国子监。国子监长官称为祭酒,设一人(明初正四品,后改从四品),统领国子监训教之政。在其下设有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掌馔等职。[8]1789成化十三年至十六年(1477—1480 年),海南人邱濬任北京国子监祭酒。[15]1177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有海南人王弘诲任南京国子监祭酒。[15]1186又见明王弘诲《明修〈玉海〉序》。[16]7明代居然有两位海南人分别掌管全国两所最高学府,这说明什么问题?
表现之五,入选《明史》的海南人多。明代有九位海南人入选《明史》,即:邱濬(卷181)、海瑞(卷226)、唐胄(卷203)、廖纪(卷 202)、薛远(卷 138)、邢宥(卷 159)、冯颙(卷188)、郑廷鹄(卷319)、荣瑄(卷297,琼州人)。其中前四位都有专传,后五位均为附传。至于《明实录》记载海南人的事迹更多,除以上各位外,还有南京兵部尚书薛远、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梁云龙、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等,都分别有传略。[17]50-95万历末年,海南岛在籍人口才25万多人,竟然有9位海南人入选《明史》,可谓人才辈出。
表现之六,各种著作多。明代海南岛进士和举人大都有著作传世。经本人不完全统计,明代海南各种著作(仅含海南各级地方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本岛人著作两种)至少有198部,其中属于地方志的有31部,本岛人各种著作有167部。个人著述最多的是邱濬(35),其次是林士元(11)、郑廷鹄(9)、王宏诲(9)、钟芳(8)、唐胄(5)、王佐(4)等。参见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乾隆《琼州府志》、道光《琼州府志》及明清海南各州县志、《永乐大典方志辑佚》、②详见马蓉、陈抗等辑:《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页2828-2839。《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方志考》、[18]395-397《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19]《广东文献综录》[20]等。
表现之七,俗尚礼文,读书风气浓。明代文献对此屡有记载。诸如:
万历《广东通志》卷57《琼州府·风俗》说:“琼居海外,民性朴茂,习礼义,有华夏之风。”“圣祖开基,文教畅于南裔。名相钜卿项背相望。”[11]454-455
万历《琼州府志》卷3《风俗》说:“明兴,道化翔洽,文教四讫。今不患其不文也,特患文之太过,流而弊耳。”“民性朴茂,习礼义之教,有华夏之风。”“为士者咸务诗书,科第不乏人,其余男女各务农桑织紝,风俗丕变,为岭南望郡。”琼山县“俗尚礼文,士专诗书。”澄迈县“民性颇淳,士习读书。”定安县“读书尚礼者众。”文昌县“雅洽诗书,衣冠文物大类琼山。”儋州“俗尚礼义……家多习读儒书。”[6]114-115、118-119
明邢宥《海南村老歌》云:“海南村老非真村,家能识字里能文。……得钱只欲买书读,不置田庐遗子孙。”[6]859
明邱濬《南溟奇甸赋井序》云:“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6]857
又邱濬《琼山县学记》云:“洪武中,姚江赵谦古则来典教事,一时士类翕然从之,文风用是丕变,至今琼人家尚文公礼,而人读孔子书,洗千古介鳞之陋。”[4]1696
明王佐《南溟奇甸歌》云:“南溟为甸方恰才,未及十纪,而人物增品之盛,遽与隆古相追陪,衣冠礼乐之美,遽与中州相追陪,诗书弦诵之兴,遽与邹鲁相追陪。”[6]860-861
明王赞襄《问琼南人物风俗》说:“……值我朝文物之盛,教化之深,各自愤发,更相劝勉,习礼敦雅则大异于前矣。以琼人之人物风俗甲诸他郡有如是者,故我朝太祖有南溟奇甸之称,尹直学士有北极名邦之状,李阁老东阳、何尚书乔新、吴祭酒、张御史、秦学士、徐琼、程敏政、张元贞辈交册各赞为琼南望郡。藩臣守令凡司是邦者,下车之日即以小苏杭目之,至有称为闽浙不过者。”[21]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表现之八,许多妇女都有文化,并出现冯银等五位女诗人。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已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但长期以来女子并没有真正享受学校教育的权利,直至清末民初,我国才开始出现女子学校。明代的海南岛,由于家庭教育和社会读书风气的影响,出现了许多知识女性。诸如:海瑞之母谢氏,“口授瑞以《孝经》、《学》、《庸》诸书”。[6]774琼山举人张玉妻王氏,“涉书史”。[4]1604临高王佐之母唐氏,“知书闲礼,幼寡守节,抚孤子佐,教以诗书节义,中礼魁,以文学名世”。[6]777儋州廪生蔡荣妻刘氏,“生四子,教诲成名,三子俱登宦籍”。[6]788文昌韩节俭妻王氏,“通《孝经》、《列女传》”。[6]781澄迈庠生李璟妻吴氏,“教子文炯为邑名士”。[4]1607定安王昌言妻陈氏,“侍父读书,素谙义理”。[21]424-427以上所举,皆为烈女节妇。至于其他知识女性,则不知其凡几。
尤其是,明代本岛破天荒出现了冯银、丘夫人、林淑温、黎瑜良、苏微香等五位女诗人,皆为琼山县的家庭主妇。其作品均收入明末陈是集编的《溟南诗选·闺媛诗》里。[22]303-310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冯银,该书收录其《五言绝》诗3首,《七言绝》诗1首。明代本岛举人王佐称其“博通经史,尤隐约深厚,谨守礼法,有古幽闲淑女之风”。[23]429
表现之九 ,各种楼亭、坊表和名胜古迹及名人墓葬多。据旧志记载:明代为纪念先贤、名迹及胜事而兴建的楼、阁、亭、堂、轩等各种建筑物,全岛共有61座,其中琼山20,澄迈2,文昌2,临高1,儋州20,昌化2,万州5,崖州9。明代为表扬科第和旌贤励俗而建立的各种牌坊,全岛共有414座,其中琼山180,澄迈33,文昌27,定安30,临高 10,会同 11,乐会 9,儋州 26,昌化 14,万州 27,陵水 5,崖州 29。[6]176-196明代全岛各种名胜古迹共有 556 处,其中琼山123,澄迈42,定安 32,文昌44,合同 26,乐会 12,临高 29,儋州 63,昌化 19,万州 80,陵水29,崖州41,感恩16。[4]483-531清代以前的名人墓葬全岛共有 96 座。[4]531-541众多的楼亭、牌坊和名胜古迹及名人墓葬,反映了明代海南岛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上情况正如明代本岛先贤王赞襄在廷试对策中所说:明代海南“衣冠文物彬彬然与中州等”。[21]424-425
表现之十,明代海南岛被称为“海边邹鲁”或“海外邹鲁”。所谓“邹”、“鲁”,皆为古国名,其都城故址分别在今山东省的邹县和曲阜。因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后世遂以“邹鲁”作为文化教育兴盛之地的代称。明代由于海南岛文教发达,人才辈出,故也享有“海滨邹鲁”或“海外邹鲁”之称。如:明代邱濬《重建琼山县署记》云:“予尝在吾乡僻处遐外,而海内士大夫未尝以遐外视之,评其艺文俗尚,则曰海边邹鲁。”[6]819又明王佐《赠吴肃里正周年序》云:“国初,琼俗敦朴礼文……当时南北之士,莫不景仰吾琼为海外邹鲁。”[23]330又清代琼州知府贾棠《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志序》云:“明初改郡统之,生齿日繁,人文蔚起,至号为海滨邹鲁。”[4]5-6
二 明代海南文化发展的原因
明代海南文化之所以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由于明王朝对海南岛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经略。历史和现实都已充分证明,任何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都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密切相关。明代海南文化之所以获得高度发展,其首要原因也当是如此。明朝中央对海南岛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经略,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明太祖认识到海南岛战略的位的重要,彻底改变对本岛的传统看法。在明代以前,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轻视甚至丑化海南岛,把本岛作为罪犯和贬官的收容所,以致唐宋时期曾成为仕宦畏途。但到了明代,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如《明太祖实录》卷48载:洪武三年正月壬寅,“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广东儋、崖等处。’上曰:‘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17]8可见明太祖朱元璋是反对把“罪人”驱逐到海南岛的。不仅如此,明太祖还大力赞美海南岛。如他在《洪武二年十一月宣谕海南》的诏令中说:“海南、海北之地,自汉以来列为郡县,习礼义之教,有华夏之风。”他又在《劳海南卫指挥》敕里说:“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数千里。历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热少寒。……今卿等率壮士连岁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劳。”[6]792明太祖赞美海南岛为“南溟奇甸”,并遣使赍敕慰劳海南岛最高军事长官——海南卫指挥,说明他认识到海南岛战略地位的重要而给以高度的重视和期望。明太祖以上诏谕,代表了明朝统治者对海南岛的积极态度,使海南人尤其是年青学子,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慰藉,从而对明王朝的衷心拥护,并激发起勤奋读书、报效祖国的热情。如明代海南先贤邱濬和王佐,曾分别作《南溟奇甸赋》和《南溟奇甸歌》,[6]852-859对明太祖的《劳海南卫指挥》敕给以高度的评价,盛赞明太祖的英明。明代海南岛之所以出现人文昌盛的局面,与明太祖以上诏谕对本岛的高度赞美显然也有密切关系。这正如万历《广东通志》所说:“逮我明兴,高皇帝以为南溟奇甸,往往振作焉。自是鼎臣继出,名满神州。”[11]446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说:“琼本海中一大洲,去中国绝远,自孝陵称为奇甸,人文因以奋兴,若海公瑞清刚正直,又为琼之特出者。惟奇甸故产奇人。”[13]285
二是从民族众多的广西行省割出海南岛,改隶于广东行省。据《太祖实录》卷43载:洪武二年六月戊子,“以广西海南、海北府州隶广东省。”《明史·地理志六·广东》也载:“洪武二年三月,以海北海南道属广西行中书省。四月,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六月,以海北海南道所领并属焉。”按上所载,则海南岛在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后,改隶于广东行省。广东居民以汉族为主,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广西。明朝把海南岛从广西划出而改隶于广东省,显然有利于带动本岛经济文化的加快发展。
三是加强对海南岛的治理,先后在岛上设置众多的管理机构。明朝先后在海南岛设置众多机构:属于中央和广东省驻琼机构的,有察院、布政分司、海南兵巡提学道;属于行政机构的,有—府、三州、十三县及诸土司;属于治安机构的,有二十七巡检司;属于军事机构的,有海南卫、琼崖参将府等。[24]管理和统治机构的增多,加强了对海南的治理,不仅为发展海南经济文化提供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也有利于推行教化。这从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明成化间海南道副使涂棐广建社学179所。[6]312二是万历七年,朝廷采纳翰林院检讨王弘诲“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的建议。[6]290,797-799此后,凡由提学主管的岁考和科考等考试,只在岛上举行,琼士大为称便。这显然有利于促进本岛文教事业的发展。
其二,由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在海南岛设立地方政权,并进行直接统治和管理,使中原文化得以在本岛长期传播,对海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南岛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本岛土著居民就已归向于中原王朝。古籍记载表明:唐虞之世,海南岛称为南交之地。夏商周三代,海南岛在《禹贡》扬州或古扬州之域内。春秋战国时期,海南岛为扬越地或百越地。秦代,海南岛属象郡地。秦末汉初,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时,在海南岛上设立珠崖、儋耳二郡和十六县。此后,中原王朝一直在海南岛设立地方政权。从隋代开始,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海南岛的统治和管理,设置的统治机构越来越多,如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全岛分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和十四县,三郡均直属中央政府,并督于扬州司隶刺史。唐代,先后在岛上设立三个都督府(即崖州、琼州、镇州都督府)、七州(崖、琼、振、儋、万安、忠、镇)和二十六县,隶属于岭南节度使。[24]1-180由于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在海南岛设立地方政权,并进行直接的统治和管理,在岛上推行封建制度和教化,使中原文化得以在岛上长期传播,对本岛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广东和海南许多旧志中都有记载。诸如:
正德《琼台志·风俗》引《宋进士题名记》载:“琼管在古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朝,文化始洽。”所谓“文化始洽”,意为至唐朝宣宗在位时期(847-859年),文化教育已经普及全岛各地。同卷又云:“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5]138-139此又见万历《琼州府志·风俗》、道光《琼州府志·风俗》等。
万历《广东通志》卷57《琼州府·风俗》载:“琼居海外,民性朴茂,习礼义,有华夏之风。……郡城之中尤多近古,如婚礼迎门、见庙诸多仪文,不异中州。”[11]454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卷21《风俗》也载:“琼郡地居海外,民性朴茂,习礼义,有中土之风。”[25]241
上文所谓“皆秦旧俗”、“不异中州”、“有中土之风”等,都说明海南岛居民的风俗习惯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地区差不多。而“风俗”属于狭义文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中原王朝长期在海南岛设立地方政权,没有中原文化在本岛的长期传播,就不可能出现明代海南文化的昌盛局面。换言之,明代海南文化的昌盛,就是中原文化在本岛长期传播的结果。
其三,由于秦汉以来大陆汉人不断迁入本岛,逐渐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使汉族文化成为海南文化的主流。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在岭南地区和海南岛建立地方政权,祖国大陆各地的汉人,或宦或戍,或迁或商,或谪或流,纷纷迁入海南岛。汉武帝时,海南岛已有民“户二万三千余。”[2]2135这些民户,显然都被编入西汉政府的户籍,属于所谓“编户齐民”。每户若以5口计算,则有11.5万多人。他们应当多数是秦汉以来从大陆各地迁移来的汉人。因为当时汉朝统治阶级根本不把岛上的黎族先民当人看待,诬蔑他们为“禽兽”、“鱼鳖”,因而不可能把他们编入西汉政府的户籍。从隋代开始,随着中央政权不断加强对海南岛的治理,从大陆迁入的汉人也不断增多,使汉人成为本岛居民的主体。至元代,全岛各州军共有户 92,244,口 166,257。[26]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岛有户68,522,口 291,030。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全岛有户 56,892,口 250,524。[6]230-231这些编入政府户籍的户口,也应当多为汉人。因为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起,明朝才开始在海南开展抚黎活动,黎人始逐渐归化。[8]8272人脑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文化可以随着人口的迁移而转移。这些来自大陆的汉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且不断改良岛上的人口素质。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陆许多著名文官先后被贬谪或流放到本岛来,如唐代的王义方、韩瑗、敬晖、李邕、李昭德、韦执谊、李德裕,杨知至、韦保衡、刘崇鲁等,宋代的卢多逊、丁谓、苏轼、任伯雨、李光、胡铨、赵鼎等,他们在岛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播中原文化,为海南社会进步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如宋人苏轼《伏波庙记》说:“白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6]543-544明丘浚《南溟奇甸赋》也说:“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国,而与四方髦士相后先矣。”[6]580由此可见,大陆汉人的不断迁入,对海南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使中原文化或汉族文化成为海南文化的主流。
其四,由于唐宋以来海南岛文教事业的发展,为明代文化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任何事物一般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并非骤然兴起,文化发展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有必要介绍明代以前海南文化的发展情况。考诸史籍,唐代海南岛文教事业当已兴起。主要理由或证据有七:
一是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州县都普遍设立了各级各类官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①详见《唐会要》卷35《学校》、《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州县官员》、《新唐书》卷98《儒学上》及卷49下《职官志四下·州县官员》、唐人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l儒教》、宋人郑樵《通志略·选举略第二·学校》等。唐朝既然在海南岛设立众多的统治机构,并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制度,进行直接管理和统治。②详见《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七上》;拙著《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第153-180页。按理,唐朝在海南岛也应当建立官学。
二是武则天时,既然海南岛和大陆各州一样都奉命建造佛寺。③参见唐代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唐会要》卷48《议释教下·寺》。按理,唐代本岛各州也应当奉命兴建学校。
三是唐初王义方被贬为吉安县丞时,尚能在黎区召集黎族子弟传授中原文化。④见《旧唐书》卷187上《王义方传》。由此可知,当时本岛汉区的州县官员,肯定不会对岛上的汉人子弟置之不理,何况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就是推行封建教化。
四是唐代珠崖人何履光,在唐玄宗、肃宗朝先后担任都督、特进、左武卫大将军、岭南节度使等高级职务,时人称之“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⑤《 见《太平广记》卷464“南海大鱼”条引《广异记》;《全唐文》卷402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新唐书》之《玄宗纪》、《南蛮传·南诏》、高祖诸子传·虢王凤》、《鲁炅传》;《旧唐书》之《李巨传》和《鲁炅传》等。他能够胜任这些重要职务,说明他肯定不是文盲,其文化知识当是年青时来自故乡的文化教育。
五是正德《琼台志·风俗》引《宋进士题名记》载:“琼管在古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朝,文化始洽。”意谓至唐朝宣宗时期(847-859年),海南岛的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全岛各地。
六是北宋苏轼在谪居昌化军时所作《和陶示周掾祖谢》诗:“游城东学舍作。闻有古学舍……”⑥苏轼《和陶示周掾祖谢》诗。见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银河出版社,2006年,第19页。所谓“古学舍”,昭示其历史悠久,古已有之。这说明早在苏轼贬儋以前或北宋以前,儋州地区已建立了学校。
七是北宋宰相卢多逊《水南村崖州为黎伯淳题赠》诗云:“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6]866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卢多逊被配流崖州,雍熙二年(985年)卒于贬所。其诗中的“水南村”,在今三亚市崖城镇。该村曾是唐代振州、北宋崖州治所故址和卢多逊、赵鼎、胡铨等名人贬所。所谓“犹有幽人学士家”,意谓水南村黎伯淳之家乃书香门第。这说明在北宋以前水南村一带的文教事业已有一定的发展。
以上史实表明:唐代海南岛当已建立了学校,文化教育开始兴起。
宋代,海南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旧志记载,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本岛各级地方政权陆续建立起官学,计有州学4所,县学11所,书院2所,社学2所。⑦参见万历《琼州府志》卷6《学校志》、道光《琼州府志》卷7《学校及书院》、康熙《琼山县志》卷4《书院》。此外,还有1所官立民族学校“新学”。⑧见《舆地纪胜》卷124琼州。两宋时期,全岛共有进士12人,举人13人,制科(贤良方正)2人,诸科40人(举文学6、举人材2、荐辟32),并出现一位全国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诗人和书法家白玉蟾。⑨详见道光《琼州府志》卷26《选举志》、卷36《人物志》。至于宋代海南各种著作,至少有37部,其中地方志4、海南人著作 19、贬官著作 14。(10)参见《宋史》卷204至卷209《艺文志》、《舆地纪胜》卷124琼州、《道藏》、道光《琼州府志》卷43《书目》、万历《儋州志·艺文志》、万历《琼州府志》卷11《艺文志》等。
元代,海南文化教育继续发展:沿置州学1所、军学3所、县学11所和书院1所,增设县学2所、社学3所。(11)参见正德《琼台志》卷15-卷17、万历《琼州府志》卷6、道光《琼州府志》卷7。还在新附黎区“分立黎学,谕教新附”。(12)元代邢梦璜《至元癸巳平黎碑记》。见光绪《崖州志》卷19《艺文志》。科举方面,因元朝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和海南士人对元朝大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故进士空白,举人仅有2人。但诸科较多,全岛共有 77 人。[6]614-617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文化的发展更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何况明代海南各级学校大都是沿用前代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唐代以来海南文教事业长期发展的基础,就不可能出现明代海南文化的盛况。
其五,由于科举制度给海南学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大好机会。科举制度实行到明代,虽然存在许多弊端,但对于边远地区来说,其利仍然大于弊:不仅有力地促进边远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给边民子弟进入仕途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竞争和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明代海南科举中式者,几乎都是平民子弟,富家子弟或官僚子弟可谓风毛麟角。他们能够进入仕途和不断晋升,几乎都没有任何靠山或社会背景,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奋斗。试想,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那么,明代海南岛能够出现那么多人才吗?先贤丘浚、海瑞等人能有机会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纵情驰骋吗?
其六,由于明代海南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文教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明代,由于大陆移民的增多和明王朝对本岛的大力经略,使海南经济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明代海南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全岛耕地面积,元代只有15,519顷。明洪武二十四年有19,856顷,万历十年有36,763顷,万历四十五年有 38347 顷。[6]232-237比元代增加 2,782 顷。二是田赋数量比元代增加。元代全岛征收田赋米16511石。洪武二十四年全岛征收 96,384石,比元代增加 79,873石。[6]233-235三是水利建设事业有较大的发展。明代本岛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岛兴修各种大小水利工程共有 148 处。[6]95-108共灌田 7,140 顷。①见明郭棐《粤大记》卷29《水利》。黄国声等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1页。
明代海南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墟市多。明代全岛共有墟市 192 处。[6]211-214墟市多,说明商业繁荣。
二是桥梁、津渡多。明代海南岛共有桥梁130座,开辟津渡共有79处。[6]196=210俗话说,“津渡设而涉川利”。可见广辟津渡,不仅便利交通,而且更有利于货物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工商业税收的增加。洪武初,全岛各项工商业税收共有银807两余。万历间共有银1,268两余,比明初增加银461两。此外,每年还征收鱼课银1,870两、盐课银1,876两,其数量远远高于商业税。[6]251 -252、258
由于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文教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后盾。据万历《琼州府志》载:明代全岛各级儒学学田,平均每年收租米共有5,585石,折银2,807两余,“作为师生俸廪、香烛之用”。[6]247明制规定,“拔赐学粮,府学岁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以供师生俸廪祭费。”[6]287办学经费的充裕,显然有利于文教事业的发展。
其七,由于明代海南地方官重视发展文教事业。明代,由于朝廷对海南岛的重视,加上有不少海南士人先后在朝廷担任要职,尤其是先贤丘浚和王弘诲曾先后分别担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和南京国子监祭酒,其门生故吏遍天下,因而被朝廷选派到海南的地方官大都重视和热心发展海南文教事业。除上文提到的副使涂棐外,还有许多值得表彰者。如万历《琼州府志》载:“宋端仪,莆田人,提学佥事。崇正学,考校一时,号称得士。”[6]571林如楚,福建侯官人。“以按察使分巡海南。厘剔诸弊,注意学校,课土先德行而后文艺,有不率者辄三尺绳之,士行、文风翕然丕变”。[6]572蔡梦说,福建龙岩人。以宪副备兵督学,“阅诸生会课,谆谆提诲,外州县赴者优之饩,而时简其败群”。[6]572-573王伯贞,泰和人。“在郡十五年,辟田野,兴学校,政教大行”。[6]577张俊,吉水人。嘉靖间守琼时,“尝刊《四礼节要》,以易琼俗。创立崇文书院,以萃英贤”。[6]578-579张子弘,庐陵进士。“历郎中,擢守琼,冲雅清廉,政尚宽厚,持大体,尤加意斯文。建县学文庙,立各关社学”。[6]579吴俸,浙江庆元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抚黎通判。“建水会所社学,取府学弟子员教黎童习读,黎人因此知学”。[6]580-581罗杰,南昌人。成化九年(1473年)知儋州。“廉政公勤,兴学校,黜淫祠,疏水利,驯生黎,鼎新公廨、桥梁,儋之民风文物丕变。”。[6]583李恭,湖广宁远人。弘治间知万州,廉明公恕。“士有俊秀者,课试资给”。[6]584贺沚,庐陵人。万历甲申(1854 年)知文昌。专尚德化。“开玉阳书院,亲与诸生讲学课艺,一时文风丕变”。[6]590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明代海南文化的兴盛与地方官员重视发展文教事业密切相关。
其八,由于明代海南成才士人及乡绅、乡儒热心家乡文教事业。明代海南府州县儒学均为官办,但也有部分书院、义学和社学是由本岛乡绅、乡儒或成才士人创建的。明代本岛先贤,几乎每个都能奋发图强,苦学励行,勇于进取。他们成才以后,还把兴学育才、栽培后学作为己任。诸如:国子学正曾宝,洪武年间在儋州天堂都创建义斋书舍。“训乡子弟,买田五十亩,以给来学之贫者”。[27]119举人徐祜,在儋州城东建湖山书舍。“延儒士梁成为塾师。”[27]119
举人唐维,在儋州城西北十里建玉山精舍,“为藏修之所”。[27]119贡士陈文徽,正统年间在琼山县东五里创建桐墩书院,“会乡子弟讲学。”[5]392举人李金,成化初在澄迈县倘驿都率建秀峰书院。[4]350大学士邱濬先在琼州府城西北隅创建奇甸书院。[4]339后又在琼州府学堂后建藏书石室,将平生所珍藏之书存放其中,让家乡有志于学问之后生小子,“于此取资焉”。[6]288、811侍郎唐胄,正德年间在琼州府城东创建西洲书院。[5]394参政郑廷鹄,嘉靖年间在琼山县博崖都西湖上创建石湖书院。[4]339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万历间在定安县创建尚友书院。[4]354给事中许子伟,在琼山县西建敦仁义学,在儋州城外东南隅建许氏义学,在儋州城内建兰村德义书馆,并捐款在京师创建琼州会馆,供琼士赴京应试前住宿之用。②参见万历《琼州府志》卷6《学校志·乡义学》及卷10《乡贤》、万历《儋州志·书院》、道光《琼州府志》卷7《书院》等。户部主事何其义,捐赀拓建京师琼州会馆,以便琼之赴京者。[6]742
明代本岛乡绅、乡儒也积极办学或聚徒讲学,培育家乡子弟。诸如:琼山县士人吴效,弘治末在府城南道义衢西宰建南关精舍。琼山县乡绅林有鹗,在琼山县西建敦仁义学。[6]314澄迈县乡绅曾惟唯,在那杜都建义芳垫。[6]314乐会县乡绅明王鸿序等,合力创建东荣坊、崇文乡等 12 所社学,以训子弟。[4]361-362临高县乡绅,崇祯十三年(1640 年),在城内城隍庙左捐建通明书院。[4]363-364儋州乡儒陈瓒,在州西二十里薛官都建松台书屋,以教授子弟。[27]119儋州乡儒王勉,在州西四十里建龙溪耕读轩。[27]119琼山县乡儒唐英(唐舟之父),“博通经史百家之学,尝筑义学,教乡子弟十余年,不计束修”。[6]703琼山县乡儒曾应唯,“尝构义芳堂,郡乡族弟子日讲习修身齐家大义”。[6]757琼山县乡儒邝信,“力学笃行,设家塾教子弟”。[6]754琼山县乡儒吴恪,有君子风。“始训晋庠,不责生徒修贽”。[6]756
琼山县乡儒蔡廷椿,“居乡训戒子弟,捐田四十亩为灯油”。[6]759崖州乡儒纪纲正,“教授生徒,表正乡里,崖士出其门者,多苦学励行”。[6]757琼山县乡儒王宏,“开乡塾,训子弟数十年”。[6]76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明代海南文化的昌盛,与本岛成材士人及乡绅、乡儒们热心家乡文教事业也密切相关。
其九,由于明代海南各级学校有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人才之兴,主要靠学校培养,而教师的综合素质至为重要。明代海南各级学校不乏优秀教师。诸如:全国学术界名流、入选《明史·文苑传》的赵谦曾长期担任琼山县学教谕。赵谦(原名撝谦),余姚人。博洽经史、百家之学,尤精六书,时号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1379),召至京师修《正韵》,时年二十八,授中都国子监典簿。后为琼山县学教谕,造就后进,一时士类翕然从之,文风丕变。守令为之筑考古台于学右,为著述之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卒,年四十五。所著有《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造化经纶图》、《学范》、《历代谱赞》等书。①参见《明史》卷285《文苑传·赵撝谦》、万历《琼州府志》卷9《秩官志·名宦·教职》。徐益,丰城人。“博通经史,尤长于诗赋,为乡校师数十年,造就者众,若尚书薛公远辈皆出其门”。[5]728杨升,永嘉人。通《春秋经》,博洽能文。“举临高校官。后以老谢政,与郡守王伯贞过密。尝改补蔡止庵《琼海方舆志》,文行冠于一时”。[5]728蒋科,电白进士,教谕琼山。“笃意校文,以器识为先。捐赀修学,移建御书阁于讲堂”。[6]591郑济,闽县人,永乐间儋州学正。“日与诸生论讲不倦。曾著《四书书经讲说》,传于世”。[6]591林璟,漳浦人。永乐间由举人谕乐会。“博闻多识,训诲有方。后升监察御史,祀于祠”。[6]591周坦,莆田举人。“正统己未训定安,讲解寒暑不替,诸生有贫乏者悉心周给。邑人吴汝逊遣诸子从学,继而子孟矩、孟球、孟传相继登科。后升武陵教谕。所著有《经书讲说》、《续古千字文》等书传世”。[6]591黄溁,潮阳人,成化间万州学正。“教谕有方,士习用变。先是,本学《书经》无传,溁授诸生习读,登仕籍者数人,祀于祠”。[6]592韩鸣金,广东博罗人,教授府学。“博洽经史,工于诗文,勤课艺,精品骘,动由礼度”。[6]593方圯,福建莆田人。弘治年司训澄迈。“操履端方,博学洽闻。以《书经》授弟子,外庠亦趋受业。升汾水谕,寻升国子助教、南康府判”。[6]594黄鹏,茂名人。“任昌化谕,师模端正,信义服人,捐俸金以置学田,贫生德之”。[6]593唐衡,琼山人。“通经学博,善古文。洪武初,以经明行修起为府学训导,后升都司断事”。[6]754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明代海南岛之所以出现人文昌盛的局面,显然与以上名师的辛勤教诲密切相关。
明代海南岛之所以出现人文昌盛的局面,无疑是上述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47-35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35.
[3]李勃.汉元帝罢珠崖郡后海南岛之归属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121-123.
[4]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5]唐胄.正德琼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6]欧阳灿,等.万历琼州府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
[7]郝玉麟,等.雍正广东通志[M].纪昀,等.四库全书,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本.
[8]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印出版文渊阁本.
[9]金鉷,等.雍正广西通志[M]//纪昀,等.四库全书(文渊阁),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嵇曾筠,等.雍正浙江通志[M]//纪昀,等.四库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印出版文渊阁本.
[11]郭棐.万历广东通志[M]//纪昀,等.四库全书存目.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纪昀,等.四库全书存目.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7]唐启翠.明清《实录》中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8]林平,等.明代方志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9]黄荫普.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M].香港:香港崇文书店,1972.
[20]骆伟.广东文献综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21]李光先,等.嘉庆澄迈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22]陈是集.溟南诗选[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23]王佐.鸡肋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24]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25]金光祖.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26]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7]曾邦泰,等.万历儋州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A Probe into th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inan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Causes
LI B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The Mi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ainan,as is manifest in ten aspects:firstly,the establishment of numerous schools;secondly,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ccessful students in the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thirdly,the emergence of“renowned ministers and the spread of their fame far and near”;fourthly,two natives of Hainan respectively in charge of two highest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 the Ming Dynasty;fifthly,the inclusion of nine natives of Hainan inA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sixthly,the publication of numerous works of various kinds;seventhly,a veneration for prevailing customs,ceremonies and propriety as well as for learning;eighthly,the occurrence of numerous literate housewives and of five poetesses like Feng Yin,etc.;ninthly,the rise of various pavillions,places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terest,and of tombs of numerous celebrities;tenthly,the acclaim of Hainan Island as a“seaside land of cultural prosperity”.There are nine reasosn for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Hainan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being the great attention to and support for Hainan Island by the Ming imperial government
the Ming Dynasty;Hainan culture;reasons of development
K280.7
A
1674-5310(2011)-05-0111-09
本文系海南省社科联2009年立项课题“海南编年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NSK 09—24。
2010-11-02
李勃(1957-),男,海南万宁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海南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胡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