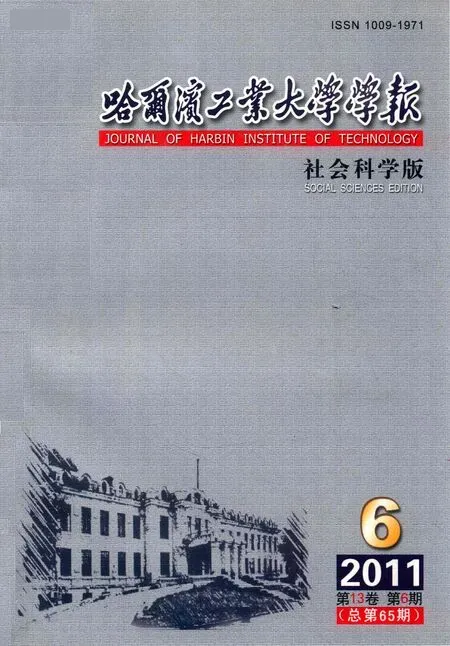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历史变迁
2011-04-07李文祥
李文祥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历史变迁
李文祥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清代早中期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模式呈现为“贵族权利”型,局限于进入八旗的鄂伦春子弟,其根基在于鼓励、管控、培养统治阶级同盟者的需要。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教育福利模式呈现为“平民扶助型”,面向全体鄂伦春子弟提供接受教育所必需的扶助,其根基在于抚绥、管控鄂伦春族民众的需要。新中国以来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模式呈现为“民族优惠型”,面向作为少数民族的鄂伦春子弟提供优惠性的教育福利,其根基在于贯彻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需要。
鄂伦春族;教育福利;模式转型
鄂伦春族是世居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长期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直到库页岛的辽阔土地上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从清代开始,面向鄂伦春人的教育福利制度陆续出现,并伴着从清代到民国及伪满、新中国的历史演进而不断变迁。这其中既有福利保障对象逐渐拓展与福利保障水平螺旋式上升,也有福利模式的变迁及福利根基的转换。
一、清代早中期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
清代早中期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首先是隶属于国子监的专门教育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制度,是为教育八旗子弟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亦称旗学、满学或满官学。八旗官学的教育内容为国语骑射,包括进行八旗制的组织纪律、作战技术方面以及学习满语、蒙古语等的教育和训练。
与鄂伦春人相关的清政府的八旗官学主要是黑龙江西部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黑龙江地方的官学和东部宁古塔、三姓地方的官学。八旗官学的保障范围较窄,仅仅限于少数上层子弟。墨尔根官学为最早面向鄂伦春族的旗学,也是鄂伦春族教育福利保障之始。1695年3月15日,根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建议,清廷决定在墨尔根地方设满洲官学两所,设助教,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教习书义。而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康熙三十四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应于默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应补教官之人,该将军选择优长者,将姓名咨送吏部。其教官照京师例,称为助教。学舍,该将军拨给。”[1]《黑龙江述略》对墨尔根两翼官学的记载更为详细:“设助教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教习书艺……有同额缺,凡八旗子弟愿人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2]26-27。《墨尔根志》对此亦有记载,“满官学三间,大门一间,照壁一座,以及缭垣,康熙五十八年建。在东门内。设教习学官一员,由笔帖式内选用,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出考,送部引见。额定学生十六名,由每佐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有文艺、清语稍通者,各司挑充帖写”[3]。
齐齐哈尔、呼兰、黑龙江等地方旗学情况与墨尔根相类似。据《黑龙江述略》记载,“齐齐哈尔、呼兰、墨根、黑龙江四城,均设满学官一员,有同额缺,凡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习清文骑射,日不过一二时为率,多至百有余人。”[2]26又据《黑龙江外记》:“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八旗官学,各草堂五楹。”[4]18齐齐哈尔官学建于康熙年间,校舍5间,位于城东门外,官学生每年学额40名。呼兰官学位于呼兰府城内大街之西城守尉府,“教习一员,道光十四年设。由旗营长官保充,以无品级笔帖式拣补,兼差,无俸廉。三年期满,送部引见,以本旗骁骑校补放。”[5]
宁古塔的官学肇始于康熙十五年,当时被赐名曰“龙城书院”。后清政府又在宁古塔城东南建左右翼官学。根据《吉林外纪》记载,“在城内东南隅,学舍六间,雍正六年,公捐营建。乾隆五十七年,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六名”.[6]84雍正五年(1727)三姓地方承准建左右翼官学,官学设址于旧文庙之内,增修东西厢房共六间,设教官一名,每年收学生四名。《吉林外纪》对此也有所记载,“在城内东南隅,学舍六间。雍正十二年,公捐营建。乾隆十七年,奏请官项修葺。八旗每佐领每岁额送学生四名”。[6]84雍正九年(1731),宁古塔将军常德疏言,宁古塔助教,请照驿站官之例,定限六年。年满之后,令该将军出具考语,具题送部,其由八品笔帖式补授者,以主事等官用,由无品笔帖式补授者,以七品小京官等缺用。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规定,宁古塔等处官学教习,须清文熟习之员,向由官学生内挑补,如一时不得其人,请即于帖写马甲内,通融选补,三年期满,教课有方,报部以笔帖式补用。八旗官学尽管保障范围较窄,只限于少数上层子弟,但其保障水平高。清政府对黑龙江地方的官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经常予以检查,而且“满官学生岁给膏火银二两。”[4]32
八旗官学受规模所限,仍有众多八旗子弟不能入学。为此,清政府又设立八旗义学以为补充,从而拓展了教育福利保障的范围。八旗义学隶属于各旗参领,大多建立于驻防城内,主要是官兵倡建或捐建,生源主要以鄂伦春等新满洲子弟为主。清政府鼓励义学的设置,对其由当地八旗衙门、将军、副都统按官学制度进行管理。针对鄂伦春族的八旗义学以齐齐哈尔义学为早,嘉庆元年(1796),“宗室永琨为将军,选齐齐哈尔八旗子弟二十人,从龚君光瓒习汉书,岁给束脩八十两,柴炭费二十余两。”[4]32但较之官学,齐齐哈尔义学相对简陋,“初用御史府空舍,后将军那启泰以为御史奉裁,旧府当毁之,生徒乃就教者私寓受业,十余年来学虽不废,而讲肄迄无定所。”[4]18同时,齐齐哈尔义学对学生资助较少,这造成学员的日益匮乏。齐齐哈尔义学“生徒之额遂不足,虽补送之令,户司时下,八旗虚应故事而已。说者谓满官学生,岁给膏火银二两,义学生无之,然则满官学生尝溢额,义学生尝不足额,膏火有无所致也。”[4]32
二、清末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
清末,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尽管只有较之清代早中期的保障水平大为逊色,但毕竟逐渐褪去了清代早中期的封建化特征,首开鄂伦春族现代教育福利制度之先。
直到清光绪早年,鄂伦春族教育福利保障仍然维持着清代早中期的传统。清光绪八年(1882),在“东接黑龙江,西达墨尔根内兴安岭太平湾兴建兴安城,设立总管衙门,并照布特哈总管衙门体式修置,另设官学一所。”[7]103但自清政府新政开始,与办实业、练新军相互呼应,也开始了举办学校教育的革新。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朝野上下,一时谈论‘新政’者,莫不以为‘欲振兴地方,非开通民智不可,欲开通民智,非兴学校不可。”’[7]103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参照西方教育制度的基础上,颁布《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三年;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8]25“论教育之正理,自宜每百家以上之村即应设初等小学堂一所,令附近半里以内之儿童附入读直;惟僻乡贫户,儿童数少,不能设一初等小学学堂,地方官当体察情形,设法劝谕,命数乡村联合资力,公设一所,或多级或单级均可。初办五年之内,每二百家必设初等小学一所。”[8]26
在此背景下,东北边疆的鄂伦春族地区也开始推行新式教育、兴办新式学校,黑龙江等地的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由此得以肇始。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瑷珲、墨尔根、西布特哈设立初等小学,在东布特哈创设初级师范预备科。”[9]19吸纳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子弟就近入学。这些学堂多为私塾或私塾改良性质,教学也不正规。多是教习生字或启蒙课本,教学方法欠佳。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毕拉尔路协领庆山始创办毕拉尔路蒙养小学堂,并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2月开学。“招收鄂民学生20名,聘有兼通满汉文语言教员一员。”[10]“办学的经费,刚开始时从补发鄂伦春官兵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的俸饷共三万余吊中开支;后来则由黑龙江度支司拨款专项。庆山兼任毕拉尔路协领的时间不长,同年即由鄂伦春人佐领全德升任拉尔路协领。他仍继续‘设学校以兴教育,拨生计地以劝农,悉心抚绥,冀策实效。’”[8]29-30学生伙食费自理,书本,笔砚文具由该路傣饷费内发给。校址设于协领公署驻地车陆屯(今逊克县内)。这是黑河地区鄂伦春族单独设学之始,也是中国最早兴办的鄂伦春族小学[11]38。尽管福利保障的水平下降,但福利保障的范围由少数上层的鄂伦春子弟转换为一般的鄂伦春族子弟。兴办两年之后,由于经费用尽等原因而停办。
而呼伦贝尔城原来也设有一所官学,在举办新式学校的浪潮下,呼伦贝尔城官学先是被“改为初等小学堂,后来又改为初小、高小都有的‘两等小学堂’,即完全小学。学生由附近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蒙古等各旗挑选,教员由黑龙江提学司遴选派往。该校学生名额每年为六十人,以后按年添班。学校的开办经费‘于蒙古报效银两项下拨发’,常年经费‘就地由牲畜皮毛新捐筹给’。这是设在鄂伦春族附近城镇的招收包括鄂伦春族儿童入学的规模较大的新式完全小学校。”[8]27
清政府不仅为鄂伦春族提供了教育福利,对少数民族新式教育的管理也较为严格,这可从视学员对学堂的视察情形中可见一斑。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墨尔根城视学员刘振声视察博尔多拉哈两站学堂。他在禀文中写道:“该站学堂常年经费,按该站二千余垧地亩筹划。该站有私塾一处,学生郭全发等六名,先生裴仲裕,年逾六旬,嗜好洋药,文字不通,每日仅教诸生读百家姓而已。似此教育,未有不误人子弟者。”[12]177
三、民国及日伪时期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在鄂伦春族地区颁布《鄂伦春族国民教育简章》,规定与普通国民教育不同的措施和方法,进一步强化了鄂伦春族教育福利,其核心是公立鄂伦春国民中小学的官费生制度。民国二年(1913),根据第四学区视学邹召棠的建议,黑龙江省教育司向内务部、教育部咨请建立鄂伦春小学,内务部、教育部批准其在呼玛、瑷珲、嫩江三县各设一所鄂伦春族学校,训令中明确了针对鄂伦春族学生的福利保障[12]178。
民国三年(1914)4月1日,黑龙江省立第三鄂伦春国民学校在嫩江开学。8月20日,黑龙江省立第二鄂伦春国民学校开学,“此日该校高悬国旗,凡本屯有学生之家长及鄂伦春素孚众望者皆被邀请来校参观,诚为车陆屯空前之奇观。其后学校即特请俄国医生为学生引种牛痘以防天花”[11]39。从民国四年(1915)起,宏户图、爱辉、嫩江、车陆等地先后办了多所鄂伦春族小学校。“1915年7月1日,库玛尔路宏户图第一鄂伦春小学开学。有官费生30人,草正房5大间,全年经费大洋3 348元。”[13]19“1920 年,民国九年5月,设在哈尔通的库玛尔路公立第一鄂伦春国民中学成立,校舍有草正房5间,学生25人,住宿5人……同年,设于迈海的库玛尔路公立第二鄂伦春国民学校开办,有租草正房2间,学生 15 人。”[13]19
1920年,鄂伦春族初、高级小学校已增至8所,在校生达226人。鄂伦春族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汉族学校相同,由汉族教员教授汉语和汉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这些学校的建立使鄂伦春青少年受到较好的汉语汉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教育,培养了大量具有文化知识的鄂伦春族人才。
对于鄂伦春族学生的福利保障,也可见诸《视察鄂伦春学校总报告书》[12]214-216。
为优待鄂伦春族儿童求学,普通小学校也向鄂伦春族儿童提供教育福利。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七日,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郑林皋向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呈文:呈文中附优待鄂伦春学生规则[12]219-220。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鄂伦春实行“不开化其文化”的政策,多数鄂伦春族学校因经费短缺而停办,鄂伦春族教育福利制度在这段时期中断。“后来虽在小二沟、呼玛兴农村和爱辉九道沟鄂办起了三所学校,目的并非为了开展鄂伦春族人民的文化,而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的奴才,课程大部分是用日文,纯粹是奴化教育,开办的时间也很短。”[14]66
四、新中国以来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
新中国的成立迅速终结了鄂伦春社会的氏族公社状态,鄂伦春族从路佐制的原始氏族阶段一步跨入现代生活。1947年春,经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黑河地委在黑河成立了黑河鄂伦春协领公署。“1953年7月3日,中共黑河地委对鄂伦春族工作做出决议:鄂伦春族是一个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扶助他们是我们的根本政策”[13]30,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建设也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福利政策的一面旗帜。
1948年,內蒙古扎兰屯纳文中学开设鄂伦春族青年班,鄂伦春族学生衣、食、住全部由政府免费供给。同年,黑河鄂伦春协领公署在逊克、黑河、呼玛等城镇学校里成立鄂伦春子弟班,招收鄂伦春族学生,并对学生实行大供给制:每年发给冬衣、夏衣各一套,棉鞋、夹鞋各一双,袜子三双、两年一床被褥、皮帽一顶。另外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费35工薪分、文具日用品2工薪分,医药费实报实销。“鄂伦春族的学习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呼玛县为例;1948年在校生16人,到1952年猛增至94人。”[9]201953年10月1日,黑河市爱辉区新生村鄂伦春小学开学,27名儿童免费走进新学堂。随后,各猎民新村相继建立了小学,至1958年黑龙江全省鄂伦春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1961年10月30日,黑河专署民委在上报省民委《关于黑河区民族工作方面的几个主要工作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重新明确了对鄂伦春族学生的待遇问题:凡入小学的学生,免收学费、书费等。中学以上的学生除享受国家一等助学金外,每两年发给学生棉衣一套,每年发给单衣一套,并负责学生寒暑假回家往返路费,以及患病医疗费。同年,黑河专署民委送5名鄂伦春族学生到齐齐哈尔医士学校、民族中学学习[13]37。1963年,鄂伦春族定居 10 周年后,鄂伦春族各乡共建学校6所,在校生达360余人。“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黑河三乡共有鄂伦春族624人,而此时三乡所培养的大学生有14名,平均每44人中就有1名大学生。1990年全国鄂伦春族总人口为6 965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为191人(平均每36人中就有1名大学生);中专文化程度者为272人,高中文化程度者为575人,初中文化程度者为180人,小学文化程度者为2 034人,而此时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已下降至7.81%。走出深山不到4年(至1990年)的鄂伦春族,文化素质指标已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有了鄂伦春族第一位博士。”[9]20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新生鄂伦春族进一步制定了教育优惠福利政策。1981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1981]209号《关于解决鄂伦春族人民当前生活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其有对鄂伦春族学生发放助学金的规定。同时,鄂伦春族学生还享受加分政策与择校权利。另外,政府每年都有计划地在鄂伦春族教师中选拔学校中层干部,组织他们参加岗位培训,创造条件安排他们到城区学校挂职锻炼。不仅如此,国家还对新生鄂伦春族学生提供教育救助。
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还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以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鄂伦春族村调查资料为例:新生村有劳动力276人,近年来,按照上级工作要求,乡党委、政府结合“科普之冬”活动,聘请专家为农户讲解种、养殖技术,外出务工知识,组织农民工技能培训。2003年以来,共培训新生村农民651人次,转移劳动力240人,其中外出务工半年以上32人,年劳务收入20万元。①此资料来自2007年吉林大学赴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开展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
五、教育福利演进中的模式转型与根基转换
从清代早中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族的教育福利不仅在保障对象、保障水平上不断变化,还存在着福利模式上的转型。
清代早中期的教育福利制度可称之为“贵族权利型”模式。清代鄂伦春族被大量地编入八旗而成为“新满洲”,而清政府对旗人“特加恩惠以养瞻之。”[4]58作为八旗兵的鄂伦春人不仅在俸饷、田宅上远高于其他人,还大多拥有奴隶,其身份即相当于贵族。史载鄂伦春族较多聚居的布特哈地区被大量赐奴,“共家奴婢二千五百九十一名。”[15]而清代早中期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保障对象,都是身处八旗的鄂伦春族子弟。其保障水平也具贵族色彩,八旗官学“满官学生岁给膏火银二两”[4]32,八旗义学学生入学后,亦资其膏火、酌补衣履。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教育福利制度可称之为“平民扶助型”模式。清末教育福利的保障对象,就已拓展至处于游猎状态的鄂伦春人。这可见证于关于选择教员及学员的相关记载:即“学堂拟设兼通满汉文字语言之教员千员,以毕路牲丁不通汉语,非借满文、满语译解不能传其义理也。学生之额以二十名为率,选其资质稍为聪颖者入堂肄业。”[12]61毕路牲丁即处于游猎状态的鄂伦春人,而非以贵族身份存在的八旗军士。民国时期更是如此,不仅国家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还努力劝导鄂伦春族基层民众送子弟入学。而保障水平则以“扶助”为特征,教育福利的目的在于帮助贫苦的鄂伦春学子完成学业。清末是“学生之伙食令其自备,惟应用书籍、笔砚、柴薪、厨役等项,拟由该路俸饷内筹给”[12]61;民国则是“每人月给火[伙]食银四两,按十个月计算……每校柴炭、油烛、笔墨、纸张等费,月支二十两,全年二百四十两”[12]178。
新中国以来的教育福利制度可称之为“民族优惠型”模式,与“平民扶助型”的福利模式不同,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保障对象,是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的鄂伦春族同胞,教育福利作为少数民族福利,其保障水平由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具体规定。“少数民族劳动者……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16]毛泽东重视由国家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7]
鄂伦春族教育福利制度的模式转换,是整个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而其根基则在于不同时代的国家政策与战略的具体需要。
清代早中期将鄂伦春族以“新满洲的形式”纳入统治阶级行列,清政权给予鄂伦春族将士诸多福利,以鼓励、管控鄂伦春族将士,教育福利也在其中。1632年,镶红旗相公胡贡明就上奏建议设八旗官学。“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之事,反看做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若要他自己请师教广,益发不愿了,况不晓得尊礼师长之道理?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18]皇太极采纳此奏,鄂伦春族等各族部民遂成为守纪善战的八旗勇士,对清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贡献巨大。因此,清代早中期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根基,在于鼓励、管控、培养统治阶级同盟者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其模式呈现为“贵族权利”型,仅仅局限于进入八旗的鄂伦春子弟。
清末及民国初期,东北边疆的鄂伦春族处于旗佐废弛状态,鄂伦春族略知满语、罕通汉语,相反却多通俄语。在鄂伦春族同胞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与俄人日亲日近,与国人日远日疏,甚至有入俄籍,送其子弟入俄国学校者。俄人亦利用其愚蠢,甘言诱掖”等现象。”[18]178-179为巩固国防,清政府即在鄂伦春族地区兴办新式学校,并提供教育福利以吸纳鄂伦春族子弟入学。北洋政府更是在鄂伦春族地区颁布了《鄂伦春族国民教育简章》,积极兴办鄂伦春族学校教育。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十六日,《黑龙江省行政公署为呼玛、爱辉、嫩江三县设鄂伦春学校给黑河观察使的训令》中就写道,“而今之地方官又困于经费,办城乡小学尚虞不逮,岂有余力以办理鄂伦春学校。事关国防大计,应由国家费补助,至兴学之责不可责之协领,仍当责之地方官。”[18]178可见,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教育福利的现实根基,在于抚绥、管控鄂伦春族民众的需要。是故其模式呈现为“平民扶助型”,面向全体鄂伦春子弟提供接受教育所必需的扶助。
新中国遵循的是建国前在革命根据地就已践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强调各民族机会平等,但也并没有忽视对结果平等即事实上平等的追求,不仅主张为各民族提供平等地获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会,而且还主张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在竞争发展中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差距,把最终取得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目标。即如列宁所说,革命以后要首先实现各族群在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然后通过优惠政策努力帮助各落后族群发展起来,最后达到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因此,新中国以来鄂伦春族教育福利的根基,在于贯彻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需要。所以其模式呈现为“民族优惠型”,面向作为少数民族的鄂伦春子弟提供优惠性的教育福利。
[1][清]鄂尔泰,等,修.钦定八旗通志[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584.
[2][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3]柳成栋.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357.
[4][清]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5]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1800.
[6][清]萨英额.吉林外纪[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84.
[7]郭美兰.论兴安城总管衙门的兴废[J].历史档案,1987,(4).
[8]李瑛.鄂伦春族教育史稿[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9]任国华.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J].民族教育研究,2001,(4).
[10]纪凤辉.清末黑龙江教育初论[J].北方文物,1989,(2):110.
[11]潘树仁.黑河早期的鄂伦春民族教育[J].黑龙江史志,1999,(1).
[12]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档案史料选编(1903—1931)[M].哈尔滨: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1985.
[13]新生乡乡志编撰委员会.新生鄂伦春族乡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伦春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八年—光绪十五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16.
[16]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1.
[17]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02.
[18]罗振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
[责任编辑 郑红翠]
Research on Historical Changes of Education Welfare of Oroqen Nationality
LI Wen-xi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In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the education welfare pattern of Oroqen nationality was"nobleright",the welfare was limited to the Oroqen nationality belonging to the eight-flag group,and its base was the demand to encourage,control and train the leaguers of ruling class.In final and phas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China period,the education welfare pattern was"populace-support",the welfare served all Oroqen Nationality,and its base was the demand to console and control the Oroqen Nationality populace.From the new China,the education welfare pattern is"nationality-preference"and the welfare serving all Oroqen Nationality,thus demanding to carry out Marxism nationality policy.
Oroqen nationality;education welfare;pattern transformation
A8
A
1009-1971(2011)06-0096-06
2011-10-07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421021851001)
李文祥(1971-),男,辽宁铁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及少数民族社会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