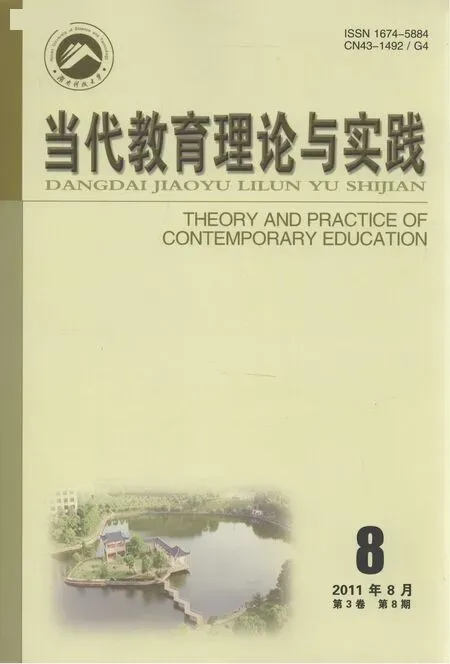语文课堂:谁的文本来作主
2011-04-03王超
王 超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语文课堂:谁的文本来作主
王 超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语文课堂存在着2大类文本: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读者文本又包括3种类型:编者文本、教师文本、学生文本。在作者文本、编者文本、教师文本、学生文本这4种文本之中,语文课堂到底由谁的文本来作主?就现实的语文课堂来说,在作者已死、师生失语的状况之下,编者这位“隐形的”读者成为文本解读的惟一权威与终审裁判,编者文本成为语文课堂的权威文本。
语文课堂;文本权威;编者文本
在当今最为流行的文学术语中,“文本”无疑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教育领域,人人言必称“文本”。至于文本的概念,则处于人言言殊的状况,无法也不可能达成概念的共识。在笔者看来,文本内涵大致可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来理解。宏观的文本内涵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一切事件都可称为文本,文本即生活。中观的文本内涵为:人类所创造的由各种符号凝聚而成的、承载着人类的文化、思想、观念、传统、意识等的物品[1]。微观的文本内涵为: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编织体,包括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本文中笔者的“文本”概念系指语文课本中的一篇文学性的“文章”或“课文”。
一 语文课堂上的两大文本
文本的创作主体是作者,文本的阅读主体是读者。这样,语文课堂就存在着两种文本: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
1.作者文本。所谓作者文本,也就是作者已写成的、通过语言发送的、蕴含作者本意的文本,简言之就是“内孕”着作者本意的文本。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性文章或课文也是语言的艺术。文本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语言的组合体或语言的编织物。众所周知,语言既有指称的或认知的功能,也有表现的或情感的功能。“语言(说与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的背后是人的心灵世界。文本作为一种语言与情感的载体,必然蕴含着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
2.读者文本。文本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是读者借助语言与作者进行交流、对话的平台。作家萧乾将文本的语言比喻为有待兑现的“支票”,将对于文本的鉴赏形象地比喻为“经验的汇兑”。他曾在《经验的汇兑》一文中说道:“文字是天然含蓄的东西。无论多么明显地写出,后面总还跟着一点别的东西:也许是一种口气,也许是一片情感。即就字面说,他们也只是一根根的线,后面牵着无穷的经验。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正是因为文本中的语词运用,除了通过它们的辞典义来实现一种指称的或认知的功能,更多的是要传达一份情味,显示一种旨趣[2]。
二 语文课堂上读者文本的类型
绝大多数人认为,语文课堂上文本读者指的是教师与学生这两个群体,或仅指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其实,语文课程标准就明确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因而,语文课堂上的读者包括编者、教师、学生,读者文本自然也包括3种类型:编者文本、教师文本、学生文本。
1.编者文本。编者是指编辑教材、编选文本的人。教材尤其是中学语文教材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培养道德品质与高尚情操的基本材料。相对于教师与学生这两类显性的读者而言,编者作为文本读者的身份是隐性的,通过文本内的编辑语言体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本的单元提示、课前提示、课文注释、研讨与练习、附文、插图,以及教学参考书、教师用书等看出编者对作者文本的取舍。这种取舍包括编者对教材与文本内容的处理、加工、增删、更换等,它规约着师生理解文本意义的大致思路。如人教版教材,单元提示往往旨在告知单元主题和单元学习目标,课前提示往往旨在揭示文章解读方向,而练习则明确检测重点难点,这些都是编者给师生的暗示。教参结论也是编者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尽管本质上编者编辑教材、编选文本是为了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材中的每一个文本基本上都是编者之文本,都是编者基于特定社会的需要与价值观念,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独特感受、体验、理解来解读与编选的。因而,教师和学生阅读的文本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编者文本。
2.教师文本。教师是一个成熟的读者,作为一个对文本有着丰富体验和细致感受的读者,结合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对文本一定会有自己真实的独立的感受。教师文本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对文本的个人感受与理解传达给学生,从而达到帮助学生感受和理解文本的目的。因而教师对文本的解读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阅读文本、获取教益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需要站在作者、编者和学生这三者的角度对文本进行三维分析,即理解作者感情,了解编者意图,把握教学目标,弄清学习重难点,组织学生阅读,教授学习技巧等。
3.学生文本。学生读者不同于编者、教师这2类读者。编者与教师都是成熟的读者,而学生从年龄、心智、学识、经历等,相对而言是“半完成人”、“不成熟的读者”(阅读学意义上的读者是“成熟的读者”,而中学语文课堂里的学生却是“不成熟的读者”)。学生尽管是语文课堂的学习主体,是文本解读的真正主体,被赋予“一千个学生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学生也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类的自由解读特权,但终因其身心各方面的不成熟,才导致了语文课堂上许多“无中生有式创造性”的学生文本的存在。如有学生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解读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有学生学了《愚公移山》后批评“愚公没有经济头脑没有效率观念”,学了《南郭先生》后赞扬南郭先生有“参与意识”,“善于抓时机,有胆识”,而最后“激流勇退,毅然地离开乐队让贤的做法实在令人赞赏”[3]。王荣生先生把这种对文本的不了解、求标新立异而刻意曲解文本所产生的阅读方式称为“读误”。蒋成瑀先生则把这种形式的文本阅读称之为“漫无目标的‘野餐’”。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文本是一种浅层次的、散步式的自由解读。
三 语文课堂上的文本权威
在作者文本、编者文本、教师文本、学生文本这四种文本之中,语文课堂到底由谁的文本来作主?当前,对于“文本解读”大致有这样3种见解:第一种观点是,作者是课堂“文本之父”,由作者文本作主;第二种观点是,教师是课堂的话语权威,由教师文本作主;第三种观点是,学生是课堂的真正主人,由学生文本作主。
就现实的语文课堂来说,笔者认为,这3种见解只触及了现象的表面,并未真正参透现象的本质。实际上,语文课堂是由一位“隐形的权威”——编者的文本作主,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恐怕也是。有以下3点理由:
1.由“原意说”到“作者已死”论,消解了作者的绝对权威,形成了“读者中心”论
“原意说”认为作者是文本的“父亲”,也是解释文本的唯一权威。阅读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努力靠近作者原意,理解作者原意,重建作者原意。只有作者的原意即“客观的度”才是衡量理解文本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只有寻找到这种客观的存在于文本内的作者原意,理解与解释才能是充分有效的,否则对意义的阐述将是非法的[4]。在“原意说”中,文本意义是确定的,读者只是客观意义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作者已死”是指1968年罗兰·巴尔特发表的“The Death of Author”(《作者之死》)一文。该文引发了文论界关于作者﹑读者﹑文本三者间关系的各种论争和思考。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并不是抹杀作者的存在,而只是否认作者享有的绝对权威,不承认作者是文本的主宰,也否认作品终极意义的存在,主张读者通过自由自主的阅读形成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因而对作者和读者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解构主义话语下,作者的中心和权威地位被消解,读者从传统的客体变成了主体,文本因摆脱了作者的主宰而成为开放性的文本。这种“读者中心”论的文本解读观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等“尊重读者”的教学要求。
2.作为读者之一的教师,是戴着镣铐解读文本的“假权威”
笔者认为,编者才是教师背后真正的隐形权威,教师只不过是编者的显性“代言人”,是戴着镣铐解读文本的“假权威”,可从3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教材的编选主要体现出编者的价值取向,而非教师的价值取向。教材不仅是知识载体,也是价值载体。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通过教材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教材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因为它往往决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从本质上说,教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教材里的文本也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并积极参加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5]。一篇文本进入教材,除了要受到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编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教育理念、文学观念和学识素养等的影响,而他们对文本的选择,往往折射出编者的价值取向。试以鲁迅的《故乡》为例而言之。《故乡》1923年首次选入课本,而在建国后“文革时期”就没有再进入语文教材,因为在编者看来,其中复杂的阶级关系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精神不协调,同时“我”对故乡的失望不具有革命性。“文革”之后《故乡》原汁原味进入课本,因为在当时的编者看来,鲁迅的《故乡》的主题体现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萧条景象”[6]。
第二,教师因被赋予一定的文本解读自由权,长期成为编者的“替罪羊”。尽管文本的编选主要体现了编者的意图,但教师作为读者,对文本解读也被赋予一定的理解自由权,而正因这一理解的某种自由度,语文教师成了编者的“代罪羔羊”,承担了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原因的全部责任。有例证之:许多教师长期坚守一套封闭的(甚至是过时的、错误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置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去观照,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研究作品“歌颂了什么”“揭露了什么”,看到《我的叔叔于勒》,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看到《项链》,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爱慕虚荣;提到周朴园,就是自私、冷酷;提到王熙凤,就是狠毒、刁滑、工于心计……[7]。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的批评何其多也,语文教师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要“去蔽”深思:语文教师曾经也是学生后来成为教师,他们的二元思维定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深层的原因也就自然不难得出:其实,教师文本解读的结论出自于编者的文本提示或教参中的“参考答案”(我以为“参考答案”不过是变相的“标准答案”),而提示与教参通常倾向于只提供答案但未交待得出答案的具体过程,导致教师只能在“参考答案”这一指定圈内进行有限的过程解读,而不能进行结论解读。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教参中的答案是:“新事物是要取代旧事物”的哲学命题。其实,胡同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市民文化,汪曾祺只不过是在叙述一种文化:有品味,有咀嚼,有赏玩,有依恋,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皇帝的新装》中,编者提示主题:“作品……以皇帝这个典型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其实,作品不只是揭露一个皇帝,而是要抨击人类共有的媚俗与虚荣。这2种理解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把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后者则直指超越时代、国别、阶级的人类灵魂深处的某种共性。散文家于坚说:“我们从文化中接受了太多的关于自然的认识,使我们不再认识真正的自然;我们心中的鸟和树叶已经不再是鸟和树叶本身,而是附着了太多其他东西的鸟和树叶。”这句话对我们的文本解读应有很大的启示。
第三,教师处于一种实然的“失语”状态。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教师似乎永远是语文课堂上的话语权威,不管是独白式的一言堂,还是对话式的多言堂,真理(此处指“正确答案”)总是掌握在教师手中。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话语不是简单的表达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任何话语都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即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教师话语权是从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中获取的,教师话语权力主要是一种制度性话语权力。它是教师经由教育制度被社会所赋予的、运用规范的权力”[1]。但是,教师并不是话语权的真实主体。在现实社会中,“教师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代表,承担着传承文化、传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责任。他的一切教育活动都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社会价值取向。因而教师的话语权力实际上是屈从于国家意志,对于教师自我意志来说,这种话语权是虚假的”[1]。在文本解读中,阐释话语权虽然是教师天然的话语权力,但却“有名无实”,教师拥有话语权在一定期程度上能反映自身的体验,但文本解读的最终结论仍得按照编者的意图得出,教师的个人话语权被压抑甚至被剥夺,教师用自己的脑子嘴巴说着编者的话,教师的个人话语成为“弱音”或“盲音”,处于实然的“精神失语”状态。
3.作为读者之一的学生,也并非是解读文本的真正主人
新阅读教学观强调编者、教师、学生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编者的阅读提示和教师的讲解点拨,都应该为学生的阅读理解与感悟服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生作为不成熟的读者,从各方面很难与作者、编者、教师进行真正的有效对话,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读平等,“因为学生生理、心理处在成长中,以及知识的后天积累性,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面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话语沉默地位。在以课本为指南、以考试为考核手段、以分数为成绩标准的教学中,学生的话语基本是围绕‘正确知识’而展开的,还停留在形式层面。学生的话语表现为检验自身理解和教师讲授、考试意图的一致性”[1]。
综上所述,语文课堂在作者已死、师生失语的状况之下,编者这位“隐形的”读者成为文本解读的惟一权威与终审裁判。一家之言最终成为大家看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陈小玲.师生话语权丧失及其原因分析[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2]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李海林.“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批判[J].中学语文教学,2005(1):9.
[4]周险峰.教育文本理解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林喜杰.群体性解读与想象——新诗教育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7.
[6]寿永明,李乾明.编者:课文教学文化视点的规约者——以鲁迅的小说《故乡》为例[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7(12):9-12.
[7]蔡 俊.把好语文教学文本解读的“位”[J].语文教学之友,2008(6):7.
G623
A
1674-5884(2011)08-0038-03
2011-04-20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成果之一(湘教通[2004]284号)
王 超(1971-),女,湖南祁东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责任编校 谢宜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