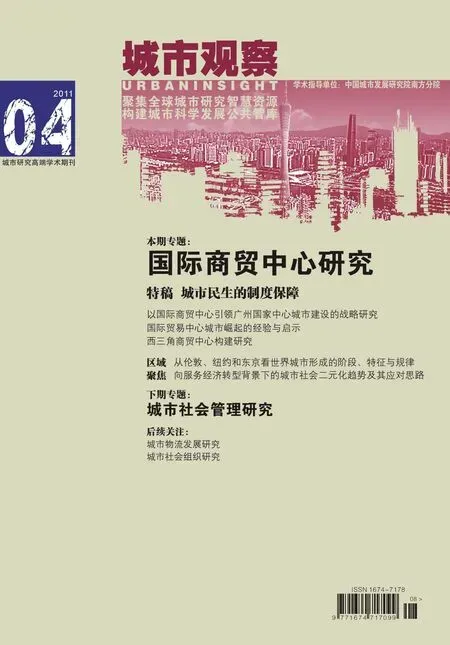论城市村落的现状、发展和保护
——以广州城市村落为例
2011-04-01朱志刚
◎ 朱志刚
论城市村落的现状、发展和保护
——以广州城市村落为例
◎ 朱志刚
“城市村落”的概念提出,是对“城中村”概念的一次批判性反思。“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正如其概念一样,形成了单一性、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本文拟就广州城市村落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空间形态现存状况的分析,探讨广州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模式及注意问题,并提出“城市村落”的研究应从人文关怀之意义出发,更侧重于对其保护和发展。
城市村落 保护发展模式 人文关怀
“城市村落”,过去紧邻城市边缘,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有的开始进入到城市中心区域。相比近年来较为常见的称呼“城中村”这个概念,可能会更为有效地避免呆板而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模式,譬如有研究者将其认定为“畸形社区”①、“问题村”②。而城市村落,亦称都市村庄(Urban Village),实际上也是一个较为学术化的概念③。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村落的研究甚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就已经关注到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问题④,不过大多研究仍是沿袭这种从“城中村”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其概念的形成和演变、类型、特征、问题、规划和改造等,在此不一一赘述⑤。这些研究显然忽略了从城市村落的人文关怀之意义出发去谈其保护和发展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珠三角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伴随经济的发展,广州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广州新城区建设或改造过程中,尤其是近10年来在房地产业的推动下,曾经属于城市边缘地带的乡村社会,绝大部分正在或即将转化为都市型社区⑥。故将广州城市村落作为一个研究样本加以分析,有一定的典型性意义。本文拟以广州城市村落为例,从人文角度的眼光出发,通过对其空间形态现存状况的分析,探讨广州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模式,以及在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且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和几组关系。
一、广州城市村落的现状
广州地处岭南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水系发达,河网密布,属于南亚热带温暖潮湿气候,居住于此的先民们创造出了富有自己独特特色的岭南聚居村落。这些村落曾经或至今仍为广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但是,随着广州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城市村落的变迁极为剧烈,其发展现状在今天显得让人堪忧。我们可以从目前广州城市村落呈现的三种空间形态来分析。
首先,广州城市村落的自我生产空间发生改变,作为村落存在的标志性特征逐渐消失,农业用地、传统生产方式几近不复存在。作为一个村落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对土地强烈的依赖性,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广州城市村落的土地,包括粮食用地、蔬菜地、果树用地和鱼塘,迅速减少甚至消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极大改变,村民不再依赖土地的产出作为生存生活的来源,以集体经济形式出现的股份制公司代替了村委会,以住房和厂房出租为基础的现代工商服务业愈来愈成为广州城市村落经济的支柱产业。有的村落或者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如广州番禺区石楼镇的大岭村。固然,城市的发展会带来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带给从旧有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们带来新的更好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强烈依赖于失去土地之后的集体分红、“包租婆”或“二世祖”式的不劳而获。
其次,从广州城市村落的地理空间来看,包括村落生态环境、村落布局规划、村落建筑、基础设施等,都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广州城市村落中环村的水网河道多已淤塞,要么不再清澈。2010年广州在亚运前进行大规模的河涌整治,使原始乡村意义上不作任何雕饰的河道,演变成为城市景观中的人工亲水长廊。村落以巷道为脉络的空间布局和岭南风格建筑被肆意地更改和摧毁。广州城市村落中有的是以大量“握手楼”、“接吻楼”为主的民居聚落,道路狭窄,空气污浊,如天河区的棠下村、白云区的元下田村。原来极具岭南风格的民居和祠堂大量地被拆除或改造,村落建筑被“房地产化”为密集耸立、不见阳光的高楼大厦群落,如天河区的猎德村、林和村。岭南水乡这一独特的标志性地理特征逐渐泯灭。
再次,我们看到广州城市村落的文化空间逐渐萎缩。广州城市村落中的居民因为富裕或从事工商业活动逐渐搬迁离开,甚至外来的流动人口比原来居住在村落里的人口还要多。广州城市村落里曾经发达的民间组织、人际网络关系出现解体或不再起关键作用。村落中原来那种熟悉而亲密的邻里社会逐渐演变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和冷漠的都市社区,村落中世代传承的传统民间文化习俗也简约淡薄甚至有的已经消亡。
上述三个层面的城市村落现状,既体现于外在的物质景观的变化,也体现于其内在的文化底蕴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力量来自于国家政策,也来自于自身主观的需求;既是被动的、消极的适应性变化,也是主动的、积极的调整性变化。如果这种现状持续变化的话,那么独具岭南地域并承载着人群集体记忆的鲜活遗产,或许最终将变成一种广州人心灵深处无法触摸的想象。
二、广州城市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随着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政策出台,作为广州民间文化的符号性象征载体,广州城市村落逐渐被重新认识和发现,并被予以保护和发展。按照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的方针,目前,广州城市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模式:
首先,是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包括国家各级行政单位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等的制定以及授予相关荣誉和奖励。国务院在1986年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谈论到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问题。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历史文化村镇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并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明确界定,是在2002年国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时。2008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了对村落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标准,规定了政府以及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国家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2009年底广东省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论证。自2003年11月起至今,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在2007年被授予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开始广东省也开始组织评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2009年底广州市天河区珠村被授予广东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这些评选活动极大帮助和促进了对广州城市村落的保护。同时,城市规划和旅游等部门也出台各种政策对城市村落进行有效的保护管理和开发。这几年,广州还利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与村落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
其次,利用经济的杠杆驱动对城市村落进行保护和开发。在资本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之后的精神生活水平,旅游开发、文化创意产业聚居地、农庄饮食休闲经济、房地产经济等开发模式成为比较常见的保护开发手段和方法。例如,一些保存古建筑民居群落较为完整、具有一定欣赏价值的城市村落,如番禺区的大岭村,以吸引游客前往旅游为主;或者发掘和利用城市村落中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因素,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庙会、天河区珠村的乞巧节,打造节庆旅游;而增城市、花都区、南沙区、白云区等距离广州城市中心略远的乡村,则纷纷开展农庄体验模式,通过回归自然、品尝乡村绿色美食、了解乡村生活、甚至租地给来自于城市的游客而代为耕种等,并在不破坏或修缮的情况下进行开发和利用;而从化的温泉休闲旅游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相结合模式,充分发挥以温泉为主导的资源优势,结合乡村风情,开发房地产;海珠区小洲村的文化创意产业聚居地模式,以距离城市较近、村落相对廉价的房租、较为优美而宁静的村落景观和自然闲散的生活方式为吸引力,使得文化人或文化产业入驻并形成规模效应等。
第三,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况。这是城市村落一种自然而然状态下的选择,主要依赖村民自身的力量无为而治,村落中成功人士或民间组织的稍加修葺,或不加干涉的自生自灭。这也是广州大多数城市村落无奈的自我生存保护法则。虽然不是最有效的,但比起一些在外力强加的随意随性改造的行径,这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当然,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城市村落,主要是由于距离广州城市中心区较远、人文历史积淀相对较浅、村落民居和建筑等物象的景观特色并不突出,或并未被发掘,从而既不为国家政策所关照,也缺乏资本力量的进入,而依赖于村落居民自身的调整和适应城市化的发展。
最后,广州城市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大多是以上多重模式之下共同构建的复杂综合体。其实,在城市村落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常常是多重保护和开发力量的集结,如果这种结集协调运作恰当且合理的话,未尝不是最好的一种模式。民间、国家、资本三者各就其位,又相互利用渗透,各显其功能。譬如广州天河区珠村的“七夕乞巧节”的“复活”,就是本地村民潘家的能人、天河区政府、珠村集体经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和运作的结果。
三、广州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广州的城市村落充分体现了岭南水乡社会的聚落形成和历史演变过程,是展示岭南优秀传统建筑风貌、优秀建筑艺术和建造技艺、传统空间形态和民俗风情的真实而具体的载体,对于弘扬岭南文化,增强广州市民对岭南文化的认知、认同和自豪感,带动城市村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民间、国家、资本的多种力量如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一个地方社会,这些力量的确对于广州城市村落的保护和开发起到了十分必要的作用,有的甚至已经取得轰动的效果。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喧嚣的力量背后,也暗藏了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例如,尽管广州有少数城市村落获得了国家、省市级历史文化名村荣誉称号而得以保护,但大多数的城市村落由于资金、人力、制度和方法等原因,仍旧淹没于荒山野草之中。由于没有设立相关的保护机构,缺少必要的保护维修资金,定期动态的监管和资源普查工作未能开展。许多村落基础设施陈旧老化,传统建筑日渐衰败甚至坍塌,也影响了历史文化遗存的有效保护。在一些区域,国家政策往往被地方政府误读,新农村建设演变成“大拆大建”,诸多古色古香的岭南建筑被仿造、被统一、被美观。旅游开发的过度和滥用,对村落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精神环境都造成巨大的伤害,地理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当地人的思维、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甚至造成当地民众与资本力量的矛盾冲突。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需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加强对城市村落中极具文物或文化价值的实体建筑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确立相关能够严格执行的制度程序。综上而言,我们在面对城市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时必须要注意处理好几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村民和村落的关系、生态环境和地方发展的关系、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创造的关系、保存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等。否则,古老的乡村不再宁静,将变得和城市一样庸常、喧嚣、单调和同质。这些也正是我们人类生存多元世界所要设法警惕和摒弃的。
四、结语
李培林在讨论城市村落巨变的时候,似乎预言了城市村落的终结⑦。这种悲剧性的预言,诚如2006年浙江西塘“中国古村落保护”高峰论坛《西塘宣言》中所言:村落是祖先创造的第一批文化成果,是一个群体的历史纪念碑,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精神家园,“村落的消失,或者说村落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景观,中国将从此沦为文明的弃儿和文化的乞丐”。这里虽然谈到的是古村落,其实城市村落又何尝不如此。城市村落的消失,何尝不是现代都市人精神家园的沦丧和消失。我们希望,对广州的城市村落保护和发展,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当下中国急进的城市化浪潮过程中,多一份人文的关怀,可以为城市人的后代留下一份都市乡村美好的田园记忆。
注释:
①白涛、叶嘉国:《珠江三角洲城中村问题探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P123
②刘梦琴、傅晨:《城中村国内研究文献评述》[J],《城市观察》,2010年第6期
③张建明:《广州城中村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
④周大鸣:《论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广东都市化之一》[J],《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⑤相关研究参见:刘梦琴、傅晨的《城中村国内研究文献评述》[J],《城市观察》,2010年第6期;仝德:《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及原因——以深圳特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1年第3期;卓彩琴:《“城中村”改造的文化障碍与策略——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等。
⑥在广州这座城市,有的村落已全部完成从一个乡村社会到都市社区的转型,例如天河区的猎德村,该村村民于2010年底基本全部回迁到位于广州市城市核心区珠江新城新建的社区居住。
⑦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The Status-quo,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Urban Villages: Guangzhou’s Practice
Zhu Zhigang
The concept of “urban village” is a way to reflect on this urban form in a critical way. The treatment towards this issue is monotonous and dualistic.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quo of the spatial form of urban villages is analyzed by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with focuses on the aspects that 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wh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s urban villages is in concern. The author advocates a more people-oriented research mode of the urban village issues and leaning towards it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urban village; conservative development mode; humanistic care
TU984.18
朱志刚,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人类学、民俗学、区域文化的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陈丁力)
广东省“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