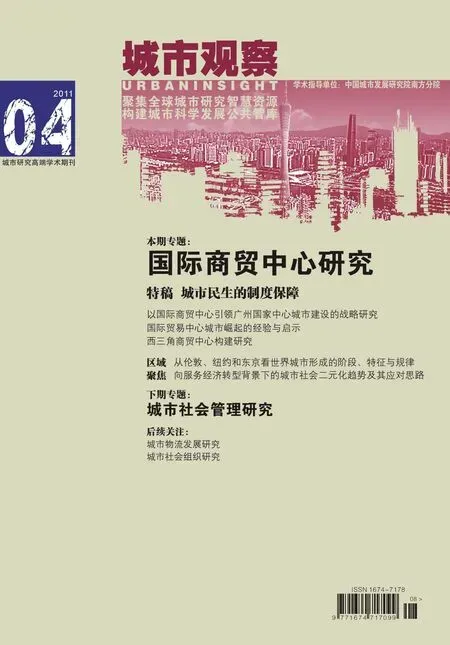城市民生的制度保障
2011-04-01潘家华
◎ 潘家华
城市民生的制度保障
◎ 潘家华
民生保障与收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保障。中国城市发展要从“中等收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民生标准是一个必须逾越的门槛。“排他性”的民生安排必须转向“包容性”的民生保障。民生保障并不是“均贫富”,而是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民生保障 包容性 社会选择
民生,民之生路或生计①,西方多界定为“体面的生活”,内涵涉及健康、教育、就业和均等享有社会公权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等。对于以自然资源利用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生产、消费和治理相对封闭,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资源禀赋问题,核心在于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占有。对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来讲,经济活动强度大、环境空间容量小,具有开放和相对程度的对外依赖特性,民生成为一种社会命题,社会资源分配成为核心问题。而社会资源的理性分配,并非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收入的增加,可以通过市场途径解决的;在很大程度上,民生是一种制度规范的结果。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已经趋于完善的民生的制度保障是一个必然的要素和标准。
一、“中等收入”不等于“中等发达”
没有人否认收入增长是民生保障的基础。但是,高的收入水平并不意味着民生就有保障。如果说“暴发户”是一种暴富,那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家族和官宦的收入是相对长期而稳定的。他们可以在民生保障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构建“富人区”,可能有着比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更高的收入,但是,他们缺乏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文化服务等许多基本民生的覆盖。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官二代”、“富二代”纷纷漂洋过海,移居到发达国家寻求具有综合覆盖的民生环境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整体上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显然,中等收入水平并不等同于中等发达水平。城市民生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严峻挑战和步入中等发达社会必须跨越的门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而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普通百姓,民生水平和保障程度低。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在两位数增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的一项预测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即可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②。2010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些沿海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中国城市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接近2万人民币,按汇率计达到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则超过1万美元。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超过日本的人均水平。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接近1亿辆;主要消费群体为城市人口的私人轿车,达到3443万辆③。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从无到有,上海、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数超过伦敦。但是,无论是国内自我评价,还是国际主流观点,客观地讲,并没有多少人认可中国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④。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之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⑤。显然,在经历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和工业发展后,中国政府转向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进程。客观讲,中国城市发展的硬件设施在许多方面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中国一些一线城市举办的国际重大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许多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些城市的民生问题得到了解决吗?从总体上讲,我国城市的民生改善空间大,保障能力弱;调整发展导向,是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水平”的必然选择。从“中等收入”到“中等发达”,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可见,民生水平是实现这种飞跃的前提和标准。
二、“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民生涉及每个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排他性”设计,人为地将国民的民生保障水平加以区分,在制度上歧视非城市户籍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物质保障水平低,城市容量十分有限,以户籍制度隔离城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基本民生保障的需要。但是,这种保障的基础不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是“生来不平等”的一种强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这样一种制度惯性和体制环境下,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⑥。不仅如此,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在城市因身份而享受差别待遇,大批农民工工作在城市,贡献于城市发展,而民生保障却被排斥在外。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保、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性质的社会服务;而且,政府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甚至将他们排除在市场之外,例如城市房地产市场和私人轿车的“户籍”要求。
“排他性”的民生安排是民生保障鸿沟;如果不加以根除,社会进步与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墨西哥已经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三倍,墨西哥城每三人就有一辆汽车,与欧盟日本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世界上少有人将墨西哥列入发达国家名单。原因很简单:如果墨西哥城的贫民窟不能消除,很难想象,墨西哥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日本的食品安全只是对少数人负责而排除其他社会群体,也不会有人认为它是发达国家。1980年代后期笔者在英国念书时,一次骑自行车被汽车撞倒,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检查完毕,临出院时送上一杯咖啡,说没事了,不需治疗,可以回家了。没有交押金,没有交任何费用。然后保险理赔,程序规范。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孩子随笔者在英期间,上了一个学前班、换学校上小学,没有赞助费、不用交学费,小孩生病取药全免费,还有每天一英镑的小孩福利。应该说,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短期居留的学生,没有在英国缴纳社会保险,更没有交税,没有对当地社会有什么贡献,但是,在英国,基本民生的保障却是“包容性”的。当时感到发达国家的民生保障,超出我们的想象。试想,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没有学上,急症不缴费就不治疗,即使是城里户籍孩子也没有幼儿园上,而且费用高企,这样的民生水平,我们很难想象是“中等发达”的水平。
“包容性”的民生保障,不仅需要全覆盖城市地区,而且还要延伸到农村。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高出农村居民三倍以上⑦,如果这一差异不消除,城市民生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人口的自由迁移是基本民生-人权-的一个基本要素,消除“排他性”的户籍体制,城乡人口是互动的。
三、民生保障的社会选择
发达国家的民生保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收入增长到民生改善,制度构建是关键。这种制度构建,显然带有“计划”的色彩。但是,这种计划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发达国家的民生保障才能够稳定、规范、持续而行之有效地得到落实。
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一个强势政府的把控和推动下,迅猛而有效。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有民意基础,但更多的是政府的强力推进。城市民生改善,当然也需要政府担当责任,总体谋划,贯彻实施。国家在宏观层面,不仅明确了民生的发展导向,而且制定了具体措施。“十二五规划”要求,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促进就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大规模保障房的建设,应该会极大地改善民生。
但是,民生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或赐予,不是共同富裕。民生是一种社会选择,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社会尊严的保障。社会需要的,不是同等水平的富裕程度,而是老幼病残的基本生活保障,低收入群体社会尊严保障。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⑧中提出的“最大‘最小’化”原则,就是一项促进和保障民生的基础。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选择。假设每一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进行一项最优的社会选择投票。他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笨,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疾弱。在这样一种“无知之幕”后,每个人做出的社会选择,无疑是要确保最弱势的群体(即“最小”)的福利改进最大化。财富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基本需求是有限的。
民生保障不是均贫富。相反,民生保障程度高的发达国家还鼓励社会精英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财富对民生有一种外溢和保障效应。我们需要的民生,不是财富无限扩张,而是基本生活质量的保障。所谓民生,内涵非常明确,就是要求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在就学、就医、就业、居住、尊严等方面能够有基本保障。
发达国家有许多我们需要批判的,但是其民生保障的一些实践,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到“中等发达”水平的跨越,民生的标准必须要满足。保障民生,不仅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还需要有社会客观冷静的思考与选择。
注释:
①孙中山1924年在《民生主义》中提出的民生概念为:“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宋迎昌等将人民生活水平视为民生水平的一个测度。见潘家华和魏后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7月。
②IMF, 201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ensions from the Two-Speed Recovery:
Unemployment, Commodities, and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2月28日。
④当然,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1)出于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同考虑,将中国等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界定为“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以区分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
⑥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城市化率达到49.68%(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而统计数据则表明为47.5%(作为国家十二五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基数),相差2.18%百分点。即使是47.5%的城市化水平也通常被认为是“虚高的城市化”或“不完全的城市化”。
⑦2010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人均的3.23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2月28日。
⑧John Rawls, 1971. The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ecuring the Urban Livelihoods
Pan Jiahua
Livelihoods is linked to income levels, but the enhancemen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s a more crucial factor for securing urban livelihoods. Livelihood measurement is certainly a threshold for judging whether Chinese cities are transformed from middle income to medium developed status.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exclusiveness to inclusiveness in urban management. To secure urban livelihoods does not imply an egalitarian system, but rather to ensure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disadvantaged.
secure the urban livelihoods; inclusiveness; social choice
C911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卢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