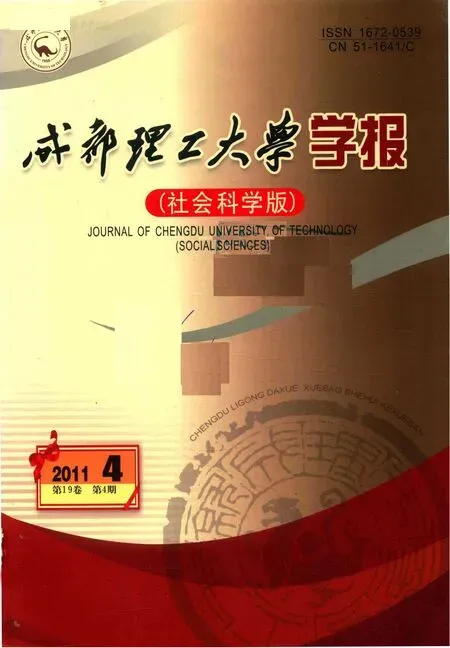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效率公平观
2011-03-31吴仁明柴剑锋
吴仁明,柴剑锋
(1.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 610059;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3.四川省社科院,成都 610071)
论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效率公平观
吴仁明1,2,柴剑锋3
(1.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 610059;2.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3.四川省社科院,成都 610071)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难题之一,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重视公平,不放松效率;邓小平重视效率并以此来推动公平;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他们都契合了当时民众对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
效率与公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难题之一,难就难在两者不能协调并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深刻思考,反映了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们各自面临的时代任务的不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性,正确认识和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历史的归纳。尽管以往学者对党的领导核心在公平效率问题上的认识有所探究,但对历代领导核心整体上的归纳研究还未曾有。(1)笔者在这里抛砖引玉,并希望同行们批评斧正。
一、毛泽东的效率公平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把效率与公平在一个适当的度之上统一起来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一些学者曾评论毛泽东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是“均中求富”,或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这实则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误解。不错,在民主革命时期,时刻要做的经济工作就是人和人的经济公平,从土地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正是这样思想的体现。但这也相当程度地体现了效率。因为它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得到提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所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079毛泽东在七大上说的这句话深刻体现了其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思想。
在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方面,毛泽东坚持效率优先,但不损害社会的公平。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28年,毛泽东亲自到井冈山的遂川县发表讲演,宣布红军保护私人商业活动,红军还打掉了当地压迫商人的地主武装——靖卫团,废除了土豪劣绅勒索商人的苛捐杂税,根据地的商业活动便迅速恢复、发展起来。[2]3781930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地方党委制定和实施了以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政策。这些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产、利润与封建的产业、封建剥削收入加以严格的区分,并对前者实行严格的保护,这得到城镇私人工商业者的拥护。在赣南,“商人就愿意和我们做生意,把盐运过来,所以,吃盐问题解决了”[2]132;在闽西,“私营商业很快兴旺起来,当时长汀县城,私人商店由革命前的几十家发展到367家”[3]。对“左倾”领导人的过火行为,毛泽东说:“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4]毛泽东等制定和实施的工商政策,从商品流通、金融税收、劳资关系、生产投资等方面,对城乡资本主义工商业给予保护、优惠和奖励,从而成功地调动了根据地及其邻近的白区的私人工商业者为苏区经济发展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毛泽东又主张适时地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引导,克服效率对公平造成的伤害,引导其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为此他说:“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5]。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在1939年就制定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6]之工商业政策,注重利用私营工商业的效率,尽可能地增加生产、丰富生活,以为抗战服务。从1940年初开始,边区私营各厂矿中逐渐都建立了工会组织,注重劳资的和谐,分配上更为公平合理;注重“不要强调阶级对立,而是在劳资协调、双方互让下求得工人生活的改善”;注意克服“只强调改善工人生活,不注意提高劳动热忱和提出过高要求”的倾向,劳资双方都获其利,以求公平与效率之统一。同时毛泽东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7]毛泽东在论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时指出:“按照孙中山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然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的国家,一定不是少数人所谓的国家,一定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1]1058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除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不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经济地位平等的思想,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想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节制资本”的思想,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给资本主义企业以一定限制,并不在产权归属上限制资本主义的存在。在这种政策下,资本主义的竟争仍然能在包括产权归属在内的广泛领域存在。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当时实际上是要在首先保持效率的条件下,一定程度地渴望公平的实现,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
可惜的是,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优先考虑公平而不是效率,也就是说,毛泽东把效率与公平调了个。他认为,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才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8]437。需要说明的是,在主观上,毛泽东并不是要以牺牲效率来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平,而是他相信,在社会主义集体经营形式下,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也利于技术改造和机器的使用,因而在生产效率方面“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8]426,他并没有找到在消灭其时还比较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后如何建立一种更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的方法,公平也就没法真正得到保证。到文革时期,一切效率手段几乎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因素否定,效率与公平的严重背离,使公平问题失去了凭借,社会到了失控的边缘。
二、邓小平的效率公平观
平均主义既牺牲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文革时期对公平问题的极端重视并未带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与公平正义。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的绝对公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早在1975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就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事实上他是在纠正完全否定效率的错误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逐渐使全党全国恢复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效率公平观,并且实现了超越。
首先,邓小平明确界定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确立了效率优先与注重公平统一的原则。这个原则事实上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直坚持的,邓小平则把这一原则加以明确。在时间顺序上,效率无论如何都是优先和第一位的,因为没有效率就根本谈不上公平,邓小平为此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9]142”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让那些效率高的人和地区发挥出自身的效率而先富,实质上是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竞争开辟空间。而竟争是一个社会有效率的根本原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证竟争的存在,也就为社会经济效率的存在铸就了最基本的根基。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需要效率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由先富带后富这个基本途径来实现,而不是同时同步和同等富裕,效率优先于公平的原则在时间上得到了确证。
其次,邓小平认为,因为效率不同引起收入的差距不是对公平的伤害,而恰恰是公平的体现和必经步骤。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公有制条件下唯一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它是实现公平的具体途径。但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0]因此,这就意味着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种公平与不公平的对立统一中,按劳分配恰恰既兼顾了公平,又提高了效率。因为有了劳动质与量的差别,就会引起个人收入的差距,就会产生竞争进而提高效率,而劳动差异造成的收入差异是非常有限的,它不致于损害社会公平。所以邓小平更多的是强调起点的公平,他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片面地强调结果公平的历史误区。邓小平经常从效率方面来考虑社会主义的原则或任务,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9]172为有效提高社会效率,邓小平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思想;在分配上,他强调“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在宏观管理上,他强调生产责任制。他在20世纪80年代搞承包、租赁形式的基础上提出和实施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市场经济原则,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投资主体协同发展、实现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经济结构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的高效率。
再次,邓小平把效率优先原则贯彻到全社会的领域中,提倡效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同时注重发展中的公平。社会高效率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生产力标准某种程度上就是效率标准。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公平是目的,但在社会发展上,效率却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10。“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9]11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在十三大上总结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一项大政策不能用是否符合教条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判断,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13]372。邓小平在说到生产力发展时,总是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落脚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为发展而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一方面是“先富带后富”,直白地说,即效率高的带效率低的,最终效率低的变成效率高的;另一方面是国家通过制定均衡发展战略,从各方面给贫困落后地区以帮助,“特别是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最终赶上富裕先进地区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9]111
总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效率公平思想,使效率与公平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明显提高。
三、江泽民的效率公平观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两级格局解体,中国进入从温饱到小康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和国情背景下,在效率公平问题上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
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江泽民主持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江泽民指出:“从理论上讲,以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11]生产决定分配,只有通过改革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才能使分配制度和政策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才能为根本解决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现阶段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决定的。江泽民认为,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国家工作的中心位置。但是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公平的自然到来,相反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为此他明确表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大政策”[12]。他还重申,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绝不是否定已经实行的先富政策,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必须继续坚持,这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不这样,就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没有先富,就没有共富。
其次,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效率观的认识。邓小平时期的放权让利和开放政策所释放的效率正逐渐缩减,为激发更高的效率,必须采取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举措。在科学技术上,江泽民更进一步地强调并全面论述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化建设效率的动力作用。他把科技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灵魂,并认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精华,其对生产力的先进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从物质上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效率提供了保证,他提出了要走创新之路、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重要命题,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13]在宏观管理上,江泽民强调要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运行效率,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即是要进一步把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实行优胜劣汰和有进有退的调整,使国有企业在与其他各类企业的平等竞争中显示出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在分配制度上,为激发人们劳动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经济效率的最终提高提供有利的条件,进一步完善分配体制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江泽民明确认定要用制度的形式把投资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多元并存固定下来。在对外开放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做出加入世贸组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把整个中国经济推上国际市场竞争的大舞台,使中国效率赶超世界效率,赢得比较优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最后,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他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匹配的分配制度,并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规范社会初次分配,提高各项收入的透明度;加快扶贫开发,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把公平与效率统一;采取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对口支援的办法,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鼓励东部地区的优势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办厂,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999年又果断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缩小东西差距。其次,首度提出以法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江泽民指出:“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14]再次,为应对全球人口、资源和能源问题,他提出发展注重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9]131在这里,他实际上指出了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完成人类发展模式的更新。江泽民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下,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予以了更加高度的重视。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必须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地位,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完成了我国发展理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实现了效率与公平在代际上的统一。
总之,江泽民的效率公平观契合了发展的时代脉搏,做出了许多重大创新与拓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转型。
四、胡锦涛的效率公平观
历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国际形势大分化大改组,中国由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在效率公平观上继续深化和发展,认识上和实践上都趋于更加成熟和完善,同时又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胡锦涛果断提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统筹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越来越强,对我们党和政府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胡锦涛提出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统筹效率与公平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5],公平正义被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位置。对于什么是公平正义,胡锦涛认为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15]。这其中更加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内在地包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既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论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以看得出,“更加注重公平”的提法既继承并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其次,丰富了公平思想的内涵,提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大举措。胡锦涛提出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15]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原则体系。权利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得以保证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规则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程序保障和存在形式,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目标。四个公平思想丰富了社会主义公平内涵,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胡锦涛创造性地提出以下重大举措:
一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他在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问题上有着清晰而明确的思路:“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只有不断推进发展,促进社会物质财富增长,才能为消除社会不公正创造前提条件。社会公正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为科学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
二是在分配制度上,要继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实践证明,如果初次分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就会导致分配差距过大。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切实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废除存在二千多年的农业税,对农业进行补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坚决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做法;坚决取缔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切实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三是注重以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建设首次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一同写进十七大报告。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形成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格局。创新就业体制,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全面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再次,在和谐社会的效率问题上,胡锦涛同志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效率,不只是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不只是要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调控的能力和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保障经济平衡较快发展的体制机制,而且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只是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而且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契合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对公平问题的诉求,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大发展,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五、结语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公平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逐步解决,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决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从毛泽东重视公平、不放松效率,到邓小平重视效率来推动公平,再到江泽民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后到胡锦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统筹效率与公平,他们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都契合了当时代民众对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注释:
(1)对党的领导核心对公平与效率认识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廷湘:《从平等与效率的完美统一到“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祝小宁、李茵莱:《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6期;梁超:《对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几点认识》,《传承》2008年第7期;龚立新:《从“均中求富”到“双论”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的演进与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罗伟:《毛泽东和邓小平公平效率观比较》,《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3期;袁刚、柳俊杰:《对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东方实践的思考——效率与公平的维度》,《理论导刊》,2007年第11期等。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湖南省财政厅.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3.
[4]毛泽东.毛泽东致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Z]//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4册).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1996 :50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
[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54.
[7]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G].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537.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11]江泽民.认真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J].求是,1989,(12):5.
[12]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12-18(1).
[13]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1.
[14]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
[15]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1).
On the Ancien t Concept of Equity and Effeciency of the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WU Ren-ming1,2,CHA IJian-feng3
(1.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Chengdu 610059;2.College of Histo 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3.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engdu 610017,China)
Efficiency and fair isoneof the difficult p roblem s in economic histo ry.The party’s leaders are past dynasties had a deep thought and exp loration :MAO zedong value fair,not relax efficiency;Deng xiaoping’s attention in o rder to p 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fair;Jiang zemin put forward to give p riority to efficiency and due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advocated by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p 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I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sue,they all agreed with the peop leof age at the time histo ry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of the basic demands,which greatly p romot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Efficiency and fair;MAO Ze-dong;DENG Xiao-ping;JIANG Ze-min;HU Jin-tao
D64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4-012-07
2011-06-26
成都理工大学2010~2013年度骨干教师资助项目(HG0092);成都理工大学优秀创新团队资助项目(HY0084)
吴仁明(1973-),男,四川安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柴剑锋(1975-),男,河北永年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刘玉邦